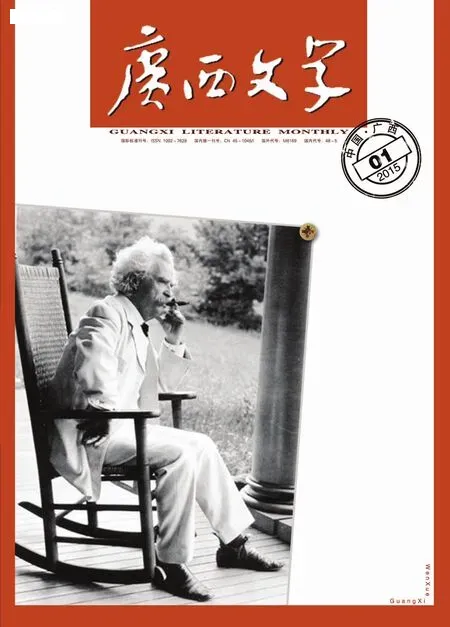直立行走的甘蔗地
2015-11-14短篇小说蓝华瑛
短篇小说·蓝华瑛/著
一
早上的太阳终于出现了,在两座山的鞍部露出金色的小半边脸,几束阳光只照到了甘蔗地的一角,甘蔗叶上的露珠被照得亮晶晶的,像几粒久经风霜色彩暗淡的珍珠。山太高了,把温暖的阳光都阻挡在山的另一侧。山的另一边现在还是阴冷的,山脚下有一团雾气,仿佛一团白烟,笼罩着几片甘蔗地。甘蔗地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一排排甘蔗东倒西歪,像是被猪拱过。声音像是蝗虫叫,又像是野猪在偷食地瓜。突然甘蔗地的尽头伸出一个脑袋瓜,一个男人躬着身子走出来。他穿着一件绿色的军上衣,肩膀和背后都湿透了。他拿起水壶,咕噜喝了一大口。头上的水流到他的脸上,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水珠。
这个人叫韦三顺。韦三顺是我的父亲。他总是起得很早,他出发的时候月亮还在天边挂着。
这是我家的五亩甘蔗地,父亲一大早就来锄草了。他扛着一把锄头,背后插着两把镰刀,一把长的,一把短的。他用长镰刀把杂草全部割走,然后用锄头连根铲掉,等杂草积成一堆,打包扎稳,抱到甘蔗地外面来,放在石头上等中午的太阳暴晒。
他又钻进甘蔗地,把东倒西歪的甘蔗扶正,用短镰刀把每一棵甘蔗的枯叶砍掉。我家种的是榨蔗,用来榨糖的,甘蔗成熟后就可以砍掉拿去卖给糖厂。这是我们当地的主要经济来源。
太阳已经升到山顶了,暖暖的阳光驱散了山脚下的雾气。现在视线清晰了,这是一大片低矮的丘陵,四周是高山,一眼望去,都是甘蔗林子。
远处传来“哐当哐当”的声音,我知道这声音是早上从南宁去凭祥的火车发出来的,铁轨穿过刚才被太阳照过的山的那边的土地。
我手里拿着手电筒,穿过杂草丛生的小路。我的裤脚被露水弄湿了,凉鞋里面湿漉漉的。我爬到一块被晒得黝黑的大石头上面,大声喊叫,爸,哥今早回来了,他叫你回去,现在就回去,他说有事找你。
二
我回来的时候,闻到了鸡肉的香味。
我知道父亲在我出去打酒的时候杀好鸡,并且已经放进锅里煮上了。父亲在厨房里突然喊我的名字,韦恩,过来一下。我跑过去,问他什么事。他说你去后院把母鸡和鸡仔们找回来。
于是我就跑到后院去找鸡。
哥哥坐在家门口前抽烟。
父亲在厨房里煮鸡肉。
我们三人围坐在饭桌前开始吃饭。父亲偏要我坐在他和哥哥的中间,说,你等下要给我们倒酒,就坐这里。我把父亲的酒杯和哥哥的酒杯全部倒满。父亲一仰头就把酒喝完了,我再倒,他再喝。他一连喝了三杯,哥哥跟着他也喝了三杯。
父亲说话了,阿德,你还是我的儿子吗?你离家出走我不说你,你三年来也不给家里来封信,你他妈的死在外面了?没死啊,你算不上什么,什么都算不上。父亲说这话时正在嚼着一块鸡脖子。我很奇怪,他吃鸡脖子不吐骨头,嚼碎骨头也没有声响。哥哥也在吃鸡脖子,但是他把骨头吐出来了。哥哥说,再怎么样我还是你儿子,你知道我为什么离家出走吗?你知道我为什么没给家里面写信吗?我不出去在家里面能干吗?父亲没有搭话,他再次端起杯子一饮而尽。
哥哥说,我和韦恩两个人读书终究不是件容易的事,让韦恩一个人去读书吧,他脑子好使,书我读不来,所以我要去南宁挣钱。我知道我没文化,可挣到一块算一块啊。你说我不写信,写了信又能怎么样?写个卵蛋信。
我现在在渠黎三中读初三。哥哥是在我读初一的时候离家出走的,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我的母亲也是在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离家出走的,那是四年前的事了,我当时上六年级,哥哥读初二。我记得那个下午,我母亲对我们哥俩说,我去砍甘蔗了,你们好好呆在家里。结果一整个晚上都没有回来。父亲也没有去找她,他对我们说她想走就走吧,我不拦着,但是走了就不要回来,回来我用斧头砍死这个女人。
后来每当下大雨的时候我就喜欢坐在家门口,呆呆地望着眼前越来越多的积水。积水是土黄色的,雨滴在水面上砸开许多的圈圈,圈圈荡来荡去很快消失了。水面上漂浮着鸡毛、树根、枯叶。我总感觉有人要走,就像这眼前的土黄色的积水一样,瞬间就流走了,然后又重新聚集成另一潭水。
父亲正在啃咬一块鸡爪,他没有修整过的胡子已经碰到了白色的爪尖。
阿德,你不是……不是我的儿子。父亲放下酒杯,他的胡子沾着几滴酒。
怎么样才算是你的儿子?难道你不是我老爸?好,我敬你一杯。哥哥抓起自己的酒杯碰父亲的杯子。父亲没有和他碰杯,而是突然哈哈哈大声笑起来,我和哥哥都吓了一跳。他站起来,右手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我听到了他粗糙得像山后松树皮的右手与桌子相碰后砸出“轰”的一声,鸡骨头被震得弹了起来。我女人是她自己走的,我没有打她。他娘的,有本事都别回来。阿德,你个兔崽子还回来干吗?父亲使劲拍打哥哥的肩膀,自己却提起酒杯喝了。
父亲喝醉了。十斤木薯酒他一个个已经喝了两斤多。哥哥还没醉,他笑了一下,看着我说,我给你五千块去读高中,你可要把书读好咯,不然我收拾你。
我身体颤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读高中?读完初中我就不想读了。
小子,你敢不去读我就打断你的腿。哥哥恶狠狠地看着我,你要是考不上扶绥中学你也趁早滚蛋吧,你也没资格用我的钱。我说我会考上的,我还想留着腿走路呢。
那才像个男子汉,你将来还要读大学呢。哥哥说完就把头压放在他面前的鸡骨头堆上了。
三
哥哥第二天就走了。
他说他要去凭祥做生意,不去南宁了。这次回来是为了让父亲跟他一起去凭祥做生意,但父亲不去,他说,除了甘蔗地,我哪里也不去。最后哥哥交给父亲五千块钱,给我留下一支金色的钢笔,然后背上大大的登山包头也不回地走了。父亲没有说什么话,跟以前一样,扛着一把锄头就去甘蔗地了。我跟在他的身后,左右两只手各提着两把一长一短锋利的镰刀。我心里觉得怪怪的,哥哥回来了,可好像又没有回来。
我家的甘蔗地和黄刚家的甘蔗地是邻近的,就像两家邻居一样。今早父亲起得很晚,现在太阳已经升到山顶了,黄刚家的甘蔗地里传来锄头嘴尖碰到硬碎石的声音,我知道这是黄刚家的老婆在甘蔗地里面干活。黄刚父子俩现在一定坐在电视机面前不厌其烦地看《西游记》,每次走过他们家的小卖部,远远就能听到孙悟空打妖怪的喊声。他们故意把音量调大,让全村的人都知道只有他们家买上了电视机,而且是彩色的。
我们走进两片甘蔗地方便走路留出来的过道,却发现过道小了一半。过道上都是新翻过的泥土,一些杂草被连根拔起,被新翻过的土块压在下面。黄刚家甘蔗地的旧土块和过道一半的新土块混在一起,成了名副其实的黄刚家的甘蔗地的一部分了。父亲把锄头放下,左右横放着一量,皱起了眉头。你先去砍枯叶,把没用的枯叶都砍掉,父亲说完就往黄刚家的甘蔗地去了。
我走进甘蔗地,掏出短镰刀飞快地砍掉枯叶。我听到了父亲的声音,你怎么私自把过道的地缩小了一半,还把它变成了你家的地?这过道两年前宽得能开进小四轮,去年你削去了一部分,我不说你,今年你又削去一半,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贪心啊?我偷偷走过去,看见黄刚的老婆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放在锄头棍的顶上,哟,这地也没说是你家的吧?你管得着吗?难道你要开着拖拉机进来收甘蔗?你开车还是你老婆开车?哦,忘记了,你现在没有老婆,可是我看你也买不起拖拉机吧,你应该先去买个老婆啊。父亲涨红了脸,一字一顿地说,那是过道的路,留着走路的,你懂不?不是我家的也不是你家的,你凭什么弄成你家的?黄刚的老婆拿起水壶喝了一口水,看都不看父亲一眼,那过道我看着有点宽了,放牛走嘛,母牛小牛都走不全,放羊过嘛,羊屎都落不到一处,我看你没有老婆又懒得动,那我就去胡乱弄了几下,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我能有什么办法?
父亲鼻孔里面喘着粗气,他朝黄刚的老婆脚下重重地吐了一口水,骂了一句不要脸,臭癫婆。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黄刚的老婆在后面说,癫婆也比你那老婆好。
父亲从我手里拿过长镰刀,呼哧呼哧快速收拾地里的杂草。他的速度很快,不一会儿,就收拾好了一大片,我家的甘蔗地出现了整齐的空间。你把这堆草都搬到石头那边去暴晒,过一两天草就枯掉长不活了。我按照他的吩咐把乱草搬走。地里面蝗虫到处乱飞,绿的灰的都有。小时候我很喜欢这些蝗虫,羡慕它们饿了就在甘蔗地里找吃的,或者飞到果园里偷吃水果而不怕看门狗,无聊的时候可以飞到山上去吹山风。
“扑哧”一声,我的头上突然飞过一只绿色的蝗虫,它的个头有大拇指一般大,硬翅下面的软翅是粉红色的。大蝗虫飞过黄刚家的甘蔗地,最后落到黄六家的甘蔗地边的石头堆。
黄六家的甘蔗地邻近黄刚家的甘蔗地,只不过两块地之间有一堆碎石块分离着。我家的甘蔗地和黄六家的甘蔗地就把黄刚家的甘蔗地夹在了中间,这样一来,想要逮住那只粉红色的蝗虫就必须穿过黄刚家的甘蔗地。我本来不想过去,但是回头一看,父亲还在忙着割杂草。用不着搬乱草,就去看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心里想。我弓下腰,像打仗的士兵一样,飞快地闯过黄刚家的甘蔗地。
我伏下身,屏住呼吸,慢慢地向大蝗虫摸索过去,靠近时,大蝗虫却“扑哧”一声飞远了。
我叹了一口气,悻悻地站起来。这时候我发现甘蔗地里面躺着一个女人,她身边的水壶倾倒了,水全部流进了土里。我走过去一看,原来是黄六的母亲。我叫了一声婶,她没应我,我再叫两声,还是没应。我想算了,也许是太累了躺下睡着了。我转身回去,走了几步,觉得不对劲。我回去仔细看看黄六的母亲,她的手里是被揉碎的土和草,衣服也沾了黄土。我一边喊一边推她,仍然没反应。我心里咯噔一下,不好,黄六的母亲累倒了。这是我第一次碰到有人晕倒,心里全是慌乱。
我愣在原地,看着她,她一动不动,我也一动不动。我打了个冷战。我赶紧跑回去找父亲。我穿过黄刚家的甘蔗地,完全不顾甘蔗叶划伤我的脸。穿过黄刚家的甘蔗地的时候,我被什么东西绊倒了。我听见一个女人“啊呀”大声叫了起来。原来我撞到了黄刚的老婆。她慌慌张张站起来,一边整理裤子一边骂骂咧咧地说,大白天的,你乱跑什么?你跟你爹都是下流坯子。说完伸手就是一巴掌。原来她正在小便。那巴掌打得很响亮,震得我的耳朵嗡嗡地叫。我摸着脸蛋,但是一点也不感到疼痛。
我喘着气说,有人累倒了,黄六的母亲累倒了,就在那边的甘蔗地里,你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吧。我还没说完,黄刚的老婆就往我的脸上吐了一泡口水。老娘活了这么久,清白差点就被你这野小子糟蹋了,你怎么不偷看你娘去啊?这事要传出去我还怎么活啊?我呆若木鸡,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又打了冷战,挣脱开黄刚老婆的双手,跑去找父亲。父亲当时正在弯腰割草,天气太热了,他把上衣脱了,后背全是汗水,流到他的裤子,裤子上面也湿了一块。我喘着气说,黄六的母亲累倒了,你快去看看,快去,就在他们家的甘蔗地里。
我把父亲带到黄六的母亲晕倒的地方,父亲把她抬起来,用大拇指使劲摁住她的人中穴。过了几分钟,父亲往她嘴里灌了些水。人还是没反应。父亲索性把人扛起来,他说,应该是中暑了,赶紧带回去看看再说。这时候黄刚的老婆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她张开双手拦住我们,眼里全是惊讶。
她“呸”地吐了一口水在父亲的肩膀上,然后用手指着父亲的鼻梁。好呀,你们父子俩,狼狈为奸,想女人想疯了吧?大的想搞人就把人弄晕了,小的跑去偷看我,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们都是他妈的下流坯子,色鬼投胎的烂骨头,我要去告诉全村人。
父亲愣了,说,不是你想的那样。
黄刚的老婆双手叉腰说,我全都看见了,你衣服都脱了,还想抵赖?我要去告诉全村人。
父亲不理她,抬手推开她,把人扛走了。我拿着水壶跟在后面。黄刚的老婆还想扯住我的衣服不让走,我用力挣扎了几下,逃脱了,但是衣服被扯开了一大块。
四
从那件事以后,我再也不敢喜欢蝗虫了。因为这件事,父亲蹲了十五天的牢房。不管警察如何询问父亲,他始终就说一句话,我只想救人,没想干什么,你们想歪了。但是黄刚的老婆一口咬定父亲猥亵女人。到了第十三天的时候,黄六的母亲去派出所把事情说明了,她说她是干活太累了,天气又热,所以中暑了。警察最后放了父亲。
父亲出来的时候,黄六父子俩正在外面等他。他们两人嘴里都叼着一根烟。黄六说,三顺叔,走,喝一杯去。他们三人来到顺丰大排档,点了四碟炒菜,一件啤酒。
黄六自己到外面买了两瓶德胜酒,他说他自己和父亲喝白酒。父亲也不推脱。连喝了三杯白酒以后,黄六歪着脑袋说,三顺叔,你爽快点,给个痛快话,谁的话我都不信,你把整件事情给我说说。父亲就坐在黄六的左边,右边是黄六的父亲。父亲扭过头看着黄六父子俩一字一顿地说,今天我把话挑明了,我当时只想救人,没想过要干什么,如果我说谎,我就切了自己裤裆里的东西拿去喂鸡。黄六听了,喝了一大口白酒,大声说好,痛快,我就知道三顺叔不是这样的人,干了这杯。三个人端起酒杯喝光了。
这时候黄六的手机响了起来,他从口袋里掏出来低头一看,然后就走出外面接听电话。屋子里只剩下黄六的老爹黄忠和父亲。黄忠的头发已经掉得差不多了,他的秃顶上现在还有一层灰尘,这是搭摩托车过乡间小路的时候带来的。两人只喝酒,不说话。
过了几分钟,黄六走进来了。他说,有人急着要买甘蔗,我得回去看看,你们先喝着,我一会就回来,三顺叔,回来我再陪你喝。黄忠站起来说,让我去吧,你留下。黄六扬起手,说你懂什么,我去。说完启动摩托车走了,路上留下一股灰尘和青烟。
屋子里又只剩下父亲和黄忠了。两个人还是只喝酒吃菜,一直不说话。黄忠头上的灰尘和汗水融为一体流到了他的额头上。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黄忠突然说,三顺啊,我知道你是老实人,但是人也有犯糊涂的时候对不对?说这话的时候,黄忠不敢看父亲的脸。父亲有点惊讶地说,你这是什么话?你到底想说什么?别磨磨唧唧地像老母鸡下蛋。这时候黄忠别过脸来看着父亲,然后又转回去了。他说,我女人是晕倒了没错,但是、但是谁也保不住晕倒后没什么事情发生,这年头你也不容易,是吧?父亲惊奇地看着黄忠,在他的印象里,黄忠可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村里面要是有条狗咬他了,他骂都不敢骂一声。
父亲说,听你说这话你是不相信我啊,是谁告诉你这么说的?黄忠自己点了一根烟,吸了两口,说,你甭管谁告诉的,你先说该怎么处理。父亲也拿了一根烟,不过黄忠伸手过来帮他点上了。他吸了几口,一直没说话。抽到烟还剩下半截的时候,父亲扔在脚下用脚尖一捻灭掉了,你不说我也知道,是黄刚的老婆教你这么说的,你不信我的话竟然相信那个糟婆子的话,别忘了你老婆可是我亲自扛回来的。
黄忠只是一个劲地抽烟,好像没听到父亲说话一样。
父亲说,好,回去我给你五百块,倘若你老婆再晕倒在地里,打死我也不会去看了。黄忠好像没听到他的话,自顾端起酒杯喝了起来。喝完一杯他甩手抹掉头上的汗水和灰尘。
父亲自己倒酒,喝了一大口,一瓶德胜酒已经喝掉了一大半。过了一会,黄六回来了,三个人又继续喝酒。黄六当然不知道刚才发生的对话,依旧和父亲碰杯喝酒。黄忠也跟着喝酒,不过从头到尾都没有和父亲碰过杯。那天晚上,父亲很晚才回来,他一回来就坐在家门口的石头上不停地说话。我知道他说的是醉话,含含糊糊的,说不清楚,听的人也听不清楚。不过他的样子很像我晚上和阿高对话的样子。阿高就在我们家的对面,是一座山,也许它听得懂父亲说什么。
父亲的猜想是对的,的确是黄刚的老婆教黄忠这么做的。那天父亲亲自去找黄忠,他们两个坐在房间里,掩上门,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的塑料袋,说里面是五百块钱,从今往后这件事就算完了,谁敢再提谁就是乌龟王八蛋。黄忠把塑料袋捧在手里说好,不提了,提了谁都不省心,谁再提谁就是乌龟王八蛋。
父亲要走的时候,黄忠在后面叫住他,叫他留下来一起喝两杯。父亲头也不回地走了。父亲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黄刚的小卖部买烟。父亲走到柜台前说,来两包烟。小卖部里只有黄刚的老婆一个人,她正在看《西游记》,音量还是很大,从外面就能听到了。父亲重新大声地喊了一遍,黄刚的老婆转过头来白了他一眼,不悦地说,不卖,没有烟了,有也不卖给你。父亲用手指敲打着玻璃柜台,这烟就在玻璃柜里,我都看见了,你到底卖不卖啊?
黄刚的老婆还是一副雷打不动的样子。我记得那晚父亲没有买到烟。
五
有一天早晨,我和父亲在松树林里整理枯黄的松叶。那些松叶可以用来当柴火烧饭。我的周围是我家的鸡群,它们在刨土,松叶里留有它们的毛。村口突然传来大喇叭的声音,乡亲们,开会了,大家都出来开会了。喇叭喊了半个钟头,最后村里面的人才不情愿地走出来。我看见两辆银色的面包车停在村口,车身写有“崇左明糖农务”六个字。原来是糖厂的工作人员。贴出一张大大方方的红纸,上面写着清秀的毛笔字:
各蔗农,今榨季以来,第一批第二批甘蔗相继进入蔗场,但是发现有七起甘蔗车夹带异物(铁器、石头、木块等)进入蔗场的事件。若这些异物随甘蔗一起过榨,糖厂生产设备将会受到严重损坏,出现停榨几小时甚至几天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各蔗农砍出的甘蔗将不能按计划拉进厂入榨。在此恳请各蔗农、运蔗司机配合糖厂从源头抓起,在装车环节严格把关,禁止各种异物随甘蔗混装,确保自己的甘蔗能尽快进厂,达到多方共赢。
崇左明糖农务
013年3月12日
工作人员又把上面的内容对着喇叭读了两遍,他们说会查清楚到底是谁做的缺德事。人群里立即像一锅热油进水炸开了。村里面的人叽叽喳喳争吵了一会,最后一致决定,找到这个罪魁祸首,一定要找出来。耽误了榨期,就是耽误了大家赚钱,耽误大家赚钱那可就不是一件小事了。在蔗农眼里,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赚钱更重要的呢?
我家的甘蔗是第三批进入蔗场的,所以父亲不担心,他叫上我回家去后院收拾松叶。我只好跟他回去。
五天后,父亲出事了。
当时我正在渠黎三中的教务处写检讨。我把一个男生的鼻梁打折了,我看不惯他把一个女孩子整哭了。
我是第二天赶到家的,我看见父亲躺在床上,他的后背被白色的绷带包住了。父亲的眼神有点呆滞。他看见我就说话了。我把耳朵凑过去,他说了一个“粥”字,他想喝粥。
我走进厨房,眼前的景象让我震惊。锅盖上都是鸡毛,白的、黑的、灰的、黄的都有。地上分布着已经变硬了的鸡屎。厨房好几天没开锅了。
我把煮好的米粥端到父亲面前,他的眼泪簌簌地落下来了。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把脸向上看,尽量让眼睛看到发黑了的天花板。他摇了摇头,嘴巴张开,但是没吐出几个字。我只好喂他喝米粥。这是父亲的性格,他不想说的事情即使有人用扳手敲落他的牙齿他也不会吐出半个字。
后来我用两包香烟从黄六的嘴里得到了一点消息。有一天晚上,父亲从自家的甘蔗地出来,就被一群人用蛇皮袋包住了。应该是四五个蛇皮袋捆住头和身子的,黄六嘴里冒出一股烟,淡淡地说。烟雾在他眼前升起来,有几缕烟气萦绕在他的头上,挥之不去。
父亲被袋子捆住头以后,就被打晕在地。他们一致认为他就是那个在甘蔗车上乱装异物耽误大家赚钱的人,黄六继续说。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太记得黄六那天下午说的话了。我只记得父亲的后背从那以后就留下了密密麻麻的疤痕,那是许许多多的小坑,小小的肉坑。那晚包括看热闹的黄六在内的一群人把五六个蛇皮袋点燃,然后往父亲的后背上放。很多人都见过滴水穿石,但是没见过点燃的蛇皮袋像滴水穿石一样滴在人的后背吧,那是一种滴水穿石般刻骨铭心的疼。一滴滴燃烧的火焰像宇宙飞来的陨石一样落在脆弱的后背,随即燃起一股肌肉烧焦的烟气。玩弄陨石的人群像是围着篝火,近乎疯狂了。
你为什么不阻拦他们?我问黄六。
唉,你不知道,他们像疯狼一样,我要是拦着,我也会像你父亲一样受虐了。
他们都有谁?你也在场的,你应该知道。我问黄六。
黄六说,他们个个蒙着脸,看不清楚,不过黄刚肯定参与了,只有他穿了皮鞋,我认得他的皮鞋。
他就是领头人吧?
黄六灭掉烟头说,谁说得准呢?被烧背的也不是你父亲一个人,村里还有几个人也被烧背了。
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不让我去派出所报警。当我告诉他黄刚是主谋的时候,他依旧面无表情地喝粥,喝得吧嗒吧嗒地响。
告他干吗?就我们两个?这事不是那么简单的,告了也没用,父亲把烟杆敲在桌子上咚咚作响。
我说,那怎么办?受苦受难的是你啊!你难道不恨他们吗?
父亲说,你回学校吧。我看了一下他古铜色的脸,没有说什么。
我把碗筷收进厨房的时候父亲又说,记住,在学校谁敢碰你你就敲破他的脑袋。我没有告诉他在学校我已经把一个欺负女生的男生的鼻子打歪了。
六
三个月过去了,有一天早上,村口又传来了清脆的喇叭声,开会了,乡亲们,开会了,大家都出来吧。村里面的人照旧是半小时过后才出来。他们都以为是蔗场的工作人员来了,可惜不是,他们是政府的几个干部。他们穿着白色的衬衫,大声地说新农村建设的喜讯,说政府要给每家每户建立一个沼气池。
全村的人全都在注视他们白净的衬衫和油亮的皮鞋,没人在乎他们的话。黄六和几个人在人群里笑着说,哎呀,这政府的干部啊就是不一样,皮鞋上面都是油,再看看黄刚的都觉得烂了眼了。黄刚也在人群中间,他没有说什么,和别人一样回去了。几个政府干部要求去探访的时候村里人却支支吾吾走开了。只有父亲带着两个人去了我家。一个戴金边眼镜,一个没戴眼镜。
父亲说,这沼气池有什么用处呢?政府真的让你们来帮忙吗?他们就说沼气池产的就是沼气,沼气可以烧火,比柴火还好。父亲半信半疑,说我家后面就是松树林,我们一直都用松叶烧饭,习惯了,我还没见过比松叶好用的东西。刚才我见你们说得老实,所以叫你们来我家看看。戴金边眼镜的干部笑起来说,哎呀,还是大叔您懂道理,外面的人都说你们村犟,一副牛气哄哄的样子,我看也不全是啊,我们打算在您家先建一个沼气池,重点示范给其他人看看,您看怎么样?父亲摇头说,我叫你们来,就是相信你们,相信政府,你们说要吃饭是吗?我现在就去拿饭。父亲转身要去厨房端饭菜,不戴眼镜的干部急忙拉住他,笑着说,叔,我们说的是重点示范,做出样子给别人看,不是吃饭,您听错了。
这两个人最后把建立沼气池的地方定在了鸡栏旁边,他们说建在这里投粪方便。到了第三天,两个干部真的带人来我家开始挖坑,他们说要挖一个大大的圆形的坑。小四轮运来水泥、沙子、红砖,堆放在我家门前的石头堆前。许多人都跑来看,他们站在圆坑旁边说,三顺,你这是要干吗呢?建房子挖地基吗?挖地基也不是这样挖的啊,没见过谁挖个圆形的地基。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干部说,不是挖地基,这是沼气池,以后你们就懂了,以后大家都会有。
那时候我从学校回来了。我说,听见没有,这是沼气池,能烧火做饭的,到时候你们就懂了。
父亲接着我的话说,到时候你们就懂了!
村里的人鄙夷地说,沼气池?不就是个坑吗?还不就是个土灶子?你家用得着这么大的火灶子吗?你去找个老婆来使劲用上三天,我们就懂了。
父亲这时脸就红了,他大声说,滚你妈的蛋。
围观的人就走开了,他们知道父亲生气了。生气的人像疯狗,随时有可能咬人的。他们也不相信什么沼气池,不相信池子能装什么,也不相信沼气这种鬼才晓得的东西能烧火。但是父亲就信了,他说到时候你们就信了。
沼气池建好了,事实证明父亲是对的,沼气能用来烧饭、烧水。我第一次见到蓝色的火焰,并且用它来老老实实烧了一回饭。那一晚我和父亲的晚餐是惬意的。我嘴里嚼着一股米饭说,我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就知道沼气池这种设备,但是没见过。父亲说,这东西今天用上了还真有点不相信,政府的人是可以相信的,至少不会在背后耍弄人。
我家成功使用沼气烧火做饭惊动了全村人,他们迫不及待地都建起了沼气池。
他们看见蓝色的火焰就兴奋,一兴奋什么想法都来了,烧火做饭,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了。于是,蓝色火焰上出现了猪肉、老鼠肉、田螺肉、番薯、土豆、韭菜。只要你一走进我们村,远远就能闻到烤肉香和菜香,像花香持久地飘进人的鼻子。
有一天,父亲去小卖部买烟,恰好碰到一群人在打麻将。父亲叫了一声买烟。黄刚急着摸麻将,不搭理他。黄刚的老婆出来了,她白了父亲一眼,极不情愿地拿出香烟。父亲伸手拿过烟,听到黄刚的老婆鼻子里传出一声重重的哼声。
自摸,哈哈,给钱。突然有人拍打桌子大叫起来。
他妈的,倒霉透了,不打了。黄刚站起来不耐烦地说。
黄刚转身的时候才发现父亲,他阴阳怪气地说,三顺,好久不见,最近怎么样啊?
父亲说,托你的福,最近很好,就是腰板有点疼。
黄刚笑了,我才托你的福呢,托你的福,我差点死在沼气火里。黄刚这么说是因为前不久他的儿子黄飞洪拿瓶子乱收集沼气不小心起火把家里的厨房烧掉了。
黄刚歪着头说,我记得是你先把沼气池这东西带进来的吧,当时政府干部还把你夸了呢。
父亲笑了一下,我还没向你道谢呢。你在我后背挖了十几个坑呢,赶明年你老婆都能种上树苗子咯。
黄刚收起笑容,严肃地说,你真会开玩笑,我怎么能在你后背挖坑呢?
父亲手一扬,说,你给我称两斤花生米。
黄刚换上了以前的笑容,有生意做的时候他脸上挂着笑容。父亲提起花生米的袋子,掂了两下,说,这不够两斤,你再称一次。黄刚嘴巴扭动,想说点什么,但是没说出来。他重新称了一次,说你看,两斤,没错吧?
父亲拿走装花生米的袋子,把秤子的圆盘拆了,盘子底下是一块大磁铁,紧紧地吸住圆盘,就像婴孩吸住奶头一样。
黄刚的脸瞬间就红了,但是他淡定地说,哪个兔崽子把磁铁块挂在下面了?黄刚手疾眼快,收走了磁铁。
父亲笑了,他说花生我不买了,你自己留着吧。说完就走了。
打麻将的人都是村里面的人,他们生气了,黄刚原来你是个贱种啊,你他妈的坑了我们多少年啊。有人抓起圆盘飞向黄刚的头。最后黄刚把一袋花生免费送给他们,还有十几包香烟。
等所有人都离开了,黄刚才摸着发肿的头,走到门外大声地说我操你们的祖宗,都滚回你们的娘胎去吧。
从那以后,人们开始称呼黄刚叫“黄铁头”。黄刚被别人这么喊的时候,他的脸就红了一边,但上面依旧摆出笑容。
七
父亲给我办了一张存折,我就很少回家问他要生活费了。有一天他居然来学校找我。他更黑了,他的脸已经被太阳晒成了黄土的颜色,他一笑就成了古铜色的铁板。我注视他的脸,感到他身上藏有一股拘谨和不安。我知道他是因为很久没上过县城了,城里翻天覆地的变化出乎他的预料,城里建了铁路,修了公路,还架了桥。
我问他吃饭没有。父亲说没有。我打算带他去学校饭堂吃饭。他说,不用了,我们去外面吃。父亲带我去了附近一家大排档。
他点了两瓶啤酒,说,大热天的,喝两口酒,身子才爽朗。
你怎么有空来看我?
我来买几笼小鸡仔回去养养,顺道来看看你。
接下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说话。我们像两个陌生人一样,我吃饭,他喝酒。父亲突然说,你大哥阿德过两天可能回来,他给人捎信回来了。我有点激动地说,他真的要回来吗?他回来呆多久啊?不会匆匆回来又匆匆走吧?
父亲说不知道,也许不会回来,那也说不准。我看着父亲的脸,在他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喜悦和忧虑,反而是淡淡的疲惫。
吃完了饭,父亲说,我要去农贸市场买几笼鸡仔,你去学校好好读你的书吧。我们就分开走了。
我往学校的路走去。过了一个拐弯后,我看见对面的马路中央躺着一个女人。她背对着我。看不到她的脸,我从她乌黑的头发和匀称的身材判断,她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年轻女人躺在马路中间极为危险,随时都有可能被车子碾成肉饼,但是没有一个人过去把她拖走。
突然她的前方驰来一辆黑色的汽车,黑色的车身闪闪发光。车子呼啸而过,这个年轻女人是死定了,但是她没死,因为她没有被车子撞飞,被撞飞的是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竟然是父亲。没错,就是父亲,他还穿着我熟悉的绿色的军上衣。他是从我的背后冲过去的,原来他一直跟在我的身后。父亲冲上前去以最快的速度拖开了那个年轻女人,他的身子像一条死狗被主人用力甩飞出去一样,几秒钟后才重重地落地。他嘴里叼着的烟从嘴里被抛出去,无奈地躺在被晒得干干的马路上,灭了。
父亲躺在医院里,他的头被撞出血了,马路上留下他的一大摊血。两条白色的管子伸进他的鼻子里,如果他看见了,肯定认为是自家沼气池的小沼气管呢。
撞他的车紧急刹车后,车内伸出一个光溜溜的头回头看了几秒钟,然后加大油门一溜烟逃跑了。
我坐在医院走廊冰冷的凳子上,心里在暗骂父亲是个傻子,城里人不管的闲事他偏偏要管,真是狗抓耗子,多管闲事。我坐在凳子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今天躺在马路上的年轻女人了。
你干吗要躺在马路上呢?你没事可以躺在公园或者桥下啊。我问她。
女人说,我不想活了。我说,你不想活了,可是我的父亲想活啊。女人说,对不起啊,可是我真的不想活了,你们不该来拖开我。我笑了,谁想拖开你呢?马路上来来往往这么多人谁有心思去管你呢?只有傻瓜才会去搭理你。
年轻女人这时候乌黑的头发突然变成一头蓬松发散暗淡的乱发,脸色苍白。女人说,我对不起你的父亲,希望他没事。
我说,他要是死了我也没办法活了,他为了救你被车撞了,本来他是不用躺在医院的。
年轻女人低下头不说话,她的头发盖住了整个脸。
我梦见哥哥回来了。他跟以前一样,穿着黑色的西裤和黑色的上衣,还有一双锃亮的皮鞋。见到他回来,我差点就哭了,我说,爹被车撞了,他的头出血了,他在里面躺着,你去看看他吧。哥哥扶住我的肩膀说,我看过了,他现在没事了,医生说了,多休息休息就好了。我说,你去看看他吧,爹的头出血了,爹快要死了。哥哥僵硬的脸笑了。我问他,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哥哥说,我回来了,爹会没事的。
我还梦到了阿高和阿山。
这两座山像两位兄弟坐在我的左边和右边。我感到安心了许多,医院晚上太冷了,它们两个坐在我的旁边,我顿时暖和了许多。
我说,阿高,爹被车撞了,你快去看看他吧,爹快要死了。
我又对阿山说,爹被车撞了,你快去看看他吧,爹快要死了。
阿高和阿山不说话,我忘记了它们是不会说话的。我说,阿高啊,以后爹不能站在你的面前“咕噜噜”地刷牙了,还有半夜他也不会起来在你的脚下撒尿了。阿山啊,以后爹不能去甘蔗地干活了,他不会再跑上山,一屁股坐在竹子林下乘凉了。
我最后对它们说,我的阿爹快要死了。
第二天早上,我被一阵刺耳的哭声吵醒。我张开眼一看,原来是一个护士正在给小孩子打针。我发现我的身边坐着两个人,一男一女。我使劲揉双眼,终于看清了面前的两个人,男人是哥哥,女人是昨天躺在马路上的女人。
哥哥还是以前的模样,穿着黑色的西裤和黑色的上衣,还有一双锃亮的皮鞋。昨天的女人披头散发,脸色憔悴,再也没有昨天的红润。
哥哥说,你醒了,饿了吧?先吃两个包子吧。我问他,你怎么回来了?哥哥说,我昨天刚回来。我对身边的女人说,你怎么坐在这啊?要不是你,我父亲就不会被车撞了。我又对哥哥说,你快去看看爹吧,他被车撞了,他快要死了。哥哥说,我去看过了。
从昨晚到现在,原来他们两个一直呆在我的身边,我把他们当成阿高、阿山了。
父亲被撞成了植物人。年轻女人成了哥哥的妻子。
我常常在想,这是祸还是福呢?有一次我问正在给父亲擦洗身子的嫂子,你当时为什么躺在马路上?嫂子说,我被骗了,被城里的一个老板骗去了一切,当时不想活了。
那你为什么要嫁给我哥?
嫂子笑了,她把父亲的身子翻过来说,我第一眼就觉得他是好人,跟你父亲一样,都是好人。
父亲被撞成了植物人,却意外地收获了一个儿媳妇。我第一次喊她一声嫂子时,这个女人眉开眼笑了。
嫂子每天都帮父亲擦洗身子。嫂子说,爹,洗澡咯,今天天气很好哇。父亲两只眼睛盯着她看,他的眼里流露出愉快的光彩。我还记得嫂子第一次发现父亲背后许许多多像黄豆大小的伤疤时满脸惊讶,她摸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坑就抽泣了,爹你真是命苦啊。我没有告诉她那些伤疤是被活生生地烧出来的,我打算让这个秘密永远地沉在内心的湖底。
八
三年后,我考上了大学。我去了师范学院,打算毕业后回到扶绥中学当一名人民教师。
哥哥回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了。偶尔他也会上一趟南宁,买一点中草药回来让嫂子煎给父亲喝。
哥哥用在凭祥做生意赚的钱在村里重新开了一家小卖部。黄刚的小卖部倒闭了。他的小卖部被工商局端了,因为他卖假烟,让村里的人出冤枉钱抽了几年的假烟。小卖部开张的第一天,哥哥让我写一副对联挂在门口。我不知道该写点什么。哥哥鄙视地看着我。他说,你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读了这么多书难道连个对联都写不来?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尴尬,只好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 一二人千姿百态。下联是:三两步五湖四海。横批:善德施恩。我想起父亲给我们兄弟两个起的名字韦德、韦恩。我猜当初他的意思肯定是让我们兄弟俩修德行善,勿忘恩惠。哥哥看我写完后称赞说,写得不错,没有辜负我辛苦赚钱供你读书。
父亲一直想让我离开这里,离开甘蔗地,但是我还是回来了。我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地方,我离不开那些甘蔗。在夜里我常常梦到自己一个人跑进甘蔗地里抓虫子,我看见父亲穿着绿色的军上衣正在锄草。有时候我跑到山上去,大喊一声自己的名字。我站在山顶俯瞰,看见一列从南宁来的火车从我的眼皮下驶过,像一条蚯蚓爬过。我手里提着两根甘蔗,上边咬一口,下边也咬一口,但是感觉上边的甘蔗没有下边的甘蔗甜。我醒了,原来是一场梦。
每年会有那么几个月,哥哥像父亲一样天还没亮就去甘蔗地里干活了。每年也有几个月,他跑去县城做黄皮果的批发生意。用村里人的话说,哥哥是一个会活路的人。外面和他做生意的人说,他是一个实诚的人,让人放心。
后来,哥哥当了村长。因为他见多识广,头脑又灵活。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的村长是黄刚。
哥哥自己出钱在村口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了十四个字。上面是四个字:甘蔗林苑。下面是十个字:清水蒸芙蓉,天然煮琥珀。外面的人看见了疑惑地问,韦德你这石碑上的字是什么意思哟?哥哥说,没啥意思,是骡子是马,是俊闺女还是丑儿媳自个儿来瞅瞅就懂了。第二年,我们村的拐子黄六娶上了媳妇。黄六龇牙咧嘴地对大家说,这花姑娘是村长给介绍的。不久,韦贵也娶上了媳妇,虽然他哥哥韦富在工地摔断了腿,成了走路比黄六还拐的拐子。村子里的光棍越来越少了。这全是村长韦德的本事,老人们说。
今天学生放假了,学校也给我们老师放了假。我立即去火车站买了回家的票。我有两年没有回家了,两年没有见到父亲和哥哥了。谈不上想念他们,只是有种见面的冲动一直压在胸口撞击我。我坐在火车上,看着外面从我眼前一闪而过的甘蔗地。这不是我家的甘蔗地,我家的甘蔗地在铁轨的另一侧,在山峰的另一边。我想起了我的故友,阿高和阿山。
突然坐在我对面的男人站起来拍我的肩膀,他激动地说,韦恩,你是韦恩吗?你是三顺的小儿子韦恩吗?我看着这个男人的脸,有点眼熟,但是想不起来是谁了。我说,老乡,我是韦恩,我爹是韦三顺,你是?男人大笑起来,哎呀,真是巧啊,我是你黄忠叔啊,你不记得我啦?我还真有点不记得了,在我的印象里,黄忠是一个有点木讷的人,可眼前的男人面色红润,穿着讲究,不像黄忠。见我一直盯着他看,黄忠递来一支烟。我说,我不抽烟,火车上也不允许抽烟。他只好把烟收起来,说,也难怪你不认得我,你一直在外面读书,没时间回来。这个男人不停地在地上吐痰,又用脚擦掉。他用手对头发又摸又按的,原来他戴了假发,我记得曾经的黄忠差不多是秃顶的。我终于相信他就是黄忠,黄六的父亲。黄忠的旁边还有一个小孩子,我猜他应该就是黄六的儿子吧。
我和黄忠聊了一会儿就没什么陌生了,我们聊到了村里面的变化。黄忠说,村子里面现在通路了,硬邦邦的水泥路,随便走哇。
我说,是嘛,路修得这么快啊。黄忠说,那都是你哥哥的功劳啊,你哥是个有能耐的人啊,你们兄弟俩都是有本事的人。
听到黄忠这么说,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从书包里拿了一包薄荷糖递给黄忠的孙子,这孩子定定地看着我。黄忠让他喊我一声叔叔。他却摇了摇头,说了一句谢谢。我摸着他的头说,好乖。
我们坐在车厢里有点闷热,头上的空调在这个夏天根本不起多大作用。过了一会黄忠突然放低声音说,你还记得当年你爹去县城找你被车撞的事吗?
我有点惊讶,黄忠怎么突然提起这件事呢?我说我还记得一点。
当年你爹去县城是去报警的。
报警?我怎么不知道?
我们村村后的山坡被黄刚承包了,他私自卖给大老板种植一种树。这种树真是奇种,像孩子吃奶,一夜就能长高长大了,可是不久后土地就废了,种其他树都会枯死。
那你们还让黄刚承包?
当时谁都不知道会是这样,个个眼里只看钱,后来只有你爹发现了。
你们是怕黄刚吧?
我们都怕黄刚,只有你爹不怕,他是条汉子。
黄刚现在怎么样了?
现在他啊,老老实实呆在家了,听说犯了精神病。当时我们没有揭发他,是你哥不让揭发的。
黄忠最后有点愤恨地说,是我早就去揭发他了。我知道这句话是他为背后跟父亲一模一样的伤疤有感而发的。
我想当时父亲是想和我吃完了饭就去报警的,结果被车撞了。哥哥知不知道父亲背后伤疤的来源呢?他应该是知道的。
我终于到家了,村里的变化正如黄忠说的一样,修了路,还装了路灯。我是搭了韦富的三轮车回来的。韦富的脚虽然拐了,但是不妨碍开车。我给他钱的时候,他怎么也不肯要。他说,我怎么能要大学生的钱呢?他说完就走了。
我走进家门,家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人在家。我走进父亲的房间,看见了他的身子安静地躺在床上,他的衣服和指甲都是干净的,还有一股肥皂的味道,看样子是嫂子刚给他擦过身子。
我看着父亲的脸,他的脸以前是古铜色的,现在有点白了。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喊了一声爹,我回来了,我回来看你了。说完我的眼泪就来了,泪水落在他的衣服上。
爹,我是韦恩啊,我回来看你啦。
有人进来了,是嫂子。嫂子看见我高兴地说,韦恩,是你吗?哎呀,你回来了,你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
我说,今天刚到,走得急来不及说了。
嫂子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说完嫂子也跟着流泪了。
我抹掉眼泪说,嫂子你别哭。
嫂子抹去眼泪,说,我去把你哥找回来,他在山后寻鸡仔呢。
过了几分钟,哥哥回来了。哥哥比以前老了许多,我看见了他头上有了几根白发,他的身子也没有以前那么直挺挺的了。
哥哥看见我就笑了,他说,大学生,你终于回来了,回来了就好啊。他声音很大,所有人都听见了。
我看见他笑,也跟着笑了一下。我说今天学校放假了,我就回来了。
过了几分钟,哥哥收住了笑,一脸正经地说,我想筹钱建立一所小学,我想让你回来当校长,怎么样?
我叫了一声哥,声音很小。我想不起来有多久没有这样叫他了。虽然有点小声,但是我想哥哥应该听到了。哥哥只是看着我。
我抬头迎上哥哥的目光,不说话。然后我们都笑了,笑得很舒坦。
突然嫂子在父亲的房间里惊叫一声,天啊,韦德,韦恩,你们快进来,快进来呀,爹居然说话了。
我们兄弟俩赶紧跑进去,我听见父亲眨着眼睛轻轻地说出了一个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