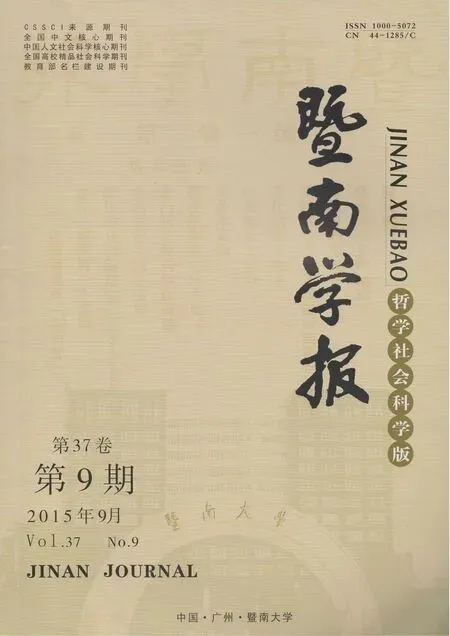论杨慎的骈文尊体思想
2015-11-14李慈瑶
李慈瑶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弘治至嘉靖间,复古派倡导“文必秦汉”的散文写作主张,一度振起明前期文坛的疲软之风。但它久而成弊,产生了机械拟古、晦涩难通等显而易见的普遍问题。与此同时,作为六朝初唐派领袖的杨慎则转立门户,别开生面。他沉酣《文选》,采撷偶俪,写了不少属于四六话性质的文论和文摘,这就较之唐寅、徐祯卿等吴中文人的地域性创作冲动,更多了几分理论探讨和技法研磨层面的自觉性与系统性。而且,就笔者目力所及而言,这些读书札记也是明代最早的一批具备一定数量与规模的四六话,无疑在明代骈文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而凭借自身的广博学识与过人才力,杨慎也足以毫无愧色地跻身于明代最出色的骈文作家行列。
目前,学界对六朝初唐派文学思想及其作品的把握基本仅限于诗歌领域,对杨氏骈文观及其创作的分析正有助于推进这一认知的广度与深度,并进一步还原当时文学历史生态的丰富性与立体性。另外,杨慎个案研究的现有成果虽已涵盖了文献的校勘整理及其生平交游、学术思想、诗作诗学、俗文学等各个领域的研究,但唯独对其骈文理论与骈文创作尚无独立、深入的涉足,而往往止步于笼统地言及他对《文选》和六朝诗文的推崇,如雷磊《杨慎诗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版)和高小慧《杨慎文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版)的第二章第二节《杨慎论六朝文学》都是着重探讨其六朝诗学观的;杨钊的《杨慎研究:以文学为中心》(成都:巴蜀书社2010 年版)第二章第一节《杨慎文论》虽然详细地分析了杨慎的各种文章观,并认为杨氏偏爱“具有‘魏晋之遗’的精警而隽永的小品文”,却也没有明确阐释他的骈文观。所以统观之下,这是一块亟待填补和开拓的未知空间。本文将先专就杨慎的骈文尊体思想展开探讨。
一、士大夫精英的尊骈话语
骈文在明代并非主流文体。它大致有两种存在形式:一是吴中地域文学的独特符号,具体表现为多样化的题材、体裁以及庞大的本土作家群;二是特定应用文的默认格式,在官方是表、笺等常用公文,在民间则以晚明泛滥的四六书启最为显著,因它代表了较为正式和文雅的社交措辞。前者指向审美,后者侧重功利,由此也就孕育出了两类迥异的尊骈话语。
洪武年间,朝廷曾屡次下令禁用四六公文,并颁布散体范文以为天下式。事实上,其后的表、笺、册文等大多仍袭旧体,只是文学性普遍较差;成、弘以后则连诏、制等其他体裁也有了明显的骈化,行文水准也明显提高。可以说,到了明代中期,骈文已经在政府的日常事务中扮演着非常活跃的角色了,但因它偏重形式、易流于虚美,所以还是无法摆脱文中末品的地位,成了名实相悖的无冕之王。吴宽在成化八年(1472)状元及第后依例上呈了《赐进士及第后率诸同年谢恩表》,其中提到:“布帛菽粟,浑然犹三代之言;月露风云,陋矣非六朝之体。辞达而已,文在于兹。”文贵辞达,故以唐、虞质实无华之文为尊,而贬斥晋、宋以降的俪词浮语。这一论调与朱元璋曾全力倡导的文学标准遥相呼应,可以看出明初以来中央文统的相对稳定性与传承性。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表本身却是一篇典型的四六文。吴氏为文取径唐宋古文大家,尚不出台阁轨迹,该表通篇也是以虚词散气运笔,明显借鉴了宋骈的表现手法,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骈体结构的存在感。但细看之下,其主题终究难脱谀圣之空言,而追求形式主义的痕迹也是无法抹杀的,如“食芹而美,虽怀一献之素心;采葑不遗,遽辱九重之清问”一联便兼用了植物对、数字对和流水对,用典妥帖,措辞得体,颇能由此一窥作者的文心巧思。
吴宽的四六表中暗含了尚质与工文间的矛盾,一叶而知秋,成化、弘治间文风转变的大势与过渡期的复杂面貌也已隐隐露出端倪。吴中派的兴起正是当时民间文学审美主义勃兴的突出表现,他们热衷《文选》,竞习骈俪藻绘,显示出有别于时体的鲜明风格。但须注意的是,其群体构成是以祝允明等在野文人为主的。社会身份的差异往往造成立论重心的区别,地方散人的处境使他们更倾向于纯文学的诉求和个性化的体验,这就进而决定了其骈文尊体思想主要是建立在对以六朝文为代表的“文”的合法性的辩护与强调之上的。而作为内阁首辅之子、少年状元、翰林院修撰,杨慎则是成长于中央士大夫圈子的绝对精英,耳濡目染的是“文以载道”的政治文化。他曾因抗议正德皇帝微行出居庸关而被迫称病还乡,起用后不久,又在“大议礼”案中哭谏,从而遭到嘉靖帝廷杖两次与谪戍云南的严酷惩罚,彻底断送了原本的远大前程。这种强烈的儒家济世情怀和文臣辅政责任也随之贯穿到了他的尊骈理论之中。
《〈群公四六〉序》写于杨慎被流放边地的近第三十个年头。早在嘉靖十一年(1532)春,他便偶得了《群公四六》这部宋人骈文集的古刻,今在友人张臬的帮助下翻印出版。虽是事隔多年,杨氏在叙及藏书始末、品评作家作品时仍难抑其生涯蹉跎的慷慨悲愤之气:
滇云僻在万里,其士夫皆江南播移,楚蜀流寓。其地高燥,无梅雨之润,绝蟫蠧之缺,故藏书亦可久焉。慎执戟其地,垂三十载。壬辰之春,于叶榆书肆以海贝二百索购得《群公四六》古刻,乃宋人所集,不知名氏。自甲至癸凡十卷,其人则首王初寮至蒋子礼五十五人,启凡四百六十五首。呜呼!四六之文,于文为末品也,昌黎病其衰飒,柳子以为骈拇。然自唐初以逮宋季,飞翰腾尺,争能竞工。观此集所载,若王梅溪、胡邦衡、王民瞻、任元受、赵庄叔、张安国、胡仲仁、陈止斋,皆一时忠节道学之臣、鸿藻景铄之士。其英声直气见于偶丽絺绘之中,直可与《陆宣公奏议》上下相映,奚可以文章末品少之!昔苏文忠公称孔明《出师》二表,与《伊训》、《说命》表里,岂屑屑于聱牙诘屈哉?大中丞百川张公,腹笥既富,手校尤勤,乃取弋于飞虫,下问于采菲。因出旧藏,装池新帙,并序所得之由,以广古贤之迹,传诸四方,亦文献之盛事乎。《陆宣公奏议》是唐宰相陆贽所作的骈体制诰与奏议的合集,其文运单成复、易短为长、骈散间行,大大改变了六朝以来骈文繁复僵化的语言形态,而出之以平实畅达的崭新气息,遂开宋体四六之先河。这种效摹散文的新四六格式极大地拓展了骈文议论、说理的功能范畴,使它能够曲尽事理、申发道德,从而拥有与古文一样明道醒世、治乱兴亡的严肃价值和厚重内涵。杨慎对《群公四六》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堪“与《陆宣公奏议》上下相映”,原因就在于“其英声直气见于偶丽絺绘之中”。这既是肯定二者在艺术手法上的源流关系,更是称扬它们在尽节弘道这一精神上的一脉性,从而有力地推翻了韩、柳等人轻慢四六的说法,赋予骈文体裁廊庙之器的无上尊严。接着,杨氏又举苏轼之言为例,进一步阐明文质互成的道理。诸葛亮《出师表》也是名垂史册的公文佳作,其主体虽为晓畅平易的散文,但其中已经穿插了一些骈偶的成分,显示出两汉古文骈散合一的特点。正是考虑到文章起源的这种混沌状态,清人李兆洛把《报任安书》、《出师表》等皆收入了《骈体文钞》。如“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等对偶句格的应用不仅不影响说理的沉稳恳切、情感的饱满真挚,反而令结构更加紧凑凝练、观点更加清晰明确。由此可见,要想达到《尚书》中《伊训》、《说命》那样的思想性,关键并不在于肤浅地模仿它们古奥迂涩的语言文字(这一持论也是对当时复古派学习秦汉古文时一味流于形式主义的委婉批评);同理,骈文虽然十分讲究声律、句式的和谐感,却也并不见得就会妨碍“质”或道的表达。
由此可见,杨慎的骈文尊体思想扎根于他所扮演的士大夫角色,官方代言人的身份和儒家文化的浸淫共同塑造了他强调“文道合一”的话语模式。
二、英声直气见于偶俪之中
早在杨慎提出尊骈理论之前,骈体公文就已经是政府部门例行事务中熟络的常客了。自明中叶起,伴随着文学复古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与审美觉醒,庙堂文学(主要属于泛文学)依赖四六文体的既成事实逐步获得认可,官方对偶俪文的道德性歧视也渐次消减。这种立场的变迁首先是通过一系列隐性语言间接传达出来的,如个人别集收录四六公文的公开姿态及其数量的明显增加、四六公文文学独创色彩的加重等。而杨慎则是进一步以明确的书面形式肯定骈文辅政、弘道价值的先驱。他大胆地提出了“英声直气见于偶丽絺绘之中”、“奚可以文章末品少之”的观点,从主流儒家文化的角度出发,正面称扬了骈文在政教领域的贡献。
这一尊骈理念不仅清晰地反映在杨慎的理论性阐述中,也是他褒贬骈文时依循的重要原则。因此,我们可以沿着他拣择摘录、批评解读前人作品这条线索予以摸索,从而获得更为直观、感性的认识。他曾全文记诵了南宋洪芹代作的一篇任命吴潜为左丞相兼枢密使的四六制词,足见爱赏之深。但因杨氏的转述存在个别字句的缺讹,所以引文仍据原文:
予方重宵旰之忧,汝不以昼锦为乐。入趋延英之召,亟奉天章之咨。惟事务之孔殷,顾弊源之滋甚。邪不可以干正,而君子小人之戒限未明;卑不可以加尊,而称侄称臣之名分未正。
士气抑郁而弗振,民力殚咨而莫纾。在庭狃于意见之偏,在边玩于守备之弛。当馈以叹,济川其谁?遗大投艰,孰念敉宁之计;任重道远,实惟弘毅之贤。云云。于戏!《诗》有《天保》、《采薇》,当厉修政攘夷狄之志;道在《中庸》、《大学》,尚明治国平天下之经。予欲祈永命,汝廸;予欲康庶事,汝为。惟至忱足以感动神明,惟大公足以信服中外。繄我耆俊,毋烦训词。
吴潜于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已官拜右丞相兼枢密使,次年罢相。开庆元年(1259),元兵南侵鄂州,他又临危受命,出任左相。景定三年(1262),他因反对立赵禥(即宋度宗)为太子而触犯龙颜,贾似道、沈炎等人趁机进谗,致使他再度罢相,贬黜外州,不久即忧愤离世。此制草于开庆元年,正当洪芹荣升翰林学士之时。他刚正能文、耿直敢言,所拟诏书可令“闻者奋激”,后在吴潜遭陷时又独力回护,可谓义薄云天。以古鉴今,料杨慎读罢此文,必五味杂陈,兴身世之慨:我固可为当世吴潜,谁又堪擎洪氏之笔?这篇骈文是替王者立言,所以对仗十分工整,显得庄严肃穆。起首两联便直入主题,足见事态紧急、求贤若渴。洪氏行文极为精短,无冗余浮词,虽不足250 个字,却能面面俱到。如论及政务之丛弊,则一针见血、切实沉痛;言及受任之义务,则真诚恳切、感人至深。而其中诸如“予方重宵旰之忧,汝不以昼锦为乐”,“当馈以叹,济川其谁”,“《诗》有《天保》、《采薇》,当厉修政攘夷狄之志;道在《中庸》、《大学》,尚明治国平天下之经”等偶句也都浑然天成,不露雕琢之刻意纤巧;“予欲祈永命,汝廸;予欲康庶事,汝为”一句又是仿《尚书》诏令口吻,顿添古意。以这种典雅、成熟的形式技法承载“厉修政攘夷狄之志”、“明治国平天下之经”,于体于用都无不符合庙堂文学的要求,也正是杨慎尊骈理论的核心思想。
骈文并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六朝的“月露风云”之体,它既可担当追逐声色之艳的美文样式,也能化身伐恶诛奸的檄书与利刃。杨慎从《群公四六》中节选过任尽言的一封《贺汤侍御鹏举启》,此文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靖言自古之奸臣,无若亡秦之巨蠹。公攘名器,报微时箪食之恩;擅立刑诜,箝当代缙绅之口。制同列如挟兔,斥异议如孤豚。厚鹰犬之养,而搏吠己憎;疏鹓鹭之行,而孤危主势。受其颐旨,捷若影从。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实事不闻,而闻事不实。私富贵之龙断,岂止使子弟为卿;夺造化之炉锤,大不许人主除吏。忠义扼腕,知识寒心。上愧汉臣,初乏朱云之请剑;下惭唐室,未闻林甫之斵棺。遂令存没之间,备极哀荣之典。
这段四六猛烈地抨击了秦桧之恶,被杨慎视为是能够集中体现任氏“诗文孤峭而有风稜,雄健而有英骨,忠鲠而有义气”特点的标志性作品。它以短句为主,且句式多变,当句对、隔句对并用。其中,隔句对又分四七对、五五对、四五对、六七对等。故而文势奔腾直下,毫无凝滞之感。控诉的酣畅淋漓再配上这一文本特点,便造就出凛冽锋利的艺术效果,如怒提三尺龙泉,冷光鉴人处犹可令愚人警醒、奸人胆寒。与任文的洋洋洒洒不同,《张谓赞刘裕》是一则简评:“刘裕近希曹、马,远弃桓公。祸徒及于两朝,福未盈于三载。八叶传其世嗣,六君不以寿终。天之报施,其明验乎!”杨慎称它胜在“简严,可以诛奸雄于既死矣”。此赞最巧妙的地方在于中间两联数字对的应用,用典型的因果恶报论辛辣地嘲讽了刘裕祸及子孙、福泽不长的命数,如匕首般短小精悍,直击要害。这两篇骈文虽是采用了不同的手法和风格,但无疑都充分发挥出了偶俪的结构优势,使得形式与内容相辅相成。于是,作者的“英声直气”不仅没有受挫于框架的层层阻碍,反而得到了更加到位、畅快的申发。
由上可知,只要运用得宜,骈文非但不会成为亡国之音,反而能够在褒贬功过、臧否善恶等方面发挥积极正面的作用,有裨于政,有利于国。
三、骈文写作与文官素养的养成
明初建国,在以皇权为轴心的政治体制下,树立了一整套以经术为尊的科举制度、教育制度和高级文官培养制度。而以帝力主导的去浮求实的公文改革运动,又以三令五申的形式不断强化了“文”与“道”的剥离状态,将四六对偶逐出国家意识形态控制的文学领土。从理学背景深厚的宋濂、方孝孺等到本之经义、推之政事的台阁体作家,中央文官倡导的文学创作都基本不出唐宋文的传统,即以韩柳、欧苏等古文大家为宗,排斥六朝至唐代流行的以骈俪为体的今文,视之为左道小技。然而,对“文”、“道”的过度割裂,不免衍生出以质朴为借口,从而掩饰才识浅陋的文学怪相。
杨慎的《陆韩论文》提到:“近世以道学自诡,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为文。’其文不过抄节宋人语录。又号于人曰:‘吾文布帛菽粟也。’予常戏之曰:‘菽粟则诚菽粟矣,但恐陈陈相因,红腐而不可食耳。’一座大笑。”这种创作弊病主要源自作者知识结构的残缺与写作训练的匮乏。《跋〈山海经〉》一文中便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杨慎与其好友薛蕙皆学术爱好广泛,志趣颇为相投。有一次二人一同诵读、校订《文选》、《山海经》,傍有薛氏同僚一人,不禁皱着眉头说:“二书吾不暇观,吾有暇则观六经耳。”杨慎当下幽默地回应到,六经好比五谷,读得再透也不过做个村野富农,哪里晓得《文选》之类“山珍海错”、食中“奇品”的好滋味。“合座为之一笑”。当时的文官队伍中应不乏像薛蕙同僚这样的人,所以才令杨慎意识到,广博的学术功底和扎实的写作基础也是一名优秀文官综合素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中也包括四六文的创作能力。
杨氏曾于旧石刻中喜得失传已久的唐代著名宰相宋璟二十五岁时所作的一篇《梅花赋》,拓而传之。皮日休亦爱此文之“清便得徐庾体”,还仿作过《桃花赋》。这篇四六的上半部主要用清丽的拟人化笔触描摹了梅花的种种“出群之姿”,如以何晏、韩寿状其色白、香幽之质,以娥皇女英、姑射神人比其含露、映日之态,又借一系列名传青史的美人、君子、文士、才女尽意渲染了梅花盛残浓淡间的别样风韵,从而展现出作者灵动的艺术直觉和高雅的审美趣味。此赋的下半部则侧重歌咏了梅花孤洁保贞的品格,如“莺语方涩,蜂房未喧,独步早春,自全其天。至若栖迹隐深,寓形幽绝,耻邻市廛,甘遁岩穴。江仆射之孤灯向寂,不怨凄迷;陶彭泽之三径长闲,曾无愔结。谅不移于本性,方可俪乎君子之节”,便带有更加明显的托物言志之意了,体现了宋氏砥砺操行的自我要求。杨慎在《〈梅花赋〉跋》中感慨到:“大抵古人事业,自学术中出,彼伏猎弄麞辈,宜其为之归与?”像这样的文学创作既能训炼才识,又可陶冶情操,正是古人事业的源泉和根基,自然远不是那些拘于六经、吞食腐谷的不学无术者所能达到的境界。
如果说四六写作对士大夫气质的正面影响较为抽象玄虚,那么,它作为文职官员处理政务时需要掌握的一项实用技能,则无疑具备了切实的政治功用价值,迎合了官僚体制的日常需求。据唐至五代的旧制,宰相拥有较大的行政自主权,朝请或下朝后与皇帝在延英殿议事时,往往仅讨论国家的宏观大局及纲领性政策,具体的人事任免或者非紧要事务的拟议则由宰相代为操刀,皇帝只要在上面批个“可”字即可施行。这些拟议多用流畅的四六文写就,正如《开元宰相奏请状》及郑畋《凤池稿草》中所录,体现了作者政治家与文学家双重身份的有机统一,也是其政治嗅觉敏锐与文字驾驭娴熟两种专长完美结合的产物。也许正是考虑到当代文职官员总体写作能力较低的实情,杨慎在言及前朝政坛风雅时,字里行间也流露出明显的追慕之意。但那些做不来唐时宰相的官员却又一味标榜“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或“术业有专攻”之类冠冕堂皇的理由,不甘坦诚直面自己才疏学浅的事实。他们多喜欢援引宋代大儒司马光也不擅长骈文的例子,以此自矜。杨慎便针锋相对,点出司马光其实并非真不能作四六:
惟司马温公《长公主制词》云:‘帝妹中行,《周易》赞其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美其肃雍。命服亚正后之尊,主礼用上公之贵。宠光之盛,谁昔而然!’此制词之工致,前嫓二宋、后掩三洪矣,岂不善为四六者耶?
宋神宗即位,欲擢升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但他执意推辞,表示不会写四六,因而并不符合成为一名高级文职官员所需的必备条件。于是,后世高唱尚质轻文的文人、文官往往以之作为巩固己方文学主张或证明自己专心政务的有力筹码。而与这类单照字面意思全盘接收者不同,也有不少人选择以更审慎的态度进行全面考量、客观分析,并提出了可信的质疑,即认为司马光此言其实只是意在反对当时公文谄媚阿谀的不良风气,并非单纯的自谦之词。杨慎就站在后者的行列中,他摘引了一段出自司马光巨笔的四六。此文是代王者立言,故而撰得雍容雅正,极得制词之体。其中,末句又特意用了《诗经·陈风·墓门》中“知而不已,谁昔然矣”的“谁昔”一词,以代往昔之意,该词在一般文人的创作中是罕见的,用在此处则既贴合了全文古朴的整体风格,又不动声色地融入了作家雄厚博洽的才学造诣,也无声地推翻了后人轻易低估司马氏四六水平的谬论。
总而言之,如果说祝允明等人的尊骈理论主要是针对长期以来被理学体系妖魔化的纯文学艺术性所做的平反,那么杨慎作为士大夫精英代言人,则是从骈文功能性、思想性的弹性特点入手,突出它在装点人类娱乐生活之外肩负宏大命题的力量,比如经纬天地、撑扶正义等,并进而肯定其附着的各种艺术价值,其中自然也包括文体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