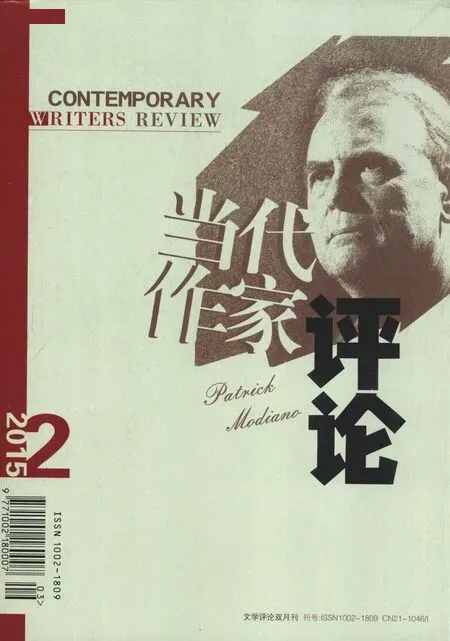城乡变迁中的飘泊童年——以《山羊不吃天堂草》、《余宝的世界》为例
2015-11-14何家欢
何家欢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无论国家的经济总量还是人民的生活,都提升到一个相当高的阶段。然而,在解决相对困窘的经济问题时,并不意味着人们在时代的伴生性成长中出现的精神性忧虑会得到很好的缓解。事实上,在一定程度来说,不同状态的精神性忧虑依然在困扰着这个时代的人们,而且,相对物质的实体性变化,对于精神性问题的解决会有更大的难度。因为精神是飘忽不定,而又无限存在的,这正如被无数次宣告死亡了的文学,隐秘在人们的情感和潜意识中,也表达在或单纯、或复杂的语言中。在这个时代对文学本义的不断衡量中,我们通过儿童文学作品,发现了这个巨变时代隐藏的新特征:它是飘泊而又分裂的精神,是改变而又被动的人生。
一、进城:身份的焦虑与成长阵痛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但实现经济总量跨越式发展的还是在城市。城市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的普通劳动者,这为农民进入城市提供了机遇。然而,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这为农民进城设置了制度障碍。很多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感受到的各种不平等,其原因也就在此。曹文轩的《山羊不吃天堂草》(一九九一)就是这样一部展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农村少年明子进城务工的小说。明子是一个在小豆村土生土长的乡下少年,为了赚钱帮家里偿还债务,十五岁的明子随着木匠师父三和尚和师兄黑罐踏上了进城务工之路。穷苦乡下人的出身使明子的自尊心变得格外敏感,伴之而来的是一种强烈的身份焦虑。对于刚进城的明子而言,五光十色的城市散放着无穷魅力,但是那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诱惑感却让他感到莫名的自卑和压抑。其中,最让他感受到切肤之痛的是城市对每个人身份角色的区分,以及人与人之间三六九等的差异。明子进城后和师父、师兄三人栖身在一个矮小的窝棚中,靠帮人做木工活维持生计。在这个三人小组中,明子常常要忍受师父三和尚的指使和盘剥,这时常让他感受到委屈和愤怒,但他也敏锐地察觉到,在那些城市人眼中,他们三人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他们都是在城市底层摸爬滚打的外来务工者。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这伙人和城市人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城市人是选择者,而他们是被选择者,这种关系注定了他们永远也无法拥有城市人那种高傲的神态,这便是城市对他们这群人的角色和身份的设定。明子意识到自己和城里人身份的差异,并将这种差异和自己在城市所遭受的待遇联系起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和城市之间永远无法消弭的隔膜。来自农村的“身份”成为了明子的隐痛,为了维护他在这个城市中仅有的一点存在感和尊严感,他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自己和患有腿疾的城市女孩紫薇之间的友情,然而,随着紫薇的康复,以及城市男孩徐达的出现,让明子这仅存的美好也转化为了低人一等的自卑。明子无力改变自己的身份,这也让他对城市产生了一种抵触和抗拒,并对回乡充满了渴望。
比之身份的苦楚,更令明子感到痛心的是城市中人的金钱观念对他人格尊严的践踏。明子亲眼目睹了师兄黑罐在利益的驱使下,一步步走向深渊的过程,他固执地坚守着自己的道德原则,试图通过对不劳而获的拒斥来维护自己做人的底线。然而,在金钱与道德的角逐中,明子内心的道德防线却在不断溃退,在见证了一系列蝇营狗苟的事件后,他终于走上了为金钱所奴役的道路。与其说他心甘情愿地臣服于金钱的魔力,不如说他是在宣泄自己心中的“气”。自从进城后,明子的心中一直有一股气,这既是一种谋生的志气,也是一种对处境愤愤不平的怨气。这股气在明子心中渐渐滋生出一种和城市对抗的情绪,并在自卑心理的作用下走向了偏狭。它激发出了明子对金钱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渴望,以及对城里人莫名的仇视。明子在欲望和仇恨的泥潭中挣扎、堕落,直到滑向犯罪的边缘。在最关键的时刻,一个埋藏在潜意识里的梦境将他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他想起了草摊上那些宁愿饿死也不肯吃天堂草的羊群,父亲的声音犹在耳畔:“不该自己吃的东西,自然就不能吃,也不肯吃……”明子猛然惊醒,终于抛下怨念,回归正途。
明子在灵与肉的抉择和挣扎中完成了自身的精神成长,实现了由少年到成年的蜕变。这个过程也是所处这个时代中的每个进城者所面临的“成长”阵痛。小说在第二十四章,借助明子的回忆与梦境讲述了山羊不吃天堂草的故事:明子的父亲为了改善贫穷的家境借钱买了一百只山羊,在村子里的草被啃吃光了的情况下,这些山羊被送往草滩,最终却因不肯吃草滩上的天堂草而全部饿死。作者以“山羊不吃天堂草”作为小说题目,不只是以此影射明子进城后心路历程,更是对整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农民离乡进城致富这一重大历史趋势的隐喻。工业文明改变了乡村的面貌,也消解着乡村的家园属性,率先感应到城市文明召唤的农民将农村的各类资源抢占一空,而后来者则只能背井离乡,到城市去另觅谋生的土壤。城市化进程所造成的城乡差异,既是欲望萌生的缝隙,也是怨恨丛生的渊薮。明子进城后的痛苦、挣扎和陷落,所展现出的正是这一代农民对城市“怨羡交织”的情结。一方面,他们远离故土,又遭到城市的拒斥,却依然难以消解心中对积累经济资本的焦虑和渴求。另一方面,面对城市富足的物质生活,联想到贫穷的家乡和自己在城市的境遇,又让他们深深地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对改变个人现状的乏力。对于这一代进城者而言,乡村已不再是可以寻求心灵庇护的家园,而城市却仍然是他者的城市。然而,面对滚滚向前的现代文明,和被其所改变的乡村,回头已经绝无可能,唯有破釜沉舟,才能在逆境低谷中寻觅新的生机。这种怨羡交织的情节生成了明子心中的那股气,也生成了这一代进城者求变的动力。
二、在城:底层身份的代际传递
如今距离高加林、孙少平进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三十余年,在这三十多年中,踏着他们当年的脚印奔赴进城之路的人群有增无减。如果说曹文轩的《山羊不吃天堂草》表现了一九九○年代初进城农民对故土家园依依不舍的精神诀别,那么二十年后的今天,这些曾经的城市闯入者是否已经融入到城市之中?他们的家庭和子女又遭受着怎样的境遇?这依然值得今天的文学去关注和书写。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农村流动人口在不断扩大规模的同时,也在实现着“从流动趋向移民”的整体变迁。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以家庭的形式进入到城市,大批学龄儿童跟随父母在城市生活,成为流动儿童。他们大多是在城市出生,或是在学龄前就进入了城市生活,相较于他们的父辈,他们的乡土记忆较少,对城市拥有更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但是,由于社会体制改革的缓慢,他们在经济、户籍和生活方式上仍和真正的城市人有较大的差别,这使得他们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继续遭受着重重阻碍。进入新世纪后,由社会转型所造成的城市流动儿童问题和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而文学作为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也将作家们的创作视野引向了这个曾经被忽视的群体。
近年来,一些展现城市底层儿童生活的文学作品陆续涌现出来,黄蓓佳的《余宝的世界》(二○一二)是其中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小说以十一岁男孩余宝为聚焦者和叙述者,讲述了他在二○一二年暑假中遭遇的一段令他终生难忘的经历。不同于《山羊不吃天堂草》中对进城者内心冲撞的书写,《余宝的世界》进入到人物的生存层面,为读者铺展开一幅较为开阔的底层景象。故事围绕着一个叫“天使街”的地方展开,这里是城乡结合部,也是外来务工者聚集区。现实中的天使街并没有它的名字那样美丽动听,肮脏不平的街道,陈旧破败的房舍,还有操着天南海北各色口音的打工者,构成了一派不为城市人所熟知的城市底层景观,也构成了余宝童年生活的全部底色。故事起因于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长途货运归来的余宝和爸爸作为目击者目睹了这次车祸发生的经过。爸爸认出那个肇事车辆正是自己所在货运公司老板温总的座驾,为了保住工作,他没有报警,而是带着余宝驾车飞快地逃离现场。在爸爸的调查下,事情的真相渐渐明晰,那天夜里是温总的朋友驾驶温总的车外出,撞死了公路上的一个流浪汉,事后,温总找了同公司的一名司机去顶包。余宝的爸爸虽然对隐瞒真相深感不安,但他还是答应温总将永远保守这个秘密。而在这个时候,余宝的家里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余宝的爸爸为余宝转学和亲属生病的事弄得焦头烂额,最后在留下一笔巨款后突然神秘失踪。半个月后,爸爸再次出现,随着他的投案自首,这桩肇事逃逸案,以及其后所发生的失踪谜团终于水落石出。
在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背后,掩映着挣扎在城市边缘的底层人群的苦辣辛酸。余宝的父母和大姐三人用微薄的收入支撑起这个五口之家的日常开销,任何一笔巨额支出对于这个家庭来说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在大是大非面前,余宝和他的家人并非没有清醒的认知和判断,然而迫于对权势的畏惧和谋生的艰难,他们又不得不做出趋利避害、明哲保身的选择。他们的身上既有农民式的善良和质朴,也有弱势群体在长期的社会挤压中滋生出的懦弱和狡黠。余宝一家的生活处境和精神状态,正是城市底层千千万万外来务工者家庭的一个缩影。
在贫穷的困境中,天使街上的童年也呈现出另外一副模样。和余宝一样,孟小伟、成泰和罗天宇都是农民工子弟,因为没有城市户口,他们在城里只能上师资差,各种硬件均不达标的民工子弟小学。对于城市,他们并没有体会到明子进城时那种隔膜甚深的体验,但是经济的拮据依然让他们感受到金钱的焦虑。为了赚钱请朋友们看一场3D电影,孟小伟想要捕捉粉蝶,孵化菜青虫卖给菜贩,结果却在外出时遇到大雨,被坍塌的砖墙夺去了生命。我们无意去苛责一个十一岁男孩为实现梦想而付出的行动,但是,面对悲剧的发生,我们不由得发出追问:是什么促成了这样一个年轻生命的陨落?是贫穷,是道德失范,还是价值观的陨落?如果一定要从中揪出罪魁祸首,底层的贫穷和家庭教育的缺失应该是促使这一悲剧发生的根源。对于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底层家庭来说,生存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儿童的心灵成长往往被家长所忽视。是贫穷加剧了儿童对物质需求的渴望,而缺少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则导致他们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误入歧途。
孟小伟的死犹如底层儿童对社会所发出的一场无声的控诉。然而,比底层童年的苦难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在这个阶层固化的时代,进城者已经丧失了冲出底层的渴望和诉求。在高加林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狠劲’”。在明子的身上,我们也能感受到一股怨羡纠结的不平之“气”。然而,在余宝和他的父母,家人,以及其他外来务工者身上,我们却只能读出他们对底层身份的认可和承受。小说中,余宝的妈妈言谈之中一再强调“我们这种身份的人”,正是对这种底层身份的确证。而当余朵问爸爸觉得这个社会是否公平时,爸爸的回答是:“鸡吃鸡的米,鸭吃鸭的草,有什么不公平?”他们对于自己糟糕的处境并不加以质疑,反而以身份的差异性对其进行解释。可以看出,在天使街混乱、嘈杂的表象下,实际上暗含着一种稳定的深层秩序,每个人都安分地接受着这个城市分配给自己的位置和角色,借此获得一种居于底层的安稳。他们从未将贫穷的处境归咎于社会分配的不公,反而感恩于城市的施舍,让他们脱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而对于拮据的生活,他们自有一套“鹅吃草鸭吃谷,个人自享个人福”的底层人生哲学来面对。这种对底层身份的认可态度也经由父辈之手传递到余宝那一代人身上。小说中,余香、余朵、余宝三姐弟对于底层身份有着不同程度的认同表现,相较于余香的逆来顺受和余朵的怨声载道,余宝的沉默流露出一种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他肩负着整个家族的希望——读书上大学,可是民办学校的教学状况却让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和大学、公务员之间遥不可及的距离。同时,他也在父亲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影子:“我爸爸就是我的镜面,从他的身上我能够看到二十年后的我自己。”“我也许会像爸爸一样开卡车,呼呼啦啦奔波在南来北往的高速公路上,超载,罚款,为了付罚款更多地超载;也许连卡车都开不上,只能上建筑工地做小工,砌砖扛大料。”在余宝这一代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底层身份和围绕这种身份所产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的代际传递。这种传递并非借助学校教育或是家庭教育,而是通过社会现实,以及大人们的言行举止直接映射在儿童的心灵之中,对儿童的精神成长,特别是身份认同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余宝的早熟折射着城市底层的苦难现实和童年的凄凉处境。童年,本应是个充满幻想的年纪,然而,天使街上的孩子们却在城市底层的镜像中过早地完成了对自我身份的确认。糟糕的现实处境,加之对未来的无望,让底层儿童消解了追逐梦想的渴望,也丧失了改变个人命运的动力。
三、飘泊者的身份与命运
相对于大量飘泊在各大中城市的农村青少年,以及暂被固定在乡村的留守儿童,现在的儿童文学作品对他们的关注显然还是不多。当下的儿童文学多服务于城市中的儿童,其内容也多以仙侠奇幻,或是反映城市儿童家庭校园生活为主。出版社对这些题材的关注,固然考虑到购买力的因素,但儿童文学对底层儿童的关注度不高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方面有作家体验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底层生活者,无论是儿童,还是他们的父母,本来就是缺乏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当然,他们的沉默,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城市没有自己的认知,而是因为他们缺少表达的媒介和途径。
从《山羊不吃天堂草》到《余宝的世界》,我们看到的是进城务工者和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生活中的不同遭遇。它们之间的共同处在于,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来自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的人,他们的生存压力和未来的人生走向,都将迥异于城市职工、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和工作预期。正常来讲,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应该是有利于个人实现自身价值、人生梦想的社会。但在现实中,对于不同群体中的人,这种成长的道路显然又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在这里关注城乡变迁中的儿童文学,其实也就等于对这种尚处于萌芽期的社会问题进行相应的文学反思,以此来推进以文学为道义的社会变革。城市流动儿童的出现,是农村社会解体、城市急剧扩张时期的产物,他们跟随着不断转换工作地点的父母,为了生存而奔波在祖国的大地上。相对于拥有稳定生活和充足教育资源的城市儿童,流动儿童更像是城市的陌生人,伴随他们成长过程的,也必将是在各种不同起跑线下的群体歧视,而这也正是黄蓓佳在《余宝的世界》中所关注的问题。
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然而,发展着的“城市”和进步着的“生活”并不会公平地给予城市里的每一个人。来自边远乡村的明子,和来自城市底层的余宝,显然不同于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对城市生活的感受。就《余宝的世界》中的人物来说,余宝在心目中所认同的自己,其实就是如其父亲一样的底层劳动者。余宝的未来,也许正如鲁迅《故乡》中的闰土,在既定的社会规则中,他们的成长只是指向一个模式化的结果。而这也才更可能是他们永远的命运。当然,“‘现代性’有问题,但也有它不可阻挡的巨大魅力。”虽然进城者在由乡入城的流动中遭遇到种种问题和困境,但现代化的洪流已经不允许他们再回到乡村,而对于从小就跟随父母进入到城市的儿童来说,乡村中也再没有他们可以容身的位置。无论是在生活体验上,还是在情感归属上,这些孩子都对乡村缺少足够的心理认同。融入城市,获得城市身份,才是他们的必然命运和人生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