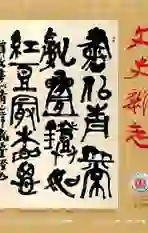漫谈武则天和唐代女权意识
2015-11-09方洋
方洋
武则天(624—705)原籍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正月二十三日出生在利州绵谷(今四川广元),系出身木材商的利州都督武士彠之女。她14岁时被唐太宗选入宫内为才人,太宗死后为尼;高宗时复被召为昭仪。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武则天被高宗立为皇后,参预朝政,号“天后”,与高宗并称“二圣”。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十二月,高宗病逝,太子李显(武则天第三子)即位,是为中宗。武则天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嗣圣元年(公元684年)二月,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改立豫王李旦(武则天第四子)为帝,是为睿宗。载初元年(公元690年)九月七日,武则天宣布接受皇帝禅让,降李旦为皇嗣,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改年号为“天授”。武则天历经三十余年的艰难拼搏,终于苦尽甘来,堂堂正正地登上金銮宝殿,坐上了千百年来一直由男人们独享的龙椅。这年武则天66岁。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81岁的武则天于洛阳上阳宫驾崩。李显急忙托称上皇“遗制”,去掉“则天大圣皇帝”号,改为“则天大圣皇太后”,又谥曰“则天大圣皇后”,意欲抹煞唐史上曾出过异姓女皇帝的事实。只是趁武则天年高多病,不能视事才重新夺回政权的李唐大男人们在仓促间暴露出他们在女权意识普遍高涨形势下的张皇失措与自卑、脆弱心理以及由此而生出的对以武则天为代表的女权主义者的嫉妒和仇视。
武则天从公元690年起改李唐为武周,到公元705年退位,整整做了15年的女皇。倘从她于公元655年以皇后身份参政算起,则统治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她以一个来自边鄙之地(广元地处四川东北山地,从秦至唐,都是朝廷流放政治犯的处所)的外姓妇女的身份,十分成功地驾驭了一个属于他姓的男权国家,掌控了一段通常由男人书写的历史。在这方面,武则天是骄傲的,单从她称帝以后频频改换年号(15年间换了l4个),而且一个比一个令大男人们心急气短、无地自容(如天授、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即可看出。
武则天的骄傲不仅仅是一种女性的骄傲。因为历朝后宫,粉黛如云,佳丽如林,其中不少是拥有聪慧头脑的女才子、女政治家;可是,只有武则天能够从她们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传统社会里惟一的女皇帝,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武则天之前,出过一位擅权的吕后,可是尚未有多大作为,便被既有皇权连根扫除;又出过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赵飞燕,武则天之后还有杨玉环接踵,虽一度势焰炙人,却最终未能摆脱任男人宰割的厄运。只有她武则天,不仅能从老皇帝身边成功脱逃,成为新皇帝须臾不可离的依靠,而且还像大男人一样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使当时的中国得以继续保持世界头号大帝国的发展势头,功盖半个世纪之久,令数千万子民佩服得五体投地,由衷地拍手叫好。所以,由武则天执掌大纛的唐代女人们的历史活动,从本质上讲,乃是中国女权主义在古代所刮起的一场完美风暴。武则天的所言所为,彻底打破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一以贯之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传统,完全颠覆了中国男权社会长期以来专有不贰的皇帝宝座。武则天实际应当被视作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女性主义者。她比西方的第一位女性主义者——法国的彼森(1634—1430)要早740年。(当然,中国以外的西方及东方中世纪,也出现过女皇帝、女国王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女英雄,但她们在变革女性地位、争取女性自主权、话语权方面的作为,实在太小;与武则天相比,当有云泥之别。)难怪武则天会那么自得意满,傲视群雄,自称弥勒佛转世,废黜李姓皇帝而创立武周政权;难怪她可以像男性皇帝一样纳妾封宫,钦点男宠(史籍记有薛怀义、张昌宗、张易之三人),让他们因了自己的宠幸而拥有令人称羡的权力及财富,从而死心踏地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为武周政权效力。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女权意识的一个闪光点就是对自己女性人格的反省、尊重、爱惜和把持。这是进而张扬女性人格的基础所在。作为一代大帝国的掌舵人,武则天具有极为冷静的政治头脑和坚定的行为准则。她能很好地把持自己的感情,没有因为私情而耽误朝政。她能认真地处理好家事与国事、私生活与大政方针的关系,敢于约束身边的人(包括爱女太平公主及侄子武承嗣、武三思等),没有因拥有男宠而疏离朝政,疏离与她同过磨难,以后又共商国是的臣子们。她重用狄仁傑、姚崇、张柬之、上官婉儿,严惩薛怀义,即为显例。同为皇帝,武则天的政绩堪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媲美;只是因为她是女人,便不能取得与这些皇帝同样的历史认可,甚至还比不上“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直至当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败作。(按:《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评武则天为“奸人妒妇之恒态”,“牝鸡司晨”,“秽亵皇居”,“穷妖白首”云云,极尽诬蔑攻击之辞也!)
不用说,武则天是唐代女权主义的一个象征。但是,唐代女权意识在政治上的强化不独表现在皇权的更易上,而且还表现在命妇朝谒制度上,即命妇在宣政殿拜见天子。这在此前的历代王朝是绝无仅有的,《新唐书·袁利贞列传》记载,唐太宗“欲大会群臣、命妇,合宴宣政殿,设九部伎、散乐”。这时太常博士袁利贞上《谏于宣政殿会百官命妇疏》说:“臣以为前殿正寝,非命妇宴会之地……望诏命妇会于别殿。”宣政殿是天子颁布政令的地方,朝廷命妇在那里聚会,说明在唐太宗眼里,她们与男性大臣享有同等地位。而命妇们也安然享受这一待遇,像男性大臣一样昂首挺胸进入正殿,没有丝毫自卑感;朝谒时则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如唐高宗《禁帷帽敕》所云:“又命妇朝谒,或将驰驾车,既人禁门,有亏肃敬。”命妇乘车一直达于禁门之内,车不减速,马嘶人噪,如同街市漫游一般。
此外,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初,武则天还亲率公主及各亲王命妇,登泰山祭天献清酒;以后韦后也像武则天一样登坛祭天献酒。这在当时即招来某些守旧男人的抗议。宰相张说为此专写《祭天不得以妇人升坛议》,但朝廷并未多加理睬。
另据刘达临先生在《中国古代性文化》一书里的研究,在唐代宫廷中,后妃、宫女都不回避外臣,甚至可以亲近接交、不拘礼节。例如,韦皇后与武三思同坐御床玩双陆,唐中宗在旁为之点筹;唐玄宗的宠臣姜皎与后妃连榻宴饮;安禄山在后宫与杨贵妃同食,戏闹,甚至通宵不出;宫官们更时常“出入内外,往来宫掖”,结交朝廷外官……尽管其中不泛淫乱,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社会风气的开放,人性的复归,人们对男女间的相识交往极其自然,漠视封建礼教的条条框框。所以云阳公主成婚时,吴人陆畅做傧相,宫女们笑话他的南方口音,吟诗嘲弄他。陆畅也以诗酬和,其中有“不奈鸟鸢噪鹊桥”句。可以想见当时宫女们围在他身边逗闹嬉笑,根本没有“男女之别”的观念。
此外,唐代上流社会,官员夫人之间也经常走动,像现代外交场合一样,互相设宴招待。至于在唐代民间,女子走出家庭、家族之外的联谊交往更是不胜枚举。她们像男儿一样呼朋引类,称兄道弟,互相帮扶,颇有任侠之气。如《教坊记》云:
坊中诸女以气类相似,约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辈,有儿郎聘之者,辄被以妇人称呼:即所聘者,兄见呼为新妇,弟见呼为嫂也……儿郎既聘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学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相怜爱,欲得尝其妇也。主者知亦不妒,他香火即不通。
这段记载,大致讲的是唐代长安城内街坊里巷间的女子事。而在地处遥远的敦煌地区,民间女子甚至组成了团体(据敦煌遗书载,那里有“女人社”“夫人大社”“夫人小社”一类的组织),大有近代女权运动的妇女团体的味道。在敦煌遗书中发现的两件“女人社”社约,其中一件题为《女人社再立社约》,系五代末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的文件。这些事实表明,唐代妇女,无论是上流社会的士女,还是民间小娘子,已经具有了独立于男性之外的女性(女权)意识,已经在自觉和自然地争取或维护女性在社会生活(包括国家政治生活)与家庭生活中的自立、自主地位,并在这一过程中团结起来,形成合力。敦煌发现的那份《女人社再立社约》,即有“遇危则相扶,难则相救”、“山河为誓,中不相违”等条款。
在唐代民间,女子与男子自由交往,热烈而奔放;但也纯朴和充满真情,毫无上流社会的那种矫揉造作,虚情假意,荒淫无耻和“始乱终弃”——像《莺莺传》里的张生那样。大家熟悉的中唐诗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诗(中有“人面桃花相映红”句),便记录了这种纯朴和真情,因而传为千古佳话。他如崔颢的《长干曲四首》之一,白居易《琵琶行》《井底引银瓶》等不少诗人的许多诗篇,都反映或透露出唐代民间男女普遍崇尚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信息。
唐代婚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贞节观念比较淡薄,离婚再嫁较为容易。南北朝时期,中国开始出现“离婚”之说。隋朝曾有限制再嫁的诏令,但唐太宗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主持颁行的《唐律》在“户婚”一篇,却顺应婚姻自主的潮流,允许自愿协议离婚即所谓“和离”,不反对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在这种风气下,唐代由妻子主动提出离异者有不少——这在官宦人家是这样,在平民家庭亦如此。唐末范摅《云溪友议》卷一载,庶民杨志坚的妻子坚决要求离婚,太守颜真卿亲自出来审议调解,不果,最后还是任由杨妻脱离夫家另嫁他人。
考古工作者还在敦煌遗书里发现了唐代敦煌男子的《放妻书》,表明对移情别恋(今称“外遇”),不能回头的妻子给以三年衣粮,欢喜送走,末了还写上“伏望娘子,千秋万岁”的祝福话。其字里行间,满是理解与宽容,闪耀着民主和自由的光芒。毋须多言,我们在赞美唐代男子的博大胸怀的时候,也应该对唐代女子追求真正爱情的执著精神——那种一旦有了心上人,或者一旦与丈夫有了感情上的鸿沟,即坚定不移地走出婚姻“围城”的破釜沉舟的勇气,给予崇高的礼赞!而敦煌发现的《放妻书》——类似于当代的“好说好散”式的《离婚协议书》,不正是她们勇于追求爱情、勇于走出“围城”的斗争结果么?是她们追求心灵解放、追求人生美满的精神和勇气感动了上帝——她们的男人们。
当然,唐代妇女之所以具有这种精神和勇气,乃是与整个大唐帝国普遍高涨的关注人的价值、关注人的心灵的人文主义气氛息息相关的。
在人文主义观照下的唐代,妇女的自立、自主意识像挡不住的烂漫春光一样充溢在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体现在服饰打扮上,也是各喜所好,花样百出。《花蕊夫人宫词》有吟:
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
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
这说的是上流社会女子仿回鹘族服装着小腰身衣装。这大约是安史之乱后的妇女流行服装。白居易《上阳白发人》诗则云:
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
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
这意思说,老妇人入宫几十年,不知道外面妆扮已时兴长袍大袖了。你看她穿着天宝未年的窄袖衣服,还自以为美呢!老妇人所珍爱的这种小袖袍小口的“时世妆”,大约盛于天宝至元和时期(公元742年—820年),为中亚一带波斯、石国或吐火罗(即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的服装。它们被唐朝妇女接管过来加以改造,成为女装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可是,半个世纪后,妇女们就将它们压到箱底去了,又穿起袖宽过四尺的大袖大袍;脚下也不是小头鞋,而是宽大的如意履了。开放的女性们将流盼的目光不断瞄向域外生动的世界,喜新厌旧,趋奇求异,花样翻新之快,令男人们目瞪口呆。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这样描述说:
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衩衣之制度,衿袖窄小。识者窃怪之,知其兆矣。
初唐至盛唐,特别是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妇女还流行一种袒领装,里面不穿衬衫,袒露出大半个胸脯。所谓“粉胸半掩疑暗雪”、“长留白雪占胸前”便讲的是它。当时上层妇女又喜穿薄如蝉翼的丝绸衣服。这样一来,便真个成了薄、露、透装了。可是那时的男人们大多不以为怪,普遍怀着平和的心态投以欣赏的眼光。据说当时杨贵妃为了标新立异,在露透装内系一条红绢于乳前,虽仍半遮半露,却毕竟不透两点了。那时的妇女随心所欲,想怎么穿就怎么穿,既不顾忌是否有碍传统,也不管男人们高不高兴。这样的举措,只有在人文主义高涨、女权主义高标的背景下才做得出来。
隋及唐初,上流社会的妇女们还仿男子骑马奔走。她们由此又学胡人,以(以轻薄透明的罗沙制成)障蔽全身,隐若云中仙女,给人一种朦胧飘缈的美感。然而到了武则天时期,她们又扯掉,代以帷帽(又称席帽,高顶宽沿,帽沿周围缀有一层网状面纱)。至唐玄宗开元年间(713年——741年),妇女们仍觉不够爽快,干脆连帷帽也不戴了,遂以一种胡帽(时称“浑脱帽”,尖形,帽身织有花纹)加靓妆露脸,有的甚至“着丈夫衣服靴衫”。对此,《旧唐书》的作者们摇头叹息道:“尊卑内外斯一贯矣……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旧唐书·舆服志》)女子们仿习外域文化,打破男女尊卑内外之别,展示出那个时期女子们无所羁绊、张扬个性的精神风采。可是刘(《旧唐书》监修)、张昭远、贾纬(《旧唐书》作者)们却将它说成是安史之乱的祸根,则未免太不负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