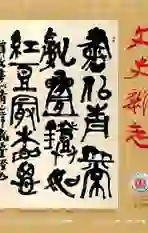唐朝防范腐败的考课制度
2015-11-09萧曼
萧曼
摘 要:唐朝考核官员的标准是“四善”“二十七最”,包罗对各类职官的不同要求。其主要内容就是检查官员是否清政廉洁、勤政为民。《唐律》中的《职制律》五十八条,则是惩治贪腐官员的法律准绳。以唐太宗、武则天为首的唐代前期皇帝大多能以身作则,带头遵纪守法。
关键词:四善;二十七最;职制律;君臣守法
有唐一代,与对官吏的监察制度并行的是考课制度。它与监察制度一起,成为确保吏治清明、防范腐败的双翼。考课制度首创于西汉元帝永兴、建昭间(公元前43—前34年)。这实际是年终朝廷对地方官政绩的一种考核方法。
一、“四善”与“二十七最”
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甫即位,就强调“任官惟贤才”,即任用才德兼备者,用魏的话来说,就是“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这见载于《贞观政要·择官》。那里面还有这么一段记载: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
贞观三年,唐太宗又对侍臣讲:“县令甚是亲民要职。”[1]唐太宗认为,只要把府、州、县一把手的官员选好了、用好了,天下也就太平了。唐太宗为“致治”而求贤、任贤,并以此为出发点要求对在职在任的官吏进行考课。为此,他亲自指导制定了“考课之法”。考课大抵分两种,第一种是对各级行政官员而言,主要考核其所在单位时间(一年)内,所属部门和地区户口增减、农业生产、漕运水利、治安情况等;第二种是对其他各种专业官吏而言,如仓储、司法、监察、军事等。他们的考核各有标准,包含着各自不同的考核内容。
唐朝设有考功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之考法及其行状”[2]。
皇帝以下官吏,上至宰相、亲王,下至流外(九品以外)乃至差役、杂任,均要参加考核,综合德、行两方面内容,分九等判以等级,以定加禄晋级、守本禄或夺禄解任。
唐朝考核官吏的德包括品质、道德修养,对君主的忠信笃卫的状况;考核的行,则指官吏的能力大小、守职的勤惰、政绩的好坏等情况。
德的标准是“四善”:“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3],简称德、慎、公、勤。这“四善”是政治、道德品质、敬业方面的要求,是对全国所有官吏而言的。
行的标准共有27条,称“二十七最”,这是针对各种不同业务的官吏提出的要求:
一曰献可替否,拾遗补阙,为近侍之最;二曰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三曰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四曰礼制仪式,动合经典,为礼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谐,不失节奏,为乐官之最;六曰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之最;七曰部统有方,警守无失,为宿卫之最;八曰兵士调习,戎装充备,为督领之最;九曰推鞫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十曰雠校精审,明于刊定,为校正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纳明敏,为宣纳之最;十二曰训导有方,生徒充业,为学官之最;十三曰赏罚严明,攻战必胜,为军将之最;十四曰礼义兴行,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十五曰详录典正,词理兼举,为文史之最;十六曰访察精审,弹举必当,为纠正之最;十七曰明于勘覆,稽失无隐,为句检之最;十八曰职事修理,供承强济,为监掌之最;十九曰功课皆充,丁匠无怨,为役使之最;二十曰耕耨以时,收获成课,为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谨于盖藏,明于出纳,为仓库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虚,究理精密,为历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医卜,效验多者,为方术之最;二十四曰检察有方,行旅无壅,为关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廛弗扰,奸滥不行,为市司之最;二十六曰牧养肥硕,蕃息孳多,为牧官之最;二十七曰边境清肃,城隍修理,为镇防之最。[4]
对州县地方官的考课,除了上述标准外,还要根据所辖的户口、赋役、田亩、治安等情况的好坏进行考核。
唐朝根据以上标准来评定官员的考第。其细则为:
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无最而有 一善为中中,职事粗理、善最不闻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阙为下中;居官谄诈、贪浊有状为下下。[5]
以上是职事官考课标准。流外官则以行能功过另列四等:“清谨勤公为上,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为下,贪浊有状为下下”。[6]
二、倡廉惩贪,双管齐下
朝廷对官员考课是一年一小考,四年左右一大考,并将考核结果告知被考者,亦公之于众,“悬于本司、本州之门三日”[7]。本人不同意者,可以申诉复核,同意则发给“考牒”。朝廷根据大考结果予以奖惩:
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中中,守本禄;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夺禄一季。中品以下,四考皆中中者,进一阶;一中上考,复进一阶;一上下考,进二阶;……有下下考者,解任。[8]
“四善,二十七最”强调对官吏考课以是否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为主要内容,体现了唐朝对治吏的高度重视。不过,通览“二十七最”,唐朝最为看重的还是官吏的治绩,以官吏在本地区、本部门取得业绩的优劣作为考查官吏的首要标准、最主要标准。“二十七最”订得很细,包罗了唐朝职官的方方面面。任何只靠溜须拍马、钻营舞弊、说大话放空炮或不学无术、滥竽充数或懒惰平庸、缺乏干劲和活力者,在“二十七最”面前恐怕都难以过关。唐朝考课制度如此细致严密,针对性、目的性如此强,这是前代(即如西汉)难望项背的。而唐朝官制在其他方面亦与此一样,“各统其属,以分职定位”,事实上是将治绩作为“辨贵贱、叙劳能”[9]进而奖赏晋爵或惩罚降黜的首要标准——因为这是一条最简单方便、有力,最容易把握,最切合实际的标准。它反映出自唐太宗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努力倡行的实干精神、务实作风。诚如《新唐书·百官志一》开篇所赞:
其为法则精而密,其施于事则简而易行,所以然者,由职有常守,而位有常员也。方唐之盛时,其制如此。
为了更有效、有力地倡廉惩贪,改善吏治,唐朝对官员除了有一套考课制度、监督制度外,还在《唐律》中专设《职制律》五十八条,对官吏渎职擅权、贪赃枉法等行为列为罪名,予以司法惩处。其具体名目为:置官过限及不应置而置、贡举非其人、刺史县令等私出界、在官应直不直、官人无故不上、之官限满不赴、官人从驾稽违、大祀不预申期及不如法、大祀在散斋吊丧问疾、祭祀朝会等失错违仪、庙享有丧遣充执事、合和御药有误、造御膳有误、御幸舟船有误、乘舆服御物持护修整不如法、主司私借服御物、监当主食有犯、百官外膳犯食禁、漏泄大事、私有玄象器物、稽缓制书官文书、被制书施行有违、受制忘误、制书官文书误辄改定、上书奏事犯讳、上书奏事误、事应奏不奏、事直代判署、受制出使辄干他事、匿父母及夫等丧、府号官称犯父祖名、指斥乘舆及对捍制使、驿使稽程、驿使以书寄人、文书应遣驿不遣、驿使不依题署、增乘驿马、乘驿马枉道、乘驿马赍私物、长官及使人有犯、用符节事讫稽留不输、公事应行稽留、奉使部送雇寄人、长吏辄立碑、有所请求、受人财为请求、有事以财行求、监主受财枉法、事后受财、受所监临财物、因使受送遗、贷所监临财物、役使所监临、监临受供馈、率敛所监临财物、监临之官家人乞借、去官受旧官属士庶馈与、挟势乞索、律令式不便辄奏改行。
《唐律》的最早版本是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布的,史称《武德律》。唐太宗即位后,立志“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10],遂任命长孙无忌、房玄龄和一批“学士法官”厘改法律,“意在宽平”。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新的《唐律》成书并颁行全国,史称《贞观律》。虽说朝廷主张宽刑,但对贪墨枉法,玩忽职守者,仍严惩不怠。其专设《职制律》以及《名例律》等篇,便是明证。
三、率先垂范,君臣守法
法律既定,唐太宗便以身作则,带头遵行。广州都督瓽仁弘勾结豪强,收受贿赂,“法当死”。起初太宗怜其年老,又曾建有大功,便法外开恩,“贷为庶人”。不过,太宗仍知触犯司法尊严,“弄法以负天”,于是要“请罪于天”。房玄龄等诸老臣就出来苦苦劝阻,说什么今上“宽仁弘不以私而以功,何罪之请”[11]等。但太宗还是不肯饶恕自己,终下罪己诏,称自己有三罪:知人不明、以私乱法、未能善赏恶诛云云。今天来看,这或许是唐太宗的一次“做秀”而已;然而他毕竟身为人君,却能引咎自责,以维护法律尊严,这在上下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史上还是难得。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河南道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贿事发,受到“追还解任”,即退赔撤职的处理。他向唐太宗上书,希望看在自己是秦王府故旧份上, 能原谅这次罪过。唐太宗于是心软了,认为他“今取他物,只应为贫”,要赐给他绢百匹,“即还原任”。但魏即向太宗进谏,指出今上是“以故旧私情”而枉法。太宗这才恍悟过来,“欣然纳之”,收回成命;还将庞相寿找来训诫了一顿,使之“默然流涕而去。”[12]此事过后一年,即贞观四年,唐太宗特地告诫诸公卿:
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中心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13]
从这开始,唐太宗诏令对重大贪污犯均处死刑;行刑时,命令各地进京官员一律前往观刑,以儆效尤。在唐太宗的垂范与劝诫下,加之成文法的威力(《贞观律》形成之前有《武德律》推行),贞观一代,大小官吏 “多自清谨”,形成君臣守法,吏治清明的局面。
迨入武则天时期,她于长寿二年(公元693年)亲自编写出《臣轨》二卷,计“国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诚实”“慎密”“廉洁”“良将”“利人”凡十章。朝廷不仅规定它为举人考试科目,而且还规定它为全国臣民必读的教科书。此书指出法令“明不可蔽”,赏罚“信不可欺”,是“良将”必然具备的两个重要条件。一般官吏也是如此,必须“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贤则不避仇雠”;应该“奉法以利人”,而不能“枉法以侵人”。《臣轨》还援引《说苑》关于官吏行为有“六正”、“六邪”的说法,要求官吏“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所谓“处六正”、“不行六邪”的中心意思,就是要求官吏奉公守法,不图私利,为国家尽力;反对违法损公,搞阴谋诡计,走歪门邪道。《臣轨》对官吏的要求,与“四善,二十七最”是一致的。它们与《唐律》及《贞观政要》一道,说明唐朝特别是初盛唐时期的君主们对吏治可谓殚精竭虑而又苦口婆心,其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有唐一代,特别是初盛唐,之所以政治相对清明,君臣上下团结,勤勉和高效率的执政、行政,比较完备和有效的宰相制度、官吏监督制度与考课制度以及法律制度功莫大焉。
注释:
[1][3][4][5][6][8][9]《唐会要》卷六十八《刺史上》。
[2]《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一》。
[7]《唐会要》卷八十二《考下》。
[10][11]《新唐书》卷五十六《刑法志》。
[12]《魏郑公谏录》卷一。
[13]《贞观政要》卷六《贪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