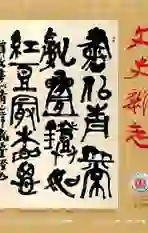庄子与禅宗的“瞬间永恒”意识
2015-11-09侯李游美
侯李游美
摘 要:在“瞬间永恒”的时间意识下,庄子与佛教禅宗在解放人性、释放审美精神领域可谓殊途同归。这种东方式的生命时间智慧,对中华民族的艺术精神、文化精神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庄子;禅宗;“瞬间永恒”;时间意识
我们知道,时间意识中的过去、现在、未来汇合于刹那的生命体验是一种东方式生命时间所具有的特征。这种东方式生命时间的形成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有一定的学理承接和历史连续性。唐代赵州大师说:“诸人被十二时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时辰。”不为时间左右,这是中国禅宗哲学的重要表现。禅宗作为中国化的佛教,它继承了大乘空宗的般若空观。刘广锋认为“禅宗是对庄子、魏晋玄学的一种继承”[1]。从宇宙范围以大乘般若智观照,去、今、来三生变迁,亦不过须臾一瞬。而在庄子哲学看来,只有在“道”的境界里,人的本真生存状态才真正有了所归,纯粹内在的直观才会有澄澈明净的生命体验。张中行曾说:“禅法到了慧能,作为一种对付人生的所谓道法,是向道家,尤其是庄子,更靠近了。我们读慧能的言论,看那些自由自在、一切无所谓的风度,简直像是与《逍遥游》《齐物论》一个鼻孔出气。”[2]
禅宗大师所说的瞬间永恒境界,与庄子的时间意识相似,特别体现在庄子对死亡的达观态度上——“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庄子·大宗师》)生死存亡乃人类无法逆转的自然规律,无论庄子的“不物于物”还是禅宗的“自性清静”,外在都强调对名利、欲望乃至生死的超越。但从外在自然-物我-内在瞬时的结构模式来看,在庄子那里,自然是人的归宿,人要去除一己之欲以回归原始朴素之自然状态。而在禅宗那里,这种自然观被颠倒了过来,人的心灵是自然的归宿,自然是人悟道的中介和手段,万事万物只有归于心灵才呈现出意义。这是二者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但庄子与禅宗都不同程度强调“净心”,且其根本特征在于“虚空”。这样就能使心灵涵容天地万物,传统的“心”“物”关系随之发生逆转,不再是“我”观“物”,而是“物”自显。呈现在心灵中的不是“人为选择的世界”,而是“世界自身”,这样的心灵“触目皆知,无非见性”,成就的乃是一个“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的鲜活生动之世界。
由庄子的“道”到禅宗的“悟”,是对“生命时间”神秘玄奥的体验,更是人自身潜在的升华。禅的最高境界——“悟”境就是瞬间永恒——过去─现在─未来汇合在这一瞬间。用庄子的话说即“无古无今,无始无终”(《庄子·知北游》)。质言之,生万有的“空”与化万物的“无”都融于这一瞬间。无论庄子还是禅宗的“瞬间永恒”,其最突出和集中的表现,都是对时间的某种神秘领悟,即“永恒在瞬间”的直觉感受。再进一步来看,对“生命时间”的神秘体验就是把人之存在置入时间之流并忘记来自时间的束缚,用生命去诗化、丰富时间的意味。宋朝词人张孝祥在《念奴娇·过洞庭》中叹道:“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这里对机械、客观性时间的遗忘就意味着对诗意审美时间的回归。
禅宗的“顿”悟所触及的是时间的短暂瞬间与世界、人生、宇宙永恒之间的关系问题。既然称之为“悟”就不是逻辑性的,而是直觉体验领悟性的。表现为在某种情况或境地下,参悟者(或审美者)突然感觉到这一瞬间超越了一切时空、因果,过去、现在、未来融于当下,不可分辨也无须分辨,不再关注内在身心于何处(时空)、何所由来(因果)。其结果超越了一切物我、人己之别,与对象世界(如与自然)完全合为一体,凝成为永恒之在,达到真正的“本体”自身。如除去一切时空、因果,在瞬间的永恒感中,直接领悟到的东西,在禅宗看来,是真我,亦即真佛性。就成佛而言,这不是“我”在理智、意念、情感方面相信佛,或屈从于佛;相反,而是在属己的瞬间永恒中,我即佛,佛即我,我与佛合而为一。禅宗常说三种境界,第一境是“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这是寻找禅之本体而不得的情况;第二境是“空山无人,水流花开”,这是已破“法执”、“我执”,已悟道而尚未实现的阶段;第三境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这是瞬间得永恒、刹那成终古的实现。需要注意的是,瞬间即永恒,必须有此“瞬间”(时间)才成其永恒。因而这永恒既超越时空但又必须在某一感性时间之中。经此“悟”之后,原来的对象世界尽管山还是山,水还是水,外在事物并无任何改变,但经此“瞬间永恒”的感受经验后,其意义的性质则有了根本不同。它们不再是参悟者执著的实在,也不再是他们追求的虚空;对象世界既非实有,也非空无,因为本无所谓空、有。反映在审美上,由于禅的最高意境是这种瞬间永恒式的精神体验。前面提到的“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是禅宗所说的生命个体在主观精神中体验到的一种意境,在这种意境中能达于永恒。这种瞬间永恒体验在中国传统艺术,尤其是山水画与诗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庄子的“心斋”“坐忘”,以求达到齐物我、同生死的精神境界,正是这样一种主观精神上审美式的永恒体验。二者的确有许多相通、相似之处,如破对待、空物我、泯主客、齐死生、反认知、重解悟、亲自然、寻超脱等,特别是在对艺术领域的影响中,庄、禅更常常浑然一体,难以区分。
“瞬间永恒”另一重要方面在于其对“当下性”的强调。所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庄子·达生》),庄子认为即便可以分神,但要精于一物与当时。庄子的“佝偻者承蜩”(《庄子·达生》)也旨在突出把全部本事瞬间凝注在手头上,心无旁骛。这种瞬间、当下是自我的,不由“依他起”,相反,由生命直接转出。当下性意味着生成性,而非现成性,它是一种活泼泼的当下呈现;当下性也意味着直觉性,即一种不关乎功利、不关乎知识的直接认识活动。我们知道,体验的根本不在于“陈述”,而在于“发现”。它意味着这个境界由我创造。它是一个独特的、唯一的、无法复制的新颖世界。纯然的体验是转换主体视角。中国艺术论中发挥道家哲学的这种思路,突出审美者去发现一片活泼的世界,唯有无心,才会有活意,才能创造出迷人之境。
在禅宗中,觉悟的片刻就是我们所说的“刹那”,慧能说:“西方刹那间目前便见”(《坛经》),西方就在刹那,妙悟便在此刻。悟在刹那间,并非形容妙悟时间的短暂。《坛经》曰:“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临济曰:“一刹那间透入法界”。性修禅师曰:“悟在刹那。”刹那是一个时间概念,在印度佛学中指极短的时间。《慧苑音义》卷上曰:“时之极促名也。”《华严经探玄记》卷十八曰:“刹那者此云念顷,于一弹指顷有六十刹那。”在禅宗及受禅宗影响的中国艺术理论看来,一切时间都虚妄不实,妙悟就是摆脱时间的束缚,进入到无时间的境界中。所谓“透入”(即悟入)之法界,则是无时间的境界。刹那在这里是一个“临界点”,是时间和非时间的界限,是由有时间的感觉进入到无时间直觉的一个“时机”。
在妙悟中,一般时间和刹那有根本区别,一般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个时间段,是具体时间。但在妙悟中,刹那却不具有这种特点,它就是一个“现在”,是将要透入法界的“现在”,是将要进入无时间的“现在”。禅宗的妙悟,是在“刹那间截断”,在突然的悟中,放弃对虚幻不真的色相世界的关注,放弃起于一念的可能性。在刹那间见永恒,即已超越时间。瞬间就是永恒,意味着当下就是全部。所谓当下,意味着截断时间,妙悟只在“目前”。“目前”不同于眼前。“目前”并不是一个区别此处和彼处的概念,它并不强调视觉中的感知。“目前”并不是眼中所“见”,而是心中所“参”,它是直下参取的。万象森罗在“目前”,并非等于在眼前看到了无限多样的物。如果这样理解,那么人仍然没有改变观照者的角色,仍然在对岸,与物处于外在的、对峙的状态,没有回到物之中。实际上,在“目前”中无“目”,也无“目”所见之前,无“目前”之空间存在。
但在“呈现”上,刹那永恒之境则都是任由世界自在的兴现。无论庄子还是禅宗,都主张一种纯粹体验的即世界即妙悟;换句话说,二者都消解了脱离外在世界的空茫索求,见到的是一个自在彰显的世界(最理想的“无待”之境见于《庄子·逍遥游》)。它不经人感官过滤,也不在人的意识中呈现。水自流,花自飘,人自在。庄子讲的委运任化,全性葆真,养生尽年,安时处顺正是这意思。在这样的时间意识背景下,人易于创造、生成一种与自我生命相关的真实意义。在“瞬间即永恒”之中,由于实现了某种真正的超越,因而一切常识之别(有无、色空、虚实、生死、忧喜、爱憎、善恶、是非、荣枯、贫富、贵贱等)已混然失去意义(这一点在庄子与禅宗那里皆成立),于是就获得了从一切世事及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自由感,既不用算计世俗事务,也不必故意枯坐修行,一切皆空,又无所谓空。不管是禅宗的“超凡入圣”,还是庄子的“目击道存”、“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作为一种亲历,均获得了体验性上的神秘感受;特别是对自然生命的欢喜,完全接近于审美愉悦之感。禅宗在作为宗教经验的同时,又仍然保持了一种对生活、生命,特别是感性世界的肯定兴趣,这一点与庄子相同——即使“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却仍具生气。
否定生命厌弃世界的佛教最终变成了鲜活生气的禅宗,承认生命困境逼迫的庄子最终在“苦”中寻求了一条摆脱一切外在束缚,实现自由与生机的“无待”“逍遥”畅适之游,既悦志又悦神。二者通过给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增添安慰、寄托和力量,而对中华民族的艺术精神、文化精神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
注释:
[1]刘广锋:《庄、玄、禅自然观的内在转化及其美学效应》,《学术论坛》理论月刊2008年第5期。
[2]张中行:《禅外说禅》,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5页。
作者单位:成都学院音乐与影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