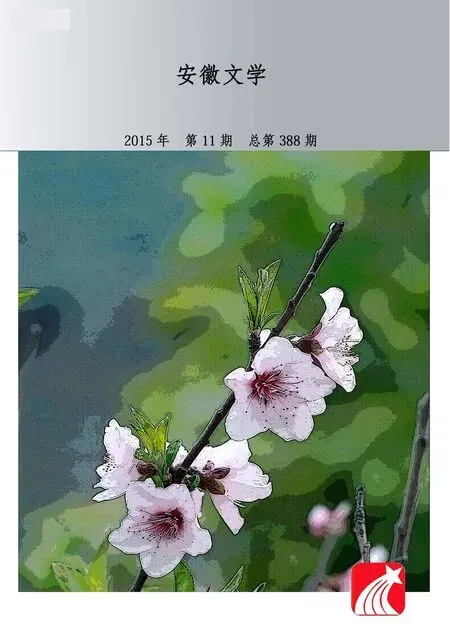论师陀小说集《果园城记》中的“时间”
2015-10-26于萌
于萌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师陀在《果园城记》初版序言中这样描述,“果园城”是他“羁旅于上海一间像棺材的‘饿夫墓’”里“心怀亡国奴之牢愁,而又身无长技足以别谋生路,无聊之极,偶然拈弄笔墨消遣”[1]时想象出的一座小城。相比于小说集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小城本身在作者的心目中同样“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情感、有寿命,像一个活的人”。[2]作家拓展了创作视野,“从前清末年到民国二十五年,凡我能了解的合乎它的材料,全放进去。这些材料不见得同是小城的出产,它们有乡下来的,也有都市来的,要之在乎它们是否跟一个小城的性格符合”[2]。
师陀在虚构有限空间的同时赋予其庞大的时间意识。“时间”,在整个“果园城”中的分量陡然增重,无一篇小说不暗含“时间”。小城的兴衰更替、百姓的喜怒哀乐都因关涉了“时间”而涂上了浓浓的象征色彩,具备了深潜的存在哲学意涵。钱理群先生曾评价“果园城之于芦焚(即师陀),不仅是因为果园城中的人物是‘习知的人物’,事件是‘习知的事件’,其中更浸透着他的理想追求,他的哲学感悟,他的审美情感和他的性格力量”。[3]作者并没有为“果园城”指认该走的出路,因为“等到他们忽然睁开眼睛发觉面临着那个铁面无私的时间,他们多么渺小、空虚、可怜,他们自己多么无力啊”。[4]
一、停滞的假象
果园城给予主人公马叔敖最大的感触就是一切如常,这是拜时间所赐。除却经年不变的街景、家畜、聊天的女人,果园城最能展示时间的器物无疑还有时钟。马叔敖拜访和女儿秀姑相依为命的亲戚孟林太太,“我们不自然地坐着,在往日为我们留下的惆怅中,放在妆台上的老座钟,——原来老像一个老人在咳嗽似的咯咯咯咯响的——不知几时停了。阳光从窗缝中透进来。”[5]11时间概念一旦停摆,安静祥和的小城风景也能保存得完好无缺了。城郊长长的河岸,从仙人袍子里“掉下来”的塔、像云和湖一样展开的果园……果园城让人流连忘返。
但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是,小说将时间模糊、暗示时间停止,事实上遮蔽了我们的目光,因为时间本身完全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有论者曾言人在进入生命之前根本体验不到时间,死后也不会体验到,因此没有人便没有时间。但若针对生和死这两个最终阶段中间的存在状态来看,人与时间之间绝非是简单的有此即有彼的关系。感受到时间时人往往表现出无能为力,而无能为力的原因并非其停滞的外表,而恰恰是无法阻挡的流动。[6]在几乎无事、几年十几年如一日的状态中,果园城里的人们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变化并非外貌和语言,而是直指人物心灵的变化。贺文龙彻底放弃了写作,自己这虚假的梦被儿子的胡写乱画戳穿之时,贺文龙感到“人生草草,岁月匆忙,一转眼便都成过去”。而在经受了丧子之痛的徐大叔徐大娘家中,还多摆放一双筷子,“一年一年被等待,被想念,他的母亲还担心他胖了瘦了,每天吃饭她还觉得和平常一样,跟他在家的时候一样。”[5]73作者的化身马叔敖无论如何承受不了这种痛苦,不忍打碎徐大娘的幻想,最终夺门而出。可以说这些都是由于时间的“停滞”所造成的。时间“停滞”的假象其实没有带来任何美好事物的停驻,而恰恰相反的是那些看似平静的事物掩藏着时间无情流逝所带来的更大悲哀和痛苦。我们感慨着这座稳定安详的小城,我们也叹息着这座被无情时间吞噬了的小城。假象,只能使我们在看到真相之后产生更大的苦痛和想要逃离的冲动。
二、“时间”的功能
时间在整个《果园城记》中不单扮演着故事发生背景的角色,它还积极地介入故事情节,帮助作者塑造人物性格,勾连过去与现实。论者在讨论果园城的悲剧人物时时常关注到统治阶级和旧官僚对普通大众的压迫和侵害,逼使他们一步步走向死亡。[7]这样的理解当然具有其现实意义,但我们应当注意到,相当一部分的人物其实是由于“果园城”本身所塑造的,而果园城所象征的恰恰是“时间”。孟安卿不忍自己青梅竹马的姨表妹必将经由婚姻从青春靓丽变作厌恶的管家婆,因而他一声不吭地走了,十二年没有消息;邮差先生缓慢地在街上踱步,他享受着这小镇的庸常和安宁……从这些情节中能够看出,果园城人的生活其实和他们对待时间的态度有着紧密的联系。南辕北辙的性格无一不来自于“时间”的塑造,它促使人物进行着选择。存在哲学中时常论及“决断”这一命题,而《果园城记》里激发“决断”的,恰恰是由时间而引发的存在困境。
时间将种种过去定格,给现世之人以无限的感慨,这也是其功能之一。这一方面在师陀着意落笔的大户家族没落的故事里表现最为明显。朱魁武号称魁爷,四进深宅大院里的秘密和一手遮天统治果园城十五年的事迹,总是令老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但时过境迁政权更迭,“有臭味的地方就有苍蝇”,魁爷最终落得侯门深闭、独居不出的落魄景象。路人不禁感叹,“唉,好的时候总归要过去的,有那么一天也就有这一天!”(《鬼爷》)另一大户胡家前代做过布政使,贴着布政使三个字的灯笼始终明晃晃的挂着,不肖子孙们生活极尽奢华铺张淫逸之能事。儿子胡凤梧无恶不作,挥金如土,为给马夫人做寿“除开堂戏不算,他在果园城四门唱四台戏;宰一百五十口猪;果园城以至五十里以内的鸡鸭被搜索光了;果园城以至五十里以内的人都被号召光了……只要肯向马夫人磕三个头的,都可以白玩三天,大嚼大醉三天。”(《三个小人物》)师陀详细记录这些富家巨子们的生活,把一个个鲜活的画面定格在时间之轴上,再以时间的推移展示现在,形成强大的反差。这种反差里固然有着对地主阶级的憎恶和诅咒,但这毕竟是果园城历史的一部分,没有了这些也就无从谈起今天的小镇和今天的百姓。由此,师陀实际上跳脱了因果报应和阶级倾轧的固有套路,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历史和时间。门房老张冻馁惨死,他的儿子小张则参加革命执行任务,没有为父报仇的结局、没有改过自新的乐观,只有“时间”将这些画面定格,留给后人作为谈资和消遣,作为唏嘘和感慨的由头。师陀想要告诉读者的正是“时间”的冷静和沉默,它包蕴着所有,只是见证而毫不发声。
时间曾让世人感到恐惧和茫然,但他又有着与之相反的消泯恐惧和烦忧的功能。虎头鱼在和完全认不出来的大刘姐的对话中,透露出魁爷、十二美女、锡匠等人如今的处境。胖头鱼认真地回答着已经成为贵妇的大刘姐的问题,但他最想知道的只是重复了好几遍的那句:“现在朝哪儿去?”那些有关某个果园城人是否还在的问题,他毫不在意。通篇师陀没有给胖头鱼多少心理描写,只有一句“世上充满了怪人,有钱的无聊人,虎头鱼不以为意”。这恰恰能表现出生活已经消泯了此人掀起感情涟漪的能力。年轻时逗乐打趣大姑娘的虎头鱼已经消失了,与其说是他自己丢弃了这些,不如说是时间的磨洗所导致。
但这遗忘的快速度反过来加剧着当事人回忆过去的力度,因而游子归乡的孟安卿,出嫁偶回的大刘姐,途径小镇的马叔敖,惨遭丧子的徐大爷夫妇……当事人的记忆往往更加清晰准确,得不到回应的失落也就更令人唏嘘。师陀用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告诉我们,“时间”不会偏袒任何一人,唯有揉碎、模糊着过去和现在,世人才能安稳地度过余生。
三、失败的“逃离”
果园城的时间仿佛是停滞的,但师陀建构的“果园城”并不是封闭的,它和已经具有了现代性的中国某些地方紧密联系着。故事讲述人马叔敖乘火车来到这里,而火车站的兴建恰恰是小镇衰败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因为火车的通行和中小学的普及,新一代果园城人开始意识到生命的短促和时间的宝贵,他们厌倦了这个千篇一律的地方,要离开并见识庞大的世界。这群人里面有从小特立独行的“傲骨”,生性开朗追求新式的油三妹,成为画家的孟安卿,参加了革命的徐立刚、小张等等。但无一例外的,作者给予了他们失败的结局,有的失魂落魄回到故土,有的命丧异地,即便是做了师爷姨太太的大刘姐“衣锦还乡”,也难遮掩她现在独身寡居,“满身肥肉和金子”的俗厌之气。逃离“果园城”的他们都是值得肯定和褒奖的,但幻想和憧憬都被现实击碎了,而已经接受现代文化了的青年们又无法再全身心融入到“邮差先生”和“葛天民”那样平顺安命的日子里去。逃离的失败不仅仅只针对“逃离”行动本身,还断绝了他们碰壁后返乡的道路,悲剧命运也就自然而然了。
存在哲学认为时间和存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存在”之所以存在有赖于时间流动的支撑。失败后返乡的主人公们是清醒的,他们隐隐约约意识到果园城或许已经不会和离开前完全一样,但真正返回之后还是被深深惊讶了,“这在他看来像做梦的,在果园城人心目中比他过的十二年更长。”(《孟安卿》)在这里,逃离行动因为“时间”的作祟而更显得毫无意义,进不能保持现代性,退而返乡却遇到了时间制造出来的厚重隔膜。
四、结语
《果园城记》运用了娴熟的小说技巧和以小见大的象征意象,尤其是其对“时间”这一问题的反复咀嚼和思索,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隐忧和担当。果园城上空始终悬临统治一切的“城主”正是时间,借助时间,果园城浓缩了所有中国小镇,让我们能够窥一斑而得全豹。师陀曾借马叔敖之口说,此生最大愿望是做个说书人:“说书人,一个世人特许的撒谎家!”说书人和小说家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想要以故事扩充读者脑海中的天地,以有限的篇幅拓展无限的时空。研究《果园城记》,有助于我们获得对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心灵悸动的真实记录。
[1]师陀.果园城记序[A]//刘增杰,编.师陀研究资料[C].北京出版社,1984.
[2]师陀.果园城记序[M].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46.
[3]钱理群.试论芦焚的“果园城”世界[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0(1).
[4]师陀.芦焚散文集 《行脚人》[M].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5]师陀.果园城记[M].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11.
[6]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生活·读书·新知[M].三联书店,1995:113.
[7]马俊江.论师陀的“果园城”世界[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