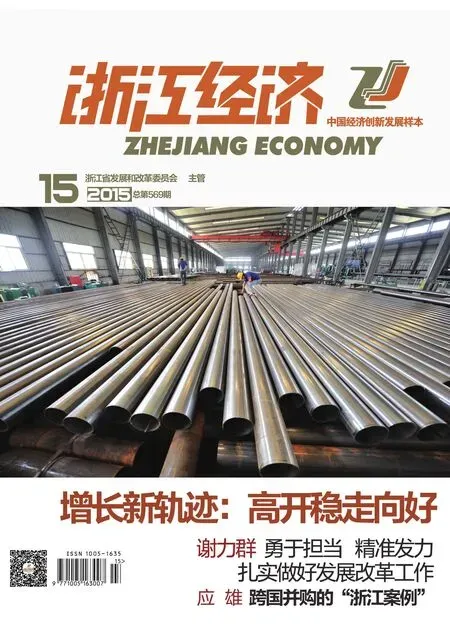浙江未来十年劳动力供给分析及预测
2015-10-26赵静
赵静
浙江未来十年劳动力供给分析及预测
赵静
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下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参与率的降低使得劳动力市场上的经济活动人口更趋减少。长期以来,浙江过多依赖低端产业、低成本劳动力的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本文将通过对未来十年劳动力供给的预测,从经济模式、产业结构和公共财政支出等三方面分析劳动力短缺对浙江经济产生的影响。
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及其变化
(一)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变化
浙江作为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的省份,自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已然走过十几年的历程。2000年至2010年,随着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省外流入人口数量大,年龄结构相对较年轻,使得十年中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3300.3万人增至4155.5万人,增幅达25.9%,明显快于全部常住人口16.4%的增幅,进而推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仍能持续提高,达到76.3%,比2000年上升近6个百分点。
随着建国后两次“婴儿潮”出生的人口逐渐步入老年以及外来人口回流等影响,近几年16-64岁劳动年龄段人口增长速度明显递减,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比重均在2011年达到顶峰:2011年,全省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4169.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6.3%;2012年开始减少,幅度不大,比2011年减少1.7万人,占比下降0.2个百分点;但2013年一下就比上年减少6.9万人,占比又下降0.4个百分点,且2014年还在继续下降。也就是说,浙江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符号”的变化,即过去劳动年龄人口是正增长,从2012年开始,就是负增长,绝对数在减少。
(二)劳动参与率的变化
劳动力的供给不仅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有关,同时也受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劳动参与率在计算上是指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是测量并反映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的一个最基本的指标。它体现的是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反映的是人们参与劳动的状况。劳动参与率是经济发展、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水平、退休制度和人口结构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总体劳动参与率较高但趋向逐步降低。浙江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较高,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总体劳动参与率为73.4%,略低于2000年“五普”的74.5%,在全国位于中等水平,但与发达国家和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仍属于较高水平。从发展趋势看,伴随市场经济水平和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浙江总体劳动参与率呈现的是一种逐渐下降的态势,与发达国家的趋势基本一致,快速的城镇化进程是总体劳动参与率下降的重要影响因素。
分性别、分年龄的劳动参与率呈现不同变化。劳动参与率曲线是劳动参与率随年龄变化所形成的曲线,既反映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劳动参与率的差异,又反映出人口生命周期中的劳动就业变动规律。下图描述的是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调查时点的分性别、分年龄劳动参与率,显示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浙江分性别的劳动参与年龄人口的形态变化。
(1)低年龄组劳动参与率有较大幅度降低。自2000年以来,无论男性人口还是女性人口,16-24岁组的劳动参与率大幅都下降。女性人口从2000年的70.2%下降到2010年的61.7%,下降了8.5个百分点;而男性人口也从2000年的74.8%下降到2010年的68.0%,下降了6.8个百分点。这显然与浙江初高中就学、升学率的大幅度提高以及大学“扩招”等教育因素密切相关,就学时间的延长导致新加入劳动年龄人口的人群劳动参与率不断降低。

分性别、分年龄劳动参与率
(2)在其它年龄组,男性劳动参与率总体保持稳定,女性同期劳动参与率在稳步提升。由上图描述,劳动参与率随着年龄的增长缓慢上升,高参与率一直保持到50岁左右,然后开始逐步下降,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生命周期特征。分性别看,男性劳动参与率一直维持相对稳定的状态,10年来基本没有变化,55岁以上男性劳动参与率比2000年还有所降低;女性各年龄段劳动参与率比五普时均有了明显的提升,其中以25-50岁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最快,平均上升约6个百分点左右。
(3)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劳动参与率也在提高。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综合素质的高低是其获得就业机会的前提条件,其中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和专业技术水平是劳动力素质的主要体现。从浙江2010年分教育程度的劳动参与率来看,很显然,劳动参与率和受教育程度之间呈现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基本上是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劳参率和就业比也相应提高,两者趋势基本一致;从未上过学的劳动者劳动参与率和就业人口比重都最低,仅为32.6%和32.0%。
(三)未来劳动力供给的趋势判断
由于不同阶段的劳动年龄人口在个人特征和劳动供给行为上存在不同的特点,劳动年龄人口的老龄化必然会对劳动供给的数量产生影响。一方面,接近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年龄人口,其劳动参与率呈明显下降的趋势,考虑到劳动年龄人口的老龄化,劳动供给的数量会由于老龄组劳动力的比重提高而下降;另一方面,基础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拓展,青年人的受教育年限将不断提高,导致低龄组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下降。
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会因为队列效应而不断提高。即便教育部门维持当前的发展水平,到2020年,浙江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量也将由于队列效应提高约5%。队列效应带来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负面冲击。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在保持现有退休制度的情况下,总体的劳动供给形势会因为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而更加趋于紧张。同时,临近退休年龄的人口数量逐年增加,也意味着生产性人口和赡养人口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开始加速,这不仅会对养老保障制度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也将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浙江未来十年劳动力供给预测
一个区域实际的劳动力供给(即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不仅取决于劳动年龄人口,也受该区域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所以,本文对未来十年的分年龄段劳动参与率也作出了相应的预测,分别列出低、中、高三个方案:
低方案:受升学率提高、大学教育普及等因素的影响,16-24岁组的劳动参与率继续降低,降幅与2000-2010年间的年均降幅一致,为0.76%,其它组劳动参与率保持不变。
中方案:各年龄组劳动参与率维持不变。
高方案:51-64岁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由于受教育程度水平、社会政策引导等因素而有所提高,其它组劳动参与率保持不变。关于51-64岁年龄组劳动参与率年均上升幅度的预测,本文把浙江情况与北京、上海人均受教育程度较高的2个直辖市,以及江苏、广东(经济结构与浙江类似,外贸依存度较高)两省作了分析对比,结果显示:2010年浙江50-64岁年龄组劳动参与率比2000年还略有下降,但在五省市中仍位列前茅,仅次于江苏;北京、上海由于大量青壮年外来人口占用了岗位,50-64岁老年组的劳动参与率处在较低的水平。浙江50-64岁老年组的劳动参与率已处于高位,未来十年并不会有较大的增长,年均增幅0.2%左右。
基于以上三个方案,本文对浙江未来十年的实际劳动力供给进行了测算,得到以下结果:2014年的劳动力供给约为3360万人,根据预测,十年后的实际劳动力供给至少要比2014年下降60万人左右。
对浙江经济产生的影响性分析
(一)降低储蓄率,促进向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个人储蓄率随人的年龄增长而呈倒U变化,青年时期和退休时期收入低,储蓄率相对较低,而中年时期收入较高,储蓄率一般随之升高。随着浙江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浙江储蓄率也应呈现逐步走低的趋势。我们将2004-2014年这十年的个人边际储蓄倾向来进行测算,将人均城乡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年末增量作为储蓄增量,人均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年度差额作为收入增量,来计算这十年来的边际储蓄倾向。得出的结论是,2004年-2010年间,边际储蓄倾向一直不断上升,但2010年以后,边际储蓄倾向的趋势发生逆转,呈逐渐走低的态势,与上文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不谋而合。另一方面,根据IMF对115个国家数据的研究发现,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与总储蓄率呈正相关关系,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1个百分点,总储蓄率下降0.7个百分点,浙江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2011年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下滑,总储蓄率也随着降低,这与个人储蓄率的变化趋势也基本一致。
因此,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结构老龄化,浙江的储蓄率在未来会持续走低,从而改变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分配的比例,影响资本形成,一定程度上压低投资率,促进经济由投资主导模式向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变。
(二)提高劳动力素质,驱动“倒逼式”产业结构调整
早在自2004年浙江小微企业就感受到“招工难”,劳动力短缺现如今已成为常规现象。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若维持浙江现有产业结构模式不变,未来企业缺工率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将越发凸显;与此同时,由于地区间的发展差异,资源禀赋不同、政策倾斜等多方面原因,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正发生从东部沿海省份向中西部地区的“雁阵式”转移,这将进一步降低安徽、贵州等主要劳务输出省份的劳动力外出打工意愿。
另一方面,浙江劳动年龄人口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情况与外来人口素质不高具有较大关联性。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每5个常住人口中就有超过1人来自省外,在这些外来人口中,低学历人口占比在80%以上,大专及以上人口比重仅为4.0%,外来劳动力素质位居31个省区市的最末位。随着外来人口回流趋势的显现,省内劳动力素质结构有望进一步优化。同时全国高校毕业人数仍在大幅增长,预计未来几年将持续年均20万左右的增幅,这也为企业提高技术创新和科研能力提供了扎实的人力资本基础。在省委省政府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总战略后,由企业主导的创业创新平台已在各地不断涌现,随着“千人计划”的深入实施,以大学生和科研人员为主体的“技术红利”时代即将到来。
(三)赡养比下降,增大社会公共财政负担
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会从赡养比方面,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收支产生重要影响。当该比率较低时,说明缴费者多于领取者,会形成收入大于支出的情况;当该比率较高时,表明领取者多于缴费者,会逐步形成收入少于支出的情况。
从国内来说,浙江在全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的8省市中也不占优势。浙江人均GDP位于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和江苏省之后,仅排第五;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却高居第三,低于江苏约1.5个百分点,与天津基本持平。2014年浙江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75%,按目前趋势发展下去,到2050年该比例会低于65%。即未来几十年浙江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赡养比会不断下降,且有可能下降为2∶1以下,即每两个在岗职工要供养一个领取养老金者,这意味着依靠在岗职工不到20%的工资收入所积累的养老基金收入会远不足以支付约占领取养老金者工资收入60%的养老基金支出,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将会迅速扩大。同时,政府使用于老年人社会保障的费用也将大幅增加,这会给社会公共财政带来较为沉重的负担,从而使得经济增长面临结构性制约因素。
作者单位:浙江省统计局人口就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