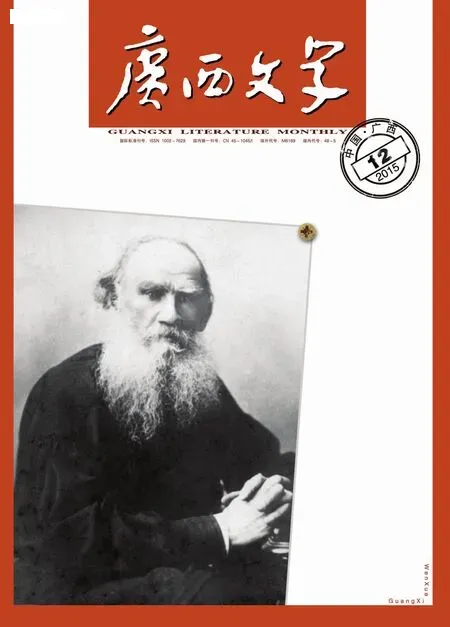鼻 血
2015-10-22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钟 欣 /著

本来只想擤鼻涕的,却把鼻血擤了出来,红红的,像涂棺材用不完的油漆。黄俊不由得骂了一句,踹了一脚冲水摁钮,走出厕所。
天已经大亮了,太阳早已升起,照进来,有些刺眼。看了一下手机,七点十九分,闹钟还没有响。他又躺回床上,刚躺下,就响了。是成龙的歌: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开始使用这首歌作为闹钟铃声了。那会儿,他报名了研究生考试,每天早晨,只要闹钟一响,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从床上一跃而起,随便洗漱一把,就往图书馆跑去,浑身充满了斗志。现在,听到这个声音,他反而感到厌烦了,举起手机掐停闹钟,用被单把脑袋蒙住。但又怕睡着了,始终不敢再闭上眼睛,在被单里躲了一会儿,还是探出了脑袋,把被单掀过一边,很不情愿地从床上爬起来。
稍微洗漱一下,他就扛自行车下楼了。每旬的三、六、九,是县城的圩日。今天是十九日,从乡下来的人们老早就在路边抢占了摊位。尤其是卖菜的,担子横在道路中间,把路堵得水泄不通,连自行车都没办法骑过去。黄俊不停地摁车铃,还是没有用。他又骂了一句:“肏他妈的!”有个老头儿回过头看了他一眼。老头儿戴着个草帽,脸色焦黑,有些面熟,好像经常把簸箕摆在这个地方,和黄俊对视了一下,依然纹丝不动,对着天空大声吆喝着:“辣椒,正宗的指天椒,一块钱一两!”黄俊刹了车,跨下来,从旁边慢慢走过。
早餐是在政府办楼下的小摊买的,三块钱的粉饺。办公室在三楼,走路上来,正好八点整。门是虚掩的,裂着一条小缝儿。灯却还没开,推开门,里头一片黑暗,双层的窗帘把窗户重重遮挡。办公室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烟味,扑面而来,很呛鼻。他忍不住屏住呼吸,止步不前。和烟味一起扑来的,还有寒气,很冷,让人一下子起鸡皮疙瘩。他往后退了一步,却冷不防撞上了从背后走过来的杨老师。杨老师托着他的后背,问:“来了?”他回过头,喊了一声杨老师。杨老师走进去开了灯。陈股长不由得吓一跳,从沙发上一跃而起。他睡眼惺忪,被子已经掉到了地上。他揉了揉眼睛,问几点了。黄俊说:“八点了。”
陈股长从办公室斜对面的小会议室洗漱回来,黄俊已经吃完早餐,开着电脑继续整理昨天晚上的录音材料。是昨天下午的会议录音。开会时,他坐在最后一排,县长和其他部门领导的普通话说得磕磕绊绊,加上周围有些嘈杂,录音效果不是很理想,他昨晚整理到子夜一点,都还没能完全整理成文字材料。陈股长和杨老师则不知道加班到什么时候。陈股长总是责备杨老师文章哪里哪里不合格。他也被吓着了,一整个晚上都不敢说话,只顾戴着耳机听录音。从十一点钟开始,他就一个劲地打哈欠了,眼睛也疼得难以睁开。直到子夜一点,陈股长才发话:“你先回去休息吧。”
陈股长还是没有完全睡醒,懒洋洋地坐在办公椅上,点燃一根烟,摆出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他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了,满脸都是疲惫,黑眼圈十分明显。坐在他对面的杨老师脸色也有些暗淡,但是腰坐得很直,显得十分认真。把烟抽到一半,他问杨老师吃早餐没有。杨老师突然把腰坐得更直,说:“你不问我还忘了。”陈股长骂了一句他妈的,然后把脸转向黄俊,让黄俊去帮他们打两碗粉回来,老友粉。
上午九点,还有一个会要开。是一个合同的审议会议,一家公司要在城南的一个乡镇建厂,厂址初步选在县道边。黄俊买了两份老友粉回来,已经是八点半钟了。陈股长又在责备杨老师:“你进来也有一年了,别总拿自己当新手!你说你这样的文章叫我怎么拿给周主任看?”啪的一声,把稿子扔向杨老师。是一份关于昨天的会议的新闻稿,杨老师昨天晚上就开始写了。陈股长坐回去,又点燃一支烟,说:“多看看我以前的稿子,看看我是怎么写的!你到底是211大学毕业的,还当过两三年的高中老师,总不至于要我手把手去教吧?!肏他妈的!”把烟叼到嘴上,猛地吸了一口,却被呛着了,一个劲地咳嗽,把泪水都咳了出来。杨老师垂着头没有回嘴,一张一张地拾起散落的稿子。
两人把粉吃完,开会的时间也快到了。陈股长率先走出办公室,杨老师和黄俊也拿着合同稿与笔记本以及录音笔尾随走了出去。会址也在三楼,是个可以坐下百余人的大会议室。财政局、国土局等部门的领导都来齐了,各就各位,就差县长没有来。杨老师和黄俊依然是坐在最后一排,并且是最角落的地方。会议室还有些吵闹,聊天的聊天,打电话的打电话,有两个看起来和杨老师年龄差不多的青年男子还公然要挟一个刚入职的小姑娘,说:“都是这样的。我们刚进来的时候,也请办公室的人吃了一顿。你看什么时候方便,也意思意思一下?不用很讲究的,一般的大排档就可以了。”
小姑娘刚抬起头想说话,县长就走进来了。他腆着个大肚子,西装革履的,皮鞋跟额头一样光亮。所有人都停止了说话,不约而同地望向他,像向他行注目礼似的。他在最中间的位置坐下,一坐下,会议就开始了。
父亲带了些油和米来。油是自家的花生油,刚榨出来的;米则是今年的早稻,刚收割回来的。他下午五点左右就到了,独自坐在门前等候。他好像很累的样子,倚靠在门框上,用草帽盖着脸,似乎想偷偷睡一觉。
黄俊没有加班,但是很晚都没有回来,在外面和同事一起吃饭。一个原来也是在县政府办当秘书的人,后来调到了乡镇,如今已经当上副书记,来县里办事。事情办完了,要请他们办公室的人吃饭。黄俊不认识他,原本不想去的,但是陈股长说:“难得张副书记瞧得起我们,是我们的荣幸啊,怎么能不去呢?”他就去了。
吃完饭回到家,已经是将近九点了。喝了点酒,他的头有些晕晕的,一时没发现门前坐着个人。掏出钥匙准备开门,一个黑影突然爬动了一下,踢到了他,冷不防把他吓一跳,叫了一声,钥匙掉到了地上,与此同时本能地往后退好几步,举起近旁的扫把,做出自卫的姿势。父亲慢慢站起来,喊了一声黄俊。他又吓了一跳,浑身都软了,慢慢放下扫把,往前走了两步,冲父亲上下打量,好一会,才喊出一声爸。“你怎么来了?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不事先打个电话给我?不是给你配了个手机吗?”
父亲说:“手机没带,怕丢了。”
他却更加理直气壮了,说:“怕丢?那手机值几个钱?我原本晚上还要加班的,想吃完饭就直接回办公室,说不定一晚上都不会回来。”父亲没有再说话,垂着头,像个知错的孩子。
父亲还没有吃饭,黄俊把他带到了最近的小餐馆,点了几个小菜,还要了一瓶一斤装的三花酒。父亲好像饿坏了,只顾埋头喝酒吃饭,一句话也不再说。黄俊没吃多少,就放下碗筷,打了个电话给陈股长,说今晚怕是不能再去办公室加班了。陈股长骂了一句他妈的,就把电话挂了。他心中有些忐忑,又给杨老师打了个电话。杨老师说:“没什么要紧的,我帮你跟陈股长说说话,你跟你爸好好聊聊天吧。”父亲抬起眉毛看了看他,想说什么,犹豫了一下,又没有说,埋下头去继续吃。
黄俊没有再吃,坐在一旁玩手机,把手机玩得叮咚作响。父亲几度抬起头看他,几度想开口说话,但都没有说,直到黄俊放下手机,望向他和桌上的酒菜,他才终于说出话来,问:“在里面——做得怎么样?”问话时,不看他的脸。
黄俊说:“能怎么样?还不是那样?没日没夜地加班,累得像条狗。”
他哦了一声,抿了一口酒,又过了很久,才问:“在里面,认识个把女孩子了吗?”
黄俊瞪着他,显得有些不耐烦,很干脆地说:“没有,办公室就三个人,三个都是和尚。”
他又哦了一声,埋下头,直到吃饱,都没有再说话。
回到住所,已经是十点多钟了。父子俩先后简单地洗了一下澡,就上床准备睡觉。屋里只有一张床,他们只能睡在同一张床上。父亲点了一根烟,咂巴咂巴地抽,像吃一样。黄俊看了看他红色的烟头,和由烟头照出的模糊的脸,也从枕边摸过手机,登录Q Q和微信,进入Q Q空间和微信朋友圈,翻看好友们的最新动态。
“你怎么还不睡?”是父亲的声音。
“睡不着。”黄俊回答,没有望向他,继续划手机屏幕。
“你每天晚上——都这样吗?”
黄俊没有回答,放下手机,望向他,依旧只能看到他的烟头,和由烟头照出的模糊的脸。他想按亮灯,却刚摸到开关,又把手缩回来。他听见父亲继续说:“别想那么多,好好干下去。到目前为止,你是村里唯一一个能够在县政府工作的人。”
黄俊随即打断了他:“得了,别说了!”把手机扔到一边,躺下去。
父亲却仍在继续:“我今天来,其实是想跟你说一件事的。”
“什么事?”
“你堂弟——黄寅——在广东——砍了人。”
“什么?!”黄俊从床上跳起来。
黄寅是一个星期前从广东逃回家的。最初,他支支吾吾,什么都不肯说,逼问了两天,才将事情交代出来。被他砍的是他的同事,也是舍友。他在广州一家酒店当保安,看上了酒店的一个女服务员。女服务员和他很聊得来,他就以为她看上了自己,在宿舍里跟所有人说她是自己的女朋友。他的舍友和这个女服务员是老乡,都是湖南益阳人,平时喜欢说家乡话,也经常在酒店里追逐打闹,不相信她就这么成了黄寅的女朋友,问他:“你和她拉过手吗?”
黄寅说:“拉过。”
“那你知道她的手是凉的还是热的?”
“废话,当然是热的啦。”
“错,是凉的。”
“放你妈的狗屁,你妹的手才是凉的。”
舍友却不以为意,轻蔑地笑了笑,说:“好的女人,手都是凉的,你知道个卵!没拉过就别乱说。我告诉你吧,她才是我的女朋友,我才拉过她的手。上个星期五,正好我跟她一起休息,我就约她去了北京路,一路上拉着她的手走到珠江边,又从天字码头乘船去了中山大学。你知道中山大学吗?那是我这辈子最向往的地方,我从小学就梦想能考进去。在中山大学里面,我也一直拉着她的手,人们都以为我们是里面的学生。那是我第一次拉女孩子的手,她的手是冰凉冰凉的,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词,就是冰清玉洁。你知道冰清玉洁是什么意思吗?你连小学都没毕业,猜你也不知道。”
黄寅头皮都发痒了,咬着牙说:“你放屁!”
“你才放屁!她会看上你?跟我抢女人,再等十八辈子吧,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个卵样,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吃屎都没你的份!”
黄寅的头皮更痒了,又咬着牙喊道:“你他妈的说什么?有种再说一遍!”
“老子说,你他妈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连吃屎也不会有你的份!怎么?不服气?不服气就尽管放马过来。”
黄寅抖了抖身子,操起桌子上的水果刀就走过去。对方临危不惧,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斜着眼睛看着他笑。黄寅却始终只是咬着牙瞪他,把他都瞪得不耐烦了。他说:“砍啊,有种你就砍啊,像条卵似的!”黄寅再瞪他最后一眼,就举起刀捅了过去。他说,捅了五刀,对方倒下来了,地上全是血。
“死了没有?”
“我怎么知道死没死?!”
他的父亲一个耳光扇过去,把他的嘴角扇出了血来。随后,又举起门角的扁担,要继续教训他,却被他的母亲拦住了。
“事情都这样了,你打死他也没有用!”
“我打死他,让他去偿命!”
却依然被他的母亲拦住了:“你要打,就先打死我好了。”
他的父亲气得脸都黑了,吼道:“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这么护着他,难怪会做出这种事来!”去派出所报了案,民警当即就赶来了。
对方流了很多血,内脏也部分受损了,躺在重症监护室,生死未卜。父亲对黄俊说:“你二婶要我让你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尽量减轻量刑。”
黄俊说:“让我想办法?让我帮她想办法?”声音很大,吓着了他。
父亲不慌不忙地摁了一下打火机,又点燃了一根烟,说:“你在政府办工作也有两个多月了,应该认识一些人了吧?她给我塞了一万块钱。”
“什么?你说什么?你拿了她一万块钱?!”
父亲没有说话,继续抽烟。
黄俊说:“你拿她钱做什么?我告诉你,她找错人了。她应该去找律师,我可没那个本事。你赶紧把钱还给她,明天回家就还给她!”
父亲这才说:“这点忙你都帮不了?”
黄俊说:“帮不了,没那个能耐。”声音没有那么大了,但是语气很生硬,“你把钱还给她,以后别动不动就收别人的钱!”
父亲也没有再说话,丢掉尚未抽完的烟,躺了下去。
翌晨,父亲一大早就坐在床头抽烟了,整个屋子乌烟瘴气。黄俊是被他的烟味呛醒的,咳咳咳地咳了几下,就醒了。他用手在鼻子前扇了扇,连忙拉开窗帘打开窗户。天气一如既往的好,天空蓝得深不可测,望眼欲穿都望不到底端。
“你明知道我不喜欢闻烟味,还这么抽。在办公室里天天闻,我都受够了!”
父亲抬起眉毛瞪着他,吸了最后一口,就把烟扔到地上。黄俊穿上衣服,要走下床开门出去。父亲的声音却突然从背后传来:“你到底愿不愿意帮?”黄俊一时还听不明白,缓了一下神,才反应过来,说:“不愿意,也帮不了。”
父亲说:“连这点小事你都帮不了,你说你在里面是怎么混的?传出去都丢人!你是村里唯一一个在县里的人,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人来找你。你说你不把最开始的事情做好,不把自己的本事使出来给别人看看,别人会瞧得起你?你在里面干也是白干,也干不长久。”嗓门一下比一下高。
黄俊把嗓门提得更高:“瞧不起就瞧不起,干不长久就干不长久。我还不想在里面干了呢,大不了今天就不去上班了!”连门也不去开了,走了回来。
父亲跳起身冲过来,抡起脚一踹,恰好踹到他的大腿。他往后踉跄了几步,靠在门上。父亲说:“就算她不给我钱,黄寅也是你堂弟。他从小跟你一起长大,现在你进了政府工作,他有事求你,你反而说出这种话,你这么多年的书都是怎么念的?我告诉你,你不帮也得帮,不干也得继续干下去,我可丢不起这人!”黄俊摸着腿,一动不动地靠在门上,瞪着他,快要流下泪来。
父亲是黄俊去上班后离开的。黄俊中午回来,就不见人了,门也上了锁,除了从家里带来的那些东西,什么也没有留下。黄俊想给家里打个电话,摸出手机,却刚划到家里的号码,手机就先响了。打电话来的,是二婶。他犹豫着,电话响了很久,才接。二婶很客气,对他嘘寒问暖,好一阵才切入主题:“黄寅这孩子是调皮了一点,但他的本性其实并不坏……”他打断了对方,说:“对不起二婶,你还是去找律师吧。”说完就挂了,并关了机。
就要开年中经济报告会了,陈股长要黄俊校对县长的讲话稿。讲话稿很长,三号字体的A 4纸,总共二十五页。陈股长说:“最好给我逐字逐句地看,不然到时候县长念了,发现有错误,后果你是知道的。”黄俊一个上午下来,才总共看了两遍。眼睛花了,头也有些胀痛。两遍看下来,除了第一次校对时发现文中的一个“地”字错写成“的”字,他什么错误都没有再发现。陈股长说:“不可能只有这么一个简单的错误,你再看几遍。认真点看,别看几行就走神了!”他又继续从头看。
杨老师叼着烟,对着电脑噼里啪啦地打字,好不容易打了一行,想了想,又删掉继续打。黄俊看了看他,想和他说些什么,周主任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杨老师很警醒,一听到电话铃声,马上把头扭过来。看到是周主任的号码,举起话筒,喊了一声周主任,正襟危坐,然后说了一声马上过去,就放下电话。但他没有过去,而是把脸转向黄俊,对黄俊说:“你过去帮周主任倒一下水。”黄俊望向他,二话不说,就走出了门,走到周主任的办公室。
是空调的水满了。办公大楼的建筑使得这一排一至五楼的办公室空调水不能往外排,只能用桶装着。周主任的办公室有位客人,是个中年男人,站在沙发前,双手攥着拳头,面对着周主任。周主任却好像对他爱搭不理,正在埋头写着什么东西,笔在纸上沙沙响。他还不到四十岁,前额就已经光秃一片了。他特意把四周的头发留得很长,将它们梳到光秃的地方,以达到掩盖的目的,却由于光秃的面积太大,四周的头发又过于稀疏,无法达到掩盖的目的,这样做反而显得欲盖弥彰。
黄俊走进去,喊了一声周主任。周主任没听见似的,没有应他,也没有抬起头。倒是中年男人把头回过来了,看到他,有些紧张,拳头攥得更紧,身子抖了一下。黄俊愣了愣,从头到脚大致打量了他一番。他穿着双排扣西装,白色衬衣,脚下还穿黑色皮鞋。只是没打领带,衬衣的扣子扣到最上面;皮鞋也有些脏了,沾上了黄泥土。黄俊看了看他,走到空调前,刚弯下腰准备提桶,就听到男人说:“我再相信你一次。如果下个星期没拿到钱,你就试试看!”黄俊略微直起身回过头想看看他,他却已经转过身,只能看到他的背影,大步流星地走出办公室。黄俊又看了看周主任。周主任头也不抬,仍在埋头写着什么,沙沙沙的。
黄俊再次弯下腰提桶。水快要溢出来了,很沉。但他不敢表现出很难提的样子,把桶提得很高,几乎是直着身体走路的,并且故意走得很快,好让人觉得他并没有使出多少力气。然而,还没有走到门口,一边的桶耳朵就突然咔的一声,桶顿时往一边倾斜,水也迅速倾了出来。倾出了一些,桶再次咔的一声,裂成两半。几乎只是一瞬间,所有的水就都倾了出来。黄俊吓了一跳,拎着提手,木然地站在原地。周主任也吓了一跳,当即从座位上站起来,吼道:“你是怎么办事的?卵毛用都没有!”
黄俊望向他,看到他满脸的怒气,浑身都发抖了。他扔下提手,连忙跑回办公室拿拖把。他的裤脚和鞋子都湿了,一路是水。陈股长和杨老师看到他这副模样,猜到发生了什么事,也拿着拖把跑了过来。水已经几乎蔓延到了整个办公室,周主任把办公桌下的插座拿了起来,弯着腰往桌子底下看,好像在寻找什么还应该注意的东西。水漫到了他的脚边。他穿的是一双红蜻蜓皮鞋,很黑,很亮,吓得水都不敢往他这边走了,转了个小弯,往其他地方漫去。陈股长、杨老师和黄俊都不敢看他,弯着腰、埋着头慌慌张张地拖地板。他们听到他说:“什么叫办事不力?这就叫办事不力!你说留你们在这里有什么卵用?!”
三个大男人费了老半天的工夫,才勉强把水拖干。周主任再也没有心情坐在办公桌前写东西,浮躁得像只发春的猫,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边走边大声叫骂。黄俊垂着脑袋站在他跟前,偶尔抬起睫毛偷看他一下。周主任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让你到我这里来吗?要不是你的大学老师冯教授向我极力推荐你,我才懒得鸟你。还以为你真是个人才呢!这些活我要一个女孩子干也比你强得多。女孩子我还可以赏心悦目,何乐而不为?冯教授也曾是我的老师,我是看了他的面子才让你进来,你却这么令人失望。还想去考编制,现在没编制都干成这样,是人都不敢要你!回去给我好好检讨一下!”
回到办公室,黄俊呆坐在办公椅上,脖子涨得红红的,下巴不停地颤抖,整张脸灰暗如泥。陈股长没有理睬他,对着电脑,自顾自地抽烟。杨老师也抽着烟,对着电脑,但是抽了一两口,还是把脸转过来望向了他,说:“没事吧?谁都会犯些小错误的,别想那么多,啊。”像个长者似的。黄俊也把脸转过去望向他,想说什么,鼻子却突然酸了,还没来得及说出话,眼泪就先流了出来。
依然要校对县长的讲话稿,十一点之前要将定稿交付另外一个秘书股,让他们打印成册,分发给每一个与会人员。下午三点,会议就进行了。昨天晚上,他头有些胀痛,原本想不来了,但是陈股长说:“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你要更加好好表现才行。再说,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你也要慢慢适应,习惯就好了。我在这里干了这么多年,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办公室里过的。”最后还是来了,和杨老师一同在小会议室里校对了两遍。他们关紧门,一个大声朗读,一个仔细听看。读了两遍,也听看了两遍,还是没有什么发现。
黄俊说:“可以不看了吗?都已经看了不知多少遍了,不会有错的。”
杨老师却说:“你还是再看一遍吧,万一真的还有什么错别字没被发现呢?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黄俊没有开电脑,拿过讲话稿埋头看。他不再像之前那样逐字逐句地看了,而是一目一行。慢慢地,又变成了一目数行。怎么也没有新的发现,到后来就一目十行了。差不多看完时,电话突然响了,振动,在办公桌上嗡嗡叫。他拿起来,望向屏幕。打电话来的,是父亲。他看了看杨老师,又望向屏幕。备注只有一个字:爸。他迟迟没有接,手机震得他手都发麻了。嗡嗡声最终停止了。他把手机放回原处,要继续校对,却忘记了刚才看到了哪里。往回翻了一页,感觉不对。又往回翻了一页,感觉还是不对。他更加没有心情看了,望向手机,好像期待它再次响起。但是,它再也没有反应。
陈股长来了,叼着烟,挎着包,西装革履,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但是满脸疲倦,仿佛还没有完全睡醒。黄俊回过头,喊了一声陈股长。他没有应,径直走向自己的办公桌,啪的一声坐下,微眯着眼睛,一动不动,好像快要死了。黄俊没有再看他,拿起手机,摁亮,翻看通话记录。在他的记忆中,父亲从来不会一大清早就给他打电话来的。他和家人的通话,一般是在傍晚时分,相互寒暄吃饭没有,最近怎么样,好一会才进入正题,并且每次说完事就会挂,每次通话都不会很久。从大学开始,就是这样。但是每次看到家里的未接电话,他都会第一时间回过去。他盯着那串号码,目不转睛。这串数字他已经很熟悉了,就像印刻在脑子里,无法擦去。他犹豫了一会,想回过去,刚要点,后面就传来了周主任的声音:
“杨坚冰你说你这是专门找抽还是怎么的,啊?弄个标题都给我弄错,细心一点会死吗?”声音很粗犷,从身后直贯双耳,冷不防吓他一跳,像丢烫手的山芋一样,随即把手机丢到桌上。
陈股长也吓了一跳,以为被吼的人是自己,眼睛没来得及睁开,就从椅子上跳起来。但是,身子被办公桌和椅子卡住了,他还没能完全跳起,就又不得不坐下去。然而,椅子在他跳起时受力往后移了一下,他再往下坐时,只能坐到最前端的边沿了。椅子受力不均衡,又往后移了一下。结果,他一屁股就滑倒在地,椅子也翻过来盖住了他。周主任原本是没有注意到他的,怒目一直瞪着杨老师。这会儿却不由得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他身上,怒目瞪得更圆,快要从眼眶跳出来了。黄俊听到了他从身后吼道:“肏你娘的说句话都能把你吓成这样?真是废物,趁早找块豆腐碰死算了,在这里丢人!”
陈股长手忙脚乱地从地上爬起来,站在一边。周主任把责备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说:“白养你们这帮人了!你们整天都是干什么吃的,啊?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所有人都不说话,都垂着脑袋,或看自己的脚下,或看自己的办公桌,好像只要一声不吭,就能够挨过去了。事情也果然是这样的,周主任没有再说话,只是再瞪他们一下,就将手中的稿子扔向杨老师。他或许是想扔到杨老师的办公桌上的,但是稿子太轻了,掉在了杨老师的肩膀,又从杨老师的肩膀掉到地上。
中午,他们都没有回去,打电话到内招叫的快餐。黄俊将讲话稿校对了最后一次,依然没发现有什么错误,再经过杨老师的大致浏览,就把U盘交付给另外一个秘书股打印了。吃过午饭,他们已经打印并装订好了。三台打印机同时工作,噼里啪啦的,打出的稿子叠起来,有半个人高。他们把稿子搬到会堂。会堂在办公大楼的北侧,可以坐下几百号人。整个中午的工作,就是把讲话稿放到每一把椅子上,好在开会的时候,与会人员一到来就可以拿到资料。除了县长的讲话稿,还有各乡镇负责人的讲话稿。这些讲话稿分别放在两个透明的塑料文件袋里,把文件袋挤得鼓鼓的。
黄俊和杨老师仍然只能坐在最后面,拿着录音笔录音,同时还得用签字笔在讲话稿上圈圈画画,特别是一些补充,要及时记上去。黄俊觉得很枯燥,一直想眯眼睛,或者取出手机玩玩。但是会议还没开始,陈股长就有言在先了:“会堂到处都是摄像头,你们千万别给我搞什么小动作!”他什么都不敢做。
电话又响了,在大腿的口袋里,不停地振动,连杨老师都听见了,扭过头看了看他。他摸出手机看了看,打来的人还是父亲。他想请示一下杨老师,但是杨老师马上就把脑袋扭回去了,看着主席台上的演讲者,一副痴迷的样子。他等手机振停,就塞回口袋。
父亲又来到了黄俊的住所,电话是他打来的。和他一起来的,还有黄寅的母亲。开完会走出会堂,黄俊才给他回电话。他显得有些紧张,声音微微颤抖,好像和自己通话的是什么高官领导。他没有先说自己已经来到了黄俊的住所,而是一如既往地寒暄,问黄俊工作是不是很忙。黄俊有些不耐烦,说:“你给我打那么多电话,就是为了问这个?”
他这才说:“我跟你二婶,来到了你住的地方。”
“什么?!”几乎是叫出来的。
“你什么时候下班?二婶想跟你说说话。”
早就到下班时间了,太阳已经快要沉下去,距离西天的山头,只差不到一拃之遥。黄俊把车骑得很快,铆足劲蹬,似乎要把车蹬得飞起来。
父亲和二婶站在楼上的走廊凭栏而望,一副殷切等待的样子。终于看到他骑车的身影,相互望了望,就从楼上跑下来。跑下来,黄俊也把自行车停在楼梯口了。
“黄俊!”他们异口同声地喊道。
黄俊没有应,怒目望向他们。
二婶突然跪下来,泪流满面地说:“被黄寅砍的那个人……没有熬过来……他的家人声称要黄寅偿命啊……”泣不成声。
黄俊依然没有说话,看了看她就走上楼,打开房门走进去,坐在床上。二婶在父亲的搀扶下,也站起身跟着走进来。二婶还在抽噎,手忙脚乱地从衣服里头摸出一个信封塞到黄俊怀里。黄俊吓了一跳,连忙站起来,信封也跟着掉到地上。二婶说:“我没有太多钱……这已经是我们全家的所有积蓄了……希望你能打通关系……黄寅这孩子……”说得断断续续,前言不搭后语,且说且继续哭。
黄俊终于说:“对不起二婶,我帮不了你。你还是去找律师吧,只有律师能够帮你。”
二婶接着说:“我不知道怎么找,你帮我找好不好?你二婶我什么也不懂,只要黄寅没事,你说怎样都成。”捡起钱包,再次塞给他,“这就当是找律师的钱,你看看够不够。”黄俊看了看她,又看了看信封。信封很厚,像装着一本笔记本。他犹豫了好一会,再抬起眉毛望了望父亲,才把信封接过来。二婶原本是紧绷着身子的,看到他接过信封,身子好像松了一些,脸上也略微展露了笑容。
那个男人很早就又来了,还没到上班时间,就守在周主任的办公室门口。他穿得不再那么有模有样了,不是很整洁的T恤短袖,短得只能勉强盖住皮带。裤子黑色,也显得有些破旧,脚下穿的甚至是一双解放鞋,和民工毫无二致。
黄俊是第一个来到办公室的人。他又流鼻血了,从楼梯走上来时,感觉鼻子有些痒,四下里瞧了瞧,发现没有人,就把小拇指插入鼻孔,来回抠。结果鼻血倒顺着小拇指流了出来。他吓了一跳,捏住鼻子,踏着大脚步往楼上快步走。一走出楼梯口,就看到了男人。男人没有跟他打招呼,紧握着拳头望着他,脸色有些僵硬。黄俊也没有和他打招呼,站在楼梯口顿了顿,往厕所走去。
还好鼻血流得不是很多,走到厕所的盥洗池前放开手,只有几滴暂留在鼻腔的血滴下来。他捧了些水,洗了洗鼻子和脸,又对着镜子看了看。那个人长得不是一般丑,大嘴巴、小眼睛,脸色暗淡,眼窝深陷,眼袋低垂。他冲那个人皱了皱眉,转过身,走出去。
男人仍旧站在那里,面朝着他,好像是等他回来似的。黄俊没有和他对视,往左右看,直到走到他跟前,才看他的脸:“你找谁?”
“周主任。”对方回答,干脆利落。
黄俊打开办公室的门,走进去,问他要不要也进来坐坐,喝杯水。男人没有客气,走了进来,坐在沙发上。黄俊打开饮水机,走回办公桌,忙自己的。男人却喧宾夺主,没等水烧热,就走过去拿杯子接。黄俊回过头看了看他,没有说话。
杨老师和陈股长也先后来了,走进门,略微有些吃惊,但都没有跟那男人打招呼,径自走到自己的办公桌。男人可能是觉得自己受到了冷遇,有些心虚,忽然听到门外有什么动静,眼神就慌乱地往外看去。陈股长对他视而不见,抽着烟对杨老师大声说:“你今天上午必须向城投公司问清楚那几个数据,时间、金额、数目都必须百分百正确。”
杨老师说:“知道了,我等下就打电话。”
陈股长一下子把嗓门扯得老高,说:“打电话就行了?还得让他们传真过来,得有他们的公章和领导的签字。”
杨老师说:“这个我知道。”
男人望着他们,犹豫了很久,才敢站起身往门外走去。看到隔壁办公室门还没开,他又走回来,自言自语一般说:“这个周主任,到底什么时候来啊?”说话时,却是望向陈股长和杨老师。
陈股长和杨老师都没有回答他。黄俊见他们没有说话,也不敢说话,对着电脑,噼里啪啦地打字。男人没有坐回原来的位置,在门外来回走,但是走着走着,最终还是走了回来。陈股长看了看他,终于有所表示:“周主任今天下乡了,怕是不来上班了,我看你还是明天再来找他吧。”
男人看了看他,突然大声叫道:“这个挨千刀的贪官污吏,知道我今天要来就躲我了?征了我的地不给我钱,躲得了初一,还躲得了十五?”把他们都吓了一跳。但是他们都没有再搭理他,面面相觑地看了看,就继续忙自己的。
但那男人还是没有离开的意思,仍旧坐到沙发上,继续等。周主任到底还是让他等来了,稍晚了一点,就听到了隔壁办公室的开门声。他像突然得到了什么感应似的,马上从沙发上跳起来,跑出办公室。
“他娘的,你终于来了!”
“怎么又是你?”是周主任的声音。
“怎么不能是我?你这个大贪官,我的钱呢?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来了,你还想忽悠我到什么时候?”嗓门比周主任还大。
周主任没有回话,坐回办公桌。空调水又差不多满了,他拿起电话,给黄俊拨了过去。黄俊马上就跑了过来。换了一只新桶,比之前的结实了很多。即便如此,把桶提起来,他还是小心翼翼地走,几乎让桶底贴到地面,似乎害怕重蹈覆辙。他只是把水提到斜对面的小会议室,倒进小会议室的厕所里。把水倒掉,他又顺便去了小便。回来时,周主任已经跟男人叫骂了起来。周主任说:“你给我滚出去,也不看看这是哪里,这是你撒野的地方吗?”
男人却突然从裤腿抽出一把匕首,喊道:“我今天来了,就没想着回去,大不了跟你这个大贪官同归于尽。”话落,扑上去。
周主任吃了一惊,举起桌上的花瓶、书本、文件夹等东西扔向他,最后举起办公椅招架。黄俊见势不妙,大声喊起来:“来人哪,来人哪!”
陈股长、杨老师跑了过来,其他办公室的人员也跑了过来。男人不停地挥舞手中的匕首,把周主任吓得直往最里头的角落缩。黄俊也有些害怕,犹豫了好一会,才第一个跑过去,趁势抱住男人。男人一个劲地甩身子。但是,黄俊把他紧紧抱住,并用力往后拖拽,他并不能把黄俊甩开。他突然就急了,手一拐弯,匕首便插向黄俊,从腰部刺进去,没有遇到任何阻力。黄俊吓了一跳,身子一下子就软了。但是手没有松开,仍旧箍住男人的腰,男人又甩了一下,还是没能把他甩开。他再次举起匕首,往黄俊刺去。黄俊又吓了一跳,血从嘴巴和鼻子喷了出来,下巴磕在了他的肩膀上。
所有人都被吓住了,愣在一旁,一动不动。男人再次用力甩。这回,终于可以把黄俊甩开了,一甩,黄俊就掉在地上。血奔涌而出,就像决堤的水库,要以最快的速度流干。黄俊用手捂住决口。他摸到了这些快速流动的液体,热乎乎的,像烧开了的水。他眼睛瞪得圆圆,嘴巴微张微合,浑身瑟瑟发抖。整个世界都混乱了,天旋地转。一群人在打斗,在他的周围跳来跳去,跳上跳下,让他眼花缭乱。他挣扎着,想爬起来。然而,他发现自己的身体是如此笨重,拼尽全力,都无法达到这样的目的。他无可奈何,只能打消这样的念头。实际上,他感到很累,什么都不想去做,只想闭上眼睛,安安静静地睡上一觉。他也果然这么做了,慢慢地、慢慢地合上眼睛。而眼睛刚刚合上,他便发觉,自己的身体一下子变得像鸿毛一样轻了。那是一种如此难以言说的感觉,仿佛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似的。他想借着这样的机会再次爬起。果不其然,他稍微用一点力,就爬了起来。只是,爬起来了他才发现,他离开了自己的身体,身体仍旧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这个身体是如此狼狈,衣衫不整、面容憔悴、浑身是血。不过,世界恢复正常了,不再转来转去,他也终于看清了周围的人:男人被杨老师和陈股长以及其他办公室的人摁住了,匕首也被夺了过来。周主任扔下椅子,往他这边跑过来,抱住他的身体,大声叫喊:“黄俊!黄俊!黄俊……”他想回答,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