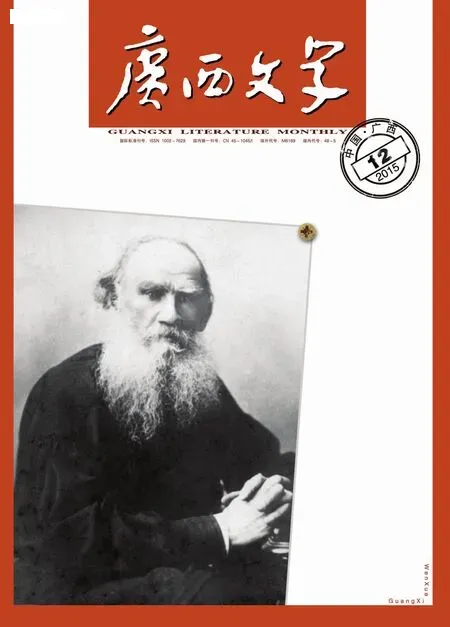庞白的诗
2015-11-14庞白/著
庞 白/著
阿鲁的手
听到快速穿过街市的行车声
就想到阿鲁,那把方向盘的手
巧手
读到魏碑结实整齐拙而纯
就想到阿鲁,那拿毛笔的手
嫩手
看到两三朋友接头般抽烟
就想起阿鲁,那派香烟的手
喔,多像兰花指
冷了,左手搓右手
就想起阿鲁,有一次表演刮胡子给我们看
靠,那完全是一双刽子手
十万光阴
十万匹白马穿过木窗,你在远方
十万缕目光穿过木窗,你在远方
十万束光阴穿过木窗,你在远方
穿过十万光阴
腐烂了离我最近的一扇木窗
圣堂湖
从山上走到湖边,我越来越安静了
波开船行,一个叫大朵的诗人
坐在船尾大声叫我
可我听不见。我正痴迷那些水
是通过什么方法把一块块石头浮起来
然后又轻而易举地把它们举到半空
后来看到一座形同残船的山
似乎摇晃着躺在水里
我于是更加沉默了
朋友们不知道我为什么沉默
他们正在赞叹、拍照,手划过清凉的湖水
像一群不理世事的小鸟
只有我知道,自己在这里又遇到了
多年前的那艘旧船
那时我刚从海校毕业
常常一个人到海边思索如何做一个船长
事实上,我只当了一段时间见习三副
就离开了大海
而大海偏偏又用博大的淡定
一直宽容着我当初信誓旦旦的背叛
看,那马
草原上那匹马
不理会远处的森林
它低头吃草
也不理会远处顶着白云的森林
不理会身边嫩绿和嫩黄的花
在山坡上起伏
它埋头于帐篷不远的草
那么安静
它就像只会埋头吃脚下的草
不会跑到远处那片森林里去
像身边的马桩
一万年前就埋在那里
现在还在那里
根部腐烂成了泥土的一部分
裸露在地面上的那部分
仍然立在地面上
只是比脚下的草高出一点点
笑 容
他们从我身边经过,迅速进入黑暗
那渐去渐远的声音
传递着某种笑容
我能感觉到那些笑容里的冰冷和火热
和衣服一样
穿到了我身上
在宁波天主教堂遗址
教堂烧剩的断壁残垣直刺云天
它们比遍地的青草长得还茂盛
那绿萝遍布的黑墙下
有人拍照,有人散步
有人躺在草地上睡着了
一位光头的老兄
站在一扇比较完整的门洞里抽烟
目光看起来虽然凶恶,但空洞
我欣赏他的表情
无数鲜花在烧焦的土地上盛开
其中一只拇指大的蝴蝶
一直站在菊花上,羽翼轻颤
我盯了它很久
感觉自己终于理解什么叫缠绵时
才举起了相机
而这时衫尾却被一个小女孩不客气地拉了一下
她告诉我,姑姑要在这里拍婚纱照
请我让开
山 川
被挖过、掘过、犁过、烧过、蔑视过的
山川
现在仍然灰着、黄着、黑着和绿着
冬天来临
远远望去
它们仍然平缓
但早已算不上平静了
感谢时光软禁我
感谢时光,软禁我。像这灯塔
十年,一百年,甚至更久远的闪亮
也可能只是一瞬间
锈迹斑斑就把蔚蓝全收进一缕光芒中了
黑 色
借助夜,我得以看清黑色
怎样越来越亮
它们亮得和在太阳底下一样透明
平稳,安详,沉默不语
我因此相信黑色的力量,连绵不断
相信生生不息的黑,会和我生死相依
相信,黑色会淹没我所有历史
让我和自己得以相忘于江湖
如果它们趁机把我身体内部仅存的
一丝绿色,连根拔走
我也没有办法。我抵御不住黑的巨大诱惑
也有可能,黑色是害怕那一丝绿色
在天色将明未明之时
把我栽入更黑的泥土里
担心那一丝绿色
在次年春天,开出一树繁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