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会吹走叹息
——传统媒体业的整体性衰退和生态媒体的无界绽放
2015-10-20文/杨溟
文/杨 溟
风会吹走叹息
——传统媒体业的整体性衰退和生态媒体的无界绽放
文/杨 溟
传统媒体业的整体性衰退并不是一个悲观的预言,因为新的生态媒体时代将绽放更多的激情、梦想与机会,它表现为一种以人为中心,以关系经营为核心,以跨界跨平台连接与协作为特征的能量组织形态。
媒介融合在国内已成显学,但这似乎并不能缓解传统媒体面对市场和行政要求的双重压力。相反,盲目跟风造成了更多的目标纠结和技术变形,新兴媒体策马驰骋攻城略地,被跨界袭击的传统媒体守城艰难,哀鸿遍野。本文试图梳理国内传统媒体危机的背景及原因,对行业趋势、特点及应对策略等做一简要分析。试图努力完成的一个任务是,让风吹走叹息,展现希望。
危机的本质和不可逆转性
传媒业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了解其本质对我们以怎样的思路与姿态对待这场危机至关重要。实际上,新媒体和新技术只是加快了危机的到来,并非元凶。
在信息短缺的工业化时代,传统媒体占据了拥有信息采写与发布权的强势地位,体制保护和信息单向传播的现实又加固了行业的权威。无论是广告还是新闻内容,只能通过这一渠道进行分发、传播,收入模式也根源于行业的垄断代理权。
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传统行业的边界模糊,这也是从工业时代跨入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因“无界”而跨界,而传媒业是最先面对跨界竞争的——行业代理权被釜底抽薪,广告商削减投放率先出逃,内容生产者纷纷在公众平台上放歌,连赖以维系的新闻信源也在快速萎缩,传统媒体的优势在迅速减弱。
确实,信息单向传播时代终结于传统媒体专属代理权的消弭。公众平台的开放、社交媒体的繁盛,释放了人性中表达与沟通的能量。而长期以来在制度保护和优越地位下的强势姿态,成为传统媒体今天在新战场上的沉重负担。如果不放下身段,就不可能真正重视用户体验及需求,亦无法在用户思维与产品设计上与跨界生长的新兴媒体匹敌。
因此,面对危机只通过技术改造提升效率是不解决根本问题的,“媒体融合”只是手段与结果,并非动机与目标。简单的业务搬家到互联网只能算是“+互联网”,而非“互联网+”。
从信息经营转变为关系经营是媒体融合时代性质的改变,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话语体系已日见分别,从产品设计理念、传播策略、组织架构到商业模式,所有颠覆皆出于此。在信息短缺时代,我们基于自身的经验与资源优势不断摸索内容制作的完美,而信息泛滥时代则更注重用户体验、习惯、特征和需求的变化,并由此对内容生产、传播、营销、组织管理等方式进行一系列调整。其实,对于“关系”的经营策略也有定量检测的体系支撑,基于互联网思维,考虑更多的并非事物本身而是“关系”,它也必导致传统传媒组织裂变,再进行新的聚合,代之以虚拟、协作、离散、聚合无常的状态。从传统的定义来看,无论报业还是广播电视业,传媒业作为独立业态会整体性衰退。
现实的危险与鸿沟
新媒体格局的重构中,越来越说不清哪些是媒体,哪些不是。这不过是一次利益与资源的洗牌,并不止步于传媒业。无边界的浪潮使“互联网+”成为传统行业进行互联网思维转型的口号。事实上,媒介素养已像水和空气一样融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各种行业。在人人可以成为自媒体的今天,媒介素养专业化的要求反而更高了。有一种观点认为传统媒体面临的不是转型的问题,而是必须全面拥抱互联网,否则难以图存。其实无需纠结于“转型”的概念,站在决策层的角度看,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
其一,决策层的视野、格局与认知。媒体高层的眼光、智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变革的方向——对于明天的趋势判断,决定了今天我们采取的策略,以及对代价的承受底线。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竞争关系,摆脱对于原有资源的依赖,放开心态与心胸,进行整体性创新与改革,是背水一战的必要选择。目前,以BAT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已不再是报道对象,而是媒体同行兼竞争者。2015年“五一”前夕,腾讯创始人马化腾高调喊出腾讯公司要做内容产业时,谁还能假装没看到传媒格局的剧变?如今,已有22个城市加入腾讯的“互联网+”生态,阿里巴巴也悄无声息地以服务联姻拿下了12个地方“盟友”。
在今天的中国媒体圈,依然可以看出两个明显的阵营:属于IT人、电商和创业科技的新媒体,以及与其一路纠缠、休戚与共的传统媒体圈。一边在不断细分用户需求中兴奋地找“痛点”、挖蓝海;一边在老生常谈中晒伤痛,晒自家闭门造车的转型。传统思维下的技术开发,更多面向集成而非面向应用,在实战中难有竞争力。
其二,组织关系中的“去中心化”流程再造。“去中心化”和主动“去界”相关。传统的组织管理体系越来越难适应变革,但组织的发展与离散聚合是大势所趋。新组织架构的核心动机是团队内部有效引导下创新力的激发,因此管理机制将决定转型成败。如:经济观察报进行了部门公司化尝试,划小经营单元,目的是激发个体创业精神;搜狐推出内部员工创业计划,总部提供天使投资;万科推出集团内部创业管理办法,鼓励员工在万科生态圈内创业,为客户创造价值。凡此种种,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传统组织内部的行政层级架构,而代之以“泛合伙人式”的管理。
强调组织方式的变化,其实质是在体制框架内,以用户导向来逐步迁转资源导向。所谓互联网思维的命门,在于能否从以往编辑部主导模式转向以用户需求营造的价值链生产模式。前者,凭借经验与资源、品牌余威,继续以传统模式进行广告销售;后者,则过渡到用户需求的分析,也由此而须依托搜索智能化、数据挖掘、精准营销等一系列技术手段。当我们更多地尊重用户消费习惯与价值需求时,旧有的生产、传播、营销与管理模式就越发显得落后。个性化的产品开发理念会反过来调整流程,引导技术理念,这是“今日头条”等创新成功的重要原因。巨系统中的离散式状态,使我们看到传媒作为“物”的行业性功能消失,作为“人”的能量输入管道洞开,接入个体而非传统组织成为常态。
其三,未来是个人数据的自媒体时代,所以对数据挖掘与数据库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对于转型媒体而言,“数据是核心”首先指传媒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来源于数据的质量、数据挖掘与分析应用的能力。其次是在媒体合作中把握用户数据的沉淀属权原则。传统媒体与淘宝合作的“码上淘”项目、腾讯与一些区域媒体开展的本地化合作、纽约时报与Facebook纠结而无奈的合作,其主要问题都是在数据的归属上。缺乏动态用户数据,就难以开展对用户行为习惯与需求的分析,自主进行产品开发的能力就很弱。即便有现实的收入,也是饮鸩止渴。再次,从员工使用数据的结构与层次、数据复用水平和效度上,可以看出企业数据应用水准。传统媒体人源于小数据的抽样调查采访方式,被奉为典范的是《华尔街日报》如何讲故事一类的专业技巧。而今后,叙事能力将归入创意与艺术的范畴,专业媒介素养将更多体现在传媒人或组织的分析能力上,这种分析能力是基于大数据的。其中,数据新闻和可视化仅指内容生产环节对于数据的分析和解读,与个人用户数据的挖掘是不同的层面。具体实践中,难点在于如何获取线上和线下的动态数据,以及如何规划数据库的底层结构。
生态媒体时代的图景——生态场景创建的关系学
传统媒体业的整体性衰退并不是一个悲观的预言,因为新的生态媒体时代将绽放更多的激情、梦想与机会,它表现为一种以人为中心,以关系经营为核心,以跨界跨平台连接与协作为特征的能量组织形态。在生态媒体时代,媒介的离散化系统将依附于生态环境和生产环节发生作用、产生影响。生态媒体将更多基于生物技术、感应技术等,与社会学、传播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学科与专业设置都面临根本性的变化。
审视内心、深入理解和洞察自身的各种需求、动机与体验,成为产品设计的灵感源泉。向外延伸人的器官功能,模拟或开发类人化智能设备、学习系统,成为产品生产的智慧结果。转型中的传媒人将亲历传统行业的解构和媒介社会化、社会媒介化的过程,从无界、跨界到去界,体会媒介素养、技能融入人类社会生活的场景,占据包括睡眠在内的几乎全部时间。日本已开展多年的梦境研究或许在演绎一个现实版的《盗梦空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关心、重视对自身的反省与反思,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敢于尝试自我的极限突破。在关系连接的过程中,通过沟通建立信任、消解分歧,达成共享、共识、共赢。
生态媒体时代,能量值=商品和服务的质量×连接系数。连接系数包括用户黏度、深度、幅度等,在这一算式里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如小米对于连接水平的重视使其对不完善的产品不断进行优化和技术迭代,“粉丝代入感”加深了其信任度,使其缺陷可以被用户善意包容,从而共同推动质量的提升。
重构生态场景是生态媒体时代重要的媒介素养要求。场景借用于此是为了便利说明在产品设计中的非线性特征,是一个阶段内的逻辑相关性展示,由若干关系主体构成,甚至包括其间的空气,相互呼应、共同获益,并具有生长性,是动态化的过程。
在传媒人的产品生产中,其实是个空间去界和时间去界的过程。考虑一篇报道的生产与传播,不仅要考虑围绕事件的相关方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考虑每一方的体验,包括尚未开发出来的潜在需求。产品经理需要设计一个能够包含在这个场景中的生态圈,并且推演出他们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创意越巧妙,逻辑搭建越合理,相关方越丰富,最终爆发的能量值就越高。
就场景营销的类型而言,一般包括了场景创造、场景参与、场景预测与场景破坏等。比如从迪斯尼动漫到迪斯尼乐园,实际上是从单一的电影受众需求中发现了儿童互动及参与的冲动——孩子们盼望参与到故事中,因而创建了这样多方协作的生态场景。“双十一”的消费狂欢其实也是一个被创造出的虚拟“场景”——电商巨头们凝聚消费需求中的“痛点”创建了“场景”生态圈。在这个圈中,并不只是电商平台一家获利,共享、共赢越来越多地取代传统竞争的“你死我活”。
场景创建的新特点是不再像过去那样满足于边界内的“专属”,而是重新组织和运营碎片化的空间与时间。常被闲置的车的空间、房的空间,甚至人们碎片化的无聊时间,都被街旁网、切客网、途家网之类的新兴媒体创建出来。传统行业的脱媒渐成趋势,河狸家是交易脱媒,淘宝是对店商的脱媒,支付宝之类是金融的脱媒,MOOC是教育的脱媒,这一切都是全新消费场景的创建。

传媒硅谷——实验室模式能否突围
媒体转型之艰难不仅在于需要克服传统时代的惯性思维和流程障碍,而且在于其技术领域的先天缺陷。传统媒体的技术部门只是从属性的保障部门,大多不具备市场开发实力,更难以承担引领前沿技术发展和进行新技术转型的能力。在日趋激烈的竞争面前,媒体设立庞大的技术研发部门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因此,借鉴海内外新科技领域产学研融合的实践经验,打造中国的“传媒硅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
欧美等国进行的媒体转型,往往有实验室的身影。2011年,《纽约时报》完成了一次重大转变,为自己的网络版建立了付费墙(Paywall)制度,一年后数字发行量就超过了纸质发行量。投资银行Evercore Partners的分析师分析付费墙为其贡献了12%的订阅收入。
《纽约时报》研发实验室(R&D Lab)开发的一款“信息级联项目”是通过捕捉报道发布在纽约时报网站后,通过不同在线媒体传播发散的情况,以可视化方式呈现读者和报道之间的联系,甄别不同新闻事件的报道内容、影像所对应的最具影响力的传播渠道,显示其传播生命周期,使每条传播渠道都成为一种潜在的产品雏形,或新的新闻制造者。《纽约时报》实验室的目标是通过创新思考改善媒体状况,其研发副总裁Michael Zimbalist说:“通过对当今前沿思潮的研究,掌握他们对明日商业模式的冲击。”其研究对象包括移动终端、桌面电脑、平板电脑、电视等所有屏幕及“云”。
波士顿环球集团“环球实验室”(Global Lab)要做的不是改变未来,而是改变当下大众对传媒产品尤其是诸多影像的体验模式,并借此改善广告商的投放成功率,并确保媒体天职的延续。在新的定义中,谷歌、微软、百度、腾讯等,几乎都已经跨界占据了原属于传统媒体的领地,如果把它们全都纳入,则实验室的意义就更加非凡了。
Google X的神秘实验室据说堪比中情局(CIA),其项目极度保密,很多员工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机器人乱跑,冰箱可以上网,食物减少时自动从商店订货,餐盘可以将菜单发到社交网站上……谷歌用这个实验室来追踪100个震撼世界的创意。谷歌发言人表示向探索性项目投资是谷歌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董事长说:“当我把时间花在一些非核心项目上时,我是希望它们未来能够成为关键业务。”
除了谷歌、微软、甲骨文以外,摩托罗拉、西门子、IBM、英特尔等公司甚至将整套实验室搬到中国,研发其最先进产品。商务部有官员预计在未来五年内中国将超过英德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企业研发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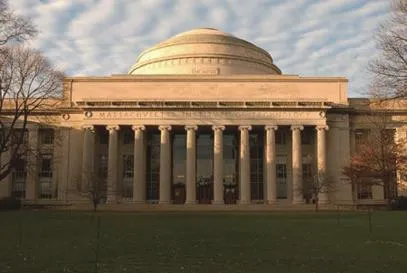
麻省理工学院及校徽
国内,百度的研发投入据说已接近谷歌。
也许美国的产学研机制会对我们有所启发。以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这三所学校为例,他们都有各自特色,但无一例外都拥有大量和业界合作的项目,或联合建立的实验室。最典型的要数斯坦福大学,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校园土地就以象征性的价格租给科技企业,再通过实验室合作获得各种研究项目和学生实习机会。此举使斯坦福大学置身美国科技前沿,创建的硅谷孕育了享誉世界的现代科技文化,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代表的人文精神巍然并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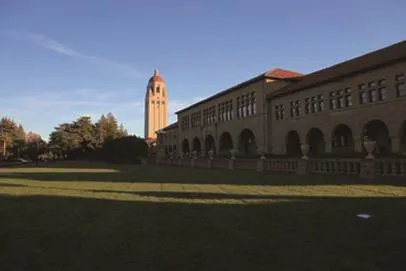
斯坦福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有33个研究小组,与逾180家全球性企业、多国政府部门及相关研究机构进行研发合作,得到源源不断的前沿项目,其知识产权及各类成果令其他院校望尘莫及。虽然是一家理工大学,但由于在传媒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的创新研究,使其人文科学的研究也保持了顶尖水平。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是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其著名的“密苏里动手风格”为全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传媒人才,其创建的未来实验室及开展的媒介融合研究具有前沿、务实和鲜明的复合性特点。
转型中的媒体,如果能够以“联合实验室”为抓手,与传媒院校形成深度合作机制,弯道超车,打造出中国的“传媒硅谷”是有可能的。“实验室”有经验型的模拟实验室和开源的探索性实验室两种。二者的分别划分出两个时代,前者是传统的中国传媒院校普遍的实验教学理念,实现的是成熟性技能培养;后者则包括了新技术的研发,需有承担失败的勇气和预计,具有探索性。大学不仅是知识传播的圣地,而且也应该是新知识创造的产房。对于现在的新闻院校而言,具有独立开发能力或趋势判断能力的还是凤毛麟角,因此有必要引入科技企业或研发团队,成立多方协作的实验室,传媒人可以小组形式融入开发过程,使技术更充分地服务于业务。

密苏里大学校徽
结合实验室的技术研发,还需要与高校师生合作,共同探索新型运营模式,其功能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转型技术与工具的研发,二是商业模式转型的研发,三是通过实训课教学改革进行产学研合作下的项目运营,四是新媒体基因的孵化与人才培养。
当我们跳出对传统和惯性依赖,会看到处处是需求繁衍出的机会,处处是蓬勃绽放的灿烂。新思维、新方法、新技术、新体系,构建出新姿态和新生命。再造组织、重塑流程、创新技术、颠覆目标、分享共识、共建多赢、创造感动,勇于放下包袱、超越自我,才能迎接未来。
没有谁可以碰巧坐在风口,风起时,只有准备好的鹰才能够飞翔。
作者系新华网融媒体未来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