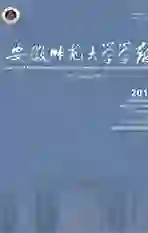道巫、佛教与理学:宋元时期徽州地域文化的变迁
2015-10-17章毅
关键词: 徽州;地域文化;道巫;佛教;理学
摘要: 理学在徽州支配性地位的形成,是社会历史长期演变的结果。从北宋到南宋以及元代,徽州地域文化的主体经历了从道巫到佛教再到理学的逐步转变。理学的优势地位,实际上直到元代才完全建立。这种文化变迁的过程,一方面与东南地区整体文化演进的趋势相匹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徽州地域社会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密切互动,反映了徽州士绅精英的成长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文化选择。
中图分类号: G1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5)05063108
一般认为理学是宋明以来徽州地域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当地最具主导性的意识形态。①
不过我们还要看到,理学在徽州支配性地位的形成,是长期文化竞争和历史演变的结果。在理学之外,道巫传统和佛教文化,都曾经在徽州深具影响力。
一、北宋徽州道巫的盛行
宋代是徽州进入中央王朝秩序的关键时期,也是科举士大夫阶层逐步形成的重要时期。据南宋罗愿淳熙二年(1175)的《新安志》,从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到宣和六年(1124)的144年间,歙州总共产生了188名进士。卷89,3对外来守宰而言,歙州也并非易于管治之地。宣和中(1119-1125)葛胜仲任职休宁县宰,被后代尊为一时名令,但他说,“某得邑黟、歙,有汤镬最沸之称。投身于兵戈杀越之乡,斗智于牒诉纷纭之地,心疲神竭,与九死为邻。”卷3,14
南宋初卫博在《定庵类稿》中也记载:“至于徽、严、衢、婺、建、剑、虔、吉数州,其地险阻,
收稿日期: 20150420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新藏徽州文书与明清商业宗族研究”(15ZS008)
作者简介: 章毅(1974-),男,安徽绩溪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明清史。
①
相关研究参见:叶显恩《明清徽州佃仆制试探》,《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汪银辉《朱熹理学在徽州的流传与影响》,《江淮论坛》1984年第1期;王光宇《论新安理学对封建社会后期徽州的影响》,《安徽史学》1993年第3期;高寿仙《徽州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周晓光《宋元明清时期的新安理学》,《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4期;朱开宇《科举社会、地域秩序与宗族发展:宋明间的徽州 1100-1644》,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4年。
其民好斗,能死而不能屈。动以千百为群,盗贩茶盐,肆行山谷,挟刃持梃,视弃躯命与杀人,如戏剧之易、饮食之常。”卷15,7朱权之侄朱申和从侄朱况也同样“效其叔之为者”,[12]附,4分别于绍熙元年(1190)和庆元二年(1196)得到进士。[15]卷6,13祁门县方岳之岳父汪清英,乾道七年(1171)乡贡进士,虽然未得高级功名,但也曾在佛庐中苦读。“霜晨雪夕,拥黄
纟由
被披吟,益悲苦。僧或为束缊火蓺松钗,辄摇手却之。”[16]卷45,2
科举士人对于佛教的态度常常也比较亲近。乾道九年(1173)徽州郡城城阳院的五轮藏落成,淳熙二年(1175)罗愿写《徽州城阳院五轮藏记》加以表彰。“佛氏之书载以五轮,此役之巨丽者也。以吾州人之勤于力,今歙县南所谓城阳院者,迺亦有之。”不仅赞美佛书的广博与经藏的精美,“今是书踰五千卷,藏之者又如此,独不为伟乎”,而且赞美经营此事者的美德,“宗仁御众以律,能使其徒皆乐事劝功,而智海尤坚忍,至以医道走四方用佐费,所以能鼓舞斯人而与之为其难者。”[12]卷3,17-19罗愿之弟罗颂为歙县江祈院写记,认为“浮屠氏之道即吾儒所谓一以贯之者”。又认为“今之士大夫”应该取法寺僧,"内信所挟,不以法俗分别为轻重,卓然有所立于世。"[12]附,8-9绍熙四年(1193)进士程珌为歙县黄坑院写记称:“我闻西方有智人,甚仁且刚,拓跋自立,欲驱六合内外,皆一信善。其说茫洋阔大,而卒不可泯绝者,吾儒之道实行乎其中也。”[14]卷11,11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到佛教对南宋时期的徽州的深刻影响。
三、南宋徽州理学的兴起
南宋也是朱熹(1130-1200)及其理学在徽州逐渐发生影响的时期,只是直到朱熹去世之前,理学对徽州士大夫的影响仍比较有限。
接触朱熹理学最早的是与之有乡亲之谊的婺源士人,而淳熙三年(1176)朱熹回乡省墓又是一个重要的机缘。最早接触理学的士人中,最重要的是程洵。程洵之父程鼎是朱熹父亲朱松的妻弟,朱熹曾写《韩溪翁程君墓表》简述程鼎的生平,称其“为人坦夷跌宕,不事修饰。好读左氏书,为文辄效其体,不能屈意用举子尺度,以故久不利于场屋。家故贫,至君益困……无以卒岁,而君处之泊如也。”程洵本人也仕途坎坷,“有子曰洵,好学而敏于文。君奇爱之,曰:‘是足以成吾志矣。既又屡荐不第,今乃以特恩,授信州文学,识者恨之。”[17]卷90,11-12同时的婺源王炎也称程洵“早列荐书、晚缀仕籍,素所藴蓄,不获见于事业,而惟寓于其文。”[9]卷24,26程鼎、程洵父子都颇不得志于科举。而程洵对于理学的研习却相当热心。
朱熹文集中有十余封《答程允夫书》,即是与程洵的通信。从中可以看出程洵如何在朱熹的指导下逐步去了解性理之学的含义。
程洵和朱熹论学,一开始将苏轼和程颢并提,朱熹告诉他这两者各是文章之学和义理之学,根本不同。将两者并提是“未得其门而入”。[17]卷41,10并告诫程洵不要为苏轼文辞的华美所炫,“吾弟读之,爱其文辞之工,而不察其义理之悖。”而真正的义理,“无声色臭味之可娱,非若侈丽闳衍之辞、纵横捭阖之辨,有以昡世俗之耳目而蛊其心”,需要“洗心涤虑,以入其中,真积力久”,才能“卓然自见道体之不二,不容复有毫发邪妄杂于其间”。[17]卷41,12endprint
朱熹又通过对程洵一系列读书札记的批改,使其对一些关键的理学概念有所辨析,尤其是使其能区别佛家所讲的义理和朱熹所讲的义理的差别。关于“道”,程洵认为:
“朝闻道夕死可矣。天下之事,惟死生之际,不可以容伪。非实有所悟者,临死生未尝不乱。闻道之士,原始反终,知生之所自来,故知死之所自去。生死去就之理,了然于心,无毫发疑碍。故其临死生也,如昼夜,如梦觉,以为理之常。然惟恐不得正而毙耳,何乱之有。学至于此,然后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朱熹批驳称:
“此又杂于释氏之说。更当以二程先生说此处,熟味而深求之。知吾儒之所谓道者,与释氏迥然不同,则知朝闻夕死之说也。”[17]卷41,15-16可见,
程洵杂糅了佛家和理学两种价值观,基本上是从自然论的角度来说明生死的不可怕。生死就如昼夜的消长,如梦醒觉一样,明白了这样的道理就可以不惧生死,就可以得道。但朱熹所阐明的“道”恰恰不是一个自然消长的过程,而具有恒常而超越的特点。所以朱熹说程洵是“杂于释氏之说”。
关于“性”,程洵认为,“身有死生,而性无死生。故鬼神之情,人之情也。死生,鬼神之理。非穷理之至,未易及。”程洵的本意在说明“鬼神”之理不可求,是古典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意思。但是朱熹认为,“如此所论,恐堕于释氏之说。性固无死生,然‘性字须子细理会,不可将精神知觉做性字看。”[17]卷41,15因为按照程洵的说法,容易将“性”看成是佛家所说的“知觉”,仅仅强调“性”“不灭”的一面。而在朱熹看来,理学所讲的“性”,虽然也具有恒常的特点,但是并非普泛意义上的“知觉”,而具有强烈的目的和道德,即理学所讲的“性”,不仅“恒常”,而且“至善”。
关于“善”,程洵认为“可欲”即“善”,即值得追求的东西就是“善”。“可者欲之,不可者不欲,非善矣乎?”朱熹认为,这个说法有简单化的嫌疑。“盖只可欲者,便是纯粹至善自然发见之端,学者正要于此识得而扩充之耳。若云可者欲之,则已是扩充之事,非善所以得名之意也。”[17]卷41,19其缺陷是忽略了“工夫”在成善过程中的作用。
关于“鬼神”,程洵注意到朱熹吸收了张载的观点,用“气”的变化来解释鬼神。
他说:
某向尝蒙指示大意云:“气之来者为神,往者为鬼。天地曰神曰祇,气之来者也。人曰鬼,气之往者也”。此说与张子所谓“物之始生,气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气日反而游散。至之谓神,以其伸也;反之为鬼,以其归也”之意同。近见兄长所著《中庸说》,亦引此义。但是,程洵也敏锐地觉察到了朱熹所讲与张载的不同之处:
“张子所谓物者,通言万物耶?抑特指鬼神也?若特指鬼神,则所谓物者,如《易大传》言‘精气为物之‘物尔。若通言万物,则上四句乃泛言凡物聚散始终之理。如此而下四句始正言鬼神也。‘精气为物,向亦尝与季通讲此,渠云:‘精气为物者,气聚而为人也。游魂为变者,气散而为鬼神也。此说如何?”[17]卷41,31
在程洵看来,张载强调鬼神是一个由气所构成的对象,即具有物的特性,但又非一般的物。而朱熹则强调鬼神仅仅是一种气化的功能。这里面存在着差别。程洵引用友人的说法,在观点上还是偏向于张载,倾向于将鬼神理解为一个外在的对象。但朱熹回答:
“《易大传》所谓物,张子所论物,皆指万物而言。但其所以为此物者,皆阴阳之聚散耳。故鬼神之德,体物而不可遗也。所谓气散而为鬼神者,非是。”[17]卷41,31
在朱熹看来,不论是万物还是鬼神,都没有区别,都是气的聚散离合。这实际上就表明,鬼神只是一种功能,而不是一个对象。
朱熹的这个观点恐怕还很难为程洵所接受,因为在当时的徽州,右鬼尚巫的风气很盛。淳熙三年朱熹回婺源省墓,说:“新安等处,朝夕如在鬼窟。”[10]卷3,53用气化的观点来解释鬼神,对程洵来说,当然颇有难度。
程洵对于理学的认识在后期有所改变。在另一封信中,程洵已经能够辨认什么观点是贴近佛家。程洵称:
“张子曰:‘天性在人,犹水性之在冰。凝释虽异,其为物一也。观张子之意,似谓:水凝而为冰,一凝一释,而水之性未尝动。气聚而为人,一聚一散,而人之性未尝动。此所以以冰喻人,以水性喻天性也。然极其说,恐未免流于释氏。”
程洵这里自觉地区别了理学与佛家的观念。他认为张载的论“性”,更多地强调了其变而不化的一面,而没有注意到“性”一方面具有善的特性,另一方面又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分。程洵的这个分梳得到了朱熹的许可,认为“横渠之言诚有过者”。[17]卷41,31
不过总体而言,朱熹还是认为程洵虽然在道理上理解了理学,但仍然缺少践履的工夫。朱熹说:“每与吾弟讲论,觉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费力,见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以少却玩味践履功夫。故此道理,虽看得相似分明,却与自家身心无干涉,所以滋味不长久。纔过了便休,反不如迟钝之人,多费功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却远。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词一义之失也。”[17]卷41,34
当时与朱熹有交往的婺源士人,还有李季札、滕璘(淳熙八年[1181]进士)、滕珙(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兄弟等人。与他们相比,程洵已经是对义理最留心的一个。其它如滕璘,虽然《朱子语类》中由滕璘记录的条目多达百余条,所涉及的内容也非常广泛,几乎涵括朱熹理学的各个方面,正文中亦有多条为滕璘与朱熹的对话,但滕璘在论学方面远不如程洵深入。
滕璘对佛教颇为热衷。曾问朱熹,“人生即是气,死则气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间人为恶,死若无地狱治之,彼何所惩?”朱熹回答,“吾友且说尧舜三代之世无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后有浮屠,而为恶者满天下。若为恶者必待死然后治之,则生人立君又焉用?”滕璘又问,“尝记前辈说,除却浮屠祠庙,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朱熹答,“自浮屠氏入中国,善之名便错了。渠把奉佛为善,如修桥道造路犹有益于人,以斋僧立寺为善,善安在?所谓除浮屠祠庙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于彼,自然孝父母、悌长上,做一好人,便是善。”[10]卷126,3033滕璘又说,“以拜佛,知人之性善。”朱熹反讽说,“亦有说话。佛亦教人为善,故渠以此观之也。”[10]卷109,2698朱熹最终认为“德粹(引者按:滕璘字)毕竟昏弱”。[10]卷118,2942endprint
总括而言,虽然在淳熙时代,朱熹因为与婺源有着乡谊亲缘的关联,当地的士人有机会接触到理学,但他们对朱熹理学的理解并不深入,在义理方面的探究也比较薄弱。嘉定五年(1212),朱熹最重要的著作《四书集注》被列入学宫,[18]卷8,4-5标志着朱熹理学在南宋完成了由“伪学”到“正学”的转变。在随后的五十余年间,朱熹本人的地位不断得到尊崇。绍定三年(1230),朱熹被追赠太师,封徽国公。诏文称,“载赐嘉名,爵之父母之邦,位以公师之品。”[18]卷10,2虽然朱熹本人出生于福建尤溪,但徽州作为朱熹的“父母之邦”的身份在此得到了正式的确认。因应王朝对于朱熹的敕封,淳祐六年(1246),徽州守臣韩补“徙朱子祠于江东道院旧基”,建立“紫阳书院”,宋理宗并为之御书额匾。宋亡前夕的咸淳五年(1269),宋度宗还赐封婺源为“文公阙里”。[19]卷9,12
随着朱熹身后的政治地位得到尊崇,理学逐渐走向正统。徽州当地的士大夫对理学的熟悉程度也逐渐加深。淳祐二年(1242)即将致仕的监察御史吕午为同乡儒学士大夫程若庸(号勿斋,咸淳四年[1268]进士)编订的《增广字训》写序称:“某东奔西走,每欲以是与四方朋友是讲是究,讵意趋向之正,问学之深,近在乡邦。”认为朱熹对于“心、性、情”等概念的解释精确明白,“昭若日星”。[11]278而到了南宋末期,在曾任职史馆编校的绩溪士人汪梦斗的眼中,理学已经成为儒学的正宗。宋亡之后第二年(至元十四年,1277),绩溪县学被毁尚未恢复,汪梦斗即以自己的祖居西园权作县学为诸生开讲。特选《复其见天地之心》为题,以理学中的“复心”观念发挥从乱世可归太平的理想。汪梦斗告诫诸生,时代动荡、新旧交替之际,往往也是儒“道”黯淡之时:
“天地之心不见于显然之时,而隐然见于杀气之中,此是生物之几……虽若不可见,而实可见者也……诸君徒伤世道之否,宇宙闭塞、贤人遯藏、万象萧条,鄙诗书如故纸,唾礼乐为何物。将谓四教可废、五常可泯、六经可弃,儒业摈于不用矣。吾道剥蚀,不殊穷冬。”
但这种危机时刻,其中仍包蕴着昂扬的生机和复兴的希望。
“毋谓时不尚文,时未及学,遽自以为吾道不振,儒不足贵,甘于自暴自弃也……吾道乃人生日用常行之道,斯民共由之而不知者,本无晦明,本无绝续。时若晦矣,而晦之中自有明之几;时若绝矣,而绝之中自有续之几。若于其几见得分晓,便足以见天地之几。既见得此几是天地阴騭斯文之心,便当于其若晦者,明之使愈明;若绝者,续之使愈续。以仰副天地生物之心,则吾道将如冬至之复而春。”[20]卷下,3-4
汪梦斗以天道论及心性,又由心性论及政治,体现出在乱世中重建秩序的用心。
显然,对于相当一部分士人来说,在此时的徽州,朱熹的理学已经不再是一个外部的思想资源,而逐渐成为其知识世界的组成部分,同时,理学中的若干原则也已开始产生了现实的意义。
四、元代徽州理学的传播
进入元代,理学才真正在徽州产生支配性的影响,其中有着理学思想史内部的演变逻辑,也有着社会环境变更的重要作用。
元朝从至元十三年(1276)统一江南,到延祐元年(1314)重开科举,之间有近半个世纪的科举停废时期,这使得众多的徽州业儒者失去了晋升的通道。即使重开了取士之路,仅就元代延祐之后的十六科科举而言,其所选进士人数中,原南宋所在地(江南)的录取配额也极为有限,大约只相当于南宋旧额的5%,而徽州所在的江浙行省更低于这个比例。 [21]573-575有元一代,徽州只有23人通过了乡试,其中又只有5人成为了进士。[15]卷6,20-21业儒出路逼仄,促使不少儒者另谋出路,或经商,或转为阴阳术士,而对于那些仍然业儒者来说,作塾馆的师儒则成为最重要的一种职业选择。在元代的徽州,乡村师儒人数众多,他们长期在基层进行启蒙性的理学教育,无疑大大加深了理学在地方社会的传播。这些师儒中最知名者当属休宁陈栎和婺源胡炳文。
陈栎(1252-1334)出身于寒微的儒者家庭,幼年时即从祖母吴氏口授《孝经》《论语》和《孟子》,7岁即跟从父亲出入馆塾,15岁即“束父书以出”,正式开始其师儒的生涯,一直到83岁去世,时间长达68年之久。[22]卷15,5-7
陈栎并非不留心科举。南宋咸淳九年(1273),陈栎年22岁“始就方州,试以《书经》,以待补选”,开始其进入科举之前的准备活动。但是两年之后的德祐元年,科举即废,通过业儒入仕的通道已经被封。在当了40年的师儒之后,元代延祐元年(1314)恢复科举,陈栎即赴江浙行省参加乡试,以《书经》登第,最终却未能参加第二年在大都的会试。
已达63岁的陈栎,晚年亟欲以乡试进士的身份就近获得教职。在《上许左丞相书》中,陈栎向上司表示,希望“任紫阳书院山长,或任徽路学学正,使得以朱子之学迪后进,以续紫阳之灯”,[22]卷10,4在《上秦国公书》中也期望“除栎一泮水近阙”,[22]卷10,5-6即就近获得一个学官,但最终都未能如愿。
在长达60余年的师儒生涯中,陈栎的教学地点相当固定,基本不超出休宁县的范围,其中在詹溪程氏家中作馆8年(1276-1283),而在珰溪金氏的家中更长达16年(1314-1329)。在此期间,陈栎编纂了大量启蒙性的理学著作。至元二十三年(1286)陈栎35岁,写成有关礼服制度的《深衣说》,这是陈栎著述活动的开始。大德三年(1299)编成《论语口义》,大德七年编成《书解折衷》,八年编成《中庸口义》。至大三年(1310)开始编注《礼记》,皇庆元年(1312)编成《礼记集义详解》。延祐三年(1316)编成《书经蔡传纂疏》,四年编成《四书发明》。[22]年表,3-6
对于自己的这些著作,陈栎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判断。他说自己的《论语训蒙口义》一书“抑不过施之初学,俾为读《集注》阶梯,非敢为长成言也。”其起初编订的原因只是出于教学的方便:“栎沉酣《四书》三十年余,授徒以来……遇童生钝者,困于口说,乃顺本书、推本意,句释笔之。其于《集注》,涵者发,演者约,略者廓,章旨必揭,务简而明。旬积月累,累以成编。”[22]卷1,5-6而其它类似的作品如《读易编》《书解折衷》《诗句解》《春秋三传节注》《增广通略》《批点古文》多种,性质都相同,主要都是在帮助修习者更好地理解程朱理学。endprint
胡炳文(1250-1330)的情况与陈栎颇为相似。元人汪幼凤《胡云峰炳文传》详细记述了胡炳文的事迹,该文也是《元史·儒学传》以及诸多明清史籍相关记述的蓝本:
“胡云峰炳文,字仲虎,婺源人……幼嗜学,年十二夜读不辍……既长,笃志朱子之学。上溯伊洛,凡诸子百氏阴阳医卜星历术数,靡不推究。四方学者云集,尝为信州道一书院山长。其族子淀为建明经书院,以馆四方来学之士。炳文归署山长,为课试以训诸生,成材者多。”
胡炳文的讲学地点主要在婺源乡里的明经书院,与陈栎依托私塾的情况略有不同,但刻苦讲学的精神则完全一致。在与江西名儒吴澄的通信中,胡炳文描述了自己在明经书院的讲学情况,“每岁正月之首,人事往还数日,十二月之尾有事于先,大率三百六旬,暇不过十余日。孜孜矻矻,相与讲求经学,旦夕不辍,寒暑不渝。”[23]1:3-4一年当中休息的时间不过十几天而已,极为勤勉。胡炳文的著述也同样宏富:
“炳文集诸说参正,作《易本义通释》,而于朱子所注《四书》用力尤深。馀干饶鲁之学,本出于朱子,而其为说多与朱子抵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书通》,凡辞异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辞同而意殊者,析而辨之,往往发其未尽之蕴。于《性理》三书、朱子《启蒙》、《易》五赞,皆有《通释》行世。《春秋》尝为《集解》,礼书皆有《纂述》……又有《大学指掌图》、《四书辨疑》、《五经臆意》、《纯正蒙求》、《尔雅韵语》、《云峰笔记》、《讲议》二百篇,《文集》二十卷。东南学者因其所自号,称云峰先生。”[13]卷71,13-14
这些著作,除了具有明显的“理学教科书”的特点之外,还有着鲜明的“尊崇朱子”的立场。胡炳文自述,自己“殚五十年心力”,用功于《四书》和《周易》等书,“不过发明朱子之说”而已。[23]卷1,6又认为“我辈居文公乡,熟文公书,自是本分中事”。[23]卷1,11
或许正因为如此,注重理学内部义理演进的明清学术史著作,对胡炳文的评价并不很高。明代宋濂主持编撰的《元史·儒学传》,对胡炳文的介绍仅附属于胡一桂之下。[24]卷189,4322晚明冯从吾的《元儒考略》对胡炳文的记述也颇为简略。[25]卷2,14清人黄宗羲、全祖望的《宋元学案》将胡炳文列入“介轩学案”之中,认为这一系的学术已“渐流为训诂之学”。[26]卷89,2970实际上,在《宋元学案》中,陈栎所得到的评价也同样不高。全祖望在《沧洲诸儒学案序录》中认为,陈栎等人只在“下中之士”的行列。[26]卷69,2258相比之下,元代末期的徽州儒者郑玉所得到的评价要高得多,《宋元学案》为郑玉设立了《师山学案》的专章,并认为在元代的理学中,郑玉是继吴澄之后,进行“和会朱陆”工作的重要学者。[26]卷94,3125显然,《宋元学案》看重的是学者在理学内在逻辑中的“理论”贡献。
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从羽翼程朱理学的正统出发,所得到的评价则会颇不相同。盛清时期名宦朱轼(1665-1736)主持编撰了一部颇具正统色彩的学术史《史学三编》,在《名儒传》的元代部分收录儒者11人,其中北人、南人各具其半,在6名南方儒者中,陈栎、胡炳文均赫然在列,且是徽州地区唯一入选的儒者。该书评价陈栎“因科举废”而“发愤于圣人之道”,有丰伟之功。而胡炳文对于《易》和《四书》的研究,洽合程朱之旨,“自程朱后解《易》数十家,独云峰最为精切,其《四书》亦比诸家为善。虽未得措之经国大业,而羽翼正道,确遵朱子,用启后学,功岂小哉。”[27]卷8,17、22《史学三编》的评价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陈栎、胡炳文的贡献,并不在于沿着理学内部路径进行义理上的发明,而在于笃遵朱子学的基本原则,对之进行解读和阐释,并将之在徽州地方社会广泛传播。
结语
在宋明以降的徽州区域社会中,理学是一种具有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但这一局面的形成,有着自身的历史演变轨迹。在两宋时期,道巫传统和佛教文化曾经分别是主导性的徽州地域文化。北宋显赫的聂冠卿家族以及普通的学道者郑八郎,分别从精英和大众的层面,显示了北宋时期当地的道师传统和
巫见
之风。大约在五代时期传入徽州的佛教,要经历一个漫长的传播和涵化时期,才在南宋发生全面的影响。不仅各类地方信仰均经历了明显的佛教化转型,而且新兴的科举士大夫也与佛教发生了密切的关联,他们往往依托佛寺准备科举,在科举成功之后,也对礼佛满怀热情,他们并不认为佛教与“吾儒之道”有什么矛盾。从南宋中期开始,徽州士人如程洵、滕璘等人,因为与朱熹有乡、亲之谊,有机会率先了解理学的思想。但总体而言,直到朱熹去世之前,理学对徽州士大夫的影响仍比较有限。在南宋的后期,随着朱熹身后的政治地位得到尊崇,理学逐渐走向正统,徽州士大夫对理学的熟悉程度也逐渐加深。元代之后,随着科举的停开,原先的业儒者当中,有不少转型为长期执教乡村的师儒,其中也不乏如陈栎、胡炳文这样才识卓越的儒者。他们面向大众,通过对朱熹理学著作的不断注解、训释和编辑,使得理学在地方社会中广泛传播。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理学才真正成为当地具有主导性的地域文化。
参考文献:
[1]
罗愿.新安志[G]∥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G]∥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
[3]
葛胜仲.丹阳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
卫博.定庵类稿[G]∥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
张君房.云笈七籤[M].北京:中华书局,2003.
[6]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
苏辙.龙川略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endprint
[8]
祝穆.方舆胜览[G]∥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
王炎.双溪类稿[G]∥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0]
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94.
[11]
吕午.竹坡类稿[G]∥北京图书馆藏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12]
罗愿.罗鄂州小集[G]∥宋集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2004.
[13]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G]∥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4]
程珌.程端明公洺水集[G]∥宋集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2004.
[15]
彭泽、汪舜民.徽州府志[G]∥天一阁明代方志丛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1.
[16]
方岳.秋崖先生小稿[G]∥宋集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2004.
[17]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G]∥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上海书店,1989.
[18]
李心传、程荣秀.道命录[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
[19]
戴铣.朱子实纪[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
[20]
汪梦斗.北游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1]
萧启庆.蒙元的历史与文化:蒙元史研讨会论文集[C].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2001.
[22]
陈栎.定宇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3]
胡炳文.云峰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4]
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5]
冯从吾.元儒考略[G]∥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6]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7]
朱轼.史学三编[G]∥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汪效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