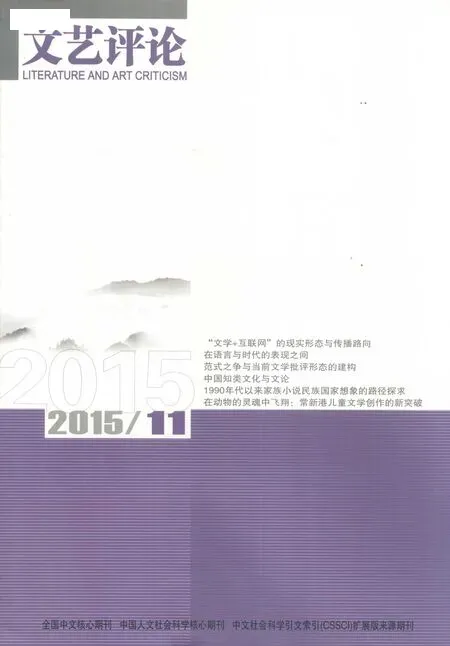关于“大连会议”及“中间人物”论问题的思考
2015-09-29王晓瑜
○王晓瑜
1960年,为应对因大跃进期间经济政策的失误与随之而来的自然灾害造成的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方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艺政策的调整也随之而来。这种调整既源于新中成立国以后新的文艺机制的运行特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被极大限度地拉近,政治经济政策的变动往往会引发文艺立竿见影的变化;同时也符合文学自身运演流变的内部逻辑——文学在经历一段昂扬狂欢之后往往会转入冷静与深沉。在此背景下,1962年8月2日至16日,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当代文学史上一般被称为“大连会议”。“大连会议”是这次文艺政策调整中的一次重要事件。
一、关于参会者的一些问题的辨析
大连会议由当时的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邵荃麟组织主持,召集了主要来自北方各个省市的作家、评论家参加会议。中国作协主席茅盾与中宣部主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周扬也参加了会议。
对于“大连会议”的参会人数与参会者,直到目前也没有个准确说法。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出版的多种当代文学史著作都采用参会者为16人的说法,但是海外学者林曼叔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中说参加会议的作家、评论家为18人①,后来也有人用了二十几人的模糊说法(如李洁非的《典型文案》)。而出席会议者具体是谁则均语焉不详。列出参会者较多是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5月版),为赵树理、周立波、康濯、李准、西戎、李束为、李满天、马加、韶华、方冰、刘澍德、侯金镜、陈笑雨、胡采14人②。但是作为中宣部的工作人员参会的黎之后来回忆说刘澍德因身体原因并未参会,却提到大连文化局长沈西禾参加了会议。③2011年洪子诚发表的《大连会议的材料注释》也提到“原定有刘澍德,但因故没有出席”④,似乎印证了黎之的说法。洪子诚的文章大量引用大连会议的发言,似应查阅了大连会议的记录,应该比较准确。洪子诚所列参会者为:“除了邵荃麟、茅盾、侯金镜外,有赵树理、周立波、康濯、李准、西戎、李束为、李满天、马加、方冰、陈笑雨、胡采、李曙光(黎之)等。”⑤如果把茅盾与邵荃麟作为文艺界的领导不计算在内(朱寨的《思潮史》是这样处理的),洪子诚列出姓名者为14人,另所引材料中有韶华的发言,有姓名可查的参会者15人。可是大连会议的记录人之一涂光群在后来写的《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中仅列出七名参会者的姓名,其中就有刘澍德。⑥或许这种回忆性的文章因年代远隔可能记忆有误,但是在收入《赵树理文集》的赵树理在在大连会议上8月16日的发言中一开始便说“刘澍德同志的发言引起了我的一些话……”⑦似乎可印证刘澍德参加了会议。但是无论采用哪种说法,能列出姓名者都不是16人。当然这里还涉及一个作家评论家、作家如何计算的问题,即茅盾、邵荃麟、周扬、沈西禾等身兼文化官员者,有着文化部工作人员身份的黎之,与作协的工作人员唐达成、涂光群哪些算在作家评论家之内哪些不算(实际上,参会人员中很多都是兼具作家、评论家与文艺界官员双重身份),这也许也是引起统计数字不统一的原因。如果不特别强调作家、评论家的身份,参会者实际在二十人上下。
关于周扬何时到大连参加会议,相关资料有一些矛盾。侯金镜在1966年的交代材料中说周扬“大概是在8月7、8日间才到的”⑧,黎之在《回忆与思考——大连会议·“中间人物”·〈刘志丹〉》中说周扬“8月8日由沈阳赶到大连”⑨。两人的说法基本一致。但邵荃麟1966年的“交代材料”中却说“会议开始时,周扬从沈阳知道后,即在安波陪同下赶到大连”⑩,而且这种说法在茅盾的日记中可得到印证,茅盾8月2日的日记中记有“三时许,周扬、安波来访,四时许辞去”⑪,4日的日记中有“交际处布置今日乘渔轮出海观拖网捕鱼也。作协来开会的人们也应邀参加,与余同在一船者有东北局于书记、周扬、邵荃麟、安波、赵树理、周立波等”⑫。据此周扬在会议开始就到了大连,当然从逻辑上讲,在大连也不能成为肯定参会的证据,但是如果邵荃麟与茅盾叙述准确的话,周扬会议开始时就到达大连,却一直等到8月10日⑬发表讲话时才到会,似乎也不合情理,周扬在发表讲话之前,很有可能也参加了会议(当然可能不是每次都出席)。如是这样,周扬在大连会议中的实际的作用与影响可能要大得多。
另外还有沈从文与大连会议的关系。茅盾日记8月2日记有“六时赴市委等为庆祝建军节举行之宴会,与德沚同往席,设大连宾馆,约有七八桌,晤见王绍鏊等,文艺界又有顾颉刚、沈从文等。在此开会之作家亦全体参加”⑭。但是文革初沈从文就此事有一个说明:“只是最后一次邵荃麟、茅盾作总结报告,东北作协(或大连市长,已记不清楚)做主人请客,我适因政协有一批人在大连休息,才被邀请吃饭,并听了一次总结报告。邵与茅盾二人南方下江口音本来即听不懂,座位又远,所以说完以后,只懂‘要扩大写作范围’,至于如何扩大,写些什么,我都不明白。会后吃了一顿晚饭,饭后即转到另外一座大楼屋顶舞会”⑮。其中与茅盾的记叙几个不一致之处。首先是时间,按茅盾的记叙,沈从文出席的是8月2日在大连宾馆举行的宴会,但是在沈从文的“说明”中,其参与的是“最后一次邵荃麟、茅盾作总结报告”的会议。根据现存资料,茅盾做长篇讲话是在8月12日,邵荃麟则在8月14日会议结束时有一个总结讲话,因之沈从文的叙述可能不是很准确。但是从其“最后一次”的说法推断,他参加的更可能是8月14日的会议。其次是沈从文有没有参加座谈会。茅盾日记中只有沈从文出席建军节宴会的记录,但是在沈从文的“说明”中,是在参加座谈会之后,出席的宴会(从时间上看,这次宴会也不可能是庆祝建军节的宴会,似乎与茅盾说的不是同一次宴会。尽管沈从文在特定的语境中的回忆性叙述可能有许多不准确之处,但其中有某些参会时的细节性描述,而且也有关于会议内容的记忆,没有参加恐怕是写不出来的;另外,沈从文写这个“说明”是为了撇清自己与大连会议的关系,如果确实没参加,这样写岂不是自找麻烦。所以沈从文参加了座谈会的某次会议应该是可能的。
二、参会者众声杂陈的自由言说与会议的中心话语
由于当时国内政策调整的大语境,会议组织者在筹划会议时就定下了“实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出帽子、不抓辫子),让大家敞开心来交谈”⑯的基调,因之会议的氛围很是宽松、自由。参会者黎之后来有这样的描述:
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神仙会”。既无主席台、首长席,也无开幕式。十六七位知名作家,依自己的习惯用舒适的姿式,在沙发上就坐。赵树理有两点“特殊化”,一是他爱坐木板椅,在中宣部开会时,有一次我特地为他找过一次。这次他好像有时也随意坐坐沙发。二是要吃粗面馒头,在这种高级宾馆也只能特意做几个了。⑰
这样的会议形式好像有一些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艺沙龙的影子。会议的组织者似乎要刻意淡化会议的官方色彩,营造一种非正式的带有作家私下聚谈的放松随意的氛围,以此消除“反右”给作家留下的心理阴影,使其在讨论中能畅所欲言。从参会的作家评论家的发言来看,话题并不局限于文学创作,而是大量地涉及经济、政治(比如赵树理的发言谈论政治经济形势与农村现状的内容远多于文学方面)。谈论最多的是大跃进以来农村的真实状况以及对农村政策的一些思考,有些发言颇为尖锐,一些人情绪也有些激动。讨论中也有看法的分歧与争论。
但是这种众声杂陈的自由状态只是会议的一个层面。大连会议虽未如新侨会议与广州会议一样,有周恩来与陈毅这样级别的国家领导人出席,但也规格相当高,文学领域的三个最高的领导人:周扬、茅盾与邵荃麟全部参会。在当时的文艺领导体制中,三人的身份有着不同的含义: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是中国作协这一文学领导机构的权力核心的代表,作协主席茅盾是这一机构与中国文学界的象征,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则是文学管理机构接入国家管理机构的中介。三人齐聚于此喻示着大连会议实际上是中国作协发布关于文学创作的政策性话语的场域。而且通过周扬使得这种话语一定程度上成为党关于文艺的政策性言说,用涂光群后来的话说“是在贯彻中央精神”⑱。为了方便茅盾参会,邵荃麟把会议地点定在大连。⑲在会议的筹备阶段邵荃麟就几次找周扬汇报商量,会议期间也几次向周扬汇报,⑳因此不管是在会议开始时还是中途到达大连(此问题参看前文注释),周扬始终掌握着会议的进程。作为一次由作协党组书记、作协主席与中宣部副部长一起参加的会议,大连会议显然不是作家私下的聚谈,而是有其来自于文艺界领导层的会议的中心话语——这才是会议的“灵魂”。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周扬、茅盾和邵荃麟在会议上的三个长篇讲话中。
周扬的讲话是在会议的中段(8月9日或10日)发表的,讲话主要围绕“不回避当前问题”与“题材要广泛”㉑展开。周扬在讲话开头就提出“作家还是要写他所看见的,所感受到的、所相信的……忠于生活,忠于真理忠于客观事实,对党讲真话,就是党性的表现”㉒;讲话中借用陈寅恪的话“实验是可以的,但是尺寸不要差的太远”㉓批评了浮夸风气;还提出“有思想的作品都是美中有刺”,“歌颂与批评不要分割,不是那种作品专门歌颂,哪种作品只批评”㉔,“对错误缺点的批评”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㉕。对于题材问题,周扬提出农村题材可扩大到写“一百零八年的民主革命”,作家“要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观察问题。不要今天上边提出个政策就去写,明天提出个政策又去写”㉖,“大跃进要写,纠偏也要写”㉗;人物方面,“农村里不仅是写生产队长、农民可以写,技术员、气象员、小学教员、知识分子也都可以写”㉘。当然在讲话中也体现出周扬作为成熟的政治领导者的谨慎,对于大跃进后农村的真实现状,周扬又说“不一定马上写……暂时不要写,还早一些”㉙,“有些尖锐问题是不能写,不好写的,还要看一看”㉚;提出“办内刊”登载“批评性作品”、“揭露消极现象的长篇短篇”㉛,目的显然是要把反映生活的阴暗面、直面当前问题的作品的影响限制在范围很小的精英阶层之内。李洁非说周扬的讲话“非常彷徨,语意流转不定,乃至互生歧义”㉜,确乎如此。
除了在会议开始时讲的“几句开头语”㉝讨论中的零星插话,㉞茅盾在充分准备之后㉟于8月12日上午作了“两小时多些的时间”㊱的讲话。茅盾的讲话这样开头:“在听到同志们和周扬同志内容丰富的发言,我感到有很多启发,才有胆量来讲几句。”㊲在这里语义的重心显然在“周扬同志”的发言。茅盾把自己的讲话定位为此前周扬讲话的理解与发挥,这其实也是周扬与茅盾在文艺领导体系中权力隶属关系的反映。茅盾的讲话分四个部分:“关于题材问题”,“人物创作问题”,“谈谈形式方面”与“谈几篇长篇小说”。在第一部分中,茅盾尽管申明同意周扬提出的“有些题材现在还不能写”“过一个时候可以写”,但又提出“可以用侧面的方法”㊳。第二部分,茅盾对文学现状做了温婉的批评:“干部写得不少,但大部分一律用干部腔,从动作到语言都是一样”㊴;“描写知识分子很少”,尤其是老年知识分子,而且“只是表面的写,通过内心深刻的表现就比较少”㊵;“工人农民写得很多”,但“也是写两头的多,写中间状态的少,写中间状态的也有,但不是作为典型”㊶,茅盾提出这些“中间状态”的人物“还是可以作为典型的”㊷,茅盾主要是以人物的精神状态的复杂性作为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接着便用大量的篇幅以林则徐与崇祯为例分析这种复杂性;第三部分涉及问题也很多,比如小说中的人称问题、结构问题、作家生活的深度与广度问题,最后还提到拔高人物失真的问题;第四部分则具体分析了几个小说文本,这几个小说后来都被看做“中间人物”论的代表性作品。茅盾的讲话的第二与第四部分与“中间人物论”直接相关,第三部分中人为拔高人物也是当时英雄人物写作中大量存在的问题,也与“中间人物”论有间接的关系。与茅盾在会议讨论中插话的随意,时有尖锐之语相比,这篇正式的讲话显得有些拘谨、婉曲。比如在以人物的精神状态的复杂性来论述其“中间状态”的人物“还是可以作为典型的”的观点时,分析的例子是历史人物林则徐与崇祯,显然是要尽量避免对文学现状做直接的批评。分析其原因恐怕在于这是一篇正式的会议讲话,做这篇讲话时,茅盾的身份更偏于作协主席与文化部长而非会议讨论中的作家评论家;另一原因在于茅盾的讲话是在周扬的讲话之后,作为受中宣部领导的作协的领导人与需团结在党的周围的非党文化官员,茅盾的讲话须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讲话为中心而展开。
三“大连会议”中的邵荃麟
邵荃麟可以说是大连会议最为关键的一个人物。在文学史的叙述中,大连会议总是与“写中间人物”论与“现实主义深化”论联系在一起,而这两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被批判起就被叙述为是邵荃麟在大连会议上正式提出的。大连会议改变了邵荃麟的人生轨迹,其晚年的坎坷人生因之而起,并最终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邵荃麟是以三重身份参加大连会议的,即会议的组织者和主持者、文艺界的领导者、文艺批评家。会议期间,邵荃麟较为集中的发言有三次,“第一次讲话(8月2日)说明开会的主要宗旨和主要议题:‘感到农村题材最重要的是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因此确定把这作为会议主要议题’。围绕这个中心,讨论‘人物创作问题’、‘题材的广泛性与战斗性关系’、‘深入生活问题’和‘艺术形式上的问题’。第二次讲话(8月7日)只是归纳宣布了小组会议上的问题,并没有发表个人看法。第三次讲话(8月14日)也就是会议的小结”㊸。
在这三次发言中涉及“写中间人物”较直接集中的有两处,8月2日关于“人物创作问题”的发言中谈的最多,对“写中间人物”的观点表述得最为明确:
环绕这个中心问题还有什么问题?主要是人物创作问题。作品是通过人物来表现的。近来的作品,写了各种人物,创造了很多的艺术形象。一九五四年前后,概念化的东西很多。最近几年,纯粹从概念出发的,还不太多。性格化比较突出,《张满贞》《耕云记》里的气象员、《静静的产院》中的谭大婶,都各有个性。创造的人物绝大部分是先进入物:倔强的老头,生龙活虎的妇女,生气勃勃的育年。强调写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是应该的。英雄人物是反映我们时代的精神的。但整个来说,反映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两头小,中间大;好的、坏的人都比较少,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矛盾点往往集中在这些人身上。我觉得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亭面糊这个人物给我印象很深,他们肯定是会进步的,但也有旧的东西。毛主席也说,要写各种各样的人物。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这样就更丰满了,写得更丰满更深刻。只有把人物放在矛盾斗争中来写,不然性格不突出。比如林黛玉,如不把她放在爱情的矛盾中心,就不可能突出。所以,要研究人物与矛盾的关系。有些简单化的理解认为似乎不是先进入物就不典型。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这是完全错误的看法。从这个理论出发又发生拔高问题。要人物高,这就容易把人物孤立起来。㊹
另外一处在8月14日的会议总结发言中:
茅公提出“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主要教育的对象是中间人物,写英雄是树立典型,但也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㊺
另外,发言中的关于当时农村题材小说中人物性格“单纯化”㊻、“人物性格只有在矛盾斗争中表现出来”㊼、人物的典型化和英雄人物的写作等内容㊽也与“写中间人物”有一些关系,但都是关于人物塑造这一较大话题的探讨,并不是仅仅探讨“中间人物”,而且其间也没有“中间人物”的说法。
邵荃麟的发言当时并未发表,现在可以看到的文本是后来依据会议记录整理出来的。这篇讲话长达万余字,兼涉文学之内与文学之外的多方面内容,谈论“中间人物”的内容其实并不多,“写中间人物”很难说是邵荃麟讲话的中心话题。
从这一文本来看,以多重身份参会的邵荃麟,尽管会前就提出“实行‘三不主义’”,尽力营造宽松的会风,但其会议的发言依然很是拘谨与温婉,其自由度与尖锐性并未超过周扬,甚至于茅盾。“非常彷徨,语意流转不定,乃至互生歧义”用来描述邵荃麟的讲话同样准确。比如,邵荃麟在提出“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存在的,作家应该去写”“矛盾是广泛的”,除了写“群众之间的矛盾”“官僚主义也是可以写得”后马上补充“但这不是主要的”㊾。后面又说“有人认为什么都可以写,我看不一定。这与宣传党的政策有关。比如农村有些干部,蜕化成敌我矛盾,像恶霸似的,能不能写?划条线也很难,编辑也很难,可以讨论一下。总之,回避矛盾是不行的。写,是为了克服矛盾是为了教育人民。为矛盾而写矛盾,也是不行的。”㊿在谈论了描写“中间人物”“是很重要的”这一问题后,唯恐留下否定写英雄人物的重要性的印象,在紧接着谈论“题材的广阔性与战斗性的关系”时马上强调“不是提倡写小人物,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不少可歌可泣的人物。如《看愚公怎样移山》,作用很大。还有一些这类报导,教育群众,意义很大;不是写灰溜溜的,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点也要说清楚。”邵荃麟似乎始终在作家批评家与党的文化官员之间游移不定,在传统文人的为民请命意识与做“灵魂的工程师”对人民做“思想教育”之间游移不定。
在邵荃麟的几次会议发言中,8月14日的发言是会议的总结讲话,较为正式,其身份更偏于文艺界领导人,“讲的比较全面、严谨、平稳。没有特别发挥‘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等论点”。“中间人物”相关的内容主要在8月2日的发言中。比较而言,此次发言,邵荃麟的身份更偏于作家批评家。从根据会议记录整理出的文本看,这篇口语化色彩较浓的发言比较放松随意,内在逻辑也不是很严谨,文意也不是前后很连贯。尽管邵荃麟在会前对发言中的问题应该有过一些深入思考,但其中很难说没有不少内容是在较为宽松的语境中与其他参会作家批评家较为畅通的交流讨论中临时生发出来的。写“中间人物”并不是邵荃麟酝酿已久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系统的理论主张。惟其如此,应该是“中间人物”论的核心概念“中间人物”含义始终模糊。即使发起“中间人物”批判的重要文章《“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主张》中,尽管归纳出“中间人物”的定义:“是农民和工人中动摇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人,是革命性不强的人,是不觉悟或觉悟程度很低的人,是充满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精神负担’的人”,也不得不承认“邵荃麟同志自己有时也把‘中间人物’同落后人物、小人物混为一谈,并没有把界限划分清楚”。直至目下,对于邵荃麟所说的“中间人物”涵义是什么,研究者仍是莫衷一是。事实上,邵荃麟在发言中本就没有这样的界定,因之“有的说是‘自私自利的人’,有的说是‘身为群众有缺点的落后人物’,这就把落后人物包括在‘中间人物’的范围了。有的说,‘中间人物’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那就是浑浑噩噩的小人物了”,这些理解都对,都可以在邵荃麟的讲话中找到依据,但又都不对,很难说哪种更符合邵荃麟的原意。甚至《“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主张》对于“中间人物”的定义也可如是观。曾参加大连会议的唐达成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次访谈中这样讲:“主要是文艺界的一个领导把这归纳为‘中间人物论’,问题就严重了。”邵荃麟关于“写中间人物”的发言理论色彩很为单薄,不是体系性规范性很强的学术性言说,显然不是邵荃麟酝酿已久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理论主张,称之为“论”,明显言过其实,所谓“中间人物”论其实是后来批判不断升级的产物。
邵荃麟是在谈论“人物创作问题”时提出“写中间人物”的意见的。在邵荃麟的发言中,“人物创作问题”是“环绕”“农村题材最重要的是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中心问题”的问题。而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是毛泽东提出的,邵荃麟在谈论“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文学问题之前就引入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概念,发言中有大量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并且一开始就提到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逻辑上讲,邵荃麟探讨的“农村题材最重要的是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人物创作问题”的理论基础即是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当然写“中间人物”的理论基础也是这一理论。在提出写“中间人物”“是很重要的”后马上引用毛泽东的话:“毛主席也说,要写各种各样的人物。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这样就更丰满了,写得更丰满更深刻。”以此作为理论依据。另外,发言中也引用了周恩来的话:“总理说,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存在的,作家应该去写。”因此有人认为邵荃麟“写中间人物”的说法“还是非常正统的……也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很周到谨慎”,后来周扬所致的邵荃麟的悼词中也说“阐释了毛主席《讲话》的精神”,甚至有人认为“邵荃麟的话没有超出毛泽东的原意,我们还可以明确地说,这位谨慎的文学家关于‘写中间人物’的观点句句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阐释和运用”。如果从逻辑的角度看,对照邵荃麟的发言,以上说法都有很充足的证据。但是这篇属于文学领域的发言毕竟与法律诉讼文本不同,仅从逻辑分析只能获取其极为表层的含义,只有还原当时的语境把其置入,设身处地的用心去感受,才有可能理解其真正的涵义与价值。所以,有的学者把“中间人物”称作“策略性的命名”很有见地。对于这样一种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具有特殊身份的主体对于文学的言说,其语义与效应的复杂性要远大于其与主流文学理论与文学规范逻辑上是否背离。写“中间人物”的主张或许思想性不高,理论性不强,逻辑也不严密,但从深层语义与效用看,邵荃麟显然试图通过这样的“策略性”阐释以缓解官方的文学规范与作家写作自由空间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样的主张如果真能被施行,显然可在不与某些“左”的文学规范直接对抗的前提下,开拓出一些自由写作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