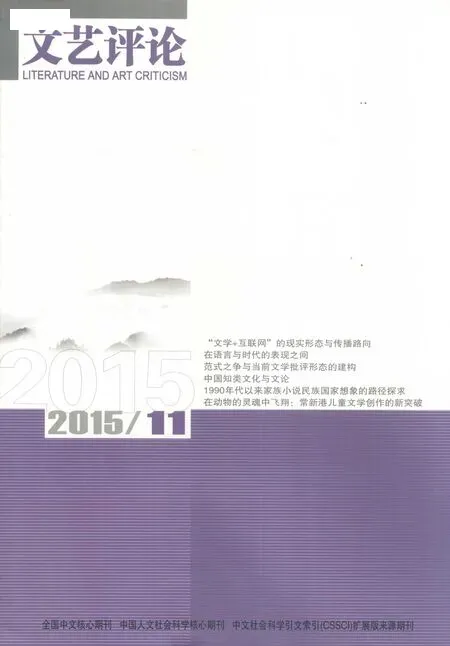宋代审美风尚视角下的花卉空间
2015-09-29吴洋洋
○吴洋洋
从整个中国文化史的发展、演进轨迹来看,两宋无疑处在历史转型之关键的过渡阶段,即从贵族文化向士大夫文化和平民文化的嬗变:一方面,正如钱穆先生在《国史纲要》中所总结的那样,宋代持续的太平景象孕育出了一种读书人自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在此种精神的感召下,中国社会由魏晋至唐前期的贵族主导,转向一种“士大夫社会”①;另一方面,由于文人士大夫大多出身平民而非贵族阶层,其所携带的平民文化基因,也随着这一阶层的崛起而弥漫到全社会,从而使两宋的文化走向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世俗性、平民性趋势。②两宋的审美文化及其历史动向,即应放置在这一整体性的历史趋向中加以考察、反思和阐释。
从某种意义上说,花在两宋士大夫和平民阶层在生活空间中的培植、设计、应用验证了上述问题。生活空间不仅包括生活中具体的物理空间,也包括人在居住环境中享有的精神空间、心理空间乃至审美空间。宋代文人将插花视为一门艺术,插花对于文人是人格修养的一部分。在花材的选择上,梅、兰、菊、莲等象征君子人格的花卉更获青睐。宋代以前花在生活空间中的应用主要还是在贵族阶层流行。“百宝栏”、“沉香阁”、“移春槛”、“金铃护花”、“锦洞天”等豪华骄纵的方式在当时并没有遭到诟病,反而引以为时尚。而在宋代,花由为贵族单独享有进入到平民阶层,成为宋人的生活方式。由于平民热衷插花,宋代鲜花的需求量惊人。在市井场所,宋人也讲求对环境的要求,出现了“花园酒店”。
1.宜居环境的营构
花本是自然之物,人工栽培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妆点人的生活环境。宋人喜欢盆景,还进一步发明了“谷板”。所谓“谷板”,《东京梦华录》是这样记载的:“以小板上傅土,旋种粟令生苗,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家小人物、皆村落之态,谓之谷板。”③如果从视知觉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对“图-底”关系加以解释,“小板”除了傅土的实用功能外,在视觉上还有底板的作用。在小板之上的部分意在召唤人们用心欣赏的“图”。“谷板”呈现的“艺术世界”,不单是自然花卉本身,更是一个“人化的自然”,这也是宋代较前代更为细腻精深之处。
宋人对居住环境的要求很高,“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④。在这里,“竹”则能起到美化居住环境的作用。而且在宋人看来,“食肉”表示较低层次的生理需要,而居住空间不但能给人美的熏陶,还是居住者生活态度、精神气质、情趣品位的外化形式。北宋文人王禹偁写过一篇《黄州新建小竹楼记》,记述了自己建小楼的经过和在小竹楼中的生活。竹楼可观山景、江景,远处风帆沙鸟、烟云竹树。在竹楼里,听雨声、雪声别有情趣。小竹楼虽然简陋,诗人从事的都是文化艺术活动。王禹偁通过小竹楼中的活动,将自己塑造成自己不慕富贵、有着良好道德和艺术修养的温文儒雅的君子形象。竹子在中国文学和文人生活中有独特的审美意义。《礼记·礼器》中将竹子与人的品质联系起来。宋代开始,松、竹、梅并称为岁寒三友,后世渐以梅、兰、竹、菊为花中四君子。可以说王禹偁借助竹子达成了抒发自己的情怀,标榜其君子品格的目的。
在花对生活环境的美化方面,宋人物尽其用、因地制宜、注重搭配,表达了讲求和谐的思想。淳熙二年前后,杨万里创作了一首名为《钓雪舟倦睡》的诗,诗前有一小序:“予作一小斋,状似舟,名以钓雪舟。予独书其间,倦睡。忽一风入户,撩瓶底梅花极香,惊觉,得绝句。”⑤此诗是杨万里在福建为官所作。当地并不下雪,他却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钓雪舟”究竟为何?“钓雪舟”取自柳宗元的诗句,“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表现了一种看似荒寒实则丰盈的美学意境。再加上书斋狭长,状似小舟,因而得名。文人为自己的书房命名,大多要抒发性情。杨万里此举颇富文人意趣,借书斋之名表达自己“独与天地之往来”的追求,瓶花在这里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诗人在书斋倦睡,抱怨梅花打扰了自己的清梦,实则是对丰富愉悦的书斋生活的委婉表达。梅花的清冷孤傲正好与“钓雪舟”的审美意味相合。如果没有梅花,或者选择了别的花材,“钓雪舟”的诗意就大大减弱了。
2.园林的实景与虚境
宋人延续了魏晋喜好园林的传统,并且与魏晋时的山水园林相比,宋人的园林大多修建于城市或近郊,生活更加便利,实现了审美性与实用性的完美结合。
花与园林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无花不成园,没有花的园林了无生趣,也是不存在的;反之园林又是赏花的主要场所,是花木种植的重要基地。宋代园林广植花木,也有所侧重,园林特色更鲜明,分工更细微了。四大名园中的宜春苑以花木闻名,是宋代君臣的赏花钓鱼之所。而另外一处名胜瑞圣园是皇室习猎之所,更像是一个动物园。北宋末年的“艮岳”是最优美的帝王苑囿。集全国之力取天下奇花异石。
花在园林审美中主要发挥两个作用:一是花木作为重要的造园素材构成了园林的主要景观,苏轼曾在《次韵子由岐下诗》中介绍苏辙的造园情况,二十一首诗,分别写了园林的主要景观:北亭、横池、短桥、轩窗、曲槛、双池、荷花、鱼、牡丹、桃花、李、杏、梨、栆、樱桃、石榴、樗、槐、松、桧、柳,其中绝大部分是植物花木,具体描写花的就有四首。花的美感诉诸于视觉,听觉与嗅觉。花可以让人们在赏园中感受到声响、光影、香味。宋人有意识地利用植物的多样色彩在园林中发挥作用,南宋的洪适在《盘洲记》一文中特别从颜色的角度强调了盘洲的花木。林逋的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就是借助梅花的影子和香气为山园增添了风雅超脱的韵味。另外园林本是空间艺术,园林中的花卉不仅为园林提供了景观,而且为园林注入了时间要素。园林在花木的点缀下,具备了四时不同的美景。洪适的组诗《生查子》提到了盘洲不同月份的代表性花卉,给园林注入了流动的、变化的美。
二是花木参与营构的景观诱发了园林的意境。园林意境是造园者将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理解,通过创造性思维,倾注在园林景象中的物态化的意识结晶,使游园者触景生情,从而生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宋代文人生活条件较为优裕,文化素养较高,相对于社会其他阶层,他们有时间、有才情追求高雅的生活空间。宋代文人不屑于追求夸奇斗富的华宇广厦,他们主要是追求自然之境。
“自然”在宋代有以下几个意思:一是有“理所应当”、“当然”之意;二是指天道的运行法则或形式;第三种意思指天地万物、自然界。在生活空间中的“自然”追求,主要侧重第三个意思。园林的旨趣之一即在居住环境中享受自然的乐趣。与魏晋时期不同的是宋人并不刻意追求将园林建筑于名山大川、真山真水之间。文人园林更多的是建筑于城市之中,在宋人及后世的意识中,欣赏自然无须远离尘嚣都市。宋人创造了所谓“坐游”或“卧游”的欣赏自然的方式,足不出户身居闹市也可以领略自然的美,生活的便利舒适与心灵的自由能够同时满足。宋代郭思的《林泉高致》认为艺术可以将自然的美景“复现”出来,不必远离尘世,也能置身于湖光山色之中。园林即给士人提供了一个可居可游的“中隐”环境。
苏轼在《灵璧张氏园记》中明确了这一观念:“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今张氏之先君,所以为子孙之计虑者远且周,是故筑室艺园于汴、泗之间,舟车冠盖之冲。凡朝夕之奉,燕游之乐,不求而足。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⑥“中隐”是宋代文人的生活理想,园林为其提供了实现理想的空间。中国文人选择在自然中寻求心灵的安慰,不同于西方人借助宗教的方式。那么园林又是使用何种手段达到自然之境的呢?当然是要借助叠山理水花木亭阁等造园形式。其中花木的作用不容小觑,以灵璧张氏园为例,用竹子、桐树、柏树、奇花异草营造了“山林之气”⑦。
3.花作为城市的重要景观丰富了市民的休闲生活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城市发展时期,北宋都城开封、南宋的杭州都是人口逾百万的大城市。城市的发展孕育出城市文化,城市文化不同于农村生活的简单质朴,推崇休闲娱乐。
时人心目中有所谓“九福”的观念:“京师钱福、眼福、病福、屏帷福,吴越口福、洛阳花福,蜀川药福、秦陇鞍马福、燕赵衣裳福。”⑧可见花在当时作为重要的生活资料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并重。洛阳是北宋的重要城市,其政治和文化地位不下于都城开封。洛阳人将赏花视作头等大事。不分士庶,无论贫富,全民狂欢性的赏花活动是市民积聚的审美冲动的宣泄。这是宋代新兴的市民阶层满足自身精神需要的体现。不仅是洛阳牡丹,扬州的芍药、成都的海棠都是当地名胜。
宋代没有公共花园,但是皇家园林和私人园林定时对外开放,供市民游玩。比如朱勔的花园“入之春时,纵妇女游赏,有迷其路者,朱设酒食邀,或遗以簪珥之属”⑨。《夷坚志》里提到“其族居姑苏有名园,当春时,纵人游赏。至三月将暮,芍药盛开,天气清和,士女群集”⑩。私人花园对普通市民开放暗含了统治者的治国之策。宋代名相韩琦在《相州新修园池记》中提到自己修建园池乃是施政策略。修建园池的目的并不为自己享乐,而是为了让州中男女老幼在游园时感念朝廷恩泽。市民的休闲娱乐活动又成了教化手段。宋代休闲活动讲求君臣同欢、士庶同乐。这是宋代社会整体呈现出平民化趋势的表现。
花与城市本来是独立的事物,但在宋代特定的城市与花卉结成了稳定的文化意象,有着特殊的文化与审美意义,“扬州芍药”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姜夔的《扬州慢》中,芍药成了扬州昔日繁华的象征,引起了词人的黍离之悲。“扬州芍药”这个意象是如何形成的?芍药如何与扬州交织在一起的?在众多花卉中,为何独独芍药脱颖而出?看似理所当然的现象背后蕴藏了怎样的因果?
扬州并非只有芍药花。扬州地处江淮平原,属亚热带湿润性气候,雨水丰沛,适合草木生长。《扬州府志》记载当地风物,多种花卉榜上有名。就文化史而言,扬州曾以琼花闻名。梅花也曾与扬州有过一段机缘,何逊是否为梅花调任扬州之事还惹出一段公案。但无论琼花也好,梅花也罢,都不如芍药与扬州这所历史文化名城深度契合。原因何在?琼花的掌故突出的是琼花天下无双不可轻移的神秘,何逊梅花的故事则在于彰显文人轻名利重情趣的风流态度,它们都缺少与扬州深刻必然的联系。在那两则故事中,并没有广大市民的参与,勾勒的只是历史上寥寥数人的影子。而“扬州芍药”则是根植于宋代扬州的本土生活的,反映出扬州的经济状况,渗透于扬州的风土人情,是宋代发达的日常审美生活与成熟的花文化碰撞融合而成的。
宋代之前也有很多名人谈论过芍药,但都与扬州无涉,到了宋代,扬州芍药才名扬天下为全社会爱重。扬州芍药的品种丰富,这在宋代的花谱中得到了验证,刘攽的《芍药谱》记录了31个品种;孔武仲列举了33个品种;王观《芍药谱》则增添了几种新品,合计39个品种。扬州有专门的花卉市场,规模颇大名品众多。除自然地理条件外,扬州专业化的花卉种植业是不可忽视的原因,朱氏、丁氏、袁氏、徐氏、高氏、张氏、都是当时有名的园户,种植规模庞大。
在宋代,扬州人以芍药花为骄傲,爱花成风,还有举办大规模芍药花会的风俗。苏轼在《玉盘盂》一诗中写道:“东武旧俗,每岁四月,大会于南禅、资福两寺,以芍药供佛。而今岁最盛,凡七千余朵,皆重跗累萼,繁丽丰硕。”⑪扬州的地方官员也借芍药花造势,《墨庄漫录》卷九记载:“扬州产芍药,其妙者不减于姚黄、魏紫,蔡元长知维扬日,亦效洛阳作万花会。”⑫美轮美奂的花卉花展扩大了扬州芍药的社会知名度,也深入到百姓生活中。
芍药高贵典雅的审美品格契合扬州富庶繁华的城市形象。扬州自古乃富庶繁华之地,到了宋代,扬州已经是屈指可数的大都市,时人称“扬一益二”。另外一方面芍药在花文化中的地位颇高,有“牡丹花王、芍药花相”的说法。在人们观念里,芍药是富贵花、吉祥花。因此“扬州芍药”就成了繁华盛世最好的图景,芍药也就成了扬州这座城市的名片。文人吟咏题诗对“扬州芍药”起到了推广作用。芍药花朵硕大,色彩绚烂,芳香浓郁,妩媚多姿,有“浩态狂香”的美誉,极富观赏价值,深受历代诗人喜爱。宋代多为著名诗人吟咏扬州芍药为其增添了魅力,在文人的吟哦中,芍药成了扬州的代名词。
综上所述,花在宋人的生活空间中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宋代文人士大夫以及他们的效仿者平民阶层成为“赏花”的文化主体,获得了日常审美的权力。这是中国文化走向平民和世俗之“下移”的重要表征,宋代是中国平民阶层整体的文化和审美素养大幅度提升的历史时代。然而仅仅以“平民化”、“世俗化”来概括两宋的文化趋向显然是不够的。花绝非最紧要、须臾不可离的物质资料,然而宋人的生活实践却将其转换为一种常行日用中不可或缺的事物,在这从“可有可无”到“必不可少”的转换机制中,蕴藏着一个深刻的生活和思想逻辑:人们的生活对物质的需求固然是基础性的、根本性的,但人在日常生活中占有的所有物质并非均是为了满足物质性的需求。换言之,花在更多时候,给宋人提供的乃是一种审美的、精神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日常生活和世俗人生的审美化和艺术化,与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所兴起的大规模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不同,后者基于一种“现代性”社会语境,以文化、艺术和审美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为技术底蕴,其所面临的问题,也是现代人在现代性语境中所面临的感性与理性、情感与精神、生活与工作、个体与群体的内在断裂和紧张关系;而两宋的日常生活和世俗人生的审美化,乃是在宋代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基础上,一种源自于传统文化内部的诗意生活、艺术人生愿望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