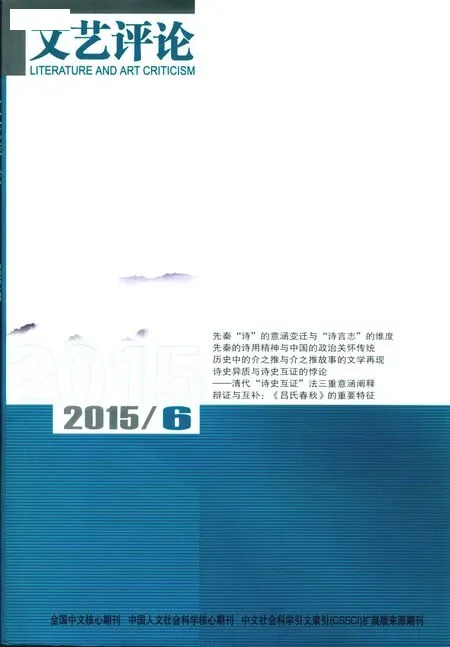汉墓神画:别于文字神话的另一神话系统
——以“雷公出行图”为例
2015-09-29张倩倩
张倩倩
汉墓神画:别于文字神话的另一神话系统
——以“雷公出行图”为例
张倩倩
学术界习惯上称含有表现神话内容的汉代画像为“汉墓神画”。对于汉墓神画的研究,大都集中在考古学领域内,从神话艺术精神和神话美学价值角度对汉画进行系统的研究首推李立先生的《汉墓神画研究》,该书从考古、民俗、神话等多角度分别对西王母、龙璧等多种神话形象进行了系统研究,内容翔实,论证透彻,资料丰富,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但受到体例的限制,仍然缺少对汉墓神画艺术精神的宏观把握。文章拟以“雷公出行图”为例,通过比较汉及汉前文献记载与汉墓画像石记载的风雨雷电等气象神灵的异同,试图揭示出汉代墓葬神话拥有自己独立于文字神话系统独特的精神内涵。可以立论,主要鉴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与先秦时期分散、尚未定型的神话形象相比,汉墓神话中许多神话形象已经趋向稳定,反映了汉人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独特心理和思想意蕴,这些具体的神灵形象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汉代神话文化精神,在整个中国传统神话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其次,以“雷公出行图”为例,主要是由于“雷公出行”在神话类题材的画像石在较为常见,分布集中,具有典型性,且特征明显,题材内容较为确定,在学界争论甚少,可以此为切入点,探讨汉墓神话的特点。
再次,人们普遍认为汉墓神话可以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因此,在研究汉代神话时,把汉墓神话当做文字材料的补充,与文字记载相符的就当做辅助材料应用,不相符的干脆避而不谈。实际上,汉墓神话与分散在史论、文赋等文献材料中的神话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形成有别于文字神话的另一神话系统,自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第一,汉墓神话与文字神话存在的目的不同,上古中国很少有《山海经》这样集中保存神话材料的著作,大多数的神话则零碎的散落在各种史学、策论及诗赋之中。史论中的神话形象是为其说理论证服务的,文赋中的神话形象或为铺张扬厉的夸张,或为一吐心中之块垒。汉墓神话则不同,它们依附于特殊的丧葬艺术而存在,一切神话形象都是为墓主人及其后人服务的,趋利避害、守灵护尸是丧葬文化最根本的宗旨。目的不同导致了二者存在的方式及神话形象的塑造上区别甚大。第二,创作者的知识文化修养不同,对于前代典籍的注重程度不同,史论文赋的作者大都为受过正统学术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可以对上古典籍中的典故形象信手拈来,并加以发挥。画像石的绘刻工匠则主要来自民间,他们的神话材料大多来自当时的民间故事和口耳相传,有些神话形象与前代典籍的记载差别很大。因此,把汉墓神话从先秦两汉文字神话研究中独立出来进行探讨,自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雷神出行图”是汉画像石常见的神话题材画像,根据蒋英炬、吴文祺主编八卷本《中国画像石全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目前被拟认定的以“雷神”为中心的气象神灵出行图有15幅,其中有11幅已确定为“雷神出行图”,尚有4幅画像石的内容是否为“雷神出行”还在探讨之中,已确定的图像大都分布在山东、江苏等东部地区。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有一幅“雷神出行图”。画左部有一车,以运气为车轮,车上前后各树一鼓,舆中乘坐一人,右手持槌作击鼓状,车前有五人用两根绳子牵引车子前进,车后有一人张口吹气。画右部有一双首龙拱成的“龙门”,龙门之下有一人举锤持凿,双脚踏在下面跪伏于地的人背上,似欲凿击跪伏之人,龙门正上方,有一人一手举鞭,一手持一罐,罐口朝下作倾倒状,龙门左右上方又分别站立一人,皆举锤持凿作敲击状。画中部还有一人持一高领壶,一人抱一大翁。画面空白处饰以缭绕的云气,肩生双翼作嬉戏状的小仙人。山东安丘汉墓前室的一幅“雷神出行”①画像左边雷神肩有双翼,右向端坐于雷车上,车有翼,车上树三建鼓,雷神执桴击鼓;车前二羽人拽绳牵引雷车,车下卷云缭绕。左端六神人执锤、椎行走。车前上方一女执鞭,车后五女执鞭,当为电母。车后还有三人顶盆、执壶、吹气,当为雨师和风伯。右边,刻一日轮,内有三足鸟,日轮周围缠绕飞云,右端刻五仙人。
各地出土的“雷公出行图”从画面内容上直观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风、雨、雷、电诸神大都同时出现在同一画面中,它们分工明确,可以凭借各自持有的物品或形体神态判断各神的属性。二是以雷神为主神,雷神手持锤桴或坐于树有建鼓的雷车之上,或置于多个雷鼓之中,其余诸神皆为雷神之从属,或为其开路,或在后面跟随护送。三是虽然也有少数气象神灵头部为动物的形象,但绝大多数的画像石中诸神都是以人的面目出现。四是以祥云和日月等形象告诉观者画面叙述的地点是天界而非人间。与先秦两汉的文献材料相比较,画像石中以雷神为中心的气象神灵在形象和功用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具体表现在:
一、神灵地位的差异——从众神平等到以雷为尊
根据文献记载,先秦时期的雷神只是众神之中的普通一员。居于水中,《楚辞·招魂》:“旋入雷渊。”王逸注云:“则回入雷公之室。”从《山海经》言其“出入水则必风雨”看,雷神出行应该有风伯和雨师同行。《周礼·大宗伯》言:“以槱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提到大宗伯的职责包括祭祀风伯和雨师,却没有提到雷公。屈原《远游》:“左雨师使经待兮,右雷公而为卫”,可以推测先秦时期雨师与雷公的地位差不多是平等的。而汉画像石中的雷公地位是相当高的(在图像的命名上就可以看出来),在“雷公出行图”画像石上只要是雷公与其它神灵一起出行,总是处于最中心的位置,而且只有他可以独享雷车之尊(在汉代车子是权势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前边有雨师开道,其形象为顶盆或执壶,后面有风伯护送,通常蹲下张口吹气,另外还各种神兵仙将左呼右拥一起陪同出行。事实上,在正统的汉代史料及诗论材料里,“雷神”依然继承了先秦时期众神平等的特点,而在一些谶纬书籍里,这种情况则悄然发生着变化。
西汉首开“以雷为尊”先河的是济南人伏生。《艺文类聚》卷十三引古本《尚书·洪范五行传》:“雷于天地为长子,以其首长万物,与其出入也。”“夫雷,人君像也”。即伏生之后,在整个社会谶纬之风兴盛的背景下,一大批纬书相继问世,把雷神附会成人君,争先恐后拔高雷神的地位,终于雷神成了有着“黄龙之体”的轩辕黄帝,《河图帝纪通》:“黄帝以雷精起”,《春秋合诚图》:“轩辕星,主雷雨之神”。根据《史记·天官节》的记载:“轩辕,黄龙体。”《正义》:“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黄龙之体,主雷雨之神。”这样就把雷神和圣主黄帝统一起来了。反过来看,雷公与黄帝的统一,雷公独尊地位的形成是汉代儒家政治等级制度学说与谶纬学说结合的必然结果。汉代统治者借助人们对雷公的崇敬心理来竭力宣传君权的至高无上,以巩固自己的政权;雷公借助汉代统治者的推崇获得了自己位居众神之上的崇高地位。②有了“神君”就必然得有“神臣”,经常与雷公同时出现的风伯、雨师等众神便成了首要选择,《山海经·大荒东经》:“蚩尤做兵伐黄帝,......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韩非子·十过》中亦有:“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的记载,黄帝在雷公得胜后自然而然地将风伯与雨师收归到自己门下,出行时由他们相伴而从,替自己进扫与洒道。两汉谶纬之书始是民间一些方士和巫师制造出来的,随后部分儒生与方士的结合造成了汉代社会浓郁的宗教气氛,将自然界的偶然现象神秘化,但总体来讲,这种神秘文化还是来自民间的。墓葬艺术与死生之事很容易吸收这种神秘主义宗教文化,汉画像石艺术正是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表现在“雷公出行”上就是原来地位平等的风雨雷电诸神变得主次分明,等级森严。《史记》《汉书》《淮南子》等书中也收录了一些气象神灵有关内容,但并没有如上述谶纬文献记载,可见作者对于这种说法是不赞同的。由此可见汉墓神话与先秦两汉史学、策论及诗赋神话相差甚远,而与谶纬神秘文献有很大的关联。
二、主神外在形体的变化——从兽神到人神;内在灵魂的变化——从神到人,从人到仙
一般认为风伯来源有两个:中原地区是由星象祭祀发展而来,《独断》:“风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兴风。雨师神,毕星也。其象在天,能兴雨。”其外形尚不清楚。楚地则以飞廉为风伯,屏翳为雨师,这种说法在汉代及后世影响甚大。《楚辞·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王逸注:“飞廉,风伯也。”洪兴祖补注:“应劭曰,飞廉神禽,能致风气。晋灼曰,飞廉鹿身,头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淮南子·真》曰:“真人骑蜚廉,驰于外方,休于宇内,烛十日而使风雨”,高诱注曰:“蜚廉,兽名,长毛有翼。”《汉书·武帝纪》有“还,作甘泉通天台、长安飞廉馆”,晋灼注飞廉曰:“身似鹿,头如爵(雀),有角而蛇尾”。《三辅黄图》:“飞廉,神禽,能致风气者,身似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总之,汉人注释或文献中的风伯是鹿身雀头的怪物形象。同样是汉人的作品,画像石中的风伯形象大有不同,他是一个力士形象,通常身材高大威猛壮硕,或跪坐或奔跑,兴风的工具是自己的口舌,而非飞廉之翅,为了增强风力有时会使用喇叭状的工具。此时的风伯已经脱离了动物的外形,完全人性化,除了四周围绕的云气和云车可以表示其为神仙以外,从外形上看几乎和世间的凡人并没有什么两样。如河南省南阳市王庄画像石墓中的风伯画像,“在图画下部有四神人,头发皆披向一旁,怀中均抱一大口罐,罐口向下倾水行雨,为雨师。图右有一巨神,赤身踞地,张口作吹嘘之状,此神应是风伯。”③
再如雷神。《山海经·大荒东经》云:“东海中有流波山,其上有兽…….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山海经·海内东经》云:“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原始雷神形象为夔,是龙身而人头的兽形神,居住在流波山,出入于雷泽之中。雷神之腹即为鼓雷声是由雷神自鼓其腹而成的。汉初的《淮南子·地形训》载:“雷泽有雷神,龙身人头,鼓其腹而熙。”很明显受到《山海经》的影响。而到了汉画像石这里,雷神的形象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不仅失去了龙身,而且其所击之腹亦被汉代的“建鼓”所代替。画像石中的雷神多为男性,尽显力士形象,也有少数雷神着女装,头戴花束,穿戴汉代服饰,敲击汉代建鼓,乘坐于雷车之上。正如王充所言“图画之工,图雷之状,累累如连鼓之形。又图一人,若力士之容,谓之雷公。使之左手引连鼓,右手褪椎若击之状,其意以为雷声隆隆者,连鼓相扣击之意也。”学术的传承是依靠文献进行的,很明显王逸、刘安等学者具有较高的学术修养,对于前代典籍如《山海经》《楚辞》等是相当熟悉的,他们进行的神话文献注释、搜集及整理工作,主要是借助这些文字材料进行的。既然没有人真正见到过鬼神,当然前人的相关记载是最权威也是最可靠的工具,重古轻今是古代包括两汉多数文人一贯的作风。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字神话系统中,雷神的形象一直没有得到统一,《酉阳亲俎·前集》说:“猪首,手足各两指,执一赤蛇啮之”;《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一说:“豕首鳞身”;《铸鼎余闻》卷一说“大首鬼形,白拥项,朱犊鼻,黄带,右手持斧,左手恃凿,运连鼓于火中”;《集说诠真》引《搜神记》说:“色如丹,目如镜,毛角长三尺余,状如六畜,头如猕猴”;《唐国史补》说:“其状如彘,秋冬伏于地中”;《夷坚丙志》卷七说其形如奇鬼,“长三尺许,面及肉色皆青。首上加帻,如世间幞头,乃肉为之,与额相连”。其体形或龙、或人、或兽;脸形或人头、猴头、猪头、鬼头。而汉画像石的作者则不然,他们对前人记载并没有兴趣,甚至从来也没有阅读过,进行绘画创作的依据是当时的民间传说或自己的主观想象,艺术幻想空间更自由,形式也更活泼。从这点来看,也许画像石中的神话符号更符合汉代人民大众心中的神话形象,也更接近汉代神话发展的本来面貌。
在外在形态上,汉墓神画中的雷神等自然神灵完成了从兽形到人形的转变,共同保佑墓主人在阴间生活能够风调雨顺,羽化登仙。在内在精神上,他们同样经历了从神到人,从人到仙的转变。
汉代神话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神性的消解,人性的突出。如果说上古文字神话多显示为对某种自然或社会现象的幻想和解释,那么到了汉墓神画中则多了明显的功利色彩。可以说,所有的汉墓画像都是围绕着墓主进行创作的,不管是描述墓主的阴间生活也好,教育墓主后人也好,中心点便是“人”,它们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墓主或其后人服务。从这一点来讲,画像石上所有的“神”便都成为了“人”的神,成为了“人”想让它们成为的样子。汉墓神画中的神祗形象众多,有创世始祖伏羲女娲,众神之王的西王母,有叱咤风云的气象神灵,英勇善战的护卫神灵,镇宅守墓的祥禽瑞兽神灵,也有勤于农事的蚕农神灵。这些神灵一方面继承了原始神话中奇特虚幻的特点,显示出超越世俗的奇特本领,另一方面也正在向拥有者大汉精神的世俗的人生转变。两汉时期的气象神灵已经从高高在上、神不可触走向世俗人间。他们拥有人的喜怒哀乐,拥有人世间的社交程序和礼仪文明,嘉祥武氏祠画像石中有一幅河伯鱼车图,在河伯出行车前后各绘有一人,分别“执笏跪迎”和“执笏恭送”,俨然一副人间送往迎来的场面。嘉祥武氏祠画像石“雷神出行图”龙门之下有一下跪之神人,其卑躬屈膝的姿势堪似汉代社会地位卑贱者对待尊者的样子,这正是在儒学独尊的两汉时期社会制度等级森严的象征。
汉墓神画世俗化演变的过程,也是神祗形象神仙化的过程,其结果是神话形象的超能本领,世俗人生的人间百态,同样具有突破生死极限的永恒生命。神仙思想在上古时代出现甚早,《庄子·逍遥游》云∶“藐如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秦汉是仙话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淮南子·览冥篇》∶“乘雷车,服应龙,络黄云,前白蜿,后奔蛇,浮游逍遥,道鬼神,登九天,朝帝于灵门。”由此可见,雷车云车是升天成仙的重要工具,画像石中的雷公诸神正是坐在云气缭绕的车子上,带领墓主的灵魂走向仙界。这里有神人驾车,有云气相随,有神怪拥护,是一个融水里、人间、天上为一体的仙界。“俗世生命的‘死’在这里变成了生命‘转化’的契机,而这种生命转化的最终结果,便是俗世生命‘死’后的再生和永生——仙”④。
三、主神功利性目的的转变——从对自然社会现象的幻想解释到幽都冥府的守护神
远古神话本来的作用是表现远古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用来解释某种自然或社会现象,表达先民征服自然,变革社会的愿望。大自然变幻莫测,各种灾难令人恐惧,因此在自然神之中既有阴险恶毒的凶神,助纣为虐的恶神,更有使风雨失调、惑乱天下的瘟神,这在《山海经》等文献中有多处明确的记载。
在早期文字神话系统中,风神与雨神虽然偶尔也具有温柔细腻的一面,但人们似乎更倾向于描述其恶性。《淮南子·本经训》:“尧之时. .....大风、封豨、俢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缴大风于青丘之泽。”此外它还是蚩尤作乱的帮凶,《山海经·大荒东经》载:“蚩尤做兵伐黄帝,......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韩非子·十过》中亦有:“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之语。即使是在两汉时期的文献记载中,风伯和雨师大多也是一对被“呵斥”的反面角色,司马相如《大人赋》:“时若暧暧将混浊兮,招屏翳,诛风伯,刑雨师”,杨雄《河东赋》:“叱风伯于南北,呵雨师于西东。”由此可见此二神为“恶神”的象征是被两汉文人普遍认可了的,他们很可能了解过先秦文献关于风伯雨师的记载,并从中受到启发。
上古时期,人们普遍畏雷电,认为“雷电为天怒”,雷电巨大的轰鸣声及伴随而来的狂风暴雨,是上天对于人们行为的不满而施以的惩罚,正所谓“惧天怒,畏罚及己也”。两汉时期,这种对雷电自然现象的幻想受到“天人合一”和道教思想的影响在文人那里得到加强。《集说全真》引王充《论衡》:“盛夏之时,雷电迅疾,击折树木,败坏蚀屋,时犯杀人”,“其犯杀人也,谓之阴过,饮食人以不洁净。天怒击而杀之。隆隆之声,天怒之音,若人之响嘘矣。”在人们心中雷电是具有神秘威力的神灵,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有“主天之灾福,持物之权衡,掌物掌人,司生司杀”的职能。
汉墓神话中气象主神的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风伯、雨师跟随雷神一起出行,“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养成万物,有功於人”。他们不仅协助雷神为墓主带来祥风好雨,而且可以护送墓主人的灵魂跟随神车出行顺利平安。雨师持大罐或神壶做倒倾状,向人间倾洒雨水;风伯往往口吹仙气,护送一行队伍平安顺风前行。他们的降临预示着墓主在阴间将会过上风调雨顺、丰衣足食的生活。风神除了能够给人们带来和顺之风,还具有助人升仙的宗教功能。山东长清县孝里铺村孝堂山石祠东壁顶端画像石上有风伯吹屋图,“画中间刻一亭子,亭内二人,一坐一立,亭左外边一羽人对亭站立,左边有一身体硕壮之人双手捧管状物向亭子吹风,亭子右柱被风吹断,屋顶倾斜。此吹气之人即风伯。风伯之后又有羽人执器物者相随从。”⑤
汉代纬书中常有大风“发屋”的记载,《易纬通卦验》云:“立夏,巽气至,巽气不至,则城中多大风,发屋扬沙,禾稼尽卧。”墓葬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画像石上的大风发屋,绝对不是对于风伯带来巨大灾异现象的简单描述,而是想借助风伯口中的巨大风力,吹掉墓室的顶部,使墓主的灵魂能够早日顺利升天成仙。这也是汉墓神话与谶纬神学紧密联系的一个例证。画像石中的雷神也不再具有破坏性,代尔替之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威严尊者形象,他或坐雷车,或置连环鼓之中,从容不迫地击打着擂鼓,在众神呵护下依然具有神秘的威力,但他却不再是恐怖得让人难以接近的恶神,他所威慑的对象由世间之凡人变为地府之鬼魅,为守候墓主的尸体和灵魂竭尽全力。汉墓画像石中各种神话形象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墓主人在阴间的守护神,它们或与鬼蜮搏斗,保护墓主尸身免受鬼蜮侵扰,或引领墓主人走向通达具有永恒生命的天国之路,又或者保佑墓主在阴间生活的吉祥如意,富贵荣华。在各种神灵从“恶”走向“善”的过程中,也体现了汉人避害趋利、化凶为吉的心理特征。
总之,神话发展到汉代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开始脱离原始的野蛮和生硬,迈向文明的进程,走向世俗的人间,并与两汉独特的文化相融合,以自身独特的气质丰富汉人的生活,塑造着中华民族风华正茂的大汉灵魂。汉墓神话是汉代神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汉代神话,不能离开汉墓画像石,也不能仅仅把画像石作为神话研究的辅助材料。除了气象神灵形象之外,汉墓神话中的其他神话形象与文献记载也存在相当差异,将其作为一个独立于文字神话之外的另一系统加以阐释似乎更为妥当,在此本文权作抛砖引玉之用,期待学界有更为深刻广泛的研究。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50100)】
①蒋英炬《中国画像石全集·山东汉画像石卷一》,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②随着这种有目的的人为的操纵,雷神的地位进一步上升,以至于到了魏晋人那里,连伏羲都成为了雷神之子。郭璞注《山海经》引《河图》:“大迹在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
③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市王庄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5第3期。
④李立《汉墓神话研究:神话与神话艺术精神的考察与分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⑤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考古研究所编《山东汉画像石选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