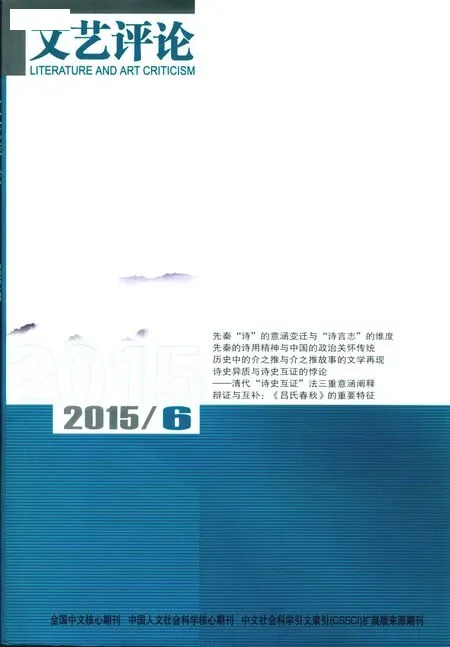诗史异质与诗史互证的悖论
——清代“诗史互证”法三重意涵阐释
2015-09-29王晓燕
王晓燕
古典诗学的现代阐释
诗史异质与诗史互证的悖论
——清代“诗史互证”法三重意涵阐释
王晓燕
清人对“诗”与“史”两种不同文体的差异有较为明确的认识。早在清初,学者张英即对作为考订的“史”和作为想象测度的“诗”进行了比较,他认为:“注者,征引事实,考究掌故,上自经史,以下逮于稗官杂说,靡不旁搜博取,以备注脚,使作者一字一句,皆有根据,是之谓注。意者,古人作诗之微旨,有时隐见于诗之中,有时侧出于诗之外,古人不能自言其意,而以诗言之,古人之诗,亦有不能自言其意,而以说诗者言之。是必积数十年之心思,微气深息,以与古人相遇。”①对于作为文学文本的“诗”而言,作者的显隐、意象的汲取、意蕴的象征、读者的差异等因素都是导致其复合性阐释生成的原因。古人作诗之微旨有时隐见于诗中、有时侧出于诗外,不能明喻其意方以诗代之。从作者写诗的不可言,到说诗人的多解,加上时间久隔,今人要与古人相通,甚是艰难。因此,考据再严谨,论证再精辟,都始终无法解决诗歌阐释多义的问题,无法得到唯一性的阐释结论,以考据的方法进入诗歌的解读,也就永远成为了一个悖论的循环。事实上,不仅是诗,小说等文学文体亦是如此。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有过类似的评议:“《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②忠于史实的史书不可杜撰,而小说这样的文学性文本却可以依据人物自身的情态加以合理的虚构与想象。实际上,清代文人比任何其他时代的文人都清楚“史”与“诗”的分野及诗史无法确证的显明道理。清人曾给出诗“不可解”的结论:“盖赋必意在言中,可因言以求意;比兴意在言外,意不可以言求”③,“诗有可解,有不可解乎”④。兴意在言外,“求言”就不能成为“得意”的绝对方法。然而,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却以唐代史实与杜甫诗歌相互参证的方式确立了诗史互证的阐释方法,对清代诗歌阐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寅恪曾对此作出了明确的总结:“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歌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见之也”⑤,指出了清人采用“诗史互证”法阐释诗歌的状况。那么,清人为何要提出“诗史互证”的方法呢?一方面,在“诗史互证”的论断里,“诗”非指一切诗歌,而是与历史相涉的诗,正如朱鹤龄所言“指事陈情,意含讽喻,此可解者也”⑥。此处之“事”,是诗人所生存的社会历史政治场景及诗人在世时已有的文献材料。在《愚庵小集》中,朱鹤龄进一步指出“注子美诗须援据子美以前之书”⑦,这便确定了“史”的范畴,使“以史证诗”的方法趋向合理。
另一方面,以史证诗的考据学者对诗歌的阐释有明晰的逻辑依据,即诗人因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或政治场景的触动,借助比兴手法、喻象系统将其“意”寄托于“诗”、融汇于“史”。在文字狱严酷的历史环境下,清人以此为前提充分肯定了涉史事、有寄托的“诗”在张扬他们索求兴趣方面的价值,所谓“比兴意在言外”、“寓意深而托兴远”⑧,“使读者知比兴之所起,即知志之所之也”⑨,甚至将比兴看作是因“本朝之治忽理乱”而作⑩。也就是说,只要用考证的功夫充分把握一首诗中的比兴含义(公共系统或私人系统)与史实依据,就能够追根溯源,找出并确证诗人的本意。因此,在“诗史互证”的过程中,考证的功夫与比兴寄托的功能同等重要。再者,虽然自汉至清,比兴寄托精神在诗歌系统中的原型意义已经逐渐消解,尤其是六朝文学对传统诗学精神产生了颠覆性影响,唐人陈子昂曾言“文章道弊五百年”,“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逶迤颓靡,风雅不作”⑪,正描述了此间的变异。至晚唐李商隐,则将原型意涵的约定俗成一变而为私人话语,将公共语境再度消解,比兴象征也就随之变得愈加多元化与多义化。此后,以才学为诗的宋人也反对以兴寄为解诗的唯一依据,主张明诗之大旨,将比兴寄托的诗学精神摈弃。黄庭坚《大雅堂记》对“比兴寄托”的穿凿附会作了严厉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⑫明人更是在心学的包裹下讲究“水月镜花”式的文本解读,将比兴寄托传统彻底抛弃。清代考据学背景下“诗史互证”阐释方法的提出,正是基于上述“诗”之范畴的界定、史以诗存的逻辑依据、比兴寄托功用的重塑和创作意旨索求的兴趣。以此为前提,“诗史互证”法自然具备了三重深层意涵。
一、必善读史学者,始可注书——拨“反诗史”观与映“乱世”之实
诗歌阐释以“史”为据的作法始于北宋学人,如任渊注黄庭坚诗,更多地关注用典而非其他艺术内涵和修辞技巧。南宋学人则举起反才学、反议论的旗帜,高扬诗人情感的抒发及诗歌艺术性的传递,当代学者周裕锴称之为“反诗史、反意图、反求实说”⑬,这一评价是中肯的。再观明人对“诗史观”的反叛,一方面基于对诗歌辨体的认识。《明史·文苑传》曾指出明代文学复古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口号的理论基石之一就是辨体,辨诗文之别、诗与非诗、诗与史之别、诗歌时代之别;另一方面,明人的反诗史观则受到南宋诗学及阳明心学影响,在审美观念上异趣,杨慎甚至直接对“诗史”观念发起了冲击:
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夫六经各有体,《易》以道阴阳,《书》以道政事,《诗》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后世之所谓史者,左记言,右记事,古之《尚书》、《春秋》也。若诗者,其体其旨,与《易》、《书》、《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⑭
杨慎对宋诗的鄙薄是显见的,他所持“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的立场也极其鲜明,原因可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从诗歌的本质上讲。六经各有体亦各有用,《诗》与《易》、《书》等截然不同,根本则在于“《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诗之成其为诗的精髓也正在于“意在言外,使人自悟”的灵性,宋人将诗与性理混为一谈,不足为道;其二,从宋人学杜的渊源上讲。杜诗“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实不应该。舍本逐末、偏其一端也只是学杜诗的末流。因此,杨慎不仅明确反宋诗,并且直接否定了宋诗及宋代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作法,否定了将“诗史说”立为最崇高诗学理念的宋代诗学观。这一立场实代表了明人“反诗史”观之新的诗学建构。另一方面,受到心学对诗歌阐释的影响,明人多强调“镜花水月”式的反阐释解读,对“史实”文字干预诗歌创作进行了反驳。复古派王廷相在著名论文《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中即对杜甫等人的长篇叙事诗发难。王廷相所列举的杜诗皆以叙事为主,“漫敷繁叙,填委事实”,抒情只是事实的附着,对于持“水中之月,镜中之影”审美观的明人来说,这种诗的确是不能被接纳的。所谓“变体”、“旁轨”,就是不入正路,是对诗学精神“最上乘”的背弃。再如明代诗评家黄清老(子肃)论《诗法》时曾言:“是以妙悟者,意之所向,透彻玲珑,如空中之音,如水中之味,虽有所知,不可求索。”⑮同为明代的学者、文艺批评家胡应麟也主张“诗贵清空”,标举“兴象风神”⑯。明代《诗境总论》的作者陆时雍也认为诗应“转意象于虚圆之中”⑰。明人谢榛在《四溟诗话》卷一中甚至提出“含糊”⑱的观点来反对写实。诸多言论都指向了诗歌超然“意”解的旨趣,巧妙地回避了诗与史的关联。然而,水月镜花式的诗歌阐释方法,虽然有其审美优势,获得了独立的作品意境,以空灵、超越的灵感对应诗歌韵味悠长、复义多解的特质,但其流弊则是主观化而导致易忽视诗歌创作的客观因素,甚至出现臆解、误解的现象,造成诗歌的误读。宋明心学的开山祖陆九渊早有洞见,在《语录》中就批评有些读书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⑲的弊病。
针对这一问题,明末清初学人对明代的“反诗史观”进行反拨,这既是对主观阐释流弊的指认,又显示其欲将“诗史互证”作为反映与记录世事的途径与方式。清人常将苏诗与杜诗作为诗史的典型相提并论,认为二者都是乱世的投影,这是绕过了明代与南宋,直接北宋诗学旗帜的典型。清人韩崶在《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首序曰:
盖少陵丁天宝之季,出入戎马,跋履关山,感事摅怀,动有关系,非熟于有唐一代之史者,不能注杜集也。长公(苏轼)亲见庆历人才之盛,备知安石变法之弊,进身元祐更化,卒罗绍圣党祸。凡所感激,尽吐于诗,其诗视少陵为多,其荣悴升沉亦与少陵仅以奔行在者异。少陵事状颇略,而长公政绩独详。⑳
杜诗正因其以天宝之乱为背景,亲身经历,感事述怀,才成就其“诗史”的美名,后世若非深谙唐代历史者,绝不能恰当地注释杜诗。同样,苏轼亦因其亲历熙宁变法,身陷元祐党锢之祸,几经沉浮,有所感怀,方才尽吐于诗。二者之诗都是“史”的承载,亦是“史”的投影。二者分别在宋代与清代被称为“诗史”(实则苏诗在宋代并未被称为诗史),理在情中。又如清人姚文燮注李贺诗时同样提出:“必善读史学者,始可注书;善论唐史者,始可注贺”㉑,将鬼才李贺之诗定位为“史”。明末清初学者朱鹤龄评李商隐诗:
吾观其活狱弘农,则忤廉察;题诗九日,则忤政府;于刘蒉之斥,则抱痛巫咸;于乙卯之变,则衔冤晋石;太和东讨,怀“积骸成莽”之悲;党项兴师,有“穷兵祸胎”之戒。以至《汉宫》、《瑶池》、《华清》、《马嵬》诸作,无非讽方士为不经,警色荒之覆国。此其指事怀忠、郁纡激切,直可与曲江老人(杜甫)相视而笑。㉒
则将李义山诗与乙卯之变、太和东讨、党项兴师等史实密切联系起来,旨在“讽方士为不经,警色荒之覆”,指出其记录“乱世”的史心可与杜少陵共论。以上几例都说明清人对“乱世”之史的重视,并将与之相关联的诗也纳入了“史”的范畴。从这一层面上讲,清人对“诗史互证”法的认同,实际上是借“史”之实以反拨明人主观空疏的学风,更是视之为明末清初历史大变迁史实的印证与记录。钱谦益《有学集》卷一八《胡致果诗序》言:
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曹之《赠白马》、阮之《咏怀》、刘之《扶风》、张之《七哀》,千古之兴亡升降,感叹悲愤,皆于诗发之。驯至于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曰“诗史”。唐之诗,入宋而衰。而宋之亡也,其诗称盛。谓诗之不足以续史也,不亦诬乎?㉓
“以诗续史”、“诗之义本于史”的观点相当鲜明,即是说作诗者乃借诗之体发千古兴亡之叹。这一观点也是清人以诗存史的逻辑依据,而钱谦益本人在注杜诗时采用的正是这一立场与方法,“钱注杜诗”的问世实可视作北宋文人注杜的延续,只是钱氏在宋人的基础上更力求还原杜诗的史实原貌,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方面将诗文作为史料补证历史,另一方面则以史释诗,疏通诗意,将“知人论世”之功发挥到极致。著名史学家洪业在《杜诗引得序》中这样评价“钱注杜诗”于清人“诗史互证”传统中的重要地位:“清代为杜诗之学者,鲜不受钱谦益《杜诗笺注》之影响”㉔,陈寅恪更是一针见血地指明了钱氏的这一阐释方法:“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斋牧所为之详尽者,尚未来之见也。”㉕
有学者认为,在我国文学传统中,“文学”定义是建立“语言(文)及其美化”和“不要虚构,要真实”㉖两大基本点上的。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的几篇序和《西厢记》评点里,把六经、诸子、史书和诗歌等抒情文学都归为“文章”,直言在作文的基本方法上,以上文章完全一样。在古人看来,诗歌中为了表达情感、反映现实而使用的“比兴”等手法亦是“表达真实的一种方式”㉗。纵使我国传统文学在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出现了“虚构”的成分,但仍不失与之伴随的“真实”,“虚构”并非只是“真实”的对立面,而是在保有部分“真实”前提下之“语言(文)及其美化”的延伸和要求。过于强调“诗”与“史”之区别,沉溺于“反诗史”观,实则遮蔽了传统文学诸样式及其观念的内在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诗”虽与“史”异质,但并非不可以“诗”映“史”,正如钱穆所言杜甫的诗把“他的生活片段,几十年来关于他个人、他家庭,以及他当时的社会、国家,一与他有关的,都放进诗中去了”㉘。因此,明末清初之反拨,实有必要。
二、词不可径,有曲而达;情不可激,有譬而喻——阐释者的主体建构
晚唐孟棨在其《本事诗》“高逸第三”中评价杜甫“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㉖精炼地指出了所谓“诗史”应该具备的两方面条件,一是叙事详赡,正如孟棨所指“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是其“毕陈于诗”的前提;二是“推见至隐殆无遗事”,以诗记史,这也正是杜诗在“当时号为诗史”的真正原因。同样的,从证“诗”的角度上讲,“诗史互证”法一方面赋予“诗”以更大的历史关联。清人相信,诗歌都由特定的历史事件触发并寄托诗人特定的情志。诗不仅是作者曲尽其意的特殊产物,其“意”也包含着本朝的兴衰治乱及其所引发作者情感的激荡变化。如清代吴江诸生朱鹤龄在笺注李商隐诗时就提出:“古人之不得志于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遥情于婉娈,结深怨于蹇修,以序其忠愤无聊、缠绵宕往之致。”㉗安徽桐城人姚文燮在注李贺诗时也说“吾谓读古人书者,必以心心古人,而以身身古人,则古人见也。人不能身心为贺,又安能见贺之身心耶?故必善读史者,始可注书;善论唐史者,始可注贺。”㉘在姚文燮看来,不知唐史即不可注贺诗,唐史成为了李贺诗阐释的必备前提。而清初钱谦益所注杜诗更是几乎将写景类小诗一笔带过,只专注于杜甫与唐代政治相关的诗篇阐释。诸多事实证明,从阐释层面上讲,“诗史互证”并非对诗质简单粗劣的定位,而是清人醉心于借助诗歌比兴寄托的功能揭示原作者基于某种政治原因而深藏于其中的隐秘指涉,实际上亦可视作清代汉族文人在亡国之痛和严酷的文字狱面前,隐藏自我身心所找到的精神归宿与寄予。更为重要的是,在清人看来,诗之比兴并非随意的选择或者偶然的构建,而有内在之必然,清人陈沆言:“词不可径也,故有曲而达;情不可激也,故有譬而喻焉。”㉙清人程梦星对李商隐诗作注时,将这一观点作了说明:“诗须有为而作也。义山于风云月露之外大有事在,故其于本朝之治忽理乱往往三致意焉。”㉚“有为而作”、“大有事在”实际都指向了对“治忽理乱”的兴寄。再如,姚文燮在《昌谷诗注自序》中也表达了同样的心绪:
贺不敢言,又不能无言。于是寓今托古,比物征事,无一不为世道人心虑。其孤忠沉郁之志,又恨不伸纸疾书。故贺之为诗,其命辞、命意、命题,皆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藏哀愤孤激之思于片章短什。言之者无罪,闻之者不审所从来。我未必尽如贺意,而贺亦未必尽如我意。第孤忠哀激之情,庶几稍近。㉛
姚文燮明确指出“孤忠哀激之情,庶几稍近”,李商隐于唐朝陷入牛李党争。姚文燮本人在清代遇“三藩之乱”亦卷入政争,出于命运的相似,为李商隐注诗,自然有在历史中寻找与建构自我精神的意味。他注李昌谷诗,非以乾嘉考证之法为宗,而以“意取”为尚的用心也正在于此:
余第以少陵之有注与昌谷之无注适等,固常不惮浩繁,尽取诸体而阐之以当日作诗之意。其与姚子初不相谋而实若相谋,同于意取之旨也。今姚子昌谷注行,人之读昌谷注者,岂无因昌谷注而并想余之谓少陵注?㉜
寻求精神上的契合,可以说是清人“诗史互证”更大范畴上的旨趣所在。从这一层面讲,以史证诗阐释的实质,就是在诗史中寻求阐释者主体性精神的建构。
值得注意的是,清人注杜诗者多有特殊的身份。比如朱鹤龄为杜诗、李商隐诗作注,作诗“颇出入二家之间,而寄兴深远,能不着掩其神韵”,顾炎武“心摹手追,惟在少陵。非如七子学唐,徒慕躯壳”。朱鹤龄与顾炎武等人都是清初“惊隐诗社”的重要成员,而此社正是清初著名的遗民诗社之一。据谢国桢《顾炎武与惊隐诗社》中的相关考察㉝,惊隐诗社虽与清代其他一般意义上的诗文社一样举行诗酒雅会一类社集活动,但其社旨之中有一项特殊的规定,即是每年定期祭祀屈原、陶潜与杜甫。《秋室集》卷一《书南山草堂遗集后》即记载:“岁于五月五日祀三闾大夫,九月九日祀陶征士,同社而至,咸纪以诗”,社员叶继武《九日寒斋同逃社诸子祭陶元亮、杜子美两先生诗》中更有:“龙沙嘉会结寒盟,修祀先贤荐菊觥。离乱家乡移酒郡,晋唐史历祭花名。一时共得南山意,千载同怀北极情。但愿久长持晚节,萧萧门外任浮荣”㉞之句。诗社成员之间彼此砥砺,以先贤“久长持晚节”的不渝忠贞,在清初“萧萧门外任浮荣”的环境下保持自身节操与故国之思,也借此体现其“借诗存人,人不得滥;以人重诗,诗不必尽工”的诗学精神与遗民志趣。故而,此中的注释者就不能不将注诗作为寄托自身怀抱的一种方式,借唐音而述己意。正如袁景辂《国朝松陵诗征》引朴村云:“惊隐社中人皆前朝遗老,绝意进取,藉诗歌以写其怀抱,往往愁苦之言多,和平之音少,独若耶居上风调格律悉本唐人,高者胎源刘文房,次亦近许丁卯,于社中独雅音。”借助诗歌文本的阐释而寄托怀抱,正是此中的真意所在。总之,无论是诗从史出的阐释思路还是诗史互证的阐释方式,都是以作者为中心,是主体精神世界建构的重要形态。
三、史重褒讥,其言真而赅;诗兼比兴,其风婉以长——诗教观复归的潜意图
将诗与史、尤其是政史密切联系,是中国传统儒家诗教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根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记载: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使基之也,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㉟
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请观周乐,从《周南》、《召南》、十五国风到《小雅》、《大雅》,季札对每一种音乐都联系其政治现实进行了评价,诗乐与政通的思想已露端倪。孟子教人读诗之法:“颂其诗,读其书,知其人,论其世”㊱,做到“以意逆志”,“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㊲。知人论世的思路与季札相同。汉代《毛诗序》进一步概括为:“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㊳,可将此视作“诗史”论的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因此,若从政教层面上讲,“诗史”观念首先蕴涵着先秦以来儒家诗教的文化精神,将内圣之学与修身成人相结合。虽然初唐陈子昂曾在其《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疾呼“文章道弊五百年”、“兴寄都绝”㊴,实则唐代白居易在新乐府运动中继续发扬这一诗教观为“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史书,务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㊵。北宋欧阳修同样指出“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所以至之鲜也。”㊶“诗史”的内涵与社稷、世道、民生相联系,成为时代历史精神的具体展现。从以“诗”证“史”的角度上看,或可将“诗史互证”法视作乾嘉学者把“诗”“泛史”化、意欲重树儒家诗教观的一种努力与尝试。清初宣城文人施闰章在其《学余堂文集》中前后矛盾的言辞,正显示出其重立儒家诗教观的意图:
古未有以诗为史者,有之自杜工部始。史重褒讥,其言真而赅;诗兼比兴,其风婉以长。故诗人连类托物之篇,不及记言记事之备。传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然作史之难也,以孔子事笔削,其于知我罪我,盖惴惴焉;昌黎为唐文臣,起衰弊至言史官不有人祸必有天刑,引左丘明、司马迁及崔浩、魏收等为戒。诗人则不然,散为风谣,采之太师,田夫野夫可称咏其王后卿大夫,微词设讽,或泣或歌,言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其用有大于史者。杜子美转徙乱离之间,凡天下人物事变,无一不见于诗,故宋人目以诗史,虽有讥其学究者,要未可概非也。㊷
施闰章已经意识到诗与史在叙事形态上的区别,诗是“连类托物”,史是“言真而赅”、“记言记事之备”。但为了说明杜甫诗歌“以诗为史”的价值与渊源,故又将之与“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及孔子笔削《春秋》寄寓“微言大义”联系起来,从叙事功能、写作目的上寻求诗、史的契合点。相应的,施闰章还列举杜甫的家学渊源来论证其具有“史官的诗学使命”。那么,他为何在分清诗史泾渭的同时又急于将二者并论呢?细究起来,这前后矛盾的观念和作法,并非源于认识上的误区,而恰是清人凭借“诗史互证”法的再阐发、重新确立“诗教”观的意图所在。清代仁和学人王文诰在其《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自序中说到“诗史互证”的本质时提出,让“诗”与“史”,甚至与“经史”贯通互融,彼此发明,实现“文以载道”的目的:
乾隆庚寅,诰七龄矣,从塾师章句读。会有求贷于先君者,已而以《文忠公诗文集》为报。先君举以授诰,且诏曰:“异日汝与经史相发明也。”诰谨受而藏之。㊸
在此处,所实现的文学文本与经史文本的相通,不仅仅是中国旧有的“文本互涉”阐释观念的作用,更是本于经籍类书中所包涵的“文道”思想对一代又一代的文学阐释者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南朝理论家刘勰在其《文心雕龙·原道》篇中就曾指出:“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前圣创制典礼,孔子阐述义训,文章的写作没有不推求自然之道及其精意的;因而“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㊹,自然之理要靠圣人以文章彰显,天下亦要靠文辞以鼓动,文辞之大、其用之深也正在于此。这一理念在唐宋儒家中间不断延续,“文以载道”思想在根底上蕴含着诗教观的命理,无怪韩愈《题哀辞后》言:“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道也。”㊺其弟子李汉更言:“文者,贯道之器也”㊻,北宋周敦颐诚以“文所以载道”之论而尽述其志。文道观自唐而明虽然几经周折,数度阐释,最终在明代以“文者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㊼的言论而走向极端。然而,清人的路数似与此不同。虽然文学的政教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深刻地影响着文人,清人似施闰章之流亦时有提及。但是,毕竟清人笔下的“文”与“道”,已非固有内涵所能诠释,个中翕然包蕴着“知我罪我,惴惴焉”的主体建构与“田夫野夫可称咏”的匹夫使命,更有“天下人物事变,无一不见于诗”的辑史意识。可以认为,诗教观在清代的回响,是传统文化的深刻沉淀,更是文人于“萧萧门外任浮荣”环境下“一时共得南山意,千载同怀北极情”心灵力量的回声。
综观有清一代士大夫对“诗史互证”命题的有关阐释,绝不仅仅局限于文体领域的探讨与论争,更是对明人“反诗史”观偏激性的驳斥与对清代世情的印证,同时亦是清人借助诗歌文本的阐释寄托怀抱的重要方式与表现形态,当然也包含着在辑史意识、匹夫使命与主体意识构建前提下之新诗教观念的复归。可以说,清人赋予了“诗史互证”以崭新的复合式意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611731)】
①张英《问斋杜意》,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页。
②陈曦钟等《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③⑩㉚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024、2034、2034页。
④⑥⑦㉒㉗朱鹤龄《愚庵小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01-302、301-302、464-467、305-306、306-307页。
⑤㉕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827、933页。
⑧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影印松桂读书堂藏版1979年版,第1页。
⑨㉙陈沆《诗比兴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⑪㊳㊴㊶㊶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30、119、141、172页。
⑫黄庭坚《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7页。
⑬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5-288页。
⑭杨慎《升庵合集》卷137,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第二卷,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599页。
⑮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十五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年版,第138页。
⑯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页。
⑰⑱㉖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20、1403、1184、15页。
⑲陆九渊《象山语录》,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版,第419页。
⑳㊸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19、28页。
㉑㉘姚文燮《昌谷集注》卷首姚文燮自序,王琦《李贺诗歌集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9、369页。
㉓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㉔洪业《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8页。
㉖㉗张法《文艺学·艺术学·美学——体系构架与关键语汇》,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5、77页。
㉘钱穆《中国文学演讲集》,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70页。
㉛㉜陈治国《李贺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4页。
㉝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200页。
㉞叶振宗《吴江叶氏诗录》,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上海书店2004年版,第186页。
㉟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9页。
㊱㊲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14、302页。
㊷施闰章《学余堂文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㊹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15页。
㊺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9页。
㊻全华凌《清代以前韩愈散文接受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
㊼宋濂《宋学士全集》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