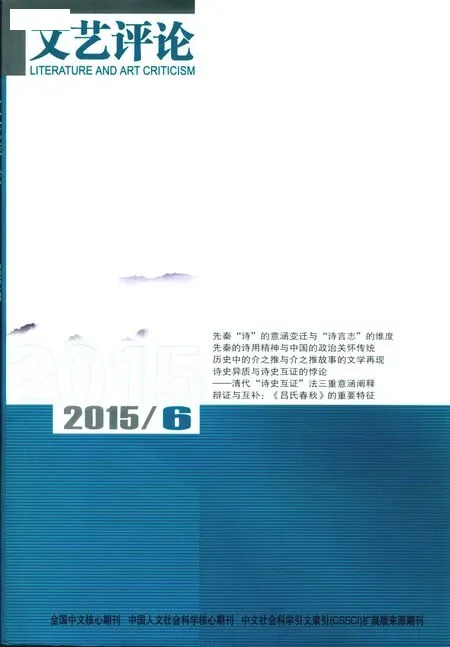历史中的介之推与介之推故事的文学再现
2015-09-29孙文起
孙文起
古代文学理论发微
历史中的介之推与介之推故事的文学再现
孙文起
一、问题的提出
介之推(或介子推)传说在流传的过程中衍生了很多异文、异说,这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更是值得深究的文学现象。以往的研究,从文化的角度多会将介之推传说与节庆民俗联系起来,如裘锡圭先生《寒食与改火——介子推焚死传说研究》一文,即在介之推传说的文献梳理中探讨了寒食节及改火风俗的起源。这种传说的文化追溯,目的在于寻找节庆风俗的历史渊源,研究的兴趣点在传说的文化意义。而从文学的角度入手,则会专注于介之推传说所依据的史实及后人增饰的情节,此类研究试图将史实与虚构分开,还原传说衍变的历程,方法上多少受到《古史辨》一派“层累造成中国史观”的影响,如张勃《历史人物的传说化与传说人物的历史化——从介子推传说谈起》,即在介之推传说增饰的情节中,寻找历史的真相与口传创作的事实。传说的节庆文化背景透露出传说在历史中的影响,而将传说情节的衍变放在叙事文学的视阈中考察,则勾勒出史学叙事与文学萌发的关系。
正像许多早期传说一样,不同文本对介之推传说记载的差异,使得文献的整理成为各种研究的前提。从文本异文中可以找寻节庆文化的起源,也可以勾勒出传说衍变的历程。然而,文献整理的意义不仅在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介之推传说至少还可以提出两点追问:一是传说异文出现的原因,或者说是传说衍变的话语背景;二是不同类型的文献在文体特征上对传说衍变的影响。
通过文本记载的差异可以更加客观地探寻传说发生的历史原貌,避免文化研究对于传说本体的疏远。以往的传说研究容易将记载传说的各种文本当作单纯的文献资料,从而忽略了各种文献的文体性质在传说衍变中起到的作用。传说的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往往相辅相成,在一定的历史话语背景和文体形式下,传说叙事的由简到繁、由实到虚的过程会丰富历史与文化的双重意义。
二、《左传》、《史记》中的介之推
介之推其人最早见载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僖公二十四年即公元前六三六年,当时晋文公重耳周流天下十九年,终在秦国帮助下回到晋国。复国后,晋文公“赏从亡者”,然而“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左传》详细记载了介之推和其母亲就此事的一段对话:
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汝偕隐。①
这段话的字面意思不难理解,“介之推不言禄”是他不愿“贪天之功”。在此之前,《左传》记载了重耳与其舅父子范“沉璧以质”的故事,“二三子”实际上是讽刺重耳随臣变相邀功的行为。介之推不愿贪功“遂隐而死”,而后“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②,算是对这位忠臣的补偿。
《左传》有关介之推的记载仅此而已,其中传达的信息主要是介之推随重耳流亡,归国后不得封赏而归隐,文公后悔莫及,遂以田地追封。因此,若除却那段母子对话,“介之推不言禄”实际上是不得禄而隐,这似乎更近人情。然而《左传》的记载使介之推成为士人品行的榜样,如同伯夷、叔齐的故事一样,种种夸张、演绎之说附着其上,以至于司马迁《史记》中的介之推较《左传》,已增益了许多富有文学色彩的情节:
是时介子推从,在船中,乃笑曰:“天实开公子,而子犯以为己功而要市于君,固足羞也。吾不忍与同位”,推曰:“献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开之,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曰是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隐,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此乎?与汝偕隐。”至死不复见。介子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曰:“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文公出,见其书,曰:“此介子推也。吾方忧王室,未图其功。”使人召之,则亡。遂求所在,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③
《史记》的这段文字基本取自《晋世家》,引文之前,叙重耳、子犯“沉璧以质”,内容与《左传》所记略同。介之推讥笑子犯还璧,大意合于《左传》,但情节有演绎的成分。介氏母子对话,《史记》则全取《左传》。介之推从者所赋“龙蛇歌”不见于《左传》,应是司马迁参考秦汉诸子作品而加,此在下文将有详述。至于文公所封“介山”应在霍山以北,超过了当时晋国的势力范围,因此,封介山之说也是后人附会而被《史记》所采。
史实中的介之推一事究竟如何,涉及到如何看待《左传》、《史记》这两段史料的问题。据王和先生的《左传材料来源考》,《左传》的史料来源有两个,一是“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的私人记事笔记”;二是“是取自流行于战国前期的、关于春秋史事的各种传闻传说”④。晋公子重耳遭骊姬之乱而流亡,直至复国,前后历经二十余年,《左传》对于这段传奇经历的记述主要集中在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其中,僖公二十三年记重耳流亡列国,二十四年记重耳复国后的几桩轶事。作者打破编年体例,集中记述了公子重耳从流亡到复国的全过程,说明其在这段史料的掌握上应比较充分。值得注意的是,僖公二十四年记载了重耳归国后的几桩轶事,除介之推不言禄之外,还包括重耳与子范沉璧以质、寺人披请见、重耳拒见竖头须等。这些故事颇富传奇色彩,并且被有意识地安排在一起,可见当时流传着不少有关重耳归国后的传闻轶事,这些传闻轶事或流传于民间,或记载于史官笔记,于是,可供《左传》采录的史料就十分丰富。
介之推其人不过是重耳随从,以此小人物能入史必因非常之事。介之推的非常之事在于他有功不得赏的事实,更在于他“不受禄”的慷慨之辞。但正像《国语》骊姬夜泣的故事受到质疑一样,《左传》既言介氏母子“偕隐”而死,那么,介之推和其母的对话又从何来?显然,为介之推赢得声誉的这段对话带有传说色彩,而不能完全被看成史实实录。
介之推有功不得禄的故事涉及到君臣伦理关系,因而备受关注。尤其是在春秋战国“士”阶层崛起的背景下,介之推的遭遇给士人留下太多演绎的空间。《左传》与《史记》所载介之推一事有史实的成分,也都有演绎的成分,因为无论《左传》的作者还是后来的司马迁,存在于他们那个时代的史料——包括传闻和前代史官笔记——都意味着一种历史的存在,史家不能漠视这种存在,于是有关介之推的传说进入了史书。但是,史家又希望为事件寻求合乎历史逻辑的解释,因此《左传》采录了介氏母子的私密对话,司马迁在组织有关介之推史料时,也加入了自己的推理:
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尽行赏,周襄王以弟带难出居郑地,来告急晋。晋初定,欲发兵,恐他乱起,是以赏从亡未至隐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禄,禄亦不及。⑤
《左传》所记重耳出亡时的随臣不过五人,并不见有介之推,可知介之推充其量是重耳微臣,其地位自然不比先轸、子犯,迟获封赏似在情理之中。况且,重耳复国并非一帆风顺,《史记》提到的“修政惠民”、“周王告难”等事件分别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四、二十七年)所载,司马迁将其糅合一处,目的是为了解释介之推不得禄的原因。
司马迁依据史实所作的合理推断弥补了《左传》记载的缺失,也让演绎过的介之推传说更符合历史的逻辑。更重要的是,这种演绎得到了史家的认可,它意味着历史传说可以在符合历史规律的前提下虚构情节,而不会背上“怪、力、乱、神”的指责。
三、秦汉诸子作品中的介之推
介之推的“不言禄”很容易让人想起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这类表现士人气节的故事在秦汉诸子中颇受欢迎。孔子曾称赞过伯夷、叔齐乃“古之贤人”,司马迁《史记》也不顾史料匮乏将伯夷置于列传之首,同样,《左传》中介之推不言禄的故事,也被诸子作品繁衍出很多新的情节,例如:
昔者介子推无爵禄,而义随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韩非子·用人》)⑥
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庄子·盗跖》)⑦
晋文公反国,入,介子推不肯受赏,自为赋诗曰:“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露雨膏泽,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悬书公门,而伏于山下。”文公闻之,曰:“嘻,此必介子推也。避舍变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万。”或遇之山中负釜。问焉,曰:“请问介子推安在?”应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见,而欲隐,吾独焉知之?”遂背而行,终身不见。(《吕氏春秋·介立》)⑧
《韩非子》、《吕氏春秋》约成书于战国之末、入秦之前。《盗跖篇》或说非庄周后学所作,但其成篇时间应与《韩非》、《吕览》相去不远。据此,可知《左传》所载“介之推不言禄”的故事在战国后期至少演绎出四段情节:
1.介之推“割股奉君”。此事不见于《左传》,但《韩非》、《庄子》均有记载。其中,《韩非》所记出于《用人》篇,割股奉君的故事在其中用以阐明君主用人之道;《盗跖》篇以伯夷、鲍焦、尾生、介之推等故事为例,说明忠义之行“离名轻死”,自残伤身。《用人》、《盗跖》篇的立意与“割股奉君”的故事主旨无关,但它并不妨碍诸子引以为据。这种言说方式无疑是功利的,然而,许多传说故事却借此成为诸子论说的材料,幸得保存,其中包括割股奉君一事。在介之推传说衍变的过程中,割股奉君情节的衍生是介之推“忠君”形象的延伸,其目的在于突出介之推的功劳,而愈显他的委屈。然而,这段晚出的情节颇受后人青睐,《韩诗外传》卷九的记载已呈现出后出转详的局面:“晋文公重耳亡,过曹,里凫须从,因盗重耳资而亡。重耳无粮,馁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后能行。”⑨里凫须其人在《左传》、《国语》均作“头须”,重耳出亡时,曾“窃藏以逃”,背叛重耳,重耳归国后不计前嫌接纳了他。“头须窃藏”本为文公复国后轶事之一,与介之推并无关系,二者的衍生与融合与其说是好事者所为,不如说是由介之推不得禄所引发的君臣伦理冲突,在更广的范围形成的共鸣。
2.介之推所赋《龙蛇歌》。《吕氏春秋》存介之推所赋无名四言诗,诗以龙蛇喻君臣,讥讽文公忘旧臣之功。全诗语言整饬,是较为成熟的四言之作。《乐府诗集·琴曲歌辞》存《士失志操四首》,题晋介子推所作,又引《琴集》、《琴操》作解题如下:“《士失志操》,介子推所作也,一曰《龙蛇歌》”(《琴集》);“文公与介子绥(即介子推)俱遁,子绥(子推)割腓股以啖文公。文公复国,咎犯、赵衰俱蒙厚赏,子绥独无所得,乃作《龙蛇之歌》而隐”(《琴操》)⑩。需要说明的是,《龙蛇歌》本为先秦古诗,其立意在为介之推不得禄而鸣不平,但作者未必是介之推,正如《采薇操》、《箕子操》题以伯夷、箕子所作,实际上不过是无名诗人借古人以显己作。《龙蛇歌》之名首见于汉末《琴操》,《淮南子·说山训》曰“介子歌龙蛇而文君垂泣”⑪,《龙蛇歌》、《士失志操》都是后人补题。刘向的《说苑》、《新序》均存有该诗,但语句出入较大,以至于《乐府诗集》录介子推《士失志操》四首,文字均不相同,经查对,应分别引自《说苑》、《琴操》、《新序》和《史记》。据《琴操》、《乐府诗集》,可知《龙蛇歌》在汉代已被琴曲,汉代文献对该诗记载的不同,反映的是该曲歌辞的不同。
3.文公访求介之推。据《吕氏春秋》,介之推归隐后,文公曾宣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万”,又云山中“负釜人”告诉文公使者介之推不愿出山。这些文字并不见于《左传》,且事迹飘渺,颇富文学色彩。笔者认为,《吕氏春秋》中关于介之推记载的很多文字应是战国士人增益,其中,文公以“爵、田”访求介之推,非常符合秦国重赏罚的风气,而动辄曰“上卿”、“百万”又合于战国士人口吻。至于山中“负釜人”,或为无名隐士,或为介之推本人,均强化了介之推的隐士形象,从而为后世《列仙传》的创作提供了素材。由于文公的“求”和介之推的“隐”易于演绎发挥,文献对于此事记载也呈现出后出转详的局面,例如刘向《新序》云:“文公使人求之不得,为之避寝三月,号呼期年。诗曰:‘逝将去汝,适彼乐郊,谁之永号。’此之谓也。”⑫这其中,夸张、虚构的成分已很明显,特别是引《诗经·硕鼠》为介之推明志,深深地讽刺了文公。
4.介之推抱树而焚。此事关系到寒食节起源,自然是关注的焦点。裘锡圭先生《寒食与改火》一文,认为寒食节起源于民间“改火”习俗,与介之推焚死的传说无关⑬;也有论者以防火解释此传说的起源。有关节庆民俗的探讨已甚周详,本文不再赘述,现就该传说的文献记载先作简要梳理。
“抱木而燔”的记载见于前文所引《庄子·盗跖》,此外,《楚辞》的一段文字也值得关注:“介子忠而立枯,文君寐而思求。封介山而为之禁兮,报大德之优游。”⑭“封介山而为之禁”对应《左传》所载“晋侯求之(介之推),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此句尚好理解,需要说明的是前一句“介子忠而立枯”。“立枯”即焚死,据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解》等解释,应指介之推抱树而焚,其故事梗概大抵是介之推归隐后,文公访求不得,遂焚山欲求其出,但介之推宁死不出,最终让文公一错再错。《庄子·盗跖》提到“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与《昔往日》之说相近。
关于《昔往日》的作者和创作年代向来争论不休,据王逸所说,屈原创作《昔往日》“陈言未终,遂自投也”⑮,这种解释自宋人魏了翁《鹤山渠阳经外杂抄》便质疑声不绝⑯,因此,将“抱木而焚”说定为战国末至秦汉间较为合理。
汉代的几种诸子作品对此故事均有所涉,其中,《韩诗外传》云“鲍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⑰,西汉桓谭《新论》云“太原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子推故也”⑱。西汉末刘向的《新序·节士》对此事记载较为详细:“文公待之(介之推),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谓: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⑲由此可见,所谓介之推“抱木而焚”的故事应为战国士人增益,将介之推不言禄“夸张”为宁死不受禄,无疑彰显了战国士人作为独立群体的自尊和气节。
以上所举是诸子作品中介之推传说情节的四段增益。相较《左传》、《史记》,子书中的介之推传说繁复多变,在这些纷繁复杂的逸闻异说背后,值得玩味的是诸子作品的言说方式及其价值取向对传说衍变的影响。首先,诸子散文以“譬论”说理,又无史乘家法的拘谨,因此许多“丛残小语”改头换面,穿梭于各家之言,司马迁将《伯夷列传》置于群传之首而广遭诟病,诸子便不会有此遭遇;其次,介之推的士人身份与诸子有着天然的共鸣,子书中介之推传说情节的增益,大都围绕着介之推的忠贞和他遭遇的不公这两大主题展开,这关系到士阶层的道德操守和群体利益,因此会引起士人演说的兴趣,构成传说衍变的话语背景。
要之,《左传》、《史记》等史家作品在记载介之推传不言禄的故事时已杂取传说,史官在处理不同性质的史料时加入了合理的推理,使得该故事增益的情节成为史实;诸子作品由于没有史家传统的束缚,它能够本着说理的需要广采众说,介之推传说也因此在秦汉间得到极大地丰富。介之推传说所蕴含的君与臣、忠贞与回报等问题触及了封建纲常关系,因而易为人所论道,这是传说衍变生生不息的动力,也构成了传说的话语背景,而史传、诸子以其各自文体的特性,为传说的衍变创造了外部条件。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210093)】
①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8页。
③⑤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62页。
④王和《〈左传〉材料来源考》,《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
⑥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45页。
⑦王先谦《庄子集解》,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29页。
⑧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2002页。
⑨⑰屈守光《韩诗外传笺疏》,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823、31页。
⑩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34页。
⑪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
⑫⑲庐元骏《新序新注新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823页。
⑬裘锡圭《寒食与改火——介子推焚死传说研究》,《中国文化》,1990年第1期。
⑭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
⑮王逸《楚辞章句》,《四库全书》(106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4页。
⑯魏了翁《鹤山渠阳经外杂抄》,《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1页。
⑱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十五),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49页。
江苏省高校基金项目“叙事传统视域下的先秦两汉故事研究”(编号:2014SJB382);江苏师范大学基金项目“早期小说史视阈下的先秦两汉故事研究”(编号:13XWB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