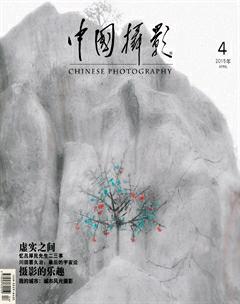从摄影的观看到图像的“拓扑”
2015-09-24海杰
海杰



蔡东东对拍摄的喜爱开始于1998年还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时他主要拍摄一些部队训练的场景。退伍后,他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做了一个以商业摄影为主的摄影工作室;一年后的2003年,他毅然转向职业艺术创作,其时探索了很多方向,但拍的最多的还是自己的生活。2006年是他的转折年,基于长时间的思考和对于摄影理论及图像生产理论的阅读,他开始转向对于图像生产及起源方面的创作实践,他的《镜子》系列中的一张就是这方面的体现:他本人站在水中,拎着一块长镜子,身边围着的少年们对着镜子做出拍照时胜利的手势。这个举动在蔡东东那里,是有着特别的隐喻:“那是一块古希腊时期的石雕,雕的是一个男人举着杯子在向一个女人要水,那个男人仿佛一个皇帝,又或者是一个乞丐,女子也姿态优美,讨水仿佛是一个仪式。”这个讨水的仪式在摄影中被他置换成向镜子做出手势的仪式,这个仪式在他那里,是和“摄影者和被摄者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
蔡东东对图像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知能力。所以,“事实”这回事,在别的人那里,是题材,是主食,是不吃会饿死人的东西。但在蔡东东这里,事实,通过图片来要挟他控制他,是无效的,同时,他要考察和利用这种控制和要挟的行为。
这一点,在前文所说的《镜子》系列另一张作品里体现得很明确:他裸体拿一面长条镜子,在河畔,旷野中行走,风景在他的镜中匆匆掠过。镜子在这里给观者一种可以“进入”的体验,但这个体验实质上只是一种“假进入”的隐喻,通过这个隐喻的设置,蔡东东把现实立刻切换成了魔术剧场,他使观众进入到一种虚假的幻象中去。镜子本身具有制造虚假空间的能力。因此,蔡东东把这一功能也引入到《光的入侵》之中,用来探讨图像在观看、介入和审判等权力性议题。
这一讨论在他的装置作品《酷刑》里有更为激烈明确的延续:两张酷刑现场的照片被挂在墙上,地上摆放各处的捆绑的枯枝跟照片上的场景形成视觉上的对应,不远处的木箱上,放置着一张中医人体穴位图,这挂图之上的一只眼睛图像诡秘地窥视着观看这个场景的人。这场景中对于“惩罚”的观看和“医学凝视”透露出蔡东东基于图像的哲学回溯与考察。而他正在朋友合作的艺术计划《刑具》也似乎是这一向度的延伸。
在越来越多的实践里,蔡东东都在尝试通过各种介入和干预,进而对图像的各种学科维度进行深度的认知,不管是利用挪用和词源学(射击与拍摄同源)等当代艺术的指认性修辞来探讨图像具有审判功能的《腊月初八》,还是针对消费社会到处可见的“游客凝视”而调转镜头进行身份实验的《台阶旁的摄影师》,抑或是以书写和翻拍唐代诗人贾岛的《寻隐者不遇》这首处处都显得模糊不具的诗来轻取图像与文字的边界这一议题,而这一举动在2006年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里早有征兆——他用左手食指指向《创世纪》里那句人尽皆知的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镜头逐渐拉近,似乎混沌初开。只是这开启是由文字完成还是图片完成,观众未可知。
正是这种从《寻隐者不遇》开始的模糊性和开放性,开启了他的创作的另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他尝试开拓作品的社会公共性和参与性,策划了一些艺术计划和项目,并将这些艺术项目所获得的认识再次传导到他对于图像的认知和处理上。
他2014的新作利用自己平时拍过的一些所谓的“废片”进行扩展,他在暗房中手工洗印出它们,反复阅读,然后动手将其本身的信息和意义进行处理,激发出新的意义空间。他的处理方案有如下:利用图像符号本身具有的属性进行语意的联想、符号的嫁接、直觉的诱导、视觉的捣乱、媒介的位移。表现在材料上,他的尝试体现在对于照片做划线涂抹、编织、折叠、堆积、撕扯、遮挡、打磨、拼贴、卷曲、灼烧、镂空、翻转等干预性动作。蔡东东拒绝接受图像自成一体的意义,他将这种干预行为进行到极致,使图片从它天生的平面优势和意义自恰中被唤醒。
这种图像实验与著名的拓扑学原理产生了一种有趣的对应。拓扑学(Topology)被称作是在19世纪末兴起并在20世纪中迅速蓬勃发展的一门数学分支,而这个学科也常常移用到其他领域。所谓的拓扑,其实是一个图形几何的概念,用最简单的例子说,就是一个橡皮圈,只要别拉断,不管你怎么拉伸和扭曲,那么它依然是一个圆圈,但这种拉伸的过程则引发了新的意义。这种模式相当于一种图形体操。著名数学家庞加莱(Poincar e)所做的拓扑变换实验更加强化了拓扑学的想象空间,比如,他将一个两端由两个圆环相扣的线条在不拉断封闭的圆环的前提下,通过拉伸和变换形成两端有两个独立圆环的线条,由此,人们总结出拓扑学上的“同胚”和“等价”概念。这就产生了几何图形意义上的空间转移和新的伸展行为。如今随处可见的网络、曲面、结、覆盖等日常对象,也成为拓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从这个层面来讲,蔡东东的创作实验就是一种拓扑学的图像实验,他所有做出的动作都是基于“同胚”,以那些多年来拍摄的照片为基础和核心,进行不同的干预行为,制造出一系列的图像奇观:在《同时》里,我们看到一个人同时从男女洗手间走出这一矛盾而幽默的情景叙事,令人手足无措:在《一棵树》里,他将明胶卤化银照片卷成一个桶,似乎成了一个立体的树,这一棵树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还是只是原有图像的信息代表?在《垂柳》中,他将风吹起的垂柳风景翻转90度,使飘起的柳枝垂下来,刻意接近其“垂柳”的命名:他将两个男人的肖像照片有意剪切,然后进行交叉编织,在不丢失任何画面的情况下,最终形成马赛克图像;在《卷起的路》里,照片中一条即将有警车行驶的路被人为撕开卷起,但没有扔掉,这卷起物成了臀车行驶的障碍;他将坐在床上的裸女实体照片向左翻卷,遮蔽了裸女的身份信息;在一张黑白照片里,汽车观后镜里却是一个注视着你的女孩。
作为一个图像的“麻烦制造者”,蔡东东对图像结构的了解和利用,恰恰表明了,他的创作与拓扑学的深度勾连,将平面二维的图像通过以上行为改造成立体的图片装置,但他没有完全改变原有图像的信息主体。这相当于拓扑学上的著名双人脱困游戏:两个被结成死扣的绳子栓死且绳子相互交叉的男女,最后在不割断绳子不解开死扣的前提下成功脱困。蔡东东的创作也是基于一种脱困的欲望,对于图像既有意义的逃离,但他是借助于这些既有意义来完成这一脱困的行为。
在此,我们可以窥见图像所隐藏的另一个空间的可能,这个空间是备用之所,是不得已之地,或者是待开发之处。而蔡东东通过图像实验与拓扑学的勾连,对图像进行干预和篡改,但这只是一种手段,本质上,他是打开并连接了图像自身存在的另一个空间。
他是揭露者,或者说是图像的体操教练,通过严苛的指导和对于动作的调整来使图像机能发生位移,从而轻而易举地拓展出另一种意义空间。比如在《无题》中,一个躺着的裸女手握一支相机镜头,如同手握枪支,这种揭露再次回到词源学纬度(射击与拍摄的词源学交集);而在《掇影者》里,蔡东东将他举起相机拍摄的自拍照镜头处切开,并适度拉起,使拉起的空白处看起来成为一次闪光。
拓扑学原理的无处不在,表明了在一个看似稳定的结构里边,运动状态的存在保证了这个结构内部的转换、调动,而能最的调配和转移在一个弹性行为中促进了交流与冲撞。废片在蔡东东的定义里有如感觉的“死海”,所以通过以上动作他可以激活其运动状态。
这些动作除了进行视觉性的干预之外,还有“命名”的干预。他将被两个男人搀扶的男子图像进行灼烧,并命名为《燃烧的人》,将图像本身的“搀扶”成功延伸为“押送”,将一个如同乞丐一样的男子的身份涂抹掩盖,他立即成了一个不明身份的反抗者或潜在殉道者。通过这样的空间拉伸,使这个被“燃烧”的男子具有了更多历史性的投影。尤其在《寻枪》中,一个站在陈列着各种各样手枪的封闭展柜前的男子这一寻常画面,被蔡东东经过打磨,模糊了男子的具体表情及身体细节,将这个只是作为观众的男子,打扮成了一个“疑犯”,而“寻枪”这一命名,使这个罪名最终近乎坐实。这样的行动在蔡东东的新作中比比皆是。他拉动了那些“废片”的筋骨,将日常的图像语境引向情节激烈、悬疑的剧场语境。这一点,也使得蔡东东的作品跟法国人尼古拉·布里奥所说的“后制品”产生了联系,当干预前的日常废片不被看作艺术品,而只是物品——一张随手拍下的银盐照片,那么经由这些银盐照片的重组之后形成的图像装置,则有如“后制品”,因为这种行为深具游戏世界的重新编排特征。
本着对于图像自身空间的不满和无感,将图像引入拓扑学游戏之中。于是,我们从他的创作实践中确认,他的所有创作都是基于一种行为,也就是说,他始终处于发生之中,对于稳定如誓言的图像惯性,他早就有了强烈的扭曲和拉伸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