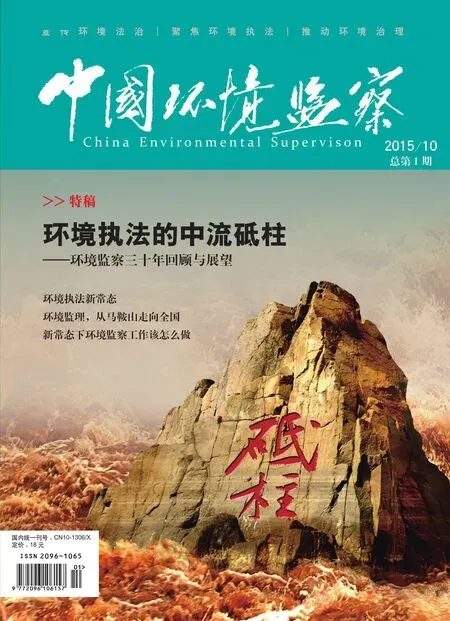遥远的清池
2015-09-18郝未宁
文|郝未宁
遥远的清池
文|郝未宁

记得有一次,同事们议论起电影《青松岭》,有人赞叹“青松岭”的村名取得实在是好。我很不以为然地说,俺故乡的名字才算好哩!众人纷纷打趣:“嘛好名?郝家庄?还是张家屯、三十里铺?”我自鸣得意:“清——池!清池的清,清池的池,怎么样!”
清池,物、形、景皆备,我以为确是地名中的上品。你不妨想象一下,有水且清,有池且清,该是个多么令人心向往之的地方!这正是我的故乡,晋东南太行山脚一个名叫“清池”的百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在我成长的记忆中,那是个多么秀美的村落啊!山上山下郁郁葱葱,村里村外柿树成荫,一道清清的小河,自北渐南,唱着,跳着,欢快地穿村而过,在村后村前形成两个数米高的小瀑布。两个瀑布下边各是一个十米见方的天然石底水池,池水透亮,一望见底。父亲说,这便是村名的来历。父亲又说,过去村前村后还各有一座古庙和古阁,生长着好几颗不知年代的参天槐树,村中央最大的一棵古槐,躯干上部分成匀称的三叉,我的祖先就在树上背北面南修了一座二、三米高的神庙,与村边的天然水池一起,成为地方奇观,只可惜解放初期毁于人祸。
山泉,溪流,清水池,滋养了草木,哺育了生灵,扮美了山村。我的妈妈,还有其她女人们常在村北的池子边上洗衣涮菜,洗净的衣被就晾在河边的大石头上,花花绿绿,与树林相衬,宛若盛开的鲜花。即便是在漫天飞雪的寒冬,洗衣的人流也没有断过,因为这条神奇的小河,仍然忠实地在雪地上流淌,并在窄窄的、清清的水面上,升腾起一层薄薄的热气。而仲夏的傍晚,放牛牧羊的人们,会赶着牲畜来河边饮水,劳动了一天的青年则三五一伙地到池里凫水,孩子们也常常跟着大人来玩水。这也是这个天然水池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候。上小学时的我,就是在这个清水池里学会的游泳。十年之后,当大学的同学们对我这个北方“旱鸭子”的游泳技能惊讶不已时,他们可曾看出,在我自信的表情里,叠加着对家乡的自豪,对清池的眷恋?
1979年,我告别母亲,离开清池到他乡求学工作,对故乡的牵挂和心往却一直未曾间断。后来,回老家的次数渐少,但对故乡的担忧却日益加重了。这些年,村村又开起了小煤窑,致使地下水位剧降,河水干枯,村后的清水池如今已变成了菜田,早先河床上洁净的石板也被灰土和枯草覆盖。不仅河水断流,甚至水井也干了,昔日清泉活跃,河水充沛的村子,现在人畜用水竟然全得依赖深井。遍地的小煤窑,兴盛的采石场,机器的喧嚣代替了鸟语蛙鸣,势利的追逐充斥了大道小路,深刻地影响着村民的生活,也无情地改变着山村的面貌。村民的口袋暂时鼓起来了,但健康问题却莫名其妙地多起来了;人们身上的衣服漂亮了,但头上的天空却日渐污浊了;农户的房屋豪华了,但山上的绿色却不知不觉地消褪了。生活富裕的同时,生机却分明在凋落,再别山村,我的心颇为沉重,甚至隐隐作痛。
这两年,村野旅游盛行南北,“吃农家饭,采农家果,住农家院”成为时尚,但凡有魅力的农家旅游点,无不以山水秀美取胜。而每次参与这样的旅游,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我的遥远的清池。前不久,住在蓟县山村的小河边,我终于没能忍住冲动,跟故乡作了一次电话交流。听说乡亲们正在补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课,从村长到百姓都在为山村的现状忧虑,为家乡的前途思索,我的心中浮起了无尽的遐想,“我的遥远的清池,何时还能与你相见?”
我面向西南,默默地许了一个愿。
(作者系天津市环保局宣教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