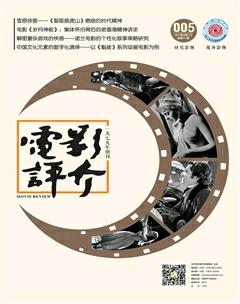娜夜:告别误读 回到诗歌
2015-09-12张蕊
张 蕊
当代诗坛,女诗人的诗歌创作越来越占据不可忽视的一域。上个世纪80年代,崭露头角的娜夜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自1991年起,娜夜就凭借持续的创作动力陆续出版诗集《回味爱情》《娜夜诗选》《娜夜的诗》《起风了》等佳作,并以傲人的佳绩连续斩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2005年)、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称号(2006年)、人民文学奖(2007年)等荣誉,展示出骄人的创作才华。
娜夜的诗歌总有种难言的魅力。究其缘由,当然同诗人横溢的才华息息相关,除此之外,这或许同诗人特殊复杂的创作身份有关——娜夜的女性创作主体、诗歌中西部风貌的地域性展示以及满族血统的族裔特征,都使得读者和研究者在关注娜夜诗歌文本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拘囿在诗人性别、地域、民族等“自传”因素的向度里,有时甚至将诗人现实身份与诗歌身份相混淆,从而造成不同程度的误读。因此,要读懂娜夜就必须告别误读,回到其诗歌本身。
一
作为一名女诗人,娜夜的诗歌是女性的。娜夜的诗中总是充满着女性特有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富于激情的理想情怀。女性立场的独特性,使得娜夜的诗歌细腻温柔,充满着丰富的包容气息。她时而温情无限,用母性的光环关怀生命,祈祷着“吹过雪花的风”“把天下的孩子都吹得漂亮些”(《幸福》);时而落目日常,像童真的孩子般珍视生活里的“黑糖球”(《生活》);更多时候,从爱情的窗子里关注女性命运:“这些窗子里已经没有爱情/关了灯/也没有”(《大悲咒》),成功地将女性独到的敏锐与多情展现在诗歌里。
谈及娜夜的诗歌创作,便不能不提及娜夜的“爱情诗”。爱情诗作为娜夜诗歌的精华展现着她独有的女性情怀。她以爱情命名诗集,自己也获得了“爱情诗人”的雅称。娜夜曾说过:“爱情并不比真理渺小。一个从未写过爱情诗的诗人是不可思议的。”娜夜笔下的爱情,多从女性的生活日常出发,却不拘囿于日常。在娜夜这里,爱情是《起风了》里“野茫茫的,没有内容的芦苇”,爱情是《离婚前夜的一场对话》里夫与妻仪式般冷静简洁的对白,爱情更是女性经历情感“昏睡”的梦魇之后,带着“把我留给自己”的箴言重新入梦的勇敢(《把我留给自己》)。这样的爱情看似平常,细细咀嚼却大有意味。当今社会,女性的自尊与独立使得她们不再梦想单纯完美的爱情,爱情对于女性不光意味着甜蜜,更可能伴随着未知的痛苦与伤害。因此,娜夜的爱情诗里总是弥漫着淡淡的感伤,娜夜笔下的女性也就拥有一种有别于以往的脆弱的坚强美。她们游走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却从不失掉对爱情的憧憬与渴望。
值得一提的是,娜夜爱情诗里的女性,是不同于翟永明笔下那些用“黑夜意识”尖锐对抗男权社会的女性的,她诗歌里的女性写作,更多是超越了女性的“身体”,让她们在“柔软而宁静的母性之光”里走向“白天”,体味人生的淡然与苍凉。[1]从这个意义上,娜夜的爱情诗,早已超越了男女的两性之恋,带着普遍人性的情感色彩,衍生出远比爱情本身复杂的宏阔内涵,展现出日常生活和生命中所蕴含的那些哲理与永恒。因此娜夜既是女性的,又超越了女性。
二
娜夜诗歌呈现的“地域性”,也是值得关注的话题。从娜夜的生活经历来看,娜夜很小便随父母去到了大西北,在西北长大,后又在南京完成大学学业,后来从兰州移居西安,2013年底移居大西南的重镇重庆。诗人由东而西,自北至南,就地域范围而言,这几乎算是对“中国”这个概念的一种实践。这种“跨地域”实践,对于关注于此的读者而言,可能是一个颇为有趣的话题。“西部诗人”的称号,便是这种“地域实践”的某种“证明”。尽管娜夜本人与大西北有着浓厚的文化的血缘,但严格意义上说,娜夜并不是高凯、沈苇、古马、叶舟,昌耀一类“纵情歌唱西部”的西部诗人,在娜夜的诗里,西部不是宏大摹写了的异域景观,更不是“文化明信片”式的特别所在,对于西部,娜夜生发的更多的是生命意识与自然意识交织下的人类灵魂深处迷失怅惘的慨叹。这种情绪的表达,既是淹没在似实而幻的感官里由“看”“抚摸”再到“听”的“新疆”(《新疆》),更是被定格在“远去的鹰”的天空里最终化为“人与神”的“忧伤”的“青海”(《青海》)。
与“西部诗人”这个称号大相径庭的,是读者似乎更多地把娜夜与“江南”关联起来,读者想当然地认为娜夜是南方人,依据不光是“娜夜”这太过婉约的名字,更多的是源于诗歌里那种别样温暖潮润的阅读体验。而娜夜本人也写过一首题为《江南》的诗,她那张倚着树干的照片也无不散发着江南女子的恬静温柔气息。她在一篇题为《慈溪:南方以远的喜乐之地》的文章中也写道:“我喜欢雨水,喜欢草木……喜欢南方……在那里,我们的日日夜夜以及贫穷富足,才更与上帝和所有人的相等。那是生命的一种平衡。”娜夜曾在采访时表示,“矛盾是生命最真实的状态”“我性情的内核是北方的”。[2]而她付印在诗集《睡前书》封面上的诗句——“我最好的诗篇都来自冬天的北方”,也佐证了她的说法。娜夜的成功在于超越地域,将南方与北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诗歌气质完美融合在诗中,使其诗歌更具神秘色彩。
三
除却“地域”这个话题,批评者似乎对“民族”的话题也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正如诗评家王珂所说:“娜夜的诗几乎没有流露出丝毫满族女子特有的火辣辣的爱的民族品格。读者和研究者也很难从诗歌文本中发现娜夜的民族性,不敢相信她是满族诗人。”[3]确实,在她的诗作中我们几乎没能找到“民族”的痕迹,至少在文本的表层无法找到她满族血液带来的影响。她不用满文写作,在诗歌创作中也从不强调自己的民族性,在她的诗中更多是女性视角下对于生命的审视与体味。这让很多关注娜夜的人大惑不解。其实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满族自身独特民族性的消逝有关。满族在历史变迁中与其他民族交往与融合,使得他们逐渐摒弃了固有的游牧生活方式,接受了汉族的信仰与文明。这种变化在清军入关后逐步达到了顶峰,更以王朝律令的形式固定下来。从娜夜个人的成长经历来看,她不同于扎根故土,接受民族文化熏陶的蒙古族女诗人葛根图雅,藏族女诗人完玛央金等人,从小就远离白山黑水的生活,沉淀并隔绝了娜夜满族血统里的民族性。纯粹的汉语教育,更是断绝了她用满文写作的可能。她曾遗憾地表示:“只认识几个满文的我,对不起我的满族血统。起了个满族姓氏的笔名也不彻底。”关于民族性,娜夜谦虚地表示:“民族性是个大问题,我是小诗人,力不从心。”她一再强调:“我写我的命运给我的——这对我很重要!”[4]这便是娜夜的真诚之处,也正是娜夜的成功之处。诗人娜夜从不勉强自己,她珍视生命所给予的,用自己的独特的生命体验,抒写自己最熟悉最擅长的生活,做回“娜夜”,不让“民族”束缚自己。
既是诗人便要用诗歌说话,正如娜夜在《当有人说起我的名字》中所写:
“当有人说起我的名字
我希望他们想到的是我持续而缓慢的写作
某一首诗
或者某一些诗
而不是我的婚史 论战 我采取的立场
喊过什么
骂过谁”
——《当有人说起我的名字》
诗人娜夜,作为一位拥有真正独立意识的优秀诗人,她独特且不容忽视。读她的诗,没有眼前乍然一亮的冲击,她的诗歌更多是用润物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你。她的诗歌更像深谷的幽兰,不做作,不谄媚,静静地绽放着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芬芳。
对于娜夜未来的诗歌创作,读者们可能有着诸多的期待,不妨借用娜夜的一句诗来作为回答,那便是:“我仍属于下一首诗——和它的不可知。”
[1]吴思敬.从黑夜走向白昼——21世纪初的女性诗歌[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44.
[2][4]任绪军,张蕊.只写诗,不说话——娜夜专访[M].成都:巴蜀书社,2014:300-314.
[3]王珂.体验爱情自然率真:论满族女诗人娜夜的抒情艺术[J].民族文学,19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