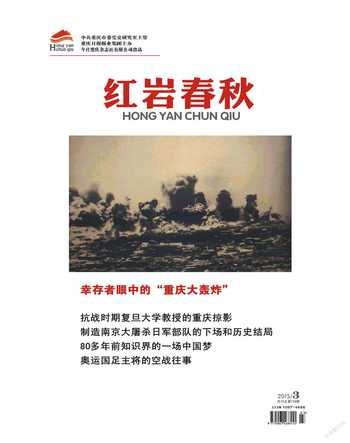口述史料的力量
2015-09-10黎余
黎余






70多年前,日本为了“摧毁中国的抗战企图”,达到“压制和扰乱敌之战略及政治中心”的目的,集其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频频出动飞机对大后方的重庆地区进行了近6年野蛮的无差别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在这场空前浩劫中,绝大部分受害人是当时社会的“草根阶层”。作为这段痛苦历史的见证人,他们留下大量的口述史料。这些真实简单的语言,反映出战争浩劫带给他们永难抹平的伤痛,是他们对日军暴行的有力控诉,让后世人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感知那场人类悲剧——“重庆大轰炸”。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移都重庆,成为中国的“心脏”。日本为了“摧毁中国的抗战企图”,达到“压制和扰乱敌之战略及政治中心”的目的,集其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频频出动飞机对大后方的重庆地区进行了近6年野蛮的无差别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重庆大轰炸历时之长、范围之广,所造成的灾难之深重,在二战期间和整个人类史上创下了战争史的新纪录。正如日本军事评论家前田哲男称:“对一个城市如此长时期固执地进行攻击,不用说在航空战争史上是第一次,就是把地面部队围攻城市的历史包括在内,也是极其罕见的。”
在这场空前浩劫中,绝大部分受害人是当时社会的“草根阶层”,是这段痛苦历史的见证人。为了客观真实地记录这段历史,还原日军暴行真相,伸张人类正义,自2005年始,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统一部署,在开展全市性的“抗战时期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调查”过程中,与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史学工作者密切合作,顶酷暑、冒严寒,深入村镇,挨家挨户对重庆境内当时健在的大轰炸受害者、亲历者进行了一次抢救性走访,搜集到大量来之不易的口述史料。
历史的生命在于真实。感谢时间能给我们机会,忠实记录下大轰炸受害者、经历者的珍贵口述,让后世人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感知那场人类悲剧——“重庆大轰炸”。
从漠然到紧张
受害者描述的大轰炸前的生活状况
随着淞沪会战逐渐走向不利局面,南京城面临朝不保夕的境地,国民政府于是确定四川为抗战大后方,决定迁都重庆。一时间,大量的人员随着军政、文教、工矿企业纷纷迁渝,随之涌入的还有大量躲避战乱的老百姓和战争造成无家可归的难民(当时重庆本地人统称他们为“下江人”)。这些饱受战争煎熬,几经辗转迁徙的逃难者当时的生存条件是相当艰难的。受害者高建文描述:“日本侵占了大半个中国,老百姓就往大西南跑。有的通过三峡坐船跑到重庆,有的是走桂林、湖南、广西、贵阳的公路跑到重庆来。有的大学陆陆续续过来了,教授、学生过来了,来的多。来了过后,流离失所,身无半文,钱用完了,要吃饭,穿的也只剩了一点,没有住的,找客栈,要(花)钱,(于是)就找茅厕,一床席子给挡住。有的大学教授就死在厕所里,较场口厕所就是大学教授逃难来住了,惨得很。那些难民一身的衣服不是像我们现在三天五天要洗一次的,他穿在身上,在旅途上怎么换呢?一身油脂的衣服,一身灰扑扑的,头发也乱了,这脸也油光油光的。大东西,小东西,一个包袱一个包袱的,有的提箱子,就像乞丐一样,住旅馆都被瞧不起,怕你拿不起钱,想起来,很悲惨。”
与这些难民相比,由于身处大后方,重庆本地老百姓还没有直接经受战争的折磨,没有亲身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性。一般民众皆“以为建设防空,全是政府和军警的事”,于自己“恍惚是漠不相关”的事情,并且此种观念“流行”“普遍”。但是,随着日本轰炸并占领上海、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日本要轰炸重庆的消息到处流传着:“那是1938年的下半年,重庆到处流传着一个信息,就是日本人将要对重庆进行大轰炸,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听传闻,中国半壁江山已落入日本手里,武汉沦陷、宜昌沦陷,日本很快就要打到重庆了。”
国民政府在重庆开始通过开凿防空洞、进行宣传防空知识等形式进行消极防空准备,加上充满大街小巷的难民,他们受战争所带来的痛苦情绪也感染着重庆人。顿时,重庆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人们也一天比一天惊慌起来。“城里有钱的人,有地方走的人都逃难去了”,但更多无地方可去和做生意的,以及必须等着挣钱才有饭吃的这些人,即使感受到了战争即将到来,还是只有选择呆在重庆城内,一方面固然是为生活所迫,另一方面,还是由于当时重庆人生活在大后方,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根本没有想到日军会如此残忍,对战争的残酷性认识不足。
虽然当时整个重庆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广大群众依然和往日一样忙于奔波生计,浑然不知厄运已经悄悄降临在他们的头上。
“全人类的耻辱”
受害者眼中的日本侵略者
1937年11月,日本制定的《航空部队使用法》第103条明确规定:“政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重要的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至关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居民,给敌国民造成极大的恐怖,挫败其意志。”同月,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这一政策的实施就直指重庆及其人民。由于日本在军事上的优势,加之重庆防空武器落后,防空设施缺乏,日机在重庆上空横行无阻,大施淫威。据当时四川省第三行政区署1941年10月对各市县遭受日机空袭情况的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10月到1941年8月,日机3585架84次空袭重庆市区,投弹9877枚。一时间,重庆市区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如今多少年过去了,这些受害者回忆当年那些火海、血肉横飞的场景,仍然心有余悸——
一是日机轰炸持续时间长,手段极为残忍,不但投掷大量炸弹,而且针对重庆房屋建筑材料的特点,投掷了大量的燃烧弹。受害者蒋昌前描述日军炸弹的威力:“连建筑最牢固的用大理石、花岗岩修的川盐银行顶楼都被炸烂,更不用说一般的民用建筑了。”日机大面积地投掷燃烧弹,妄图把重庆烧成一片废墟。“东水门一带都是平民的住房,多是穿斗结构,楠竹房,易燃烧,没多久就全部化为灰烬。”“那时候木房子结构都特别多。”加之房子都挨着建的,所以“燃起来的时候,一燃几条街……。你就算隔了几公里,都能感觉到火的热浪。”“当时没有电、没有水,无法救火,只能看着房屋燃烧。”更为恶毒的是,日本侵略者还丧心病狂地动用了毒气弹。
受害者周素华描述其亲身经历:“每当警报声响,忙于逃命的我只带一张被水浸湿的毛巾躲进防空洞。带毛巾是为了防止日本人投下的毒气弹”;另外两位受害者则描述了毒气弹的可怕之处:“日机这一次对储奇门地区投下了更可怕的炸弹(毒气弹),我们在当时根本就不知道投下的是什么。当时,国民军里的红十字医生,叫我们每人带上一张毛巾。用水打湿捂住嘴。到处都在燃烧,根本就找不到水,于是用自己的小便把毛巾打湿,把嘴捂住。我们这些住在河边的人都养了几头猪,日机所投下的炸弹,让猪的身上全部变为黄色。红十字医生把猪全部都集中在一起杀掉,放出来的猪血全是黑色的。解除警报以后,才知道是日机投下的毒气弹造成的。”“人们的伤口也开始流出黑血,发高烧,牙关紧闭,浑身颤抖抽筋,口都张不开,吃药都要把牙齿掰开,才能把药一滴一滴地灌进去。医生说,这个炸弹有毒,伤口才会流黑血,中毒很深,药起不了什么作用,很难医治。”
二是日机通过采取发放传单、日夜不停地“疲劳轰炸”等手段,企图造成人民恐慌,使人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中,疲于奔命,使其意识崩溃。日机在轰炸重庆的同时还经常撒下一些写有“少做衣多做鞋,白天夜晚都要来”“炸不死就困死、困不死就饿死”等内容的传单来瓦解人民的抗敌意志。与此同时,日军在取得绝对制空优势以后,经常不间断地派几架飞机对重庆进行骚扰,使警报长时间不能解除,最长的一次竟达7天7夜。有受害者描述跑警报的情形:“警报响起,满街的男女老少像赶鸭子似地奔跑。”“一天跑几次警报,经常是解除警报刚返回家,还没有坐下又听到拉紧急警报,又得往外跑,有时3天3夜不拉解除警报,弄得不少人患感冒、霍乱等,就这样死的人也不少。”除此之外,“日寇飞机每次都想轰炸自来水塔(今七星岗兴隆街附近),企图制造重庆人断水流”,还经常轰炸码头、电力公司、储油趸船以及报警台等。”
三是日机的疯狂轰炸给重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伤害和损失。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8年至1941年期间,有档可查的,死亡6596人,受伤9141人,伤亡人数15737人,炸毁房屋11814栋21295间。这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代表着一段沉重的、令人心酸的血泪史。受害者鲁长清共生育9个子女,在大轰炸中就死去6个孩子;受害者叶明仙的家在1939年至1942年期间,被炸7次;受害者杨泽友四世同堂的15人大家庭一次就被炸死12个……像他们这样遭遇的人在那段悲惨岁月里随处可见。
正如受害者所说,“在大轰炸中,多少人被炸成肢体分离?多少人无家可归?”“多少原本富裕的家庭从此潦倒痛苦,多少原本幸福的家庭从此颠沛流离、家破人亡。”
有努力,有缺失
受害者眼中的国民政府
从受害者的回忆材料来看,当时的人民对国民政府怀有一种复杂的心态。
一方面,他们认为日本是大轰炸的罪魁祸首,但同时也对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和防空措施的缺位深感无奈。在积极防空方面,受害者是这样描述的:“两个对打(敌、我飞机),多数是我们的遭(即挨打)……”经过无数次轰炸后,“中国的地面部队也无能力回击日机,以至于后来日机一架一组,就可以低空飞行侦察,一路畅通无阻。”防空力量建设和补充的不足,也是导致后来日军敢于投入少量飞机就进行“疲劳轰炸”的重要原因;在消极防空方面更为糟糕。据1939年防空司令部统计,重庆市各防空平洞、隧道共143处,仅能容纳73000余人避难,而当时重庆市人口是401074人。据不止一个受害者描述,有相当部分的防空洞(主要是官僚、大资本家、保甲长等有权、有钱的人修的,条件很好)是需要掏钱办证才能进去的,对于被炸得家破人亡、一无所有的普通民众来说根本就买不起票进洞,只能进免费防空洞。而这些防空洞质量相当糟糕,“洞内空气混浊”“凹凸不平,洞顶滴水,洞底积水。”而且,“洞内土质松软,用大木柱架空支撑,以电线引入之光线微弱,通风设备毫无。听得一连串炸弹落地,灯光闪烁,全洞震撼不已。”在日机空袭重庆时的现场指挥上,国民政府从指挥疏散进洞到轰炸结束后处理尸体也显得杂乱无章,也间接导致了伤亡人数的增加。空袭警报拉响后,“当时,人们只顾着逃命,没有哪个敢来维持秩序,逃命的、躲飞机的人黑压压的一片,乱得很。大人喊,娃儿哭,你踩我,我踩你,硬是惨得很哟。”
另外,受害者在描述震惊世界的重庆“六·五隧道大惨案”时,几个细节问题更能说明国民政府在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上(在此之前,已经发生过2起隧道窒息案件。一次是1939年6月11日中山公园隧道窒息案和1940年8月12日左营街窒息案)和防空指挥上存在着重大缺陷。比如:“由于连续轰炸时间长,较场口中兴路口警报信号台的红灯笼又坏了,有人(国民政府专门负责警报的工作人员)就用煤气灯套上红布代替空袭信号。这一来就使在大隧道口避难的市民产生误会,以为是敌机要投瓦斯毒气弹了,顿时围着洞口蜂拥而入,秩序大乱。”再如,当里面的人群已经开始发生窒息现象的时候,外面的国民党卫兵采取了简单而粗暴的作法,“为了不让这些(人)出来乱跑暴露目标,因此,把洞门关起来。”出事以后,只是简单地用石灰对尸体和周围地点消毒,然后把尸体拖到朝天门,运往黑石子、南岸坡草率掩埋,“结果夏季暴雨一来,很多尸体从山上冲到长江,水面上漂满了尸体,充满了腐臭。”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重庆瘟疫流行、霍乱蔓延,由此引起的死亡人数也不少。
另一方面,在大轰炸中国民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进行了反空袭斗争,采取了一些有效的应对和补救措施,开展了相应的救援救亡活动,尽量减少损失。特别是“六·五隧道大惨案”发生以后,迫于民意和舆论的压力,国民政府加大了实施这些政策的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受害者对国民政府做出的这些努力,在自己的回忆材料中也做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大轰炸开始后,面对百姓死伤严重的情况,国民党政府“开始大规模打防空洞,每人出6块钱,按人头数”,同时“积极组织精壮劳动力参加防护团实行义务服务,分为交通、消防等服务大队,专门负责空袭时的救助、收尸等,说是国家有难,人人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后来,“政府还在最显眼处、最高处挂上红球或红灯笼”表示警报,在夏天的时候“每人发了八卦丹、金灵丹、万金油、头痛粉等防暑急需品,以备急用”。此外,国民政府对伤者、受灾难民和死亡者分别实施了救济救助措施,对在大轰炸中的受伤者实施免费医疗,并提供一定的营养品帮助伤者恢复。有受害者提到:“被日本飞机炸伤的,要当地的保甲长出证明,证明你是被日本飞机炸伤的,(于是)给你治疗并免收住院费等。”“医院发的营养品,说是吃了就长肉,但我吃不来那鸡,我不吃就要挨(医生)打”;对轰炸中造成的受灾难民,采取了统一安排,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几位受害者描述当时的情景:“大梁子警备区马路边在施大头稀饭……,排单行一人一瓢稀饭,一小瓢□□。”“在医院出院后,无人接我,就把我转送到了难民所,一天两顿清稀饭,看我基本能走动,就问我什么地方人,发给我点儿路费,我就回岳池老家养伤。”“我们全家及其他受灾人民,全部集中在当时瑞丰□粉厂,坐成一排。当时的国民党乡公所,扯起一个临棚房居住,每天由他们供应饭吃”;对经过调查确认是在轰炸中死亡的,当局也给予一定安葬费。无人认领尸体的,由当局统一进行掩埋处理。受害者王西福回忆:“大约一个月以后,经国民政府的调查和核实,证实我的父母系在日机轰炸时遇难,按当时的政策,我到政府部门领取父母安葬费20个大洋,还按了手印。”
通过受害者的口述,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重庆能够在日本的狂轰滥炸中巍然屹立,并能在轰炸之后迅速恢复正常生活,客观地说,国民政府还是发挥了作为国家组织者的作用。
“愈炸愈强”
受害者回忆大轰炸下市民生存状态
残酷战争给重庆人民带来的悲剧每天都在上演,人们每天都要面对血淋淋的现实,身心疲惫。
大轰炸初期,当时政府虽普遍宣传“万事莫如防空急”,但是人们对战争这个概念认识很少,“认为他们不会轰炸无辜的老百姓”,防空意识不强,更缺乏基本的防空常识。受害者祝元庆回忆:“当时重庆人生活在大后方,根本不知道日军如此残忍,日本炸弹是那么大威力,我们还是在保甲防护团人员的反复催促下离开家的。”不少受害者回忆他们躲避轰炸的方式相当幼稚,“在家里的人全都躲在桌子下,桌上铺被子,双手合十口中不断念阿弥陀佛。”“听到紧急警报响起,全家赶紧躲到铺满棉絮的桌子下面,以为这样就可以躲过轰炸,伤不到人。”
随着日机轰炸越来越频繁,跑警报成了家常便饭,“市民白天、黑夜,晴天、雨里,严冬、酷暑跑警报,天天风餐露宿,提心吊胆度日”,每天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据受害者张远珍描述:“母亲带着我们3姐妹天天悬心吊胆地过日子,晚上睡觉从来没有脱过衣裳袜子。特别是冬天,母亲经常将我从睡梦中打醒,还要背弟或妹摸黑到处乱跑乱撞,经常摔得身上到处是伤。冬天又冷又饿,夏天被蚊子咬起全身都是红疙瘩,好像出麻子一样,那个日子不是人过的,但是没有办法,为了活命。”也有跑警报跑久了,跑烦了的,不想再跑,存着侥幸心理,结果往往代价惨重,非死即伤。
再后来,正如受害者所描述:“那时,整个重庆成了一个偌大的坟场。房上、树上、岩坎上到处都见得到挂着的、躺着的尸体、残肢,长江里随时能看到漂浮的死人。”这种精神上的压力在当时成为老百姓生活中最痛苦的煎熬,“有些人吓得屎尿都流出来了。”“从那个时候起,祖母只要一听到拉警报、爆炸声或房屋燃烧,她就会全身颤抖,不断地抽筋,也发生过几次晕倒。”“从那次轰炸后,我老婆潘氏就得了恐惧症,当时又怀孕在身,只要炮声一响,她就全身发抖、惊叫,反反复复地发作。”
战争使人们恐慌、甚至麻木,战争也可以使人坚强。面对日本侵略者嗜血成性的屠杀,重庆人民在承受大轰炸带来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等巨大痛苦和牺牲的同时,也唤醒了他们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表现出了勇于牺牲、自强不息的斗争意志。受害者在回忆材料中叙述了这样一种信念:“对日军仇恨,从来没有打消,抗战一定要胜利,你今天炸了老子,明天又摆摊,就这样子。”反空袭斗争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部分,据不少受害者回忆,那时候,大家都很团结,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挨家挨户筹钱挖防空洞,自己动手兴建了大部分的避难场所。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很多民间组织,有消防队、防毒队、空袭服务队、防护团等。据1940年全国慰劳总会慰问重庆市空袭服务人员统计,参加这一工作的计有:交通工人服务大队、医务红十字会等单位10700多人,水电工人1200多人,空袭服务总队5830人,这些组织在当时的救援救亡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日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不但没有达到动摇人民抗战意志的目的,反而激发了广大人民的义愤。正是这些小人物不屈不挠的斗争,正是这些无名英雄的默默奉献,重庆才能成为“全世界最英勇之城市”,“重庆人民的坚韧刚毅,已为世界所崇敬。”
伤痛难平
受害者谈大轰炸对其及家庭的影响
重庆大轰炸是日本侵略者强加给重庆人民乃至中国人民的灾难,给整个民族带来的是刻骨铭心的伤痛,这种伤害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
受害者刘少华描述大轰炸带来的悲惨遭遇:“我们失去了母亲,生活没了办法,姐妹几个整天在废墟周围哭声不断。几天后,小妹因惊恐和饥饿也断了气。我的五姐当时只有15岁,不得已送给别人家当童养媳。我的六哥11岁,我8岁,只得各自流浪讨生活。后来,六哥有幸被富顺孤儿院收容,而我却到处流浪,8岁开始品尝人间的酸甜苦辣。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我没上过学,先后跟理发匠、木匠当过学徒,帮别人撑过河船,在铁匠铺面做过杂活,整日衣不遮体,捡过垃圾,当‘狗屎娃’(靠拾粪来换一口粮食),去给地主家当看牛娃。”受害者孙振环也有惨痛的记忆:“父亲的去世给我们全家人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打击。中年丧夫,长年艰苦的生活,严重影响了母亲的健康,使她晚年体弱多病,过早地离开我们。少年丧父,过早地承担生活重任也严重损害了我年少的身体,超负荷的工作和严重的营养不良使得我一直体弱多病,过早失去父爱也给我的心理和性格造成了很大影响,过早的工作,使得我失去了继续受教育的机会,是我一生的重大损失。”在那个年代,有这种痛苦经历的家庭俯拾皆是。
时至今日,经历过这场劫难而侥幸存活下来的人们,他们在承受大轰炸造成的生理上的残缺的同时,精神上的创伤终身挥之不去。正如受害者蒋万锡所说,“尸骨可以掩埋,轰炸现场可以覆盖,但是已经深深烙在人们心中的痛苦记忆,永远不会忘记、磨灭。”受害者赵茂蓉“(脸部)被弹片炸伤,给她的生活及精神上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她的听觉也受到了损伤,必须要很大的声音才能听到别人说话,并且经常头痛。婚姻生活也因被炸伤而有很多的痛苦,在工作中也经常受到讥笑”;受害者周永冬“被炸断一只右腿,造成了终身残废,他的身心健康都受到极大的摧残,(至今)已达62年之久”……而这一切痛苦的根源,正是“可恨的日本强盗夺去了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我们的欢乐,给我们的一生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
“天上,弹如雨下;城中,泪落也如雨。弹下不停,泪落不息,浇不灭冲霄的火焰,洗不尽横流的鲜血,舒缓不了千万人的哀号愤激。高空日机已渺,遗恨何时消失,重庆永远在哭泣。”这是一位幸存受害者在上世纪末编写一部《重庆永远在哭泣》的电影故事所作的主题曲,虽已远隔半个世纪,却仍然历历在目,不能忘记,既是对当年重庆大轰炸真实场景的悲惨描述,也是对战后日本长期掩饰其侵略罪行的有力揭露。
历史是过去的总结,是现实的基础,更是未来的起点。经历了太多苦难和挫折的中华民族,对和平的渴望、热爱、珍惜最为强烈,对正义的追求、争取、坚守最为执着,更加懂得捍卫国家民族独立、主权、尊严予以我们的至高价值。今天,我们调查历史真相,记录历史灾难,不是为了咀嚼苦难,更不是为了延续旧时仇恨,扩大中日之间的裂痕,煽动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而是为了以史为鉴,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作者单位: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图片来源:网络)
(责任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