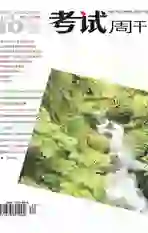读者本位观照下的翻译研究
2015-09-10张帆
张帆
摘 要: 翻译是为读者服务的,然而,当代译论对于读者修辞上的指涉掩盖了读者本位的阙如。本文通过界定译文读者的范围,廓清读者的视野版图,指出译(论)者中心主义对读者本位的盲视,从读者本位的视角考察译文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心理,并重新审视归化异化之争。
关键词: 读者本位 翻译 接受 译论
1. 当代译论中读者本位思考的阙如
1.1当代译论对读者的指涉
在当代译论中,读者日益成为重点,衡诸论者对“读者”的理解和切入点的不同,对读者的探讨可大致举三目以概括:一是将姚斯(Jauss)和伊瑟尔(Iser)的接受-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伽达默尔的现代阐释学理论及罗兰·巴特后结构主义读者观等运用到作为原文读者的译者身上,强调原文本的非自足性、开放性,以及作为原文读者的译者的接受与阐释的历史性、能动性,从而使译者得到解放,获得创造性构建原作意义的自由。然而,对作为原文读者的译者的理论聚焦,几乎忽略了译文读者的存在,或者因袭陈言,勉强套用在译文读者身上却未甄别出其与普通文本读者的不同。在斯坦纳(George Steiner)那里,翻译与读者的关系发生了颠倒性的概念置换,“理解即翻译”。斯皮瓦克(2005:237)为这种普化的翻译造了一个词RAT,即“作为译者的读者”(reader-as-translator),认为“一切阅读都是翻译”。这里,“读者”的概念范围无限扩大,然而,“翻译”的概念又游离出了经验层面的视域。在第二种情况里,论者从翻译过程和目的的角度阐发标举了读者的重要性。在弗米尔(Vermeer)的目的论框架中,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受众—译者心目中的接受者,每一种翻译都指向它的受众。奈达、纽马克的等效论更加重视读者的反应,以此指导译者的实践活动。此类译论处处以读者为尊,似乎真正做到了以读者本位为观照,却在无意中混淆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心中的隐藏读者与实际上的译文读者。诺德区分了“译文的目标读者”和“文本接受者”这两个概念,指出了“译文的目标读者是从文本创作者角度来看的,是预期的读者群;文本接受者是指在文本创作出来以后,真正阅读、倾听文本的个人、组织或机构”(Nord,2001:227)。理论上的区分总是容易,而实际上,对隐藏读者的指涉总是僭用了“读者”这个公名,无论是奈达、纽马克所服务的“读者”,还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想象读者,皆非真正的实际读者,其本质上类似于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他者”,或胡塞尔现象学里对陌生主体的意向性构成。第三种情况是研究特定时代、地域的读者作为一个整体对某个译本的社会性接受与反馈,此类译论关注的是读者的全体性和功能性存在,而忽略了其个体性与主体性。
综上所述,各种关于读者的译论虽然取径有异,却坐共同之弊,即隔靴搔痒,并未从真正译文读者的角度来观照翻译,也就是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换位思考。有人会质疑个人乃带有“前见”“前理解”之历史性存在,因而质疑真正“换位”的可能。这里的“换位”不是指与他人的换位,而是个体在自己不同角色间的换位。译者不只是原文的读者、译文的作者,也可以是某篇译文真正意义上的读者。那么,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译文读者呢?
1.2对译文读者的界定
萨瓦里(Thoedore Savory)根据译文读者的水平和个人爱好,把读者分为不懂原文、正在学习原文语言、学过原文语言但又忘记了和精通原文语言四类,认为针对不同的读者应采用不同的译法(廖七一,2004:61)。诚然,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凡是译文文本接受者,不管其阅读动机是什么,都是译文读者。但从翻译最根本的意义上看,我们必须对译文读者作出溯本探源的严格限定。翻译的本质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而翻译之所以产生,也正是因为人有了解异质陌生他者的需要,因此,对翻译的探讨不应脱离这一发生学逻辑与本体意义,否则翻译就成为一门专供人们茶余饭后品评欣赏的语言转换艺术或一门用来学习外语的捷径工具。通过翻译了解陌生异质的他者,从而扩展自我的精神生存空间,这才是翻译的鹄的和根本意义所在。因此,立足于翻译之根本,我们有必要对译文读者这一概念做出澄清。
余光中(2002:55-56)在《变通的艺术》一文中写道:“读者只能面对译者;透过译者的口吻,去想象原作者的意境。翻译,实在是一种信不信由你的‘一面之词’……一般译者不会发现自己的‘一面之词’有什么难解、累赘甚或不通的地方,就因为他们‘知己知彼’,中文的罪过自有外文来为它解嘲。苦就苦在广大的读者只能‘知己’,不能‘知彼’。”余光中的分析可谓探骊得珠,一语中的,一扫以往译论对于读者的隔阂肤廓之论,真正意义上的读者正是这些看不到原文或者不懂原语的读者。纽马克指出一些“受限制”的翻译方法:信息翻译,范围包括通过总结得出简洁的摘要,到不注重形式的对内容的完全再生产,等等。纽马克认为“受限制的翻译”应该处于严格的翻译理论之外,翻译理论的重点不是考虑受限制的翻译(厄内斯特-奥古斯特·古特,2005:351)。同样,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对译文读者的探讨范围应该严格限定在那些不懂原语或无法获知原文而只能通过译文了解他者文化的读者上。
1.3译文读者与译(论)者在视野上的差异
正本清源既竟,我们便可清楚地看到译文读者不同于作为读者的译者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可以帮助我们廓清、厘定译文读者视野版图的边界,让译者能够做到真正的换位思考,指导其翻译实践。译者就如同导游向游客介绍景物一样,将原文翻译成译文介绍给目的语读者,导游自身也是景物的观赏者,但他对景物的观感肯定是与普通游客异质的,因为导游拥有景物的详细资料,这是了解程度的不同,同时他的工作性质让他无法以纯粹观赏者的眼光去看待景物。从译文读者不知情的角度,我们也可举譬。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灯笼的摘挂在国内观众看来是一种“伪民俗”,而在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的西方观众看来却满足了他们的东方猎奇心理。知情与不知情的差别造成了欣赏效果的分野,这正隐喻了译者与读者在视野上的差异。
与不知情的译文读者相对立的不只是译者,还包括知情的译论者,这就涉及译文的评价标准。这个问题著名的阿诺德、纽曼之公案早已论及,二者就普通读者与学者谁有资格评价译文仁智互见。奈达则认为翻译评论家大都是双语专家,因此他们会下意识地用对原语信息的知识去评价译文的形式,而不会全面地为译文接受者考虑(廖七一,2000:91)。事实上,译者、论者和读者由于各自视域的不同,对于译文都有独特的感受与评价标准,因此对一个译文的完形评判应当综合不同视域下的不同观感,使其互备互证,而不应当执一面之见,做一曲之士,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但鉴于以往译论对真正意义上的译文读者的盲视,因而本文意在收矫枉之效,将视点位移,对焦读者,突出从读者本位来观照翻译,拓展读者声音的空间,重建译论的读者之维。
1.4译(论)者中心主义对读者本位的盲视
基于主体间性的译论谈到了译者与读者的平等对话关系,要求译者在翻译中设想读者的存在,将自己置身于理解主体间性的思考之中。这种与读者的对话只能是一种视域上的融合,更多的情况下则是一种独断的臆测,就像张隆溪(2005:66)认为德里达把中国文字视为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的另一选择,只是从西方的角度来判断中文的价值,是把中国文化视为西方的他者,与黑格尔式的东西文化对立观念,除了在态度上不同之外,在实质上并无区别。从译者、论者的角度看读者,则读者永远都是“他者”,因此译者、论者有必要进行真正的自我内部的角色换位。作为翻译理论,译者当然居于中心地位,事实上,即使从读者本位来审视翻译,最终还是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回归到对译者翻译实践和论者批评实践的指导上。但以译者为中心不等于译者中心主义,目前的情况是译论往往陷入译者中心主义的自我陶醉与独白,就像保罗·德曼笔下卢梭的忏悔一样,对读者修辞上的指涉掩盖了读者本位的阙如,是在剥夺了读者的话语权之后对读者进行的缺席审判。本文对读者本位的强调正是针对译(论)者中心主义所作出的回应与匡正,是对被劫持的读者从译论统筹之下的解救,所以就有一定的前提和范围,而不是对读者主体性无止境的膨胀。
廖七一(2000:82)指出:“由于长期受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影响,人们对翻译中的创作普遍持有偏见……解构主义理论的产生,从理论上充分肯定了译者的重要性,阐明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必要性,从而为创译正了名。”言之在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以译者中心主义的眼光来看,普通读者对译文的最基本的要求已经成了“偏见”,而普通读者是不懂什么“解构主义”或者其他什么翻译理论的,这是否意味着译文读者只能仰仗作为现代社会“断裂性突变”机制之一的“专家知识系统”(Giddens,引自赵一凡,2007:26),只能在福柯“话语即权力”的阴影下被挤压到理论的夹缝中备受冷落?
2.从读者本位角度来考察译文读者对译文的接受
2.1同一性假定:译文读者区别于普通文本读者的特殊性
以上我们廓清了译文读者的视野版图,指出了译论对读者本位的盲视,那么,我们进一步进行读者本位思考的意义何在?读者本位思考对于译论又有何启发?事实上,读者本位的致思路向要求我们时时牢记读者的视野范围。将其运用到读者对译文文本的接受上,我们看到,译文读者不谙原作,却又普遍要求译文如实反映原作,这就是译文读者与一般文本读者的异质之处。胡塞尔将想象的质性分为两种:带有存在设定的质性和不带有这种设定的质性(倪梁康,2007:128)。在读小说时,读者往往持不表态、不设定的心境,而译文读者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对译文是同时设定与不设定的。不设定是对文本所传达的思想内容本身,而设定是就原、译文的关系而言。问题在于,从读者本位的角度,读者在不谙原文、视野受限的情况下何以相信译文的忠实?如果他不能确信,那么又是何种信念在支持他的阅读?实际上,译文读者就如夜幕航船,为穿越暗礁驶向原文思想的港湾,除借助译文灯塔的引领之外别无它法。职是之故,译文读者只能做出权宜的假定,即译文与原文是同一的。
2.2“以史为鉴”:从读者本位角度看译文读者的接受心理
译文读者的特殊性在于他在不谙原文的情况下对原文-译文同一性的默认,而同一性假定一经作出,读者就倾向于维持这个假定。这里,我们可以将读译文与读史作类比。比如《史记》记载项羽在帐中与虞姬生死离别,但当时无他人在场,史家何以得知呢?凡此种种,不一枚举。普通读者并未因为这些经不起仔细推敲的细节而指责史家真赝杂糅之欺,并拒绝接受史书的言之凿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史家的记载在读者看来是“合情合理”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史家描述已然之事,诗人描述或然之事,而在后现代史家看来,历史又何尝不是按照“或然律”来叙事的呢?美国学者丹尼尔·艾伦(Daniel Aaron)有言:“我们可以说真实就是想象得最合乎情理,而小说家显然比历史学家更有资格找出并恢复那不可见的历史联系。”(张隆溪,2005:253)后现代史学理论认为,“真相若非绝对客观,至少可以合情合理”(汪荣祖,2006,导言:7)。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说“任何一本史书,只需评论它论述是否一致,是否连贯,是否明白”(Ibid.:209)。以上这些论述貌似是对传统史学本义的反拨,其实却冥契读者读史时的接受心理。如果我们认可赫施(Hirsh)对“意思”(meaning)和“意义”(significance)的划分,即作者的“意思”是固定的,而翻译是“对原文作者的心迹跟踪”,(刘宓庆,2001,自序:ⅩⅨ),那么,在这样的类比中,史书被看做历史的真实记载,而译文也是原文、原作者意图的如实反映,两者都强调“真”的假定前提,而真实的本原却都被遮蔽,那么史书读者和译文读者的视野和心理便有相通之处。因此,借镜历史,可以说,译文读者假定译文与原文的同一性,由于原文的被遮蔽,他不能证实,读者所能做的,只是检验译文是否“合情合理”。如果译文在读者看来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读者会倾向于相信译文是原文忠实的反映。但倘若译文在读者看来不“合乎情理”,让读者无法接受,那么读者的同一性假定就会被推翻,从而产生对译者的不信任。
3.应用:从读者本位角度重新审视归化异化之争
不谙原文的读者对译文有着“合情合理”的底线要求,一旦底线被突破,则读者对译者的信任感全无,原文-译文同一性的假定即被推翻。这启发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待聚讼颇多、执义纷纭的归化异化问题。以往论者每每争论两者孰优孰劣,从读者本位来看,由于原文被遮蔽,我们关注的就非归化异化的轩轾之分,而是从证伪的角度确定归化异化的两个极点。
列维(J.Levy)提出文学翻译的“错觉”理论,认为译者隐匿在原作后面,以原作者的面目出现,使读者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读的不是经过中间人(即译者)处理的译作,而是在直接读原作(谭载喜,2004:202)。但错觉随时有可能因为译者的过度介入而幻灭,“就像儿童聚戏时大家无形中都有一种了解,就是都相信所戏的玩意是真的。如果有一个儿童插嘴说一句露破绽的话,大家就立刻都觉得扫兴。儿童游戏时常偷偷窃窃地瞒着大人们,不肯让他们看见,也使怕他们嘲笑或批评,在热烈灿烂的幻觉之上泼冷水”(朱光潜,2005:171)。过度的归化或异化就像那句“露破绽的话”,让读者“觉得扫兴”,而译者的介入也如“大人”一样,在读者“热烈灿烂的幻觉之上泼冷水”。这样,从读者本位的角度,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归化异化之争,将过度的异化与过度的归化视为破坏读者同一性假定的两个端点,这两个端点就是读者的底线要求。以往讨论较多的一极是译文的过度异化,比如余光中就写过许多文章批评这种现象。的确,适度的归化,自然、明晓、畅达的目的语语言是必要的,就像汉语配音的外国电影里面人物说着地道的中国普通话一样,并不会破坏读者的原文-译文同一性假定。胡塞尔现象学认为自我是从本己的、内在的体验领域出发,通过意向性而超越出这个领域,构造出他人或其他的主体,并进一步构造出对于我这个主体和其他主体来说共同的社会世界、精神世界、文化世界,等等(倪梁康,2007:142)。每一个交互文化的陌生经验和交互文化的理解都是以“本己的基础为出发点,而通过共现的本质可能性”导向一个陌生文化的领域(Ibid.:197)。每一个读者都是从自己的语言出发来理解陌生文化的,因而对陌生文化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在本己“体现性”基础上的一种“共现”。目的语语言作为读者本己体现感知的依傍,必须译得易于理解,自然通畅,否则就会导致对源语文化的“共现“严重扭曲、变形、偏离,甚至让读者失去本己体现的立足点,无法“共现”源语文化,导致读者失去对译者的信任,破坏同一性假定。这样的译文显然不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一般情况下原文是不可能如此佶屈聱牙、不忍卒读的。另外,洪堡特有言,“民族语言即民族精神”,语言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文化性,与此同时,语言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因此,是否过度归化又构成了另一个极点。好的译文应该像一块透明的玻璃,尽管不免折射,但透过它,读者能够大致清楚地看到源语文化。过度的异化固然就像一块不平整的玻璃,让读者无法看清对面,而过度的归化则又如在玻璃的一面镀上了一层金,读者看到的只是这层镀金,玻璃对面的景象则永远被遮蔽。廖七一(2004:270-271)曾举一例:
原文:“Well,...Rose Kane is going to have one.”
“Oh,well,that’s fine.”
“And,”added Mother,“We are,too.”
“Great jumping grasshoppers!”cried Father,“Why don’t you tell a fellow?”
译文:“这个……甘太太也有了。”
“喔!有意思。”
“再还有,”母亲随随便便地找补一句,“咱们也有了。”
“乖乖龙底东!”父亲直叫唤。“你怎么不直爽点儿说哇?”
从奈达、纽马克等效论的角度来看,将“Great jumping grasshoppers!”译为“乖乖龙底东”可谓“精彩”,译文所表达的功能与原文也铢两悉称。但译者、论者同时知晓原译文,因而在欣赏译文之“妙”时,心里是有原文作为底片的,而从读者本位的角度来看,读者在读这句方言译文时则明显感到了源语文化的被遮蔽,感到了译者介入的痕迹,感到了一种“期望别人还债,结果收到的却是一件礼物”(谭载喜,2004:123)时的失落,尽管二者是等值的。当外国小说中的人物说着中国方言时,译文就不再“合情合理”,原文-译文同一性的假定由于对译者的不信任而遭到破坏。韦努蒂(L.Venuti)从后殖民主义角度出发,提倡一种“抵抗式”的异化译法,主张译者的现身。笔者认为,在异化译法中,与其说是“译者”现身,毋宁说是“源语文化”的显形。事实上,源语文化的显现倒会让译者隐身,并不破坏反而更加确证读者对原文-译文同一性的假定,因为读者本来就知道读的是外国作品,相反,在过度归化译法中,我们见到了译者叛逆性的身影。由此,从读者本位的角度,我们确定了异化与归化的两个极点,即译文要合情合理,以不破坏读者对原文-译文同一性假定为底线,越过这两个极点,就成了不可接受的过度异化或归化。如此,以其在归化异化问题上的应用为例,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读者本位思考的重要意义。严复“信、达、雅”中的“信”是从译(论)者角度出发的,而从读者本位的角度,我们是否应当以不谙原文的读者眼中的“信”(合情合理)要求译者呢?在上述的例子中,译者的确做到了对原文的“信”,但“忠而获咎”,个中原委即在于未能满足读者对“信”的要求。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作为维持原译文同一性假定的“合情合理”这个底线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欣赏口味和接受尺度。诚然,在这个标准多元化的时代,康德之审美判断的主观普遍性似乎应当被归入伽达默尔所言现代性批判必须超越的三种幼稚性(保罗·德曼,2005:43),但我们也可以把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提出的“阐释共同体”概念运用到译文读者身上,译文读者对“合情合理”的感觉与理解具有社会性与习惯性,存在于一个公共的理解系统之中,同贯共规,而非高度分殊。在主体间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达到“共识性真理”是可能的。其次,不同的阐释共同体之间又存有差异,如诺德所言:“忠诚是一个空位,由每个特定的翻译任务所涉及的文化及其翻译理念来实现。”(Nord,2001:125)本文显然是立足于中国读者的审美期待与接受取向而做出的分析。再次,从历时的角度看,“合情合理”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清末的士大夫们显然会认为林纾的翻译是“合情合理”的,而本文观点只能代表现今这一特定历史时段读者的审美期待,至于未来读者的接受取向,则笔者不敢断言。
4.结语
翻译是为读者服务的,译者往往写序言后记,里面的话主要是对读者说的,因而真正的读者之维对译论的多维度建构自然意义别具。读者本位的致思路向意味着要使读者由共鸣箱的地位变为自主的声源,耕种读者视野下的理论自留地。读者视野诚然有限,然而,译(论)者亦存在理论盲区,未能自外于独断中心主义的学术无意识。译者、读者也许还有原作者(著如米兰·昆德拉、辛格等作家对自己作品译本的要求。非关论题,在此不遑详述)的视野合流并现,方能构成译论之全景图。本文以归化异化为例证明了读者本位视野的证伪作用,而译(论)者原文译文两相对照之证实功能,以及原作者的权威性意见亦为重要,三者合璧,比照互参,则译论视野之坐标系可谓周全。
参考文献:
[1]Nord,Christiane.2001.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保罗·德曼.“结论”:瓦尔特·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C].//陈永国,译.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厄内斯特-奥古斯特·古特.作为语际间阐释的翻译[C].//何宏华,译.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5]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6]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7]倪梁康.意识的向度——以胡塞尔为轴心的现象学问题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斯皮瓦克.关于翻译的问答:游移[C].//陈永国,译.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9]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0]汪容祖.史学九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1]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12]张隆溪.中西文化研究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3]赵一凡.从胡塞尔到德里达——西方文论讲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14]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