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一骢:那个“被上交给国家”的网剧一哥
2015-09-10刘璐
刘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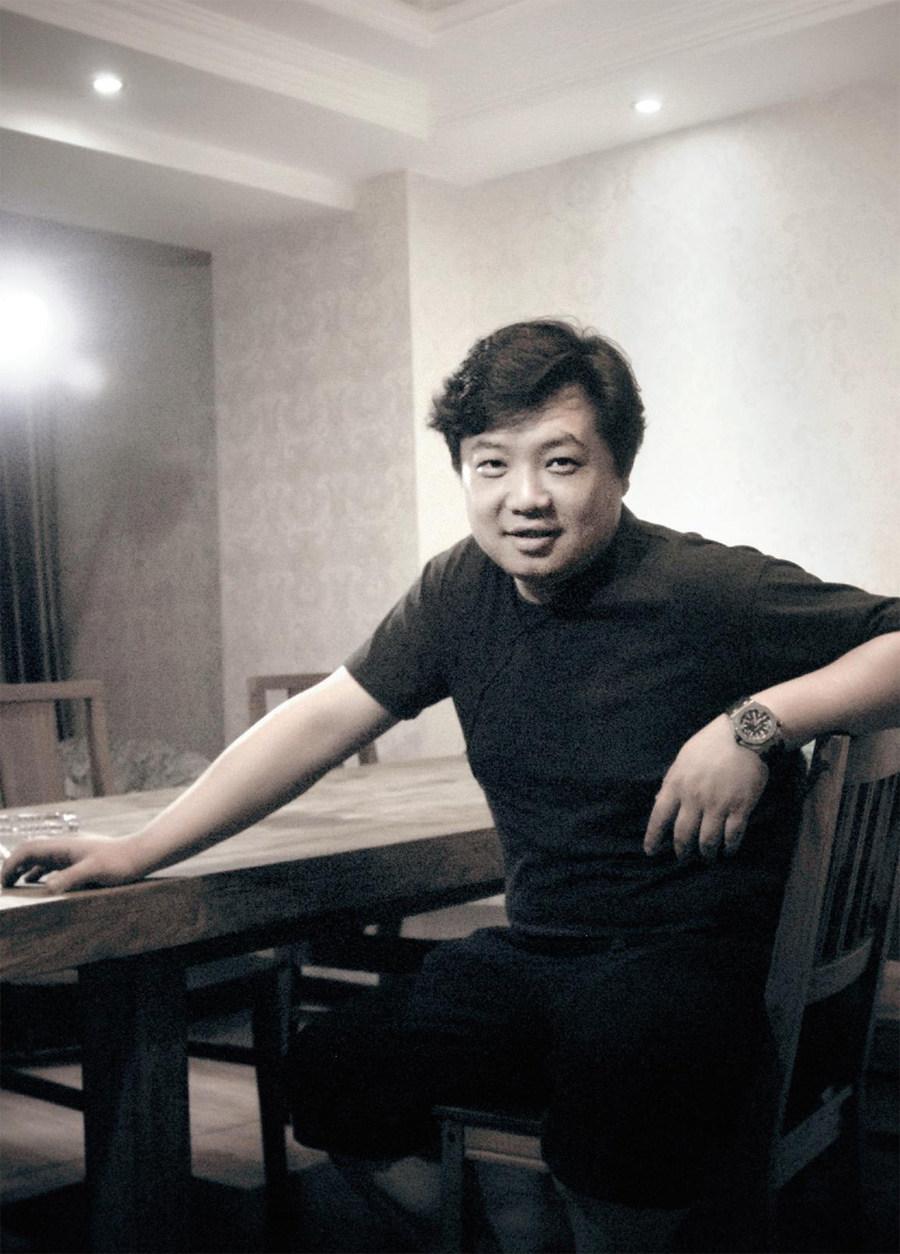
到今天为止,白一骢大部分账号的密码仍然是“戈达尔+数字”,这位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奠基者,是白一骢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时期的精神食粮。
偶像与粉丝,在同样以“偷窃者”为主人公的作品里,在不同国度却有着不同的价值导向:1960年,戈达尔首部故事长篇《精疲力尽》里,主人公米歇尔是一个存在主义色彩浓厚的小偷,他否认善或恶的人性本质,也否定法律和规则对人的制约,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者,终日被国家权力追捕。然而,在中国,根本没有戈达尔的土壤。2015年,经白一骢改变的网络剧《盗墓笔记》上线。在南派三叔的原著里,男主角吴邪是个“偶像式”的盗墓贼,而在白一骢的剧本里,他变成了一个保护国家文物的留学生,誓要“把文物上交给国家”。
这句台词,是网友揶揄白一骢的根源所在,白一骢也成了那个被网友呼吁“上交给国家”的编剧。然而对白一骢而言,这是不得不妥协的“政治正确”,一个盗墓贼在中国难道可以成为崇拜的对象吗?
在第一次看到《盗墓笔记》成片的时候,白一骢便料想到了网友可能会有的反应,他自己甚至都有点不认得这部作品了,第一场藏区雪地中的戏被改到了内蒙古的沙漠,杨洋扮演的小哥服装也从剧本里的红色藏袍换成了风衣。编剧在中国影视行业并没有很大的话语权,这种状况在《盗墓笔记》的制作过程中尤其明显。另一个编剧彭阗,在成片中名字被写成“刘阗”,助理编剧张鸢盎则被写成“张鸢鸯”。

白一骢自己也加入了吐槽的队伍中,一个周五晚上,“擦干净屏幕,不是要舔啊,是玩弹幕,和稻米们(《盗墓笔记》粉丝》)一起吐槽屎吃多了的脑残编剧!”这是白一骢在微博发的长文,“忏悔一下毁原著的心路历程”。在此之前的几年,他的微博和朋友圈都是一片空白,这源于他大学时期《艺术概论》课程中一句诲人不倦的标题—《遗世而独立》,白一骢始终认为编剧做完作品不该再去解释什么。
白一骢上一次改编名作,是金庸的《天龙八部》,他同样忐忑和惴惴,“改编名作,就是站在巨人的肩头,看到更远的风光,就要接受更凛冽的风雨”。南派三叔并没有责怪白一骢关于剧本的问题,甚至和他一起在微博上进行解释,撒娇地回答网友的为什么:“臣妾也不知道啊!”
即便是这样,《盗墓笔记》上线不到22小时点击便已经破亿,一部剧在质疑和吐槽中创造了点击纪录,在白一骢看来这只是片方的成功,但却是编剧的牺牲。
其实在《盗墓笔记》之前,白一骢就已经是江湖人称的“网剧一哥”了,题材涉猎最广,科幻、警匪、盗墓、灵异、玄幻皆有,同时作品成活率也最高,2014年,他制作的《暗黑者》以3.2亿的点击量在业内成为现象级网剧。
在此之前,白一骢做了十几年传统电视剧、电影的编剧,他做过历史正剧《忽必烈》,做过古装武侠《天龙八部》,做过民国年代《新安家族》,做过家庭伦理《中国式相亲》,做过抗日谍战《风云传奇》,唯有在互联网,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
从电视剧到网剧的转变,对白一骢而言并不存在所谓的妥协或者拥抱,他仍然两者兼顾,对好剧抱有追求。早年的电视剧工作让他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便决定在网剧领域尝试更多的创作突破,这必然不是挣大钱的路数,但网剧让他有机会自己当制作人,就可以决定剧作走向了,不会像面对《盗墓笔记》时一样无奈。白一骢工作室的编剧之一、20岁出头的女孩汤祈岑玩笑地说:“白老师在下一盘很大的叫做创作自由的棋。”
创作自由,是白一骢在更早的时候就走过的一条路,这条路曾经艰难到让他背叛自己。
那是在快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央戏剧学院,老师对白一骢说:“学院不是教给你思想的,而是教给你表达,每个人的思想是独立的,你有好的坏的思想,我只是教你怎么表达出来。”白一骢的艺术追求来源于此,追求的最初阶段人格是分裂的,伴随着年少轻狂和眼高手低,总希望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表达,“那个阶段觉得商业是恶心的,鄙视商业表达的直白和肤浅,固执地认为好的表达应该是含蓄的。”
那个时期里,白一骢热爱的都是阿巴斯(伊朗新浪潮代表人物)和戈达尔,拉片课上让越多同学睡着的作品他越喜欢。不过现实不允许他一直漂在高处,他是新世纪第一批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同学大多都走向了对文艺的叛逃。
大学毕业之际,他用平时撰稿攒的钱,穷尽各种人脉关系拍了一部毕业作品《水调歌头》,“讲的是我们这代人的迷惘”。在北京一个叫九转胡同的地方,他把摄像机架在两位主角前面。最后一个镜头,主角在胡同里走,但镜头永远要早一点知道往哪拐,镜头先拐,再拍两人拐弯。这个镜头拍了两天,在晃动和急速转弯的镜头中,白一骢想表达那个时候他们这代人的人生是看不到未来的。
后来白一骢听说他的这部影片在德国拿了奖,但他并没有钱去到德国,彼时的他已经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大学毕业以后所有的问题一拥而来,他不得不把以前鄙视的东西捡起来,“以前你觉得得给你提鞋的人,现在你得去帮他写剧”。白一骢成长中的第一次自我否定来自于此,现实越惨烈否定就越彻底,于是就在一瞬间丢掉了戈达尔和阿巴斯。
他觉得困境在于:“搞艺术的都不是主流,但是主流那帮人都在搞艺术。”即便到了今天,白一骢在专业领域有了自己的成就,他还是不会再回过头去看任何一部戈达尔,“我要是去看戈达尔,那我得有多无聊”。
在他的世界观里,这也像印象派的崛起,莫奈反对陈旧的古典画派和沉湎在中世纪骑士文学而陷入矫揉造作的浪漫主义。但革命党最终都会成为保守派,这是颇为无奈的现实,“人都会变成当年自己讨厌的样子,但你又会喜欢现在的自己。当你有了当年你想要的东西的一部分,你会觉得丢失的那一部分不重要了”,说完这话,他点燃这个采访过程中的第五支烟,坐姿随意得颇像杨贵妃,逗得周围的人大笑,看起来他很满意自己目前的状态。
在他担任制作人和编审的网剧《暗黑者》里,白一骢塑造了一个游离于法律外的杀手Daker,在黑暗中行使正义,每当一个“有罪”的人被杀害,Daker都会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你为什么受到这样的惩罚。像贾樟柯的《天注定》一般,每一个故事都是当下社会存在的问题,不同于《天注定》悲观结局的是,白一骢还想探讨什么是正义,正义也是种复杂的力量。
全剧最初的一个案件就是Daker对学校“豆腐渣”工程的惩治,利益链条被慢慢揭开的时候,观众看到的是曾经在各种新闻报道中拼凑出来的完整现实。
编剧团队对Daker的犯罪逻辑有过无数次的讨论和考量,其中网民关注的社会问题是原创案件的主要来源,比如吃狗肉、校园暴力,即便这些案件累积了网民最激烈的情绪,但在最后都做了最克制的处理,“如果Daker只是一味站在观众和舆论一边,那剧集播出后,观众是痛快了,但并不能阻止这类不公正现象的再一次发生。比如校园暴力,Daker不可能真的去惩治那些坏学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校园暴力?歧视?误解?跟风?家长和学校又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样将Daker融入到案件中去,希望观众在娱乐过后稍有思考,才是Daker行为的意义”,这是《暗黑者》编剧汤祈岑对这部戏的认可。
这也是网剧与以往刑侦剧最大的不同,天生带有互联网基因。除了作为编审的白一骢,其他编剧都是20岁出头的小年轻,即便各种剧作的技法是互通的,但在互联网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自然带有其特点,编剧之一的张鸢盎说:“白老师更像一个幼儿园阿姨—我们使劲儿开脑洞,他来帮我们缝补,我们撒丫子乱跑玩儿high了,他负责把我们抓回来。”
互联网反馈给白一骢的数据同时让他知道观众想看什么。可当年还是小编剧的时候,白一骢经常被一些制作人忽悠,总是告诉他观众要看这个要看那个,他当时颇为困惑,他们怎么就知道观众要看什么?这些制作人给的解释是:“我有经验。”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经验,但他们给钱只能听他们的。到现在,轮到他给编剧提要求了,白倒是觉得自己没什么经验,但数据会告诉他,这是互联网给他的安全感。
2015年7月,三里屯优衣库事件发生的第二天,白一骢策划拿着一张Daker的字条,放在优衣库的更衣室,罪行一栏写着“网络暴力”。
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是最孤独的人,从电视剧的迷茫里抽身出来,白一骢拿着自己的资金不断往网剧里投,希望能做一些有价值的事,回报是越来越多的点击量和更多的作品。身边不乏人对他说:“现在网剧还不挣钱,等挣钱了我分分钟进来都不晚。”白对此不以为然,“网剧是个B to C的产品,不好看别人根本不会点,好的网剧门槛很高。”
资本随着互联网的滚烫在逐步转移,“去年做网剧,演员和工作人员都愿意拿一个比较低的钱,今年演员不会因为你做的是网剧就降低一下价格,就回归正常了。所有人员的成本都在增加,整体成本都在增加,主要是演员,我们整体增加了30%,有的翻两倍,有的翻10倍,因为去年真的太少了”,白一骢说。
现在的白一骢生活在一种努力开拓疆土的希望中,棋局胜负难判。他更长远的梦想是拍摄《银河英雄传说》,科幻外壳下的权力斗争和人性一样永恒,“有压迫就有反抗,当反抗成为主导力量的时候,就会开始重新压迫,我对它的喜爱就在这儿。”这和他的个体生命有或多或少的共鸣,构成他深刻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