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歌声
2015-0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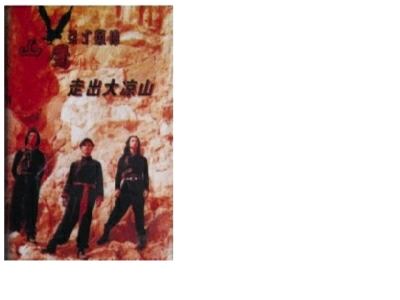
很多年里,凉山都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孤儿们的苦难故事构成了外人对那里最主要的想象。
从前的摇滚歌手,现在的彝族村官恩扎洛格经常教孩子们唱歌,希望他们有一天能通过音乐摆脱贫穷,改变命运。
在一代代的凉山年轻人眼中,音乐是一条自我救赎的通路,也是走出凉山的捷径。
南方周末记者 刘炎迅
南方周末实习生 孙良滋
发自四川成都、凉山州
37岁的摇滚歌手恩扎洛格,已经在阿尼村做了6年村支部副书记。
他皮肤黝黑,留着3毫米长短的寸头,圆脸,微胖,一说话就爱笑,憨憨的,但当他拿起自制的两根弦的月琴,随意弹上一曲,立即显现出另一番景象。他微佝着的身体、四下摇摆的脑袋,双眼半睁半闭之间,含混迷离的神情,专注于自己的琴声,像一个善泳之人沉迷于深潭的清澈和平静。
他曾在成都的夜色里跑了7年酒吧,在成都摇滚圈子里小有名气。但在家乡,他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村官。他有意识地教村里的孩子唱歌,指望他们有一天能通过音乐走出凉山。
很多年里,凉山都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毒品和艾滋病制造了大量孤儿,他们的苦难故事构成了外人对那里最主要的想象。今年8月,大凉山彝族孤儿木苦依五木的作文《泪》,成为最新的一则苦难故事。一句“饭做好,我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让无数人潸然泪下。
现实与梦想,其实充满了挣扎。
念经超度他家祖坟的灵魂
阿尼村在一座2600米的山上,属于一个叫“井叶特西”的乡,位于美姑县城向北十几公里之外。在绵延起伏的山岭之间,阿尼村小得像一粒芝麻。
时间过得如同静止。年轻男人们几乎都外出打工了,留下了孩子、渐入中年的妇女和老人,还有一些牛羊和鸡。几个带孩子的女人,几乎都是怀里抱着一个正在吃奶的,身边跟着几个四五岁到七八岁不等的。
17岁的德金古,身材苗条扎着马尾辫,早早去了东莞打工,这让她的目光与同伴不同,透露出一种明确而清晰的神色。再过两个月,就是彝族新年,她回来准备过年。“过完年,还是要出去打工的。”
“将来呢?”
她顿了顿,“最终还是要回到村里,结婚,生孩子。日子不就这样过吗?”
这里的女人结婚后,就用所有的时间带养孩子们,过完一生。
凉山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截至2014年,常住人口中,彝族人口为2226755人,占49.13%。据《凉山彝族自治州概况》,凉山是四川省扶贫攻坚重点地区之一。全州3733个行政村中,贫困村就有2561个,其中1187个列为全省重点贫困村。
回到美姑县,成为阿尼村的村官,对于恩扎洛格而言是个意外。2009年,他在成都唱歌跑酒吧的第7年,唯一的弟弟因为吸毒,死了。年老的母亲一下子无人照料,恩扎洛格不得不回家。在母亲和亲友的劝说下,他暂时放下摇滚,拿起《申论》,考了几次,终于考上了村官。
从数字上看,阿尼村共有787人,尚没有艾滋病患者,只有三个吸毒人员,另有三个孤儿。在整个美姑县,凡是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孩子,都要接受艾滋病防治知识教育。
然而,恩扎洛格很快感到:这份工并不容易。有一次建村道,规划好的路线要从一户人家的祖坟过,那家人就来把路拦截了,然后村主任去协调,还被打了。恩扎洛格耐着性子去,聊了一天才发现,这户人家感到没有被尊重,赌了一口气。
最后的解决方法是:请个毕摩来,念经超度他家祖坟的灵魂,搞定。
毕摩是彝语音译,“毕”是“念经”之意,“摩”则是“有知识的长者”的意思,是一种专门替人礼赞、祈祷、祭祀的祭师。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但他不打算再说了。“很多事儿,还得慢慢去改变,多说无益。”
唱歌是特别适合这个民族的一技之长
村里的小学上午9点半上课,下午3点多放学,之所以这样定时间,是因为家最远的孩子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中午带着土豆来吃。
凉山彝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滞后。连这个调查数据都是滞后的——到2000年底,“普九”地区人口仅占全州人口的29.4%,民族地区基本未实现“普九”。
恩扎洛格经常教孩子们唱歌,用他自己做的月琴。有时教一些流行歌曲,有时教他自己创作的歌,比如这首《巴普街》:“巴普街最富裕的是哪家?牧羊村里最穷的是哪家?有多少金钱也不会知足,那么有多少文化才能跟上你的脚步?”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本人热爱音乐。他认为,唱歌是特别适合这个民族的一技之长。就像美国的黑人孩子,往往通过打篮球能迅速出人头地。
彝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在市场化时代,中国最早走出来的少数民族歌手“山鹰组合”,就出自凉山。
“千万支的火把照着你的脸,让我看清楚你的容颜。噢我最亲我最爱的大凉山……”那是1993年,三个身着民族服装的彝族小伙子红遍了大江南北。他们的专辑封面上印着五个字:走出大凉山。不少人是因为这盘磁带,才知道了彝族和凉山。
作为众多彝族文艺青年眼中的教父级人物,46岁的山鹰组合的灵魂人物“老鹰”吉克曲布已经剪去了及腰长发。如今他也回到凉山,在西昌创建了自己的音乐公司。
深目高鼻的吉克曲布出身毕摩世家,从4岁起就背经文,一直到12岁,后来在工厂里面做了七八年的工人,电工钳工挖矿装炮眼儿什么都会。
当年在矿上,因为孤独和对未来的迷茫,年轻的吉克曲布抱着断了一根弦的吉他,写了一首彝语歌《想妈妈》,这首歌后来被视为彝族地区第一首流行歌曲。私下里用录音机翻录,传播开来。翻录的人都赚了不少钱。
尽管如此,但年轻的吉克曲布也没有想过会以唱歌为生。市场化,离凉山太遥远了。那时,彝族只有一个出名的歌唱家曲比阿乌,她是中央民族歌舞团来大凉山招募时发现的,“这是被官方认可的,然后就去上各种晚会,代表一个彝族的形象。”山鹰组合的另一个成员瓦其依合说。
看到自己写的歌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吉克曲布有了新的想法,或许可以出去闯闯,于是在1993年,他和瓦其依合等人组建了山鹰组合。这是中国第一个出名的少数民族音乐组合。带着彝族风味的旋律,铿锵的汉语加彝语的说唱,他们奇妙地火了,火得一塌糊涂。尽管他们很不习惯广东的生活,但这里当时是中国音乐的第一市场。▶下转第6版
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在凉山,每个司机都有两盘山鹰的磁带。从此以后,组合成了彝族歌手最常见的表演形式。
前几年以一曲优美的《不要怕》又火了一轮的瓦其依合是凉山昭觉县人,他的家在离西昌四十公里的一座山上,晚上看得见灯火辉煌的西昌城。“那个地方直到三四年前才通上电,(在时间上)离西昌起码有二十年的差距。”他对南方周末记者感叹。
他对这件事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年冬天,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来凉山视察,去了他的家乡。进了一个农户的家,当时就流了泪,说我没有想到,在中国还有这样穷的地方。然后就从秘书那里拿了几千块钱给这个农户。
这一段都被随行的摄像机拍下来了,新闻没有播。
你必须学会自己本民族的唱腔
在山鹰组合的影响下,大批凉山的青年希望通过音乐这条路,走出凉山。
1996年,另一个彝族音乐组合“彝人制造”也横空出世,通过北京的放大效应走红全国。两位主要成员是一对亲兄弟,曲比哈布和曲比哈日,都是美姑县人。更多的人指望:未必要走广州、北京那么远,至少能到成都、西昌,也是一种改变。这里有现代化的生活。
“当时太想唱歌成名了。”1983年出生的歌手阿甲尼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尽管彝族民间传统,视那些痴迷唱歌的青年为“不务正业”甚至“二流子”,但真要唱出了名气,就会被众人尊重,“那种感觉太好了。”
在西昌上学时,阿甲尼古就模仿山鹰组合,将自己写的十几首歌,录制成磁带,在校园里也传唱一时,又一度拉着同学搞了个小乐队。
对于好不容易走出凉山,在社会上辛苦打拼的彝族青年,唱歌成名具有巨大的诱惑力。阿甲尼古说,他当时在一家旅游公司工作,带着游客爬山。有一次下雨,山上雾很大,他独自站在海拔3600米的山顶,等着一批客人,都是某机关领导。他独自等了很久,看着自己淹没在浓雾里,四周寂静无声,就突然流下眼泪,“觉得自己辛苦,心里累,没有方向。”
他后来和乐队一起,去广州的酒吧闯荡过,但几个月下来,他就感到“大城市太复杂,又不认识人,又没有钱,怎么混?就挺想家。”很快,他从广州回到了西昌。
爱唱歌的彝族青年,试图融入“外面的世界”总是困难重重。山鹰组合也曾如此。瓦其依合回忆:在广州,他们被经纪人说过很多次:吃饭别吧唧嘴,更别那么大声,这样才显得斯文,有涵养。
“这让我们一时不能适应,要知道在山里时,吃饭都是很响的,你要是不出声,父亲就会拿筷子敲头,骂道‘你吃个饭,你见不得人吗?像个娘们一样。”
最终,山鹰组合在合约到期后离开了广州,在随后的三年里,他们游历云南贵州等地,去少数民族聚居区采风。那是他们最穷的三年,但也是最开心的。之后,他们又去了北京,开了自己的音乐公司,迅速成了彝族歌手在北京的聚会中心。
对于那些挣扎于音乐圈的彝族歌手们,想出头很难。如今在音乐圈里有些名气的“声音碎片”乐队主唱马玉龙也是彝族人,他比山鹰组合还早了一年去北京。不同的是,他是只身北漂。“当时和乐队排练时那一瞬间,是很幸福的,但在生活上,我就没办法真正融入。”他说。
山鹰组合到了北京后,马玉龙天天和他们混在一起。说彝语,聊凉山,做彝族的菜。很多年以后,他对瓦其依合说:“当时你们如果不来的话,我可能就抑郁,或者疯了。”
彝族女歌手吉克隽逸靠汉语和英文歌走红之后,给时尚杂志拍了一组大胆性感风格的照片,也在凉山地区惹起了很大争议。另外一个与此相对的现象是:很多男青年争着声称自己是她从前的男朋友。
最近两三年,吉克隽逸和莫西子诗等彝族歌手,陆续通过选秀脱颖而出。在吉克曲布看来,这让更多的凉山青年产生更大的幻觉,“太急功近利了。很多青年根本不会唱母语歌曲。我们小时候,就会唱四百多首彝族民谣。”
现在,他带徒弟时,必定告诉他们一个理念:“你必须学会彝语,学会自己本民族的唱腔。会唱汉语、英文歌曲的多了去了,还缺你一个?”
人活着,最重要的是要有奔头
恩扎洛格时常想起外面。
他时常说,有一天他还会带着自己的乐队杀回成都去。这番话常常被视为一种玩笑,没有人太当真。
“外面”有他的音乐,他的梦想,充满现代的诱惑。虽然这诱惑也会带来伤痛。他时常会想起被毒品害死的弟弟。
台湾女学者刘绍华曾在凉山扎根研究多年,写了《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一书。她指出:在凉山彝族,有抽鸦片的传统。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海洛因流入凉山,迅速成为年轻人之间展现时尚与经济能力的指标,享受流行的海洛因,象征着购买力,而购买力的高低则反映出在都市里生存本领的能耐。
在成都,一次演出后,恩扎洛格跟着朋友“飞了一次叶子”——抽大麻,第二天醒来,感觉很不好,就像宿醉一样,头昏沉沉的,从此他再也不碰。而海洛因,他更是想都不敢想。2009年弟弟吸毒死了,这一下子改变了恩扎洛格的人生。他不得不回到美姑县侍奉母亲,暂别音乐。
但他毕竟是一个在成都混过7年摇滚圈的歌手。回了家也总想着重操旧业。除了教孩子们唱歌,他平时没事就弹琴吊嗓子。在西昌,他保留着一支名叫巴普街的乐队,偶尔有空,也会坐8个小时的山路车,去和乐手们练上一曲。在他看来,这是保存梦想的火种。“星星之火,随时可以燎原。”
回乡的日子过得缓慢,也少了大城市的压力,他感到安逸,但不适之感也随时迎面撞来。他和久别的同学、朋友相聚,酒过三巡,席间谈论最多的是“谁的局长是怎么当上的,县长是怎么当上的……”
这让他感到厌烦和无聊。他发现,自己的价值观正在被改变。
阿尼村山头,山风渐起,云雾散开之处,空气清明通透,可以看出去很远。恩扎洛格停顿了一下,说,“人活着,最重要的是要有奔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