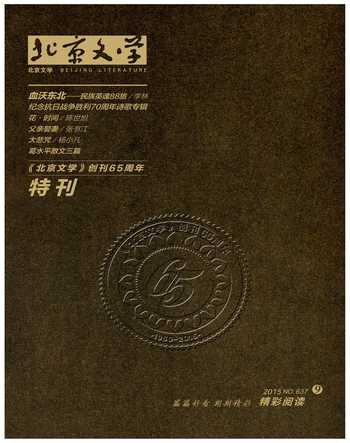北京,我的天堂!
2015-09-10毛银鹏
我幼小的时候,就唱“天安门上太阳升……”把北京当成天堂。
高中毕业时,我给北京作家写信,想在北京找事做,学写作,但没盼到回音。
后来在县城百货大楼卖匾,头儿们见我生意好,就赶我走。他们请来警察,带着手铐,我吼叫:“我打算坐牢!暂不打算杀头。”他们才散开。过后见我卖处理鞋,门口挤满顾客,他们就请来流氓,把我弟弟打得头破血流。我给当警察的亲戚1000元钱,亲戚连打几个电话,得知他们早与公安局长串通好了,便反说我不对。
这时,在我店门口,过路的女人与弟弟的朋友相碰,女人扯住他喊人帮忙,他用皮鞋“砰砰”地踢女人的头。我怕踢坏了,叫她松手。她说找不着他。我说我负责。
我带她去医院,她叫我给100元算了。我说还是请医生看看。刚进医院门,她就晕倒了。她住几天院,叫我给2000元了结。随后她不听医生劝阻,带钱回家。不久她头痛,又来医院。她的亲戚找派出所长,说她被踢成神经病,要我治好,还得把她的几个孩子抚养到18岁。
我只得让警察抓走弟弟的朋友,可所长没敲出他一分钱,就说病人躺在医院里,打她的人没钱,只有找我负连带责任。我只得偷偷到蕲春开店。
我县原叫广济,蕲春人把我当“广济儿”。我买肉,屠夫给骨头;我开自行车店,税务特地来“查税”,几千的罚我,地痞一辆接一辆推走车,民政局摸奖,叫我供自行车,可近2万元的货款一分都不给;我找法院打官司,法官把钱装到自己口袋里,还哄骗我签字了结案子。我负债9万元,利息5分。
我送大儿上蕲春幼儿园,没想送礼给老师,她们便把这“广济孙”,放在角落坐,不理他。他一天坐到黑,不吭声,裤子尿湿又坐干。冬天老感冒,以致身子瘦小,头很大。打针的护士找不着血管,连叫:“怎么办呀?小萝卜头!”我立即想到“渣滓洞”,不禁心绞。
我满脑子都是一些故去的亲友,便把他们写在纸上,取名《故人西辞》。很多熟人看后嘟着嘴:“写这么多死尸干啥?”“你心理不正常,只适合当焚尸工。”“看了绞心,看不下去。”一位朋友说写得好,而别人说他想占我便宜。
我的生意刚好点,一个蕲春小伙子就在我店旁,照我的样子开店。一次我拿黑漆喷黑车上的碰痕,觉得黑车不起眼,便喷上白点,顾客很快买去。小伙子连忙问批发的老板:“老毛的新货,黑车起白点,是在你这里进的吗?”接着,他那瘦小的妻子,不时到我店门口转,向我店里望。终于看到我在一辆红车上喷白点,他赶紧照办。后来,她在我店门口,转得更勤。几次,她把瘦长的脸伸进店里,撩开黄细的乱发,瞪圆凹陷的小眼,看到我坐在店后角落看书,才长吁一口气离开。
接到在鲁迅文学院进修的刘海东先生,对我稿子赞赏、催我来北京的信,“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我立即带全家来北京。原来我不知道可以来北京。
我送大儿上炭儿胡同小学,年轻的女班主任赵老师急得流泪:“他老不吭声,今后成个什么人?不行!一定得说话!”她一次又一次俯下身子,温柔着腔调,给他讲故事,带他玩游戏,终于让他有说有笑了。
我把《故人西辞》寄给《北京文学》,白连春老师说“直逼灵魂”,杨晓升主编说“绞心正是力量,不痛不痒不是艺术”。很快发表,获《北京文学》奖和老舍文学奖。老家那些原先嘟嘴的人现咂嘴:“杰作!”“一般人看不懂。”
老家有人说,我拎一蛇皮袋鞋,从看门的发起,由一楼发到五楼,稿子才发表,才得奖。我懒得对他说,《故人西辞》的发表,编辑没吸我一根烟;得奖,评委们并不认识我。即使得奖后,开会碰到一块儿,我也不跟他们套近乎。
2007年,女儿得回老家读高中,我全家只得回去。我拿出奖杯,母亲说:等你在县城买了新屋,摆在新屋里。
我一到县城,县文联正开会,被朋友哄到会场,主持人大声地说:“会议临时增加一项:现请刚从北京回来的著名作家、‘老舍文学奖’得主毛银鹏先生,谈创作经验!”我说我算不上作家,在台下随便聊几句。大家连声叫我上台,使劲鼓掌。地区领导来与我握手谈话。大家留影时,也喊叫:“毛作家呢?请到中间来!”
我的老朋友打来电话,说县里一位领导请我吃饭。我不善于与领导打交道,便说我忙。而朋友还打电话,说饭已办好,并有好几位领导等着我,要我一定去。我去后,说现在回乡开店。身旁一位问我有几个孩子,我微笑着说三个。那领导立即大声地说:“你今后别张扬。否则,一定有人搞得你倾家荡产!”我马上说:“我是没小心。”他才口气柔些:“在小县城生存,不比大都市。”饭后,朋友提醒我,应该回礼。可我请这领导吃饭,他今天说明天,明天又推后天。我每天脑子里就考虑着、预备着,无心干别的。他“忙”过六七天后,才挥手来到餐馆:“今天,我推掉了三个局长的宴请,我说毛银鹏请我多次了,再不去不行!”
店门一开,就有工商、税务、城管、卫生等检查,开口都吓人。在北京开店,只交房租,从不交税。他们懒得与你论理,丢下单子:几月几号前交清,否则罚款!朋友劝我找熟人,说别人有路子的少交,甚至不交税,而那些税都得上缴,只得加到没路子的人头上。他替我送烟给一个板脸收税的头儿,走到那头儿面前,低声下气:“你父亲──他老人家还健旺吧?”那头儿立即满脸红润的柔光,荡漾开来。
我回去不久,父亲就“肺癌晚期”!我多年在外,多次抱愧无能行孝。这次回乡,给不久于世的父亲洗澡,自然是轻轻地遍处擦抹。父亲说母亲粗脚毛手,“还是银儿洗得舒服!”我连忙又帮父亲洗澡,特别用心,细细地洗。父亲拖长腔叫:“好过哇!──银儿!这澡洗得太好过了!”父亲说我连他的屁股都擦得干净。
可随后,我与母亲、姐姐走在街道上,母亲对我说:“你男子汉,要多搞钱。照顾你父亲,是我和你姐,妇道人家干的。你在外,并且是在北京,搞多年,回来还租房住,别人撇嘴!没搞到钱,别人都没眼看你!”我立即粗起嗓子:“我有眼角扫这些小人?”旁边的人们,马上围拢来,睁大眼望我。母亲还说:“古话说,只有挑箩借谷,没个挑箩借字的。”我浑身冒汗,一股热血,从心里往喉管飞冲,正要张口,姐慌忙低头拉着母亲,扯闲话匆匆走开。接着,遇到一个老朋友,他说别人说:“银儿回家,是在外混不开。”他叫我对别人说,我租住的房是我买的。
大儿到县城读初中,我送烟给老师,说大儿爱上网,他立即伸手去卡大儿的颈。后来,他给我打电话,说大儿没上学。我找遍网吧不见大儿,到学校,大儿就坐在教室里。他把大儿调了座位,竟没认出来。
2009年,女儿高考一结束,我全家就又到北京。大儿到广安中学读初中,班主任也是年轻的王老师,叫大儿当学习委员、升旗手,让他到天安门前站荣誉岗,还在他的作业后批:“你是个有潜力的学生,我要全力打造你!”还教大儿注意身体。大儿渐渐长得高大漂亮,暑假在西单服装店打工,很多姑娘找他买衣服,呼他帅哥。
我写了三万多字的《父亲》,觉得太冗长,但删改不了,想听编辑老师的意见,而怕《北京文学》的老师们认识我,不便直指缺点,便写上大儿的名字寄去。新来的素不相识的王秀云老师,竟删改成一万多字,用大儿的名字送审。杨老师很快发表它,得知是我写的,他又教我写在北京的经历。
现今,我常穿着旧布衣,骑着电动车,从大栅栏去沙子口批货。路旁花草树木繁茂,空气清香。我顺便走进永定门公园,坐在树下看书、改稿,仰望碧绿叶隙上高远的天空,心里响起:
“我的天堂──北京!”
责任编辑 王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