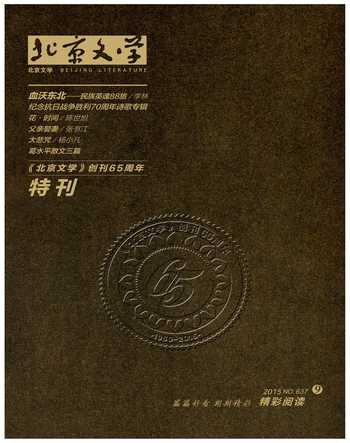每个人都有一块福田
2015-09-10安然
首夏清和,接到杨晓升社长微信,约我谈谈写作和命运的关联。
是时,我正在幽雅的杭州灵隐一带袖手闲逛:读书、发呆、登山、漫步、听雨,看鸟;或者溜进一个街铺,跟店主扯扯天、喝喝茶、谈谈花道、论论禅意;若黄昏到来,我就坐在一棵开花的树下看年轻的男僧女尼来往穿梭。这样,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迷人的早早晚晚,是中国作协给的一个采风机会。如此闲福,一方面令我沉醉享乐。另一方面,又令我惴惴感恩:这样闲适自洽宁静清澄的人生,不正是发端于写作吗?而《北京文学》,就如我的命运福田,为我开出了一朵又一朵高贵端庄的莲花。
从前我在一家大银行工作,我不喜欢。凡是与文字和花朵绝缘的职业我都无法忍受。银行之前我是气象员,也是数字,只有数字。
从前我试图打碎铁幕一般的日子,试图能够借助写作敲开一丝缝隙,试图在缝隙里种下文学的一抹绿意。我打算依靠这抹绿意喂喂饥渴的性灵,让她相信,人生即便不能风月无边,至少也能在秘境里开出三两朵摇曳的野雏菊。仅此而已。我是一头被蒙着双眼的驴,沿着生活的磨盘转个没完没了。我也不会知道,那时所有的作为,正是在寻找自己命定的一块福田。
故而,我初期的写作,纯粹是潜水玩儿的性质。
2000年左右,网络文学风生水起,我以“寞儿”之名,大量地在各种文学网站和文学论坛发稿。跟大多数网友不一样:因为怕被单位打入冷宫,我很小心地不让人知道我是谁;我也不在乎作品被说长道短;我更没想过,如此写作跟纸媒会有什么关联?我没想要名气,加上收入算得优裕,我也不图稿费。
但是,我肯定不是一无所图,而是大有所图。
我图的是,通过秘境里的悄然写作,借助隐匿身份的操弄文字,为迷茫的灵魂找到一个出口。对于我,文学是唯一的可能通途了。
谁能想到呢,这样一棵偷着下种的文学种子,会慢慢由嫩芽长成新藤,而最终,这根新藤生机勃勃地融化了一堵无望的铁幕:一切推倒重来,“诗意地栖居”,不期然成为我如今的日常而非一个梦。
转折起源于那个中篇小说——《陀螺的舞蹈》。
2003年初,不知从哪里看到,《北京文学》厚待新人,凡是自由来稿一律会认真处理。恰在这前后,有人充师傅相告,“一个无名之流,基本不要想在杂志上发作品的事,很难!”这话令我好奇,如果真有所谓“文坛潜规则”,我倒想挑战一下。
我把小说寄了出去。寄过,便也忘了。
继续写一些长长短短的所谓文章,或者放在网上任由评头论足,或者只是扔在电脑里令其如坐深宫,依旧连在报纸上发一个稿子的兴头都没有。我只管写,写出来了,就比什么都好。写是唯一的目的,写是一种疗伤。
想不到,《陀螺的舞蹈》在2004年2月发出来了。这在我就像做了一个梦。本来试着玩儿的一件事情,现在弄成了真的。小时吃瓜,瓜子顺手扔在了门前野地里,过些日子,它竟发芽生长开花了;又过些日子,居然结瓜了。那时,对着一个小小瓜儿,有些惶惶复惶惶,更有些小小人儿的小小自得,以为不小心做了一件惊动天地之事。现在,我同样似受不起这份郑重的回报:那么长的一个小说 ,写着玩儿的一个小说呀!“师傅”要是知道了,该不该自掌嘴巴?文坛并不黑暗,迎接我的是一线光明。
要到现在,我才能知道,当年一些看似无心的偶然,实在是命运一步一步的必然。
过了两个月,总编杨晓升把电话打到银行。一是夸了夸《陀螺的舞蹈》,二是就小说里的故事简单聊了几句人生,记得那些话,让我的心暖了好几下。话头一转,他问,你手头还有没有现成的作品,要质量比这个小说好的。“至少是一样好。”他补充道。
我纯属业余写作,拿得出手的小说还没写出来。但有一个近万字的散文放了半年,写后也没想过拿它怎么办,那时,也没见过有哪家报纸杂志可以发这么长的散文。
两个月后,2004年6月,《你的老去如此寂然》发表出来。我大吃一惊,一是为它能发表,它可完全没有所谓散文路子和章法;二是为它的发表之快!后来我从责编张颐雯那里知道,是总编交代,“尽量要以最快的速度发表它”。
诧喜之余,我觉出一些遗憾,因为从样刊上看到有“老舍散文奖”这个赛事,而此文并没放在这个栏目之下。遂壮着胆儿给总编打电话。杨老师这样答:你放心,不放在这个栏目同样可以参赛。
参赛, 这一等就是两年。
2006年7月,晓升老师写来邮件,轻描淡写地告知了获奖消息。“第三届老舍散文奖”,且排头名。一直到这时,我才从前两个作品发表的故作淡定中激动起来,天上掉下馅饼,“老舍散文奖”的名号烫得我有些发热。甚至,到8月颁奖时,我不顾正在住院,拔掉吊针就一个人前往北京,以至于出站后,在候车处虚脱晕倒……
我小小地爱着虚荣,令自己有几分生动和可爱。
在这两年里,其实我的工作生活已经发生了大的转变。为了可以过上“一觉睡到自然醒”的好生活,为了拥有随时看花听雨的自由,我一咬牙,从银行辞了职。
我抱着一沓稿子,其中就包括几本《北京文学》,闯到我所在城市的报社,毛遂自荐应聘副刊编辑。不过一年多时间,凭着对文字的热爱,和对终于可以睡饱觉的好日子的珍惜,我的副刊做得颇有人气。而“老舍散文奖”的适时到来,更是在报社和读者圈中激起了热烈反响。报社破天荒整版刊发了全文,版面上放有第三届老舍散文奖的LOGO。此番动作,为我赢来了众多粉丝,下至十几岁的中学生,上至八十多岁的老夫妇。一时,“安然是男是女,是老是少”的询问声不绝于耳。与此同时,网上发生了大量的转载和传颂。没想过要出名的我,一不小心成为小城的“名人”。有时候,遇到一个人,他或她,完整地背出作品中的段落并不奇怪。
而我最大的幸福,在于拥有了在银行不敢想象的自由:
获奖之后,报社更加爱重我的这支笔,不会让我去写应景文章、官样文章、文学之外的文章。“不要写坏了她的笔”。
因为个人体质偏弱之故,单位认为,破例给我弹性上班的自由是有价值的。
因为这个奖项,也因为工作实绩,单位对我足够信任和支持,给了我最大的工作自主权,“给她一个平台,她能飞多高就让她飞多高。”
从这个奖项出发,又四年,2010年,我的《哲学课》再度获得第五届老舍散文奖;又四年,2014年,《亲爱的花朵》入围第七届老舍散文奖,并获得《散文选刊》首届“新经验散文奖”。
获奖不能说明什么,但获奖所带来的工作生活的改变,心灵境界的成长,却足以说明了文学的力量。原来,一切发自心灵的文字都是有光芒的。
还要什么呢?多年前我偷偷摸摸写作,仅仅是为了暗中给铁板一块的生活增加一线生机。如今,我终于可以坦荡光明随时随性,去闻一朵花开,去看一只鸟飞,去听一阵雨落,去守一回日出……徘徊在如此风雅的人世,我变得安然明亮从容宁静,我毫不怀疑,我是真的找到了自己命定的福田。
对于《北京文学》,一万句感谢太轻。不说也罢。我且依旧,慢慢细细写下去,活下去。
责任编辑 张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