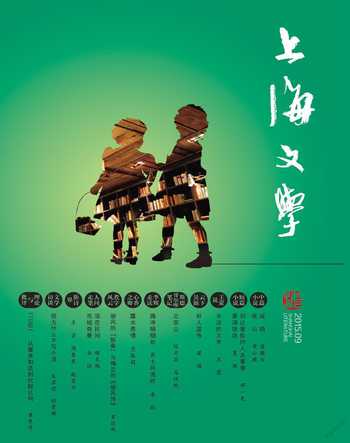好人蓝伟
2015-09-10梁鸿
梁鸿
夜晚就要到来了。
蓝伟坐在那块大石头上,从石头里传出来的寒气把他的屁股冰得麻木。他背对着工棚和湍水河道,看着河坡里通向吴镇的弯曲杂乱的路。
河岸低平,黑枯树,白芦苇,寂静无声。连只昏鸦都没有。蓝伟坐着,隔一会儿左右环顾一下,用手摸着光溜溜的下巴,抖动着腿,“嘿,嘿嘿”笑着。他的笑声怪异,有点儿奸诈,又带着点儿虚弱和掩饰。
蓝伟又掏出手机,盯着看一会儿,手机没有任何反应。他开始仔细阅读里面的一个个短信。短信也很快看完。他四下里看了一眼,把手机放在地上,双手合十,眼睛闭着,嘀咕着什么,然后,睁开眼睛,双腿下蹲,扎成马步,手腕运气,朝着手机的方向推去,嘴里断喝着,“哈,哈”。
手机纹丝不动。
一队蚂蚁在手机旁边庄重而充实地行走着,肩上似乎扛着一个大家伙。蓝伟蹲下去,认真研究蚂蚁走路的步伐,他的头随着蚂蚁的步伐而点着,嘴里不自觉地发出声音,“一、二、一”、“一、二、一”。过了一会儿,他觉得无聊,朝蚂蚁部队吐几口唾沫,蚂蚁被淹到汪洋大海里,步伐乱了,开始东倒西歪起来。
蓝伟抬起头,继续朝吴镇方向的路看着。他头仰着,眼睛略微向上,他不会让自己哭。他只是寂寞而已。
远处一个模糊的黑点,越来越近,伴随着“突突突”的声音。蓝伟“腾”地站起来,盯着那越来越大的黑点和逐渐清晰起来的身影。
毅志骑着摩托车,鼻青脸肿地出现在蓝伟面前。前踏板上放着一只锅,锅用绳子固定着,后座上绑着一个鼓囊囊的白色袋子。
毅志一边解着摩托车上的东西,一边吸着气,嘴里骂着,“日他妈,这天气,真是冷透气了。”
蓝伟在一旁,“嘿嘿”笑着,口齿不清地问毅志,“你咋想起来过来?”
“我咋想起来过来?还有谁来?红星?还是哪个啥花儿会来?”
毅志把捂得严实实的锅递给蓝伟,“这是我刚熬出来的萝卜菜,还热着哩。这些够你吃几天的。”
毅志的萝卜菜是一绝。年二十三小年,大部分人家都在集上买菜,回家炕火烧。毅志那一天的主要活儿却是熬萝卜菜。白萝卜切成厚厚的片,几大块猪肉,后腿,猪蹄,五花,几种相间,混在一起,放在大锅里熬。说“熬”,是因为要把肉炖得恰到好处,外面完整,里面一捣就烂,而萝卜吃到嘴里,还略有筋骨,但肉香完全浸入。初吃不算什么,三天之后,萝卜略显酸味,又带着香,吃起来清爽绵长,味美异常。
工棚里杂乱不堪,并且似乎比外面还要冷。一张小行军床靠在墙角,床上的被子没叠,上面乱扔着一些书。煤炉已经灭了,周边地上堆着些煤球、煤渣和没洗的锅碗瓢勺。
蓝伟折几根枯枝,重又把煤炉生起,把毅志带来的那锅萝卜菜放到煤炉上。毅志找出一个纸箱子,铺上张报纸,开始掏那个大塑料袋里的东西:热腾腾的火烧,用蒜拌好的羊头肉,一袋炸豆腐炸鱼块,一瓶泸州老窖,还有一束干粉条,一棵大白菜,几头洋葱,几把干面条,一块新鲜猪肉……
毅志变戏法似的不停往外掏着,蓝伟在旁边说,“粉条我这儿有,上次红星来带了一些,面条我这儿也有,包包菜我这儿也有,这儿啥都有。”
毅志撇撇嘴,说,“是啥都有,就是个孤家寡人了。”
“来,来,喝一口,还是这泸州老窖味儿最醇正。”蓝伟端着酒杯,贪婪地喝一大口,又挟几块羊头肉,使劲嚼几口,吞咽下去,说,“不愧是吴秃子家的羊头肉,唉,毅志,你还记得咱们上高中时凑钱去吃吴秃子家板面,真是好吃啊。咱们每个人都吃一大一小,小周能吃,每次都要一大一小,吃到最后,又要一小碗。”
“记得,咋不记得。有一次老郭就凑了一份钱,非要把刚谈的女朋友带上,吹嘘着给大家个惊喜,说该女眼睛很大,非常漂亮。到了一看,大家都笑到抬不起头,那女子眼睛极小,不过弯弯的,倒挺可爱。关键是,她也吃了一大一小,活生生地把小周那小碗给吃了。”
毅志“扑哧”一声,刚进口的酒几乎被喷了出来,接着说,“后来大家都围攻老郭,那厮居然耍赖说,我就是觉得她的眼睛最大。”
“前年我到山东找老郭玩,他请我吃涮火锅,说起那女孩,居然还说那姑娘眼睛大,也不知道老郭的眼睛是长哪儿了。不过,老郭家现在的‘老磨’也不错,虽说没知识,但一心一意跟着老郭,长得也比那女孩强多了。”
“是啊,当年老郭出去打工,走时还海誓山盟,中间也书信来往好久。可是,等老郭从山东回来,人家已经跟一个部队上的人结婚了。”
蓝伟喝着酒,“嘿嘿”笑着,嘴里不时发出“嘶嘶”的响声,像是品咂,脸上开始泛出油腻的红光。他比任何时候都怀念高中时代的生活。那个瘦小机灵的少年,笑起来灿烂阳光,充满无限活力。
中年的蓝伟,脸和身体都开始发胖。脸虚白泛红,像长年糊着一层油,眼睛和眉毛被挤在了一起,让人分辨不清,很有点可怜相。
谁都说蓝伟是个好人。
一到高中,蓝伟的好就充分发挥了出来。蓝伟高中三年,再加上复读的两年,都是班长,他热心于各种公共事务,鼓励、帮助每一个人,没有偏见,不搞派别,不弄小集团。两个关系不好的同学都可以成为蓝伟的朋友,蓝伟总是能想出办法化解掉双方的矛盾。蓝伟也深得同学家长的喜爱,夏天麦收,他带着同学轮流去各家割麦子;暑期炕烟,他去闷热的烟地掰烟叶;秋天秋收,又去帮着收玉米打黄豆。一群年轻人,突乎东西,虽然劳累,但开心无比,有些镇上的同学,家里并没有地,也跟着蓝伟跑东玩西。许多同学家长都把蓝伟当自己的儿子,依赖蓝伟甚至要超过自己的孩子。
所有人都尊重、敬佩、喜欢蓝伟,那些美好的词语,热心、无私、诚恳,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理想主义、开朗活泼,等等,用在蓝伟身上都不过分。蓝伟也知道大家喜欢他,认同他,越发好起来。
高中的第二个春天,去土谷山春游的时候,蓝伟和同班的艳春之间有了丝丝的异样情感。
土谷山离吴镇有四十公里的样子,一个灰扑扑的土山,既不高也不秀丽,但是平原之上,有那么一座山,总算有可爬的地方。
一群人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而去,到了那里,才发现,土谷山里驻扎着一支军队。交涉之后,军队的小伙子们不但领大家参观内部的兵器设施,中午还管一顿午餐。大家欢呼雀跃。
穿蓝白底格子裙的艳春坐在飞机的驾驶仓里,戴上飞行帽,只露出一张圆润娇嫩的脸,歪头看着蓝伟,娇笑着叫道,“蓝伟,怎么样?好看吗?”
蓝伟突然看到了艳春的眼睛,娇羞中似乎还带一点点嗔怨。那时候艳春还是一个清秀的小姑娘,写一手好文章,说话刻薄,高傲冷淡,同学们都不太敢接近她,不过也使她身上笼罩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魅力。艳春负责班里的墙报,也是校文学社的社长,经常找班长蓝伟商量事情,或者拿自己和别人的文章给蓝伟看。但是,蓝伟整天忙忙碌碌,几乎没有注意过艳春。
那一天,蓝伟格外兴奋。山上山下来回奔忙,安排休息,照相,检查大家是否掉队,向军队领导表示感谢,到处都是他的身影。
午饭之后,军队小伙子要和他们打一场篮球友谊赛,算是告别仪式。那一场友谊赛,这帮学生败得一塌糊涂,就连号称五高中篮球第一人,身高一米八五的张胜也几乎没有招架之力。最后一场时,另一个同学脚意外扭伤,急需有人替补。蓝伟自告奋勇上去。
蓝伟把白衬衫扎到腰带里,踌躇满志地进到场地里。大家都以为他球技很高,但是,待跑起来,才发现,蓝伟步伐僵硬,夸张别扭,虚弱可笑,像没头苍蝇一样,只是盲目地跟着大家蹦来跳去。大家第一次发现,原来蓝伟毫无章法,对眼前的形势没有任何判断。
那次春游,拍了很多照片,却一个也没成。拍照的同学不懂得对焦,全糊了。
在这之后,蓝伟并没有和艳春约会。艳春先上了大学,和别人谈了恋爱。有同学告诉蓝伟,蓝伟沉默了一下,随后“嘿嘿”笑了两声,问起了艳春男朋友的情况,说也不错,祝福她。
对于蓝伟而言,他会努力淡化一切失败感,一切无可无不可,他实在太忙了。艳春没了,只在他心底留下极淡的遗憾,他很快就被另外一个女生吸引了眼光。
两年后蓝伟考上大学,艳春和男朋友已分手。艳春给蓝伟写了一封哀怨异常的信,责怪蓝伟不常联系她,就这么忘了老同学,等等。蓝伟读着信,“嘿嘿”笑着,回了一封长长的、情深意重的信,意思是你这样兰心惠质的女孩子,一直觉得高攀不上,也希望你有更多选择机会,但心里一直藏着对你的喜欢,等等。
他这样写,当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既然是自己一字字写出来的,写着写着,就是真的了。再说,他也陶醉于自己的抒情和其中优美的词句。于是,他又把自己的回信抄了一遍,在朋友们间朗读、传看,叙说自己如何在初见艳春时就有的好感。
“那时候真是能吃啊”,蓝伟盛一碗萝卜菜给毅志,“就这一锅,不够志钦一个人吃。记得到老管家里割麦,老管家那口大锅,满当当的,面条,再加上两大盆菜,咱们几个人,一人三冒尖碗捞面条,吃得干干净净。吃完了,才想起老管妈和老管爹没吃。”
“老管这家伙,不够义气,毕业后不和大家联系。聚会叫他也不来。”
“也离婚了,孩子归他,嫌当老师工资低,当律师后才有好转。”蓝伟吃着饭,饭的热气薰在他的脸上,看不见他的表情。
“离婚了?”
“他不让我告诉任何人。我去平县看过他,胖得不成样子了。”蓝伟叹口气,“孩子才四五岁,围着老管,看着也怪难过。”
毅志看着蓝伟,蓝伟的表情非常平静。他好奇地问,“你啥时候去看的?这沙厂你能走开?”
蓝伟抖动了一下腿,“唉呀,也是说不成,他为一个案子要出差,找不来人看孩子。说我也没大事,死活要我过去。我和红星说了下,红星也同意了,都是老同学。去了,先喝一场,都醉了,哭哭笑笑的。”
毅志的表情有点哭笑不得,似有埋怨,却又无奈,停顿了一下,小心翼翼地问蓝伟,“说起来,你多长时间没回穰县看你家星月?”
“看她干啥?她妈照顾得很好。”蓝伟又喝了一口酒,“嘿嘿”了一下,“时间长不见,也不想见了。突然去了还打扰她。再说,我这儿也走不开啊。”
蓝伟的表情淡淡的,无意深谈下去。毅志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样的对话已经持续好几年了,他端起酒杯,一口闷了下去。
几年前的一个深夜,蓝伟敲响毅志家的门。蓝伟衣着凌乱,眼神恐慌,似大难将至,或者说大限将至,隐约有坍塌之感。不一会儿,艳春也赶来了,非常紧张担心的样子,看到蓝伟在和毅志喝茶,长吁了一口气。毅志和蓝伟在外间喝茶,听着里间艳春时高时低、忽笑忽哭的模糊声音,还有毅志老婆雪丽有一搭没一搭的应和声。蓝伟什么也不说,催他去睡觉,他也毫无回应。
艳春和毅志大学毕业后都在县城上班。蓝伟在供销部门,艳春在一个单位干财务,蓝伟的父母亲给他们看小孩。蓝伟在单位里逐渐风生水起,很快成为领导的秘书,跟着领导四处出差,在单位说话也颇有分量。艳春却对人苛刻,眼睛里容不下一丝灰尘,对蓝伟和他家人多有埋怨,两个人经常发生争吵。在同学圈里,艳春几乎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蓝伟是同学们心中的神,是老大,是个最好的好人,他那么热心张罗一切事情,回到家里却受到苛待,这不公平。可是,每当大家半开玩笑这样说时,艳春总是不屑地撇撇嘴。
一夜诉说之后,清晨起来的雪丽似乎对艳春的印象大有改观。她对艳春关心备至,看到蓝伟,则不屑一顾。
艳春和蓝伟各据院中石凳的一角。艳春期待地看着蓝伟,蓝伟低着头,一直避免和艳春的目光相遇。
艳春走过去,半蹲在蓝伟面前,轻声问他:“你到底做了没有?你给我说个囫囵话,我心里好明白。”她的声音有委屈,又包含着愤怒。蓝伟被摇晃着,一言不发,身体越来越低。艳春一叠声地问着,那问话的含义除了委屈和愤怒,似乎并非对所问的事情一无所知,而只是不愿意相信。她抱着一丝丝渺茫的希望,想得到对方一个否定的回答。
蓝伟的沉默正是承认。艳春坐到了地上,抓住前来扶她的毅志的手,哽咽起来。
蓝伟脑子里混沌一片,毅志、艳春,那暗红暧昧的房间,那俗艳的女子,还有那些警察,在他面前晃来晃去,一个个像鬼影一样,离他非常远,却又都瞪着他。他仿佛看到一片黑暗的湖水,他行走在上面,就要掉下去了,掉下去了。他害怕极了,想张口呼救,却发不出声来。他不知道往哪儿去。
毅志让艳春坐定喝茶,有事慢慢说,大家都可以帮着解决。
艳春盯着毅志,怒气从蓝伟身上慢慢转移了过来,“你们这帮子狐朋狗友,天天出谋划策,要他当官,教他这那,巴结这个,讨好那个。现在倒好,出事了,谁来替他?”
蓝伟朝艳春摆摆手,说,“有话好好说,扯人家毅志干嘛!”
艳春看着毅志,眼睛里是“他又是这样子”的神情,毅志知道,下面的话,他们俩可能争论过无数次了。
“毅志,你可看看,一说到他朋友,他就不高兴。我怎么伤心都可以,他朋友有丁点不高兴,家里有丁点事儿,他跑得比人家爹比人家兄弟姐妹都快。小周妈生病,他跑前跑后,我在外出差,他闺女发烧他都回不到家里去。人家妈是他亲妈?话说回来,他管他亲爸亲妈了吗?”
蓝伟不明白这女人在想什么,他从来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错,他脑子里像发烧一样,模模糊糊,微弱地辩解道,“小周在广州,回不来,我不去帮他,替他张罗,他妈连医院都住不了,总不能看着人死吧?”
“你帮了他?你帮了他,所以,到他妈死,他才愿意回来。你要是不帮他,说不定他早就回来了!你帮他,他才拖延着不回来,实际上是你置他于不孝不忠不信之地。”
艳春冷笑着,把蓝伟的话一句句驳回去。蓝伟愤怒地坐回到凳子上,头别着,一言不发。毅志也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无精打采。雪丽在一旁站着,带着幸灾乐祸的神情看着眼前的一切。
毅志确实是蓝伟狐朋狗友中的一个,并且是最要好的那个。蓝伟回到吴镇,第一个落脚点一定是毅志这里,他们在一起筹划、布局蓝伟的仕途,一起探讨该如何和领导、同事相处。蓝伟去医院帮忙看护小周的母亲,他也到处打电话给老同学,让大家去看望。小周直到母亲去世后才回到穰县,他虽略微有所不满,但却并没有想到艳春说的这一层。
“你永远都在忙着取悦别人。别人想到的,你替人家进一步想,别人没想到,你也替人家想出来。你真的因为心底善良才去帮助别人吗?你不是。你只不过想让别人说你好,想获得别人的承认。你是在表演,你把表演看得比你老婆孩子,比你爹妈要重要得多。”
此时的艳春,像个哲学家,沿着她的思路,越说越深,越说越远。雪丽崇拜地看着艳春,挨坐到她的旁边。艳春拉起雪丽的手,对着毅志说:“就说你吧,毅志。你去年到底为啥欠了人家那么多债,你为啥不给大家一个交待,你都拿钱干啥去了?你让雪丽在那儿哭,让吴叔吴婶在那儿哭,你就是不说。你这算孝顺?”
雪丽的眼泪要下来了,她瞪了毅志几眼,紧捏着艳春的手,像终于找到了靠山。艳春又盯着蓝伟,像是要盯出火来。
“毅志有难了,你个王八蛋二话不说,到处替他借钱,就差给人家下跪。你啥也不问,你不管他是吃了喝了嫖了还是干啥了,你只管替他借钱。你这到底是害他还是帮他?你们互相遮掩,肯定是知道彼此都干了些啥好事!”
艳春尖刻地讽刺着蓝伟和毅志,两个老哥们灰头土脸,各坐一角,像两个挨批的小学生。蓝伟听得模模糊糊,他说不过她。艳春能把一切事情颠倒过来说,并且让大家都信服她。她一直有这个本事。
“你最是个坏人。冷漠、自私、没有情感,一个典型的妥协主义者。你怎么都行,谁都行,生活给你什么,你就接受什么,你永远不能独立于外。什么好东西到你那儿,你都把它变成污泥,就好像人家本来就是烂污泥,然后,你假装好人,假装无辜。你到底是无辜吗?我知道老同学怎么看我,我知道他们背后骂我不孝,骂我苛刻,骂我变成个庸俗女人。可是,难道我想变成这样?难道不是你百事不管我才成这个样子吗?难道不是你自己想去嫖才嫖的吗?难道领导拿枪逼着你进去的?你永远都是个奴才,永远都是!”
毅志听到“嫖”这个字眼,吓了一跳,他向蓝伟看过去,蓝伟的腰佝偻着,头别向一边,根本不接毅志的眼睛。
“你不说,你肯定不说,你不好意思说你干了什么龌龊事,你浑身都脏透了,你们这一群人都脏透了。”
蓝伟冲向艳春,“啪啪”,打了艳春两巴掌。他不允许她这样说毅志。说他怎么都可以,但是,说他的朋友,不行。
艳春瞪着蓝伟,一把推开他,
“蓝伟,你真的就是个阑尾,无用就算了,你还害人。”
毅志看着喋喋不休、怨恨无比却又充满着生活欲望的艳春,突然有点替她伤心。
艳春走了。蓝伟站在院子里,一声不吭,身体萎缩着。土谷山里的篮球场上,那个穿着白衣胡乱奔跑的身影,突然有了某种预兆:孱弱,内在的空虚,随波逐流,为取悦别人而毫无目的地做事,一个可笑得有点让人伤心的跳跃的身影。
毅志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说,“走了也好,咱们俩好好喝一杯。”毅志没有追问蓝伟到底有没有做那件事,他不会去确证。他们是最好的朋友,彼此理解,做与没做,都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
蓝伟依然是个好人。
他忠心耿耿,没有揭发领导,也没有说领导一句坏话,反而是领导,一五一十地都说了。蓝伟被从办公室调出,成了市场部的外勤人员。艳春带着孩子离开了他,很快又结婚成家。不久之后,供销系统破产,整个机构的人都被分配到各乡,蓝伟重又回到吴镇,只在乡政府挂一个名,拿基本工资,一月千余,除此之外,竟没有任何收入。
生活就这样一下再下,走下坡路,真是快得不能再快了。
回到吴镇的蓝伟,像一个流浪儿回到了家,虽然身无分文,却享有很高的声望。那些一直在吴镇生活的老同学又慢慢在他身边围了起来,那些老同学的父母也经常托儿子叫蓝伟去家里玩,吴镇的日常生活关系网中,蓝伟又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环。通过他,你几乎可以联系到所有人。
蓝伟走在吴镇的街道上,笑眯眯的,不断和人打着招呼,看到他熟悉的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他竟有奇异的满足感。他在海家卖肉的摊前停一下,聊会儿天;他在卖菜的大爷那儿蹲下来,吆喝着,帮大爷卖菜,卖完之后,俩人坐在小酒馆里,一两一两喝着散酒,也聊得喜笑颜开;他到罗建设的“彩虹洗化”、到老吴天的五金店、王老怪的民政所那儿喝茶,一坐一个上午。当然,他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毅志的茶馆,和毅志一起扯东拉西。
毅志的新房盖好,宴请大家吃饭。蓝伟组织一帮老同学,凑出份子钱,在吴镇最好的装饰公司买一块巨幅玻璃,要挂在毅志客厅的正墙上。那天中午,玻璃割好,平放在店外的地上,蓝伟拿着大毛笔,蘸着朱砂,运腕写字。毛泽东的词: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蓝伟的字,刚硬潇洒,尤其是末笔,笔稍微微上扬,显得激扬万千,很有气势,和词的内容也相匹配。围观的人阵阵叫好,蓝伟满脸涨红,开心激动,刹那间仿佛又回到了高中和大学时代,那时候,他一直被人围着,他是核心,是阳光,照亮着自己和别人。
众人抬着玻璃,从吴镇的街道走过,有人就问,这是谁写的啊。答曰,蓝伟啊,就是蓝营蓝国栋家的二儿子。于是,就有人作恍然大悟状,朝着身边的人说,蓝伟啊,我知道,那娃是个好娃儿,聪明得很,考上啥大学了,在县里上班,可了不得。又有人说,早回吴镇了,在乡政府上闲班。
蓝伟走在人群的最前面,和大家打着招呼,他的腰挺直了许多,脸上的笑容也深了许多,发散着骄傲和对昔日荣光的留恋。
那整屏鲜红的字挂在客厅里,张牙舞爪,显得浮夸异常。有好几次,雪丽想把它取下来,拉出去,砸掉,还她一面洁白安静的墙,却遭到了毅志的坚决反对。
穰县的生活,那曾经风生水起的事业,消遁得很远。蓝伟从来不和别人谈起,他自己也说不清是否还记得那些事情。自从那个晚上,警察反扭着他的胳膊,把他从那陌生姑娘的床上拉起,让他蹲在墙角,又逼他交待,之后,他的记忆和精神就好像有一部分破损了。他选择性地遗忘了那些场景,虽然之后很多次,他像梦游一样地又回到那里,又寻找那姑娘。他是想安慰她,还是因为刺激想去,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但他是真的喜欢吴镇这地方。看见每个人,他都充满欢喜,就连那充斥在各个角落的阴谋、算计、愤怒,他也充满欢喜地看着。他好像一个心知肚明的旁观者和俯瞰者,以一种风清月白的淡然爱着大家。他觉得他就属于这里,吴镇的人们也觉得他一直就在这里生活。只有那些曾经见过他意气风发的人才惊诧于他的消沉和无为。
蓝伟打起了麻将,身上没钱,就借钱欠债,连女儿的抚养费也给不出。艳春让女儿去要过几次,也托毅志要过,蓝伟只是“嘿嘿”笑着,什么也不说。许多时候,他到朋友家里,也不说什么事,去就进厨房,热心张罗做饭,吃饭劝酒,在饭后的牌桌上替别人摸几把。最后,就歪在朋友家的床上睡着了。
看睡着了的蓝伟,让人心灰意冷。油光滑亮的脸,圆滚滚的身体,油腻不整的衣服,在睡梦里,他缩成一团,头不时惊怔一下,好像在梦里有什么东西追赶他似的。
但是,蓝伟仍然被所有人信任。一旦谁需要帮忙,他必定是第一个出现;外地的同学回穰县,第一个联系的也必然是他;有事请客,蓝伟必是首选陪客人员;婚丧嫁娶,蓝伟必是门口记礼单、收钱的那个人。他成了伤心生活的象征和符号,说起他来,都觉得难过,但他又是家庭里最核心的成员。
“我得走了。我亲戚多,得再熬两锅萝卜菜才够。”
毅志站起来,拿过他的大袋子,又从里面掏出一些东西,几本书,两个笔记本,一叠纸,还有几支圆珠笔。
毅志把书一本本地递给蓝伟,“《唐诗宋词解析》、《金刚经》、《诗经》、《古文观止》,《道德经》和《逍遥游》我找不到了,明天扫房子,我再到书房翻翻。”
高中时代,在学了庄子的《逍遥游》之后,蓝伟给自己起了一个绰号,“逍遥散人”,做诗云:“逍遥散人任逍遥,齐天大圣敢齐天。”那时候,他真觉得自己逍遥,热爱一切,蔑视一切,山河都在他手中,任他纵横驰骋。
“这两个笔记本,稿纸,摘抄写字都行。没事写几句,也不错。你那时候文笔多好,哪次作文都是范文。”
蓝伟接过书和笔记本,“嘿,嘿嘿”笑着,好像毅志在说一个笑话。
有多少年没有听过蓝伟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了?当年毅志到蓝伟的村庄读中学,清瘦的蓝伟带着毅志白天到村庄找人下象棋,打遍下营、梁庄那一片,晚上到处听男人们讲古经,三侠五义,村庄传奇,别人忘记的,他张口就来。人们看着聪慧、伶牙俐齿的蓝伟,“啧啧”称赞,说这娃儿将来要成大器。
上大学的时候,蓝伟曾经和另外一个同学为争论“什么是正义的生活”而互相翻脸。这场争论在老乡同学圈里非常轰动,因为蓝伟并非不是和人决裂的人,何况,那位同学只是一个过于成熟且有点暮气的人,习惯于给人泼冷水。
那同学回吴镇后专门让毅志把蓝伟请过来喝一场酒,席间又争论起来。那同学认为蓝伟过于理想主义,看似忙碌热情,其实毫无观点,对一切复杂的东西不感兴趣,不务实,这样会不断碰壁,最终导致失败。
蓝伟辩驳道,“所有的务实都是耍流氓。因为那意味着对精神的背叛,意味着对社会现象视而不见,那不是人,是鸵鸟。”
蓝伟的话铿锵有力,无可辩驳,那同学表示无话可说,但也并不认同。蓝伟在高中阶段全是班长,大学阶段是班长、学生会主席、老乡会联络人、演讲团团长、书法协会会长,他的身影到处可见,且孜孜不倦。他好像并不纯粹为了当官,当领导者,而是一种天生的热情和随时随地忙起来的性格。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人,在盛年阶段,竟然只能在这沙滩上帮人看沙,孤零零地,被世人所弃?一个人的变化到底从何开始?从一个热情向上的人到艳春说的妥协主义者,这中间到底有怎样隐秘的联系?它们本质上可有共通之处?
艳春说得也许有道理,当有一个小口子被撕开之后,他所有内在的虚弱就都暴露了出来。
毅志边走出去边说,“三十晚上到我家看‘春晚’啊。这破沙厂有啥看的,谁能把这些沙偷走?这红星也是个说球不成,过年都不让人过。”
蓝伟说,“也不是这样,人家红星也没有说非让我在这儿,总得有人看嘛。反正我也没地儿去,这儿也挺好。”
毅志反驳道,“那他就不会说个囫囵话?明知道他不说你肯定会在这儿看着。奸商奸商,人一经商就奸了,老同学的情面都不顾了。话说回来,他给你发工资了吗?”
蓝伟虚弱地回应了一句,“发了发了,人家还是挺照顾咱的。”
毅志发动了摩托车,刺耳的声音响起。几乎就在同时,遥远的地方传来一声闷响,一团彩色的花爆开在空中。才刚刚进入小年,有性急的人开始放烟花了。一声接一声的炸响,那声音传到空旷的河谷,格外撼人,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声音,直进到人心里面。一簇簇的,此起彼伏。从这宽阔低平的河坡里看上去,那烟花格外绚丽、雍容。
毅志打开摩托车的前灯,开走了。那笔直的白灯穿透黑暗,射向远方,一会儿又摇摇摆摆,胡乱划着痕迹。
蓝伟盯着那光亮,看着它越来越远,消失在黑暗中。他仰着头,努力抖动着腿,哼唱着歌,看四面天空上的烟花。
河底的风吹上来,挟带着细沙,刮过树林子,刮过干枯的芦苇丛,刮过他的小铁皮房,铁皮房上薄薄的铁皮发出“呜呜”的响声,又漫过蓝伟的身体,渗到他的眼睛里。那明暗交替的绚烂烟花,照亮河岸上的房屋,教堂上的十字架,清真寺上的圆尖顶,它们正在被黑暗覆盖,模糊成一片温柔的、起伏的剪影。
寒天野地中,就只有他一个人。蓝伟想着镇子里的人,想着他们一个个的神情,不自觉地咧开嘴,“嘿嘿嘿”地笑起来。
他爱这地方,爱极了生活在这地方的每一个人。
他想像着,毅志屁股一吊一吊地在熬萝卜菜,红中尖着嗓子逗自己的孩子,边讽刺着自己的老婆,红星肯定还在牌桌上,旁边换了不知道哪个女孩子。他看到了阿清、老德泉、海红,他们一个个向他走过来,他看到了他们的眼泪、悲伤和内心最细微的想法。
阿清啊阿清,你不要伤心,生活就是这样,总有伤心事。你知道阿花奶奶经历了什么你就会原谅她。我知道,我知道,阿清,你觉得,你心中的那个形象被打破了,穿黑衣的阿花奶奶应该代表一种理想、禁忌和坚守,那对少年的你是一种启发,是对未来精神和生活的向往。可是,阿清啊,你知道阿花奶奶能和小儿子在一起吃饭她多开心吗?小儿子让她吃什么她都愿意吃啊,她可以不笑,可以冥想,可以和神沟通,可是,在她小儿子面前,就什么都不是了。她只想让她儿子快乐、安全。并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是美的、对的,妥协也是美的。
毅志啊,你不要自责。这世间每天都有人无缘无故地死。有多少人走在半路上就死了。有多少人离开家就再也不回来了。可是,毅志啊,你还是不应该买传有家的茶炉平房,生活的有些界限不能超越。不能说传有的死与你有关,可是,毅志,难道你心里不觉得像缺一角吗?那一角永远缺了,再也补不上了。
海红啊,原谅你的父亲,他不是不爱你们,他也是个男人啊。忘掉那个圣徒吧,他不是有意成为你生活中的阴影的,他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啊。
彩虹彩虹,你得离开家。你去海滩边晒晒太阳,吃一次你少女时代最梦想的西餐,买你最向往的吊带长裙。你那么漂亮,你走过大街,会有无数个罗建设朝你吹口哨的。
蓝伟想起了他的星月,他可爱的星月。她已经十三岁了,见过她的人说她有惊人的美,遗传了他清瘦的脸,她妈妈的白皙和黑眼睛。他常常到穰县一初中的侧门口徘徊,等着放学,等着他的星月出来,他好偷偷看一眼。但是,放学铃一响,他飞也般地逃跑了。
眼泪涌了出来,蓝伟用手一擦,用力甩在空中,他摸黑跑进屋里,找出毅志给他的笔,写下了第一句话:
“一朵发光的云在吴镇上空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