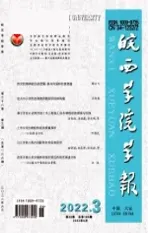宋代刑讯规制及其启示
2015-08-15华志强
华志强
(安徽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230051)
所谓刑讯就是在审讯中对嫌疑人或其他证人使用暴力手段,以取得言词证据,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或作为破案的线索。我国古代早就有“断罪必取服输供词”和“无 供 不 录 案”[1](P4214)的 断 狱 原 则。对 口 供的重视,使得口供在中国古代司法中长期处于“证据之王”的地位,这成为了刑讯现象的诱因,也是冤狱产生的重要推手之一。
以宋代为例,在宋代司法实践中,刑讯也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取证手段。这体现于宋代丰富史料记载中,但在处于“唐宋社会变革”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宋代统治者对刑狱问题的重视,文官阶层依法、据证定谳的不懈追求,加上宋代司法体制的完善,诸种因素已对刑讯现象形成了制约,较大程度上减轻了刑讯的不良作用。宋代为减少冤狱的发生,从国家立法的高度,通过基本法与系列敕令的方式,制定了一整套规范刑讯的制度。宋代防范非法刑讯之立法,较中国封建社会其它朝代相比,更为全面与严密。
一、宋代刑讯的前提条件
宋代法律明确规定了可以刑讯与不得刑讯的各种情形。确立刑讯的适用范围以遏制刑讯的泛滥。
宋代基本法《宋刑统》规定:
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覆参验,犹不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即据状断之。若事已经赦,虽须追究,并不合拷[2](P538)。
即只有那些缺乏嫌犯供认,经过反复审查以后仍难以查获案件实情者,方可拷讯,如果案情事实明白无疑者,即“据状断之”,不必拷讯。宋代贼盗犯罪极为严重,即使是对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贼盗案件嫌疑人实施刑讯,朝廷也下了敕文,进行规范,如建隆三年(962年)敕文规定:
宜令诸道、州、府指挥推司官吏,凡有贼盗刑狱,并须用心推鞫,勘问宿食行止,月日去处。如无差互,及未见为恶踪绪,即须别设法取情,多方辩听,不得便行鞭拷。如是勘得宿食行止,与元通词款异同,或即支证分明,及赃验见在,公然抗拒,不招情款者,方得依法拷掠,仍须先申取本处长吏指挥[2](P542)。
如此详尽的关于拷讯的规定,则为唐律所无。即使对于贼盗刑事案件,只有勘查结论与言词证据不符,或者赃证俱在而嫌犯不招供认罪时,方可进行拷掠。虽说此敕文的规定与宋刑统的规定略有出入,但也反映了宋朝对于严重威胁自己统治秩序的贼盗犯罪的嫌犯的处置仍然十分谨慎。唐律强调“事状疑似”时进行拷问,很容易屈打成招,而宋代强调经过反复调查,在证据确凿的情形下或直接定案或再行拷问,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防止冤诬。
除了上述刑讯的限制条件外,宋代还规定了不适合拷讯的对象。《宋刑统》规定:“诸应议、请、减,若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违者以故失论。”[2](P536)对于老幼病残者刑讯限制体现出人类普适的人文关怀价值。
二、宋代法定刑讯工具
不同的刑讯工具对刑讯后果的轻重具有重要的决定意义,因此宋代对刑具进行了规制。杖是宋代法定的刑讯工具。《宋史》记载:“常行官杖如周显德五年制,长三尺五寸,大头阔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径不得过九分。”[3](P4967)仁宗天圣年间进一步诏令官杖重量“勿过十五两”[3](P4976)。南宋初年进一步规定:“枷以干木为之,轻重长短刻识其上,笞杖不得留节目,亦不得钉饰及加筋胶之类,仍用官给火印。”[3](P4992)这样,刑讯的工具在长短、大小、轻重及表面都有法定标准,制造权也归官府掌控。两宋多次下诏,命令毁弃非法刑具,史载:
(景德四年)黄梅县尉潘义方坐获劫盗,云尝以赃物寄卖酒朱凝家,即逮凝至,遣狱卒以牛革巾湿而蒙其首,燥而愈急,凝不胜楚痛,即自诬受赃,法寺当赎金九斤,诏特勒停。仍申儆中外,应有非法讯囚之具,一切毁弃,提点刑狱司察之[4](P1500)。
南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年)四月诏:“讯囚非法之具并行毁弃,尚或违戾,委御史台弹劾以闻。”[5](P3608)但到了南宋末期,政纲废驰,刑讯现象十分严重,非法刑具开始泛滥。史载:
(宋理宗时)监司、郡守,擅作威福……严限日时,监勒招承,催促结款。而又擅置狱具,非法残民,或断薪为杖,掊击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并施,夹两脰,名曰“夹帮”;或缠绳于首,加以木楔,名曰“脑箍”;或反缚跪地,短竖坚木,交辫两股,令狱卒跳跃于上,谓之“超棍”,痛深骨髓,几于殒命[3](P4997)。
非法刑讯现象是封建社会不可根治的顽疾,但总体而言,两宋与其它朝代相比,酷吏要少得多,刑讯现象亦少得多。宋代朝廷对刑讯进行规范的努力,有效地遏制了非法刑讯的酷滥。
三、宋代刑讯的实行
宋代立法规定,刑讯须按法定程序进行,并对施刑的部位及数量作了严格的规定。
首先,宋代刑讯须经官长批准。《宋刑统》规定:“事须讯问者立案,取见在长官同判,然后拷讯。若充使推勘及无官同判者,得自别拷。若不以情审查及反复参验,而辄拷者,合杖六十。”[2](P538)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始用儒士为司理判官,令诸州讯囚,不须众官共视,申长吏得判乃讯囚。”[3](P4971)由司法长官同判决定刑讯问题显然是一种进步,雍熙年间取消此制属于退步,但由儒士掌控刑讯显然是对晚唐五代以来武人把持司法所造成的刑讯酷虐局面的纠正。
宋代捕盗官及狱吏不请示长官而擅自拷讯犯人,要承担法律责任。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法官参详:“自今捕盗、掌狱官不禀长吏而捶囚,不甚伤而得情者,止以违制失公坐;过差而不得情,挟私拷决有所规求者,以违制私坐。”[4](P2105)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十月重申:“诸州典狱者,不先白长吏而榜平民,论如违制律,榜有罪者以失论。捕盗官获盗而未问者,榜勿过二十;非盗而辄榜之,亦以违制论。挟私非理虐害平民至死者,论如故杀律。”[4](P2339)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五月再次下诏:“大辟公事,自令长吏躬亲问逐,然后押下所司点检勘鞫,无致偏由,出入人罪。若依前违慢,致有出入,信凭人吏擅行拷决,当重行朝典。时感德军司理参军杨若愚不申长吏,拷决无罪人骆宪等,加石械上。若愚特追一官,典押狱卒各刺配,因是有诏。”[5](P6720)该诏在处罚杨若愚的同时,又申儆各级长吏,必须将刑讯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防止胥吏滥刑。
其次,宋代规定了刑讯执行人、杖数及施刑部位。《宋刑统》规定:“诸讯囚,非亲典主司,皆不得至囚所听闻消息。其拷囚及行罚者,皆不得中易人。”[2](P539)《宋刑统》还明确了回避制度:“诸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五服内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并受业师,经为本部都督、刺史、县令,及有仇嫌者,皆须听换推,经为府佐、国官与府主,亦同。”[2](P539)
《宋刑统》对拷打的次数及刑讯的间隔时间作了规定:“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数总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拷满不承,取保放之”[2](P539);“每讯相去二十日。若讯未毕,更移他司,仍须拷鞫,即通计前讯,以充三度。”[2](P540)
关于施行部位,《宋刑统》明确规定:“决笞者,腿、臀分受。决杖者,背、臀分受。须数等。拷讯者,亦同。笞以下,愿背、腿分受者,听。”[2](P545)
再次,对于拷掠数满而嫌犯仍不承认罪行者,《宋刑统》规定:“诸拷囚限满而不首者,反拷告人。其被杀、被盗及家人亲属告者不反拷(被水火损败者,亦同)。拷 满 不 首,取 保 并 放,违 者 以 故 失 论。”[2](P541)《宋史》记载拷囚数满而囚犯仍不承认罪行者即行释放的案例:有盗慈孝寺章献皇太后神御服器者,即就执,李绚以属吏,拷掠不得其情,辄释去[3](P10029)。
四、宋代非法拷讯的法律责任
宋代对官员违法刑讯行为,实行严厉制裁。《宋刑统》有相关的立法规定:
诸决罚不如法者,笞三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即杖粗细长短不依法者,罪亦如之[2](P545)。
若拷过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杖数过者,反坐所剩;以故致死者,徒二年。即有疮病,不待差而拷者,亦杖一百;若决杖、笞者,笞五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半。若依法拷决,邂逅致死者,勿论。仍令长官等勘验,违者杖六十[2](P539)。
有挟情托法,枉打杀人者,宜科故杀罪[2](P541)。
另外,窦仪等人的参详则针对违法刑讯致人死亡的不同情形,规定了相应的刑事责任:
今后如或有故者,以故杀论。无故者,或影迹显然,支证不谬,坚持奸恶,不招本情,以此致死,请减故杀罪三等。其或妄被攀引,终是平人,以此致死者,请减故杀罪一等。所贵不陷无辜,得惩奸弊[2](P542)。
宋代在追究官吏非法拷掠嫌犯至死的法律责任时,以刑讯人故意或过失的不同犯意而确定其罪刑的轻重:故者以故杀论,即处斩刑,比唐律大大加重;过失者又分2等,一是拷死无罪平人者减故杀一等,二是拷死有罪之人减故杀三等。这种以故意或过失不同犯意以及被拷讯人有罪无罪为标准的原则,比唐律更加合理,而对非法刑讯官吏的处罚也更加严厉。
在《宋刑统》立法之外,宋朝廷还屡次降诏,本着从严、从重的精神惩治非法刑讯者。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年)颁行的《司理掠囚致死以私罪罪之诏》曰:
国家钦恤刑事,重惜人命,岂容酷吏恣为深文、掠治无辜,致其殒杀。损伤和气,莫甚于斯。风翔府司理参军杨燕、郑州参军张睿,并掠囚至死,已从私罪决遣。今后犯者,并以私罪罪之[6](P741)。
宋代违制失公坐之罚是杖一百,违制私坐则徒二年,可见宋代在追究违法刑讯者的法律责任方面,本着从重的原则,以“私罪”处罚。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八月诏曰:“自今勘鞫官须尽理推勘本犯,不得以刑势及元奏抑令招服,致有枉曲。如囚事□窐及被诉虚招情罪,别勘诣实,其元勘官当行朝典。”[5](P6606)可见宋代对非法刑讯行为实行责任倒查原则,追溯并惩治案件的原审判官员。
宋代不但从重惩治非法刑讯的官吏,而且在铨选官员时注意不使用那些有非法刑讯前科之人。史载:
(神宗元丰七年丙戌)给事中韩忠彦上言:“朝奉大夫俞希旦权发遣祥符县。希旦近知滑州,以拷无罪人死冲替,应入监当。神宗得知,祥符为朝廷选阙,始著令,乃首选希旦,恐非立法择人之意。”诏改差人[4](P8277)。
宋代另一个比唐代发展之处,就是对被刑讯者因刑讯死亡期限的确定。有时官吏拷囚时,嫌犯并没有被当场打死,但被打伤,一段时间后才死亡,这种情形下是否要追究官吏拷囚致死的法律责任,唐律并没有具体规定。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六月八日,臣僚上言:
州县刑禁本以戢奸,而官吏或妄用以杀人。州郡犹以检制,而县令惟意所欲,淹留汛治,垂尽责出,不旋踵而死者,实官吏杀之也。乞依在京通用令,责出十日内死者,验复。如法重者奏裁,轻者置籍,岁考其不应禁而致死者,亦奏霰。从之[5](P6724)。
这里的“十日”期限,指的是非法刑讯造成囚犯死亡的期限,可见在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之前“在京通用令”已规定,被刑讯者在拷讯后十日内死亡的,要追究拷讯者的责任,宣和四年根据臣僚的建议,朝廷又把这一法令推行到全国。
五、合法刑讯与非法刑讯的启示
在中国古代,刑讯是合法存在的,超出法律规定范围则属于非法刑讯,而在当代中国,任何形式的刑讯都是非法的。在刑讯合法的宋代,朝廷与司法官并没有利用这一合法权力恣意进行刑讯,而是努力对刑讯的运用进行限制,并且这种努力是见成效的;在刑讯成为法律禁区的当代中国,刑讯现象本不应存在,但一些司法人员却屡屡知法犯法,滥用刑讯,这种现象值得反思。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近代以来的多数国家已废除了刑讯制度,并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刑讯行为的非法性。现代中国的一切刑讯行为在法律文本意义上均属非法,为法律所禁止,通过刑讯所获得的口供也因取证手段的非法而不被采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定罪处刑并不必然地需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我国《刑法》分则也明确规定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2种犯罪,体现了我国对于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的法律规制。也有学者提出种种建议,如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完善我国的证据排除规则以及确立收集言词证据时第三者在场监督权等,这体现了学界试图杜绝刑讯的人文关怀[7]。
宋代对刑讯的种种立法规制,体现了在封建社会刑讯制度合法化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统治阶级为限制刑讯使用范围、减轻刑讯的酷烈程度而做出的努力,这些措施在具有浓厚人文气息的宋代士大夫司法官手中得到运用,对于减轻封建刑讯的酷虐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横向比较宋代与同时期的西欧社会,当时的西欧正笼罩在中世纪神权法统治下,神判司法盛行,名目繁多的火审、水审等酷刑以及司法决斗等在司法中被广泛运用,其文明程度远落后于同时期的宋代社会。
中国古代司法行政不分,行政官员兼理司法,且历代都强调行政长官亲躬事务,这就导致了司法力量的异常薄弱,司法官员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去收集各种相关证据,又迫于办案期限,只好求助于被告人自己招认,刑讯也就有了用武之地。古代侦查技术落后,如果不用刑讯,一些疑难案件不易侦破。另外依据口供定罪是封建社会许多朝代法律上的要求。在古代,刑讯属于合法行为。鉴于以上诸方面原因,对嫌犯进行刑讯也就在所难免。当今司法中,有专业化的司法队伍,有现代化的侦破手段,重证据轻口供更是法律的明确要求,因此刑讯现象在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随着人类司法文明的进步,中国封建社会关于刑讯的立法内容早已随着刑讯制度的废除而成为历史的尘埃,但宋代关于刑讯的立法规制仍然有值得今人借鉴的方面:其一,其中蕴含的轻刑、恤刑的理念值得今人借鉴。轻刑、恤刑这是古人对生命的敬畏,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理念;其二,对超越法律允许范围的非法刑讯予以惩治,可见在刑讯制度合法化的古代,古人尚且能够摈弃这一合法的幌子,能够自觉地对其进行规制,而在刑讯制度彻底非法化的今天,我们必须杜绝刑讯行为。古今司法对于刑讯现象危害性的认识与扼制其滋生的努力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1]清史稿刑法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宋刑统(卷29)[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3]宋史(卷199)[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7)[M]北京:中华书局,1992.
[5]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6](宋)无名氏.宋大诏令集(卷200)[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吕萍,张会中.刑讯逼供产生原因及对策新解[EB/OL].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2013-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