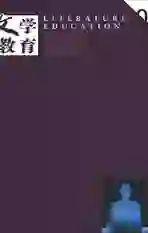多丽丝·莱辛《屋顶丽人》中的两性关系
2015-08-12刘珊蔡奂
刘珊+蔡奂
内容摘要:本文将从女性主义出发,运用福柯的权力理论,劳拉·穆尔维(Laura·Mulvey)的男性凝视学说,聚焦于小说中的女性身体,分析其所承受的男权压抑,以及反过来对男性权威的消解。以期观察在父权体制的规训下,女性身体承载的价值判断以及权力关系,指出两性应突破重重交流障碍,和谐相处。
关键词:《屋顶丽人》 女性主义 凝视 身体 权力
一、引言
英国著名作家多丽丝·莱辛(1919—2013)被文坛誉为“祖母级作家”。因“女性经验的史诗作者,以其怀疑的态度、激情和远见清楚地剖析了一个分裂的文化”而获得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莱辛的作品对女性的命运、独立自由以及两性关系都进行了深刻的探索与研究。虽然莱辛本人一直否认宣扬女权主义,但作为继伍尔夫之后最伟大的女性作家,她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关注妇女解放运动,主张两性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屋顶丽人》(A Woman on a Roof)是莱辛的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收录在她的短篇小说集《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中,发表于1963年。当时正是第二次女权运动的高潮,女性展开反传统文化的斗争,撼动了男性社会坚不可摧的价值观。该短篇小说讲述的是在六月炎热的伦敦,三个修房工人在天台上工作时无意看见对面屋顶上穿比基尼晒日光浴的女人。他们试图与她搭讪,但无论吹口哨跺脚还是谩骂,得到的只是她的冷漠和漠视。最终,三个男人悻悻离开。而最后一天的雨结束了双方的对峙。
作品情节虽简单,寓意却十分深刻。事实上,国内外学者大多研究莱辛的《金色笔记》《野草在歌唱》等几部作品,而她的这篇故事似乎是其最受忽略的作品之一。小说自问世以来,评论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理论对它进行了阐释,其中不乏关注小说中的象征和二元对立以及女性书写的研究。有学者从男女两性冲突和对立的角度对该文进行了解读[1]。也有学者以象征手法为突破口,来探讨莱辛为底层阶级追求平等所发出的声音[2]。却鲜有运用福柯权利理论结合男性凝视学和女性主义理论对其进行解读。本文建筑在前人经典解读的基础之上,尝试将三者结合起来对小说文本进行重新阐释,表现莱辛本人在创作中的女性意识以及期望两性和谐相处的愿望。
二、父权秩序的构建——男性凝视下的女性身体
自从19世纪下半页以来,身体就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福柯发表了《规训与惩罚》和《性经验史》,赋予身体以新的意义,使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福柯以谱系学的方法研究人的身体,提出人的身体体现着权力关系,受到凝视、话语的规训。女人一直从属于男人,成为男人社会的“他者”。也就是说,男人物化女性的身体,女人是男人眼中的客体,一直生活在男人的凝视中。在父权社会中,女性被简化为身体,女性所履行的职责也往往同其身体拥有的职能相关。
三位男人代表男权社会中不同年龄段,不同阅历的男性。他们都不自觉地将丽人置于其凝视之下,以男性标准来衡量女性。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身体被物化,女性的主体性也因此受到压抑。小说《屋顶丽人》讲述了一个女人(后文以丽人代替)在屋顶晒日光浴的过程中处于三个修房工人的凝视之下的故事。她一直被看着,成为觊觎和观赏的对象。当汤姆表白后期待丽人说些什么时,“她根本没有说话的意思,只是她的脊背,她的大腿,她的臂膀都绷得紧紧的——紧张地等着他走开”[3]。丽人的局促不安以及前文中她试图逃避凝视的“挪动”证明了凝视的力量在于它的控制力。福柯认为“看”是一种权力的体现。观看者被赋予“看”的权力,通过“看”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被看者沦为“看”的对象的同时,体会到观看者眼光带来的权力压力,通过内化观看者的价值判断进行自我物化。[4]丹尼·卡瓦拉罗明确指出凝视是为了控制[5],这与劳拉·穆尔维的观点不谋而合。后者进一步将凝视划分为“主动的/男性的”“被动的/女性的”凝视[6],并且主张男人是因为阉割焦虑而成为主动的观看者,从观看中获得快感。
男性凝视的极端形式是窥淫癖(voyeurism)。窥淫癖是指“对某种形式的裸露、生殖器、性行为的观看,以产生性刺激或性满足”。小说中,斯坦利是窥淫癖的代表之一。三个工人的“凝视”物化了晒日光浴女子的女性身体,否定了她作为“人”存在的主体性。女性并不是与男性平等的主体,她们被物化为等同于身体。因此,通过三个工人的的目光,晒日光浴的女子只是一个由“黑头发,晒得发红的结实的脊背”[3]构成的物化形象。女性的“被观看性”使女性沦为一个支离破碎的物化形象,“一个观看的对象,一个景观”。[7]
另外,在福柯看来,除凝视之外,话语中也渗透着权力,人的身体受话语的规训。相应地,女性主义者也认为,男性凝视、话语中都隐含着权力关系,女性身体在这些权力关系中受到压抑。当斯坦利看到丽人整个背部都裸着时,他破口大骂:“我真想去报告警察。”警察是权力的象征,从斯坦利的话中,可以看出,他试图充当警察的角色,剥夺丽人晒太阳的权利。与此同时,他坚决不允许自己的妻子做出同样的事情,“如果她是我老婆,等着瞧吧!”在他看来,女性都应该像浇花女、普利切特太太以及自己的妻子那样温顺,纯洁如“家中的天使”。而丽人在屋顶晒日光浴是有伤风化的,是不遵守“规矩”的。当然这些所谓的“规矩”完全是从男性的利益出发的。
三、父权秩序的消解——“反凝视”/女性做自己身体的主人
女性的身体在层层衣服下面,应该是自由的。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主张,“权力无处不在,身体是权力斗争的场所,女性的身体就是父权制度得以施展其权力的地方”。[8]但丽人不同于传统女性,她悠闲地晒日光浴,她几乎全裸地读着书,做她自己喜欢的事。她悠闲的抽烟姿势显示出她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在这里,父权秩序中的权力无法运作。另外,衣服象征着父权规则对身体的压制,束胸衣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塑造女人完美的曲线,束缚女性身体。而小说中,“只见她胸部裹着一条红色围巾,穿着一条红色比基尼裤。这是她第一天出来晒太阳,她雪白的肌肤晒得发红。”[3]红色在西方文化中象征着放荡淫秽,如《红字》中的女主人公受到众人的侮辱,衣服上被写上红色的A。小说中丽人向传统挑战,她用红色围巾代替束胸衣这一举动,象征着她追求女性身体的解放以及回归本我的努力。丽人通过解放身体成为自身的主人,从而建立起女性主体。她摆脱了父权制度强加在女性身上的限制。
不仅如此,丽人的身体沉默中却具有诱惑力。苏珊·鲍尔多曾指出,很多情况下,即便女人保持沉默,她们的身体也在讲一些挑逗性的语言[9]。丽人虽然只在小说结尾说了一句话,在故事发展过程中一直保持沉默,但丽人的沉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顺从和软弱无声,而是一种进入父权话语系统的他者声音的“呐喊”方式。斯坦利一遍遍地吹口哨,大喊大叫,“他的脸变得通红,他完全像疯了似的”[3]。但那女人纹丝不动,无动于衷。由此可见,三个男人无法通过凝视来规训丽人的身体。丽人通过身体语言和漠视反抗“凝视”,消解了父权秩序,颠覆了父权。
另外,在男权话语中,女性身体常常被神秘化。这种神秘化的倾向在文学传统中十分突出,比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亨利·米勒的《情欲知网》。通过女性身体神秘化,男权话语可以把女性身体描述为任何男性所需求或想象的形象。在男权话语中,女性身体变为男人的臆想对象,而不是真实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在汤姆眼里丽人看起来就像一幅招贴画,或一本杂志封面。而在汤姆的梦中,“她穿件薄薄的黑色女式长睡袍,汤姆一想起她对他的温柔,嗓子就发痒”[3]。在小说中,莱辛营造神秘气氛,将丽人神秘化,使她的身份自始至终处于不确定当中。这里的神秘化向男权话语的神秘化提出了挑战,因为虽然丽人仰卧做日光浴的举动,确实使三位男子产生性欲并使汤姆产生幻想,但在小说的结尾,汤姆在收工之后偷偷溜回来。他径直到丽人躺着的那栋屋顶,爬上屋顶,离丽人几码远。他本想从丽人那里得到他所期望的温存。但丽人一句话也不说,在棕色的毯子上躺下,理也不理他。汤姆的“结结巴巴”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男性话语权威的动摇。“走开”,她说。“听着”她以一种理智的声音说话意味着她费力地控制着愤怒。“如果你觉得看女人穿着比基尼很刺激,为什么不花六便士坐车去利多呢?在那儿能看见成打穿比基尼的女人,用不着爬这么高”。[3]至此,丽人打破沉默将故事推向高潮。17岁的汤姆原本美好的幻想破灭了,正如《阿拉比》中的小男孩,两人虽最终精神顿悟,但心灵深处却对爱情产生阴影。所以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女人对男人身体的反应负有责任。女性之所以做不了牧师,一个既定的理由是,女人只要往那里一站,就会勾起邪念。丽人在做日光浴,她仰卧在那里,使男人产生性欲,但丽人对三个男人的漠视使他们恼怒。汤姆幻想的破灭,斯坦利几近疯狂,连比较成熟的哈里也“六神无主”。三个男人的不同反应暗示男人在地位受到威胁时的某种焦虑感,也足以看出两性交流存在的重重障碍。
四、结语
莱辛曾在她的《金色笔记》1971年版序言中指出: “女人们都是懦弱的,因为她们处于半奴役的状态下太久了,那些准备为她们真实的思想、感受和经历抗争的女性人数,与那些被女人们爱着的男性人数相比,太少了。” 这位屋顶丽人就是敢于抗争的女性代表,她漠视三个工人的轻蔑,维护了自己的尊严。该小说通过表现“他者”反抗统治的力量来消解父权制。当丽人对女性身体的自由深信不疑,并决定用行动去主宰身体的时候,她便建立起女性主体性,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而不是沦为父权制/男性权力施展的对象。由此可见,女性身体是权力施展的焦点,既可以沦为父权体制掌控女性生活的标志,也可以成为女性争取自由和自主的符号。莱辛认为,人类社会是由女性和男性组成的,无论是男性统治女性还是女性统治男性,都是片面的过激行为,“只有两性之间相互支持和谐相处才是女性及至男性实现自由、幸福生活的唯一出路”[10]。这与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中国道家思想中也有类似的文化精神倾向,即“阴阳和谐”。所以,女权主义的终极目标不是解构父权制,而应该倡导一种整体伦理观,摒弃所有等级思想,建立起一个不同价值体系来重新评估出于弱势的他者的价值。
莱辛在作品中致力表现女性身体所承受的压迫,却没有在作品中就女性走出压迫给出任何简单的答案。但是丽人作为新一代女性所表现出来的觉醒的女性意识已跃然纸上。小说结尾的雨代表着希望,代表酷热中两性紧张对峙关系的结束,这不得不说是个充满希望的结局。虽然真正的两性平等在历史上还没有实现过,将来建构“女性乌托邦”之路依然任重道远。但从长远来看,两性之间建立一种更加平等和谐的关系还是很有可能的。
参考文献
[1].黄美红.“凝视”与“漠视” [J].安徽文学,2010(10):1-2.
[2].彭润润.平等的呼唤——试析《屋顶丽人》中的对比和象征[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9):16-18.
[3].多丽丝·莱辛著,吴煜幽译.屋顶丽人[J]. 当代外国文学,1995(3):66-71.
[4].周晓君. 凝视中的权力——对多丽丝·莱辛《屋顶丽人》的解读[J]. 学理论, 2009(22):61-62
[5].Dani Cavallaro. 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The Magic Variations[M].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2001.
[6].Laura Mulvey.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Key Works, Rev.ed[M] Oxford: Blackwell,2006.
[7].袁荃. 当汤姆偷窥微笑的美杜莎——多丽斯·莱辛《屋顶丽人》的福柯权力理论解读[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2):50-54
[8].刘岩、马建军著.《并不柔弱的话语》——女性视角下的20世纪英语文学[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9].苏珊·鲍尔多. 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不能承受之重[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10].彭丽华. 莱辛与两性和谐的新女性主义[J]. 求索,2009(3):198-199.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