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隔离的比较研究——理解社会背景的多样性
2015-08-06书评作者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副主任
书评作者 袁 媛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 副主任
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 副院长
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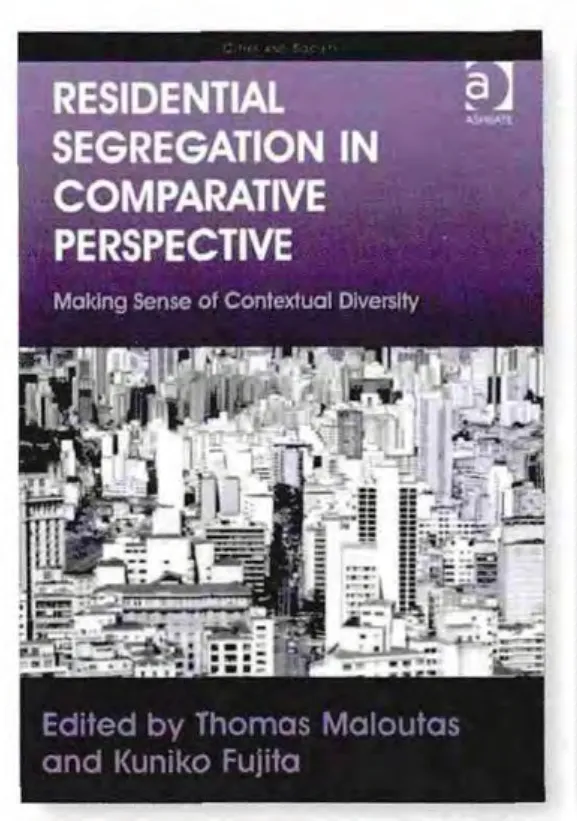
传统英美背景下的居住隔离研究,在定义、量度和尺度等方面已有丰富和深入的研究成果。然而,居住隔离会根据城市政治经济结构、阶级组成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我们对于世界上不同区域背景下的差异知之甚少。在Thomas Maloutas 和 Kuniko Fujita编写的《居住隔离的比较研究——理解社会背景的多样性》一书中,比较了全球范围内一系列城市,探讨了居住隔离的空间模式和发展趋势的巨大差异。
本书分为三部分,共13章。
第一部分即是第1章,关于居住隔离的理论研究综述和案例回顾。首先,Thomas Maloutas系统地概述了隔离研究的定义和词源、框架和研究技术,并强调居住隔离背景差异的重要性。本章对目前学界最受认可的理论提出质疑,涉及了隔离和主流的城市学说,如世界/全球城市、新自由主义城市化和中产阶级化,认为它们将城市从国家和区域背景中分离出来,忽视了历史、文化、政治和制度。然后,本章界定隔离的背景差异,包括四个维度:经济、国家、社会和长期形成的地方社会空间现状。背景差异中的隔离包含了不同的途径、影响和对隔离的政策回应。隔离是不平等和歧视的结果,也是其中过程的一部分。隔离的影响(如邻里或地域影响)最终会作用于居民。不同背景对隔离影响的政策回应也应该有所区别。
本书的第二部分(第2—12章),案例研究将空间隔离划分成截然不同的模式,深入剖析居住隔离的动力机制,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差异化的启示。基于地理特征的广泛性和社会经济类型的多元性,本书选择了11个案例城市(雅典、北京、布达佩斯、哥本哈根、香港、马德里、巴黎、圣保罗、台北、伊斯坦布尔和东京),它们被划分成5类不同的居住隔离模式,并探讨了动力机制如何对居住隔离与不平等产生助长或阻碍作用。
北京、伊斯坦布尔和圣保罗属于“高度分离和不平等模式”,它们的案例阐述了居住隔离是不平等的主要因素,美国模式也证明了此点。对于北京,住房登记、住房政策等都加剧了居住隔离和不平等。在伊斯坦布尔,宗教分歧的遗留问题、新生的资本经济和缺乏民主的寡头统治(pre-democratic oligarchy)加剧了居住隔离和阶级不平等。在圣保罗,殖民的遗留问题、国家政策、拉丁美洲的平民主义和缺乏民主的寡头统治是隔离和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布达佩斯和巴黎则被归为 “中度的分离和不平等模式”。对于布达佩斯,共产主义的遗留问题和新生的资本经济导致了居住隔离,同时官僚网络加剧了阶级的不平等。巴黎居住隔离的加剧来源于历史上的阶级分异和国家、城市的政策,同时,阶级不平等可归因于自由主义的劳动市场、城市住房政策、种族歧视和教育因素。
哥本哈根的住房隔离模式可以被命名为“隔离但平等模式”。居住隔离由于历史上的阶层分异和国家、城市的政策而存在,而协调的资本主义和福利状况阻碍了阶级不平等的产生。
雅典、香港和马德里属于“聚集但不平等模式”。这3个城市中相对融合的邻里不是阶级不平等的主要因素,但同一邻里中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很高。家族主义、公共部门的扩张和发展状况弱化了居住隔离,而裙带关系、缺乏民主的寡头统治、排外的专业组织、教育和自由主义的劳动市场塑造了阶级的不平等。
台北和东京属于“聚集和平等模式”,此模式中不存在居住隔离。发展状况、政策和国家机构抑制了居住隔离。协调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城市的政策以及紧缩的薪酬系统有助于抑制不平等的发生。
在某些城市,空间组织(地方和邻里)在重塑阶级关系和民族-种族等级关系方面起着显著的影响,但可能仍远不及其他城市。隔离的程度和影响取决于背景的差异,可以避免英美经验在全球范围内普及所带来的局限与曲解。
在结论部分(第13章),Kuniko Fujita总结了一个分析框架,对比11个城市案例与美国模式之间、11个城市之间的差异。在跨国居住隔离的研究中,背景并不是一个新的关注点,但是以往其主要指向国家或区域层面,并且忽略了实际的机制差异。因此,应当从比较机制入手,重点关注制度演化、历史发展、路径依赖等。
11个城市的实证研究挑战了主流的城市趋同和城市极化理论。趋同理论——在全球城市、全球城市网络和新自由主义城市化学说中十分常见——认为全球化导致城市趋同于一个普适的模型。11个城市的居住隔离模式与城市社会结构紧密交织,加剧或削弱空间模式的力量深植于特定的机制中。虽然在全球化过程中,许多城市已经经历了重大的社会变革,但是机制的变革仍是逐步演化的,并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因此,居住隔离模式的分异揭示了城市趋同理论缺乏扎实的比较研究基础。极化理论——可见于二元城市和分裂的城市——认为城市由于产业结构转型和移民浪潮涌入而经历了社会分化。但是,案例中的许多城市经历了去工业化而没有形成社会分化的模式;案例中的一些城市经历了增长的国际移民浪潮,但没有发展出分化的劳动市场——即包括高收入的专业人士和低收入的缺乏技能的移民。
城市的案例研究及出版方面也存在了一些局限与不足:在居住隔离的因素和过程方面需要更多的机制分析(institutional analyses);未来需要推进更多的纵向对比研究;研究者应当尝试克服缺少可比较的数据的困难,增加不同数据资源的可比性分析。
本书的价值在于一系列多样化的地方及国际背景的比较研究,打破了传统英美理论假设的局限,使其在居住隔离的相关研究中获得一席之地。对于需要系统地理解隔离及其在全球范围内差异的研究者、学生和政策制定者,本书值得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