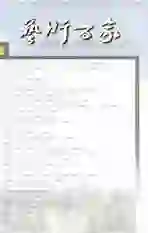贾樟柯电影的异质空间
2015-07-07倪祥保王莉
倪祥保+王莉
摘要:贾樟柯影片里有关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贫富差异及原因、娱乐场所的意义与权力等社会景观,都被构建成具有“对抗场域”特征的“异质空间”,并且非常成功地作用于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底层叙事,很好地表达了社会底层的希冀及难以实现的痛楚,由此形成其影像的独特性与内涵的深广性。
关键词:电影艺术;贾樟柯;电影作品;异质空间;城市化;底层叙事
中图分类号:J90文献标识码:A
“异质空间”(heterotopia)这个词源自希腊文,其直译为“差异地点”,也有译为“异托邦”的。福柯对此的定义是:“可能在每一文化、文明中,也存在着另一种真实空间——它们确实存在,并且形成社会的真实基础——它们是那些对立基地(counter-sites),是一种有效制定的虚构地点,通过对立基地,真实基地与所有可在文化中找到的不同的真实基地,被同时地再现、对立与倒转。这类地点是在所有地点之外,纵然如此,却仍然可以指出它们在现实中的位置。由于这些地点绝对异于它们所反映与讨论的所有基地,更由于它们与虚拟地点的差别,我称之为差异地点。”[1](p.18)所谓异质空间,是现实世界中具有质疑、消解或颠覆既有常规和关系作用的空间。相对于纯属想象的“乌托邦”(utopia),异质空间是真实空间,是一种“对抗场域”(counter-sites)。异质空间在现实中有真切而确实的位址,但事实上又自外于所有地方,即异质空间不同于其所再现的社会与文化中真实存在的场域。福柯曾以镜为比喻来阐释“异质空间”:“我相信在虚构地点与这些截然不同的基地即这些差异地点之间,可以存在着某种混合的、交汇的经验,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总之,镜子是一个无地点的地方,所以是一个虚构地点。在此镜面中,我看到了不存在于其中的自我,处在那打开表层的、不真实的虚像空间中;我就在那儿,那儿却又非我之所在,是一种让我看见自己的能力,使我能在自己缺席之处,看见自身;这是一种镜子的虚构地点。但就此镜子确实存在于现实中而言,又是一个差异地点,它运用了某种对我所处位置的抵制。从镜子的角度,我发现了我对于我所在之处的缺席,因为我在那儿看到了我自己。从这个凝视起,就如它朝我而来,从一个虚像空间的状态,亦即从镜面这彼端,我因之回到自我本身;我再度开始凝视我自己,并且在我所在之处重构自我。”[2](p.22)
贾樟柯曾经指出:“空间气氛本身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另一方面最重要的就是空间里面的联系。在这些空间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过去的空间和现在的空间往往是叠加的。比如说一辆公共汽车,废弃以后就改造成了一个餐馆;一个汽车站的候车室,买票的前厅可以打台球,一道布帘的后面又成为舞厅,它变成三个场所,同时承担了三种功能,就像现代艺术里面同一个画面的叠加,空间叠加之后我看到的是一个纵深复杂的社会现实。”[2](p.5)在他的电影中,有关异质空间的概念可成为对社会学意义上的小城镇或大城市空间考察的切入点,也可以用来审视小城镇与大城市展现的空间文化与政治,以及城市化转型中的故事及伤痛。
一、城市化转型中的差异化与抵抗
中国现代城市资本似乎以优于政治的力量在造就和扩大城市内部的不平衡发展[3](p.63)。资本与空间生产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是中国城市空间异质性不断深化的主要原因。这在贾樟柯电影中得到非常真切的艺术再现。
1.拆迁与重建
废墟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城市建设中的常见元素,它降低了所处都市区域的居住功能。建筑物被抽空,空间被重构,累累乱石弥散着破败和倾颓的气息。(后)现代社会的废墟带有总体性的都市意象,它破坏了建筑群落的连贯性,使都市建筑失去其标志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废墟也是建筑的一种代表形式,它提供着表意的两极:第一,意味着对历史意义与价值的质疑和否定,第二,代表着新的社会秩序即将建立[3](p.65)。因此,废墟的异质性就在于它和建筑这一形态始终辩证而对立的存在着。拆迁给城市人带来关于新的居住空间无尽的想象和承诺,同时也意味着家园的消逝与失守。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城市改建浪潮席卷全国,大大小小城市都裹挟其中,反复拆建和重构,在迎合世界的同时却逐渐离弃了传统,迷失了自我,失去了特色。在贾樟柯电影里,废墟以及硕大的“拆”字经常贯穿其中,其镜头中的“拆”字,永远彰显着某种权力的威慑,构成了对中国城市一种独特的空间表达。在电影《小武》中,拆迁刚刚开始,在《任逍遥》里已如火如荼,在《三峡好人》中则是一派废墟绵延的荒凉……以往所有历史几乎都物质性地融入了废墟的背景之中。种种叙事及景观无一不体现着“拆毁/重建”的主题,也意味着家园流变和丧失。为了三峡工程的宏伟目标,存在了2400年的古城,两年内便被拆得一干二净,一个被主流媒体所塑造出来的美好蓝图,却带着如此多的真实的伤痛。传统的家庭遭遇新一轮挑战,留守的留守,离开的离开,无数家庭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住房。资本的积累与拆迁中对资本的浪费,这矛盾与对立一直都在不断地折磨着城市(也延伸至农村),城市成了最大的社会实验室。消费主义的逻辑成为社会运用空间的逻辑,成为日常生活的逻辑。控制生产的群体也控制着空间的生产,并进而控制着社会关系的再生产。[1](p.8)
2.贫富比邻
异质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相对弱势者的社会实践在社会宏大叙事所建构的空间中造成的断裂带。由此可见,福柯的异质空间概念强调的是一种秩序或功能的异质性以及附着其上的人文价值的差异、对立和矛盾[3](p.15)。城市空间异质性的一个突出方面在于改造的初衷是为了把城市打造成一个崭新的、合理的、协调的城市空间,然而却因贫富不均以及资源配置不平衡造成新一轮的不公正与不公平。城市化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一方面有低矮潦倒的棚户区与破衣烂衫的穷人,另一方面也有熠熠生辉的摩天大楼、豪华的富人住宅区,五星级宾馆为跨国精英们提供工作、娱乐和休息场所。更重要的是,棚户区通常是处在豪华、富裕的丰碑所产生的阴影里[4](p.33)。拥有资本权力的人也拥有了改造城市空间的权力,可以将空间作为商品进行消费,而更多的底层人民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空间也无法获得。
《任逍遥》里,大同这座城市,介于“县城”与“都市”之间,“落后”与“发达”共存。荒凉的公路、废墟、荒地,卡车上妖娆又俗气的现代舞表演;桌球馆、录像厅和破败空旷的火车站;地方戏台和卡拉OK厅,等等。城市里到处都是游荡者,还有“小武哥”这样的“手艺人”,冷漠、刻板,却有煽动性,暗示着一个心神不宁的时代。在《三峡好人》里,以宏伟的三峡工程建设为印记,昭示着一个改革开放、高速发展的现代中国,可是也因此造成了种种异质的存在,显示出后工业化时代下破败的、即将消逝的田园意象。典型的新旧结合、盛衰共存的建筑形态以及拆迁中的废墟瓦砾、破旧的机械厂房和毫无个性的楼宇;作为拥有资本权力的人,狭隘的既得利益集团及开发商能够夜夜笙歌,在他们花两亿四千万造一座辉煌气派大桥的同时,奉节新城桥洞下面却挤满了失去家园、失去正常生活的人。贫富悬殊的结果就是城市空间的分裂和多样化社会性的缺失。排他性社群主义、狭隘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开发商的贪欲,都促成了这些困境[4](p.145)。传统的“家园”根基正遭受商业化与全球化的血洗,很多国人在一个瞬息万变的大时代里迷失、彷徨。
二、娱乐场所的意义与权力
娱乐场所的典型功能在于休闲与娱乐,其试图将现实生活与特定空间、特定欲望分割开来,构成现代城市人的个体叙事。观众在贾樟柯电影中可以看到,娱乐场所内的权力机制能提供身份的混合与并置,使这个真实空间同时包含着自相矛盾或自相冲突的多个差异空间。
1.影院、舞台:差异秩序的并置
福柯认为,电影院的空间和戏剧舞台相仿,都是在“一个单独的地点并列了数个彼此矛盾的空间与基地……因此,剧院在长形的舞台上,可以一个接一个的引入一系列彼此无关的地点,因此,电影院是一个奇怪的长形房间,在一端的二维银幕上,我们看到一个三维空间的投影。”[4](p.25)电影院与舞台的典型功能是娱乐,然而因为其可在同一空间并置数个差异的秩序,它们也表达了一种权力与抵抗。
舞台是一个流动的空间,各种人物和角色在约定性的控制下,在舞台上讲述不同的故事。《站台》刚开始,舞台上在上演一幕剧《火车向着韶山跑》。韶山是毛泽东的故乡,这暗示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毛泽东热,同时也极具戏谑性,扮演火车的演员崔明亮模仿的火车鸣笛声非常奇怪(因此在后面遭到领导批评)。导演用大远景拍摄这一场景,使人觉得虚拟的火车离开了站台,却离韶山遥遥无期。权力通过空间定义以及强制等方式,使一个早已远去的社会体制与现存的文化表达在时间与空间上逐渐弥合,又通过艺术手法将这种政治的严肃感进行解构:革命时代的政治说教成为群众娱乐的笑料。
《站台》里,崔明亮们在影院里观看《流浪者》。这部电影早在“文革”前就进入中国,然而它的故事以及主题曲“拉兹之歌”的真正轰动,却在一代人遭受苦难经历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电影主题曲不停地回荡着“到处流浪”的歌词,表征并预示文工团成员的漂泊不定。电影院门口贴有马克思画像,同时出现代表国家意志的警察(尹瑞娟的父亲)对电影的批判,则是造成这种漂泊感断裂的标志,也表征并预示着在各种现实条件的阻碍之下,崔明亮们的“流浪”终究不会成功。
2.KTV、按摩房:情色的抵抗与解构
歌舞厅、卡拉OK厅给城市中寂寞的游荡者提供了暂时的居所,也提供其心灵暂时的落脚处,两者的典型功能在于休闲娱乐,同时又是封闭的,因此具有情欲化的象征。在贾樟柯电影里,这种场所的差异性功能在于:没有情色,只有落寞。小武、斌斌在其中唱着怀旧的歌曲,诉说着内心的浮躁、迷茫与失落,表现出的是城镇青年内心焦虑、精神恍惚的青春。
卡拉OK厅这一空间形式在电影《任逍遥》中多次出现,贾樟柯以此来表现青春无奈以及经济快速发展给城市带来的后遗症。一家破旧的卡拉OK厅,本是一个不光彩乃至非法的场所,充满了情欲的暗示,斌斌和女友在这里定期约会。两人的约会非常单纯,仅仅是靠聊天、唱歌发展着彼此关系,最多牵手一起唱“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没有任何逾越的行为。第一次约会,两人并肩观看动画片《大闹天宫》。还在上学的女友说,为了高考,她要看关于WTO的新闻,不然又要被妈妈骂了。叛逆青年斌斌对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WTO?WTO还不简单嘛,不就是一些赚钱的事嘛。”这时候,一个移镜头,将画面推向电视机,电视机里在放《大闹天宫》。斌斌说:“你看孙悟空多好!没爹没妈没人管,多自在,也不用管什么鸟蛋WTO!”第二次,女友和斌斌说她母亲让她考到北京去学国际贸易,斌斌说“国际贸易就是收兔子收租儿,然后卖到乌克兰”。两次约会使得卡拉OK空间性发生了极大转变,情欲性完全被消解,取而代之的却是对经济与政治层面的曲解。在《任逍遥》中,理发店按摩房泛出晕红的光,这本是一个象征色情的场所,按摩女和斌斌却聊起了“纺织厂、国营单位”的话题。按摩女让斌斌躺下给其按摩,后者因不习惯,说了三次“算了吧”,结束了这场还未开始的服务。因肝炎未能参军、和女友分手而失落的斌斌第二次来到这个按摩房,他蜷缩在按摩女的腿上,按摩女轻轻抚摸他的头发,这是一种母性的体现,也将色情场所的情欲概念完全解构了。
3.“世界公园”:仿像、拼贴的景观社会
“世界公园”通过仿像、拼贴完成,是一个奇观化空间,是居易·德波所提出的“景观社会”,是社会再生产、消费主义的产物,具有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的做秀性质。作为著名的仿像论学者,鲍德里亚认为,仿真的特点在于模型先行,事实诞生于诸模型的交互作用中,所有的模型甚至可以同时生成一个事实,而事实与其模型之间反复混同与杂糅。“世界公园”就是这样一个后现代空间,置于其中的每一个建筑都有其原型,建筑本身仅仅是一个仿像。按照传统的本质论来说,它的“本质”“真实”应该受到根本性怀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空间是全新的,组成它的每个部分都实实在在。“世界公园”就是这样完全凭借仿像、拼贴而诞生的一个新空间,是“一种即兴或改变的文化过程,客体、符号或行为由此被移植到不同的意义系统与文化背景之中,从而获得新的意味。”[5]从仿像、拼贴的角度来说,“世界公园”是一个异质性空间。它在一定意义上类似于福柯所提到博物馆和图书馆,是一个“异托邦”场所,因为“世界公园”中的各种建筑、景观真正建立的时间是不同的,横跨了许多年代。作为一个仿像的“集中营”,它一方面把“无限”的时间堆积在一处,同时又将世界上那些从空间位置上不可能并置在一起的建筑摆放在一起,构成一个典型的“异托邦”。本雅明指出:“即使是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原作的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Esthetic)对传统的构想依据这原真性,才使即时即地性时至今日作为完全的等同物流传。”[6]所以,“世界公园”里的埃菲尔铁塔再壮观,巴黎圣母院再华贵,它们依然都只是“摹本”,都只是被复制出来的“赝品”。工作其间或游览其间的人物,也都只是“赝品”的一部分。“世界公园”演化成为一个消费主义符号,一边给身处其中的游客和工作人员提供虚假信息,一边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三、难以抵达目的地的旅程
福柯认为:“铁路是一个空间与权力关系的新面相。这关系到建立一个不必然与传统公路对应的交通网络,但是它们却必须放在社会性质与历史中考量。此外,铁路造成了一些社会现象,作为它们的抵制,他们刺激了人口的转化。……因此,在连结政治权力与领土空间或城市空间时,便发生了一些问题——这些连结是全新的。”[1](p.5)
车和船的主要功能是运输,在不同的秩序以及具有差异化的空间景观之间游移,其特点是漂泊与不定。这些都是贾樟柯电影非常喜欢的空间形式,并且都充满异质性意味。电影以“站台”为名,却从未展现过真正的站台,崔明亮们也从未坐上真正的火车。他们只能一次次在歌手张行“长长的站台,哦漫长的等待”的歌词中,在火车的鸣叫声中欢呼雀跃,火车却没有带他们去任何地方。站台既是起点也是终点,他们在人生的站台旁边充满了不知归宿的期待和渴望。文工团名称改成了深圳太空柔姿霹雳舞团,但是深圳、香港和更远处的大都市却永远不会是他们停靠的驿站。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城市化、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崔明亮们、张军们、尹瑞娟们最初的那些传统又稳固的革命理想渐渐消失殆尽,很多事都变得世俗化了,最初的漂泊感只剩下精神上的空虚、无助与绝望。《三峡好人》中的那条船能载移民迁徙,却难以将他们带往如家园一般熟悉的生活。汽笛声中,导演运用长镜头扫过移民船上的人群,船上聚集了形形色色的人,烟雾缭绕,有的在聊天,有的在打扑克,有的在看手机,有的在看手相。在这部电影中,那条船扮演了双重角色:首先是将韩三明和沈红带至奉节,将他们与过往某些生活内容和这里某个人的关系连结起来;其次是更多移民迁徙的交通工具,诸多家庭举家外迁至其他省份居住。“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歌曲一遍又一遍的唱着,滔滔的江水即将淹没奉节,正如船上广播的“为了三峡工程,县城的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以“家”为代表的私人空间被漂浮的船的空间所取代,稳定的生活被漂泊与不安定取代,造成了精神的断裂。因此,运载三峡移民的船只充满了权力性,是颇具意味的城市化政治实践的一部分。汾阳和奉节,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份子,却都被这个进程所边缘化。同样,影片《世界》中的交通工具也无法使人到达真正的目的地。赵小桃坐在单轨列车上打电话说她要去印度,这列单轨列车就是一个异质空间,因为它只是“世界公园”里的一个交通工具,是一个仿像空间里的工具,永远也不会载着小桃真正去到印度。这也就好像赵小桃和成太生们渴望融入北京乃至世界,然而一觉醒来会忽然醒悟,这趟开往世界的列车却从未载他们驶出原先的生活境地。
贾樟柯电影呈现异质化的空间的特征是漂泊的、不确定的,代表了社会底层一代人的寻找与失落。无论是《站台》《世界》,还是《三峡好人》,都充满了背井离乡与漂浮不定,都表征着在城市化进程中,有很多生活其间的人,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其精神、身份、家园都始终充满流动性,成为另一种“栖居”方式,却始终难以抵达其希冀的彼岸空间。(责任编辑:陈娟娟)
参考文献:
[1]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2]张亚璇、贾樟柯.去一个传说中的城市[A]//林旭东、张亚璇、顾铮主编.2003,贾樟柯电影——任逍遥[C] .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3.
[3]张一玮.异质空间视野中的都市意象——一种对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电影中“都市空间呈现”的研究[D].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5.63.
[4]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33.
[5][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李彬译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31.
[6]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