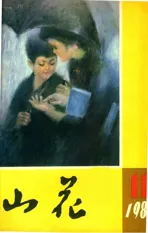从风雪中归来(外三首)
2015-06-29华万里
华万里
从风雪中归来
站在同春天最接近的地方
我没有声响
唯前世的杜鹃在远山准备着啼叫
那个风雪中返回的人
还在向千山万岭归还寒冷,白蝴蝶
大群大群的神秘词语
紧随其后
纷纷的飞吻,轻盈而不尖锐
仿佛棉花,不像
银锥
崖上的野梅树正在燃烧,花瓣
落满他的双肩,听着
簌簌而下的暗香
谁的心边绽放花蕊?像她
最初的样子
家在峡谷的缝中将门打开
胀满温暖的她
触手可及,蓝色的狗吠如同院边的鸢尾
突然怒放,我和他
那个匆匆赶路的人,立即合为一身
土墙上木箱孔中飞出的蜜蜂
嗡嗡惊讶
盘旋着,不停地将我盯视
站在拥抱中我失去了满怀烦忧的样子
仿佛有鸟语花色涌来包围
我是一份迟到的礼物,她是一个
开心的日子
冬日,读阿赫玛托娃
冬日,读阿赫玛托娃
突然,天空大亮
刚出来的太阳带着阿赫玛托娃的面庞之光
刹那,照到我的身上
如同她激情四射的诗句,虽然沉痛
但此刻,却让我
灿烂得快要燃烧
我读她的《野蜂蜜闻起来像自由》,口唇上
锁就烂了。我读
她的《但丁》,听到“门槛外
命运痛哭”。我读
她的《沃罗涅日》,感到“而夜在进行
它不知何为黎明”
我读她的《死亡》和《给伦敦人》
听见她在绝望地
叹息:“我看着我自己的岸在消失”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力气阅读”
在那铅色流动的河边,在那苦难
刻出的脸颊
当暴风雪席卷苏联大地
她从列宁格勒被疏散到塔什干地区
我听到她的心脏
不是在跳动,而是在震动
因了那么多的折磨——
花束被扔掉,樱桃树开空,诗人之死
洗碗女工,不幸的耻辱台,末日之钟……
如同热病,一齐向她袭来
她没有躲开
她迎接这一切,像泰然敞开的坟墓
我的心在为阿赫玛托娃流血!论年龄
她可以作我的毌亲
论写作,她不但是我的文字前辈
而且是我的词语引路人
她在深夜静候缪斯的来临,我在清晨
等待她如同迎接新的诗神
虽然,我们同样半生结满了冰
但我绝不成为
寒冷的继承者。虽然,我们都被苦难爱上
但我注定只能与苦难的雕像
擦肩而过。一抹春光
在前方,散发出
广阔的神秘的苹果香气
如果我是阿赫玛托娃的同时代人
我肯定会成为
她的挚友,甚至情人。我会像帕斯捷尔纳克
曼德尔施塔姆、布罗茨基
那样爱她,谈她
不仅仅用歌德式的语言,萨特式的语言
还要用李白式的语言
同时,给她写诗,写信。不仅仅用西方的斜体
花体,还要用中国的楷体
篆体。在那最初的少女的早春,在那
灵魂的玉色全裸于最终的沉睡
在历史再次受到刺伤
我听到她,复活的低语:“拿走一切吧
但请留下这枝
我可以重新呼吸的深红色玫瑰!”
冬日,读阿赫玛托娃
真的,我已经灿烂得燃烧!从第一句
开始着火,到最末一句
不留灰烬
“有一枝新鲜、黑暗的接骨木探出”
让世界前额的悲,戛然而止
一个女性的面庞
因诗歌,光芒万丈
读 诗
午后,我在紫藤架下
读一本叫《两次看同一朵云》的诗集
在预初一页,我浅米色地
认识了以色列女诗人塔尔·尼特赞,即
这册诗集的作者
即一位美貌而目光犀利
愤怒后能够悠闲地
回到自己深处喝半杯咖啡,裸露的右臂
有刺青的女人。他在告诉我:不要犹豫,走向那
爱你的唯一,把脸
埋在他的毛里,那只世界上唯一的猫
她还在告诉我,你离
那座花园很远,而离那朵野花很近,或者
反过来说,你离那朵野花很远
而离那座花园很近
远近只在一念之间,只在闪电的一瞬
她反复告诉我:对痛苦的仰望
不能超过三次
我不明白,她是诗人或是导师?她能够两次看同一朵云,而我却不行
我只能在同一次看好几朵云,甚至
一大群云。她能够让口唇
如同花苞裂开
吐出格言似的语言。而我却不行。我只能在黄房子边说大白话,或者
朗诵口水诗
当我读到最后一页,她翻书的沙沙声惊醒
此时,我在花荫中的凉床上
躺在自己一边
斜来的鸟声推我,我准备将身子翻动
她赶紧对我说:不要动
你要假设你没有另一边!我暗自惊讶
我应该这样假设:万一
另一边是花瓣的悬崖,是香气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