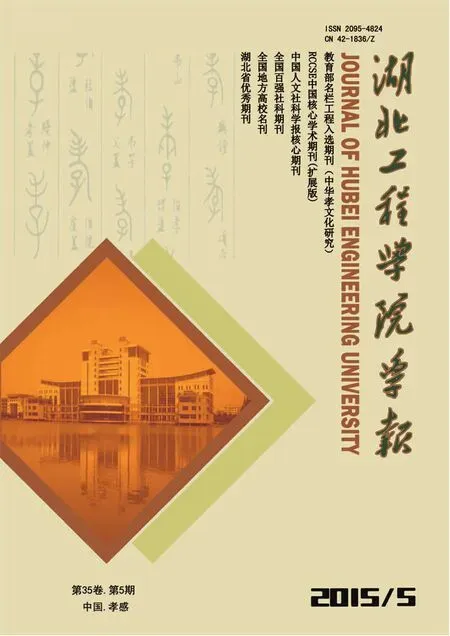“八蛮”神考释
2015-06-23龚德全
龚德全
(贵州民族大学 西南傩文化研究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八蛮”神考释
龚德全
(贵州民族大学 西南傩文化研究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八蛮”是西南各地傩祭活动中常见的一个神灵形象,其少数民族身份,在各地端公科仪中有较为明确之载录,但各地对其身世、来历以及族别却有不尽一致的表述。这一神灵形象已成为面向区域社会的“箭垛式人物”,是端公及其文化活动进行集体想像与话语建构的对象。
八蛮;地域归属;族别
考察西南乡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巫傩信仰时,我们留意到了一个较为特殊的神灵形象——“八蛮”。这一神灵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讲,已超越狭小区域的限制,成为西南各地甚至福建一带的端公*“端公”这一称谓具有多重历史语义。“端公”这一称谓最早见于唐·杜佑《通典》卷二十四“职官·侍御史”条:“侍御史之职有四……台内之事悉主之,号为‘台端’,他人称之曰‘端公’。”宋元时期,该词又衍为衙门里当差“公人”(衙役)的称呼。如《水浒传》第八回:“原来宋时的公人都称呼‘端公’。”除此二义外,“端公”这一称谓还有一个更为普遍的意义,即“巫师”(男巫)的别称。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二:“自后多说神怪,以桀黠者四出,号端公,诳取施利,每及万缗”。清·唐甄《潜书·抑尊》云:“蜀人之事神也,必冯(凭)巫,谓巫为端公。”其实从宋代起,川、陕、黔、湘、桂、滇等地就已普遍称巫师为“端公”,且一直延续至今。祭祀活动中常扮的一个神灵角色。*据相关资料载述,福建邵武市大阜岗乡河源村即举行“跳八蛮”活动。该地的“八蛮”扮演者为八人,当地人称为“八大神”或“八大王”。这八位大神分别为:开路神二、弥勒二、绿脸神二、白脸神二。其中除弥勒外,其余都是凶神。该舞内容表现为:八位大神为四方之保护神,他们巡游四方,驱鬼逐疫,安太极、定八卦,为民保平安。“跳八蛮”的宗教内容与道教较为接近,表演中以“走八卦”为主。详参叶明生《福建省邵武市大阜岗乡河源村的“跳僧番”与“跳八蛮”》,王秋桂主编《民俗曲艺丛书》,台北: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3版,第69页。它不但是法事中享祀的神灵,而且还是端公演剧中一个格外引人注目的角色。湖南西北部桃源、沅陵一带汉族端公法事中有《蛮八郎》一剧;云南西北部永胜汉族端公戏中有一种被称作《贺八蛮》的祭祀活动;四川芦山端公庆坛中有《跳八蛮》的活动;贵州遵义端公庆坛中有《八蛮登殿》法事;云南昭通端公法事中亦有《出八蛮》(亦称《当兵记》)一剧。由此可见,“八蛮”这一神灵形象在西南各地的傩祭法事中具有一定普遍性,因而具有比较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然而,“八蛮”神的历史渊源何在,文化身份为何,学界却鲜有探讨。本文不揣浅陋,拟对这些问题做一些初步的探索。
一、“八蛮”的地域归属
从名称上看,“八蛮”这一称呼即透露出其并非出自汉文化系统的历史讯息。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中,作为民族区分的“华夷之别”早已存在,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实际上就是以地域来划分少数民族的。至于“蛮”之外延与内涵,目前学界还说法不一。*《说文解字》云:蛮、闽都是它种,写成今字是“蛇种”。朱希祖先生曾指出:“蛮为蛇种,狄为犬种之说,或由神话相传而来,或由所祀祖先神祇而来。”朱先生论证蛇和犬是古代社会图腾的标志,确有卓见。参见《文献》杂志编辑部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八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352页。《礼记·王制篇》有云:“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史记·夏本纪》中亦载:“蛮,慢也。礼简怠慢,来不距,去不禁。”[1]这也只是就其文化习俗而言的,当然算不上什么严格的族群区分标志,但在文化史上,用“蛮”来指称南方少数民族应该是可以确定的。因之,端公法事活动中的“八蛮”形象也必然出自南方少数民族地区。
从形象上看,“八蛮”的面具造型别具特点,为无下齿下巴之怪异形象,现在云南昭通、湖南桃源、贵州遵义等地端公中仍有所保存,并在法事活动中佩戴演出。西南各地各种类型的祭祀活动,与此相类的面具在古南蛮之地不难见到,而在中原各地极为罕见。胡建国先生认为这种无下齿下巴的形象很有可能是古代凿齿习俗的遗存和艺术夸张。[2]256胡先生所言,颇有见地,凿齿习俗曾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地,而在中国西南地域范围内,古时行凿齿的主要流行于百越族系的濮、僚,即现今的仡佬、土家、彝等少数民族中。这也充分说明:端公祭祀活动中出现的“八蛮”形象应来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二、“八蛮”的来历与族别
“八蛮”的少数民族身份,在各地端公科仪中有较为明确之载录,但各地对其身世、来历以及族别却有不尽一致的表述。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凡祖籍湖南的人家,皆供有“八蛮先锋神”的灵位。旧时,各家每隔三年都要请端公跳《贺八蛮》。砌房盖屋安神奠土,或老人去世办丧事,都要跳《贺八蛮》,以驱邪镇妖,保佑家宅平安。[3]关于“八蛮”的来历,永胜人明确指出其来自湖南:
五代末时期,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从南方征兵去北方打仗。这时生长在湖南某县的一个农民,名叫“雀铃子”,是前娘所生,继母对他百般虐待,只得远离家乡顶替他人出征。他随湖南的一批军队一齐出去参战,由于“雀铃子”在战场上非常勇敢,所到之处连获胜战,敌人闻风丧胆,人民得到安宁。人民非常拥挤和感谢他。此时,“雀铃子”被封为大将,名列第八,当时南方兵被称为“蛮子兵”,“雀铃子”被称为“八蛮先锋”。后来,由于中敌之计,八蛮先锋死于陷马坑中,宋王天子赵匡胤封他为“八蛮先锋神”,赐他一箭之地。人民为了纪念这位英雄,把八蛮敬为斩妖除邪,给人民带来喜庆的尊神。[4]
言“八蛮”为湖南人,可谓是客居永胜的湖南人借助他们所崇祀的神灵信息来积累自身的社会记忆。但这一“蛮”字本身,表明了“八蛮”很有可能来自湘西的少数民族地区。在今湖南桃源、沅陵汉族端公法事中,即有《蛮八郎》一剧。在当地的端公法坛上,“八郎”即为“八蛮”形象,有学者认为,这里的“蛮八郎”之名,与土家族颇有渊源。[2]255-256说“八蛮”与土家族有渊源关系,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土家族人的民俗信仰中,有“八郎大神”之说,所谓“八郎大神”,即八位土家族部落酋长的俗称。民俗祭祀“八郎大神”时,杀猪不刮毛,连肉带血,传说“八郎大神”吃生不吃熟。湘西土家族摆手堂前,有这样的对联:
守斯土,抚斯土,斯土黎民感恩戴德,同歌摆手。
封八蛮,佑八蛮,八蛮疆地风调雨顺,共庆丰年。
而在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泼机乡邹氏端公“庆菩萨”中,有“八蛮将军”一段科事,其称“八蛮”为马湖(彝族聚居区)的彝族:
倮倮神来倮倮神,倮倮原是马湖人。马湖地方没地分,全家搬在水西城。水西地方汉人多,取名就叫黑倮倮。才到水西三五月,我娘有病在其身。请个医生来扎药,请个端公来跳神。降神吃药都无效,母亲死得脚长伸。[5]
唱段中“倮倮”一称,亦作“罗罗”、“卢鹿”、“罗落”、“落落”等,实为彝族旧称。“卢鹿”之称最早见于唐代史籍。元代在今四川西昌地区和大凉山一带设立了“罗罗斯宣慰使司”。“罗罗”等名为元明以来史籍所习用。明·田汝成《炎徼纪闻》即云:“罗罗,本卢鹿而讹为今称。有二种:居水西十二营宁谷、马场、漕溪者,为黑罗罗,亦曰乌蛮;居慕役者,为白罗罗,亦曰白蛮。风俗略同,而黑者为大姓。罗俗尚鬼,故又曰罗鬼。”[6]有些地区的彝族认为,“罗罗”这个称谓带有侮辱性,新中国成立后已不沿用。唱段中所提及的“马湖”、“水西”等地名,在历史上也都是较大的彝族聚居区。由此可见,昭通汉族端公法事中的“八蛮将军”已经明显打上了彝族的烙印。关于这一点,还有一个旁证,即在彝汉杂居的村子,如果祭祀和演剧中要出现“八蛮将军”,事前必须通报彝族。其原因在于:作为祭祀的神灵,端公们对八蛮是敬重的,但在“耍戏”中,八蛮将军则为喜剧性的角色,语言粗俗,表演滑稽可笑,加之表演者的即兴发挥,稍不注意,就会引起民族纠纷。这一情况,更加证明了“八蛮将军”的彝族属性。
无独有偶,在四川芦山庆坛“跳八蛮”法事中,也将“八蛮”称作“倮倮”。据四川戏剧志资料之三《四川灯戏·四川傩戏》介绍:“芦山庆坛中《出倮倮》一折的主角倮倮,其实是民族子弟,唱词中,他叙述被被征召去打仗,离家前告别父母兄弟,行军途中风餐露宿,战争中死伤之惨烈,归家后田园破败,满目荒凉。一幅古代民族子弟参战图。”而关于“八蛮”在庆坛中的作用,掌坛师罗芝茂介绍说:“因为他是一个久经战场的民族子弟,所以,坛王要召请他去参加斩鬼除邪的战斗。”而在贵州遵义一带端公庆坛法事《八蛮登殿》中,也言及“八蛮”的从军经历,并言及乃赵侯圣主封其为南方赤地八蛮王。*《八蛮登殿》主要讲述八蛮亲娘死后,父亲另娶妻并生有一子,之后对八蛮百般虐待和折磨。八蛮长大后被逐另居,分家时仅得一条狗和一头老牛。由于八蛮年小孤苦,便一心想去投军,行至黑松林,突然遭十二个黑汉怪贼攻击,但他力大无比,英勇顽强,神力助他将怪贼打败。投军后,他屡建功劳,赵侯圣主封他为南方赤地八蛮王。在后半部分的武场戏中,八蛮戴无下巴面具,使用具有神力的火棍,连续与分别上场的怪贼搏斗,最后获胜,表现了八蛮王具有降伏五方邪鬼的神威。参见政协遵义县宣教文卫委员会编《遵义县文史资料》(第十七辑),内部交流资料,2006年,第193-194页。
而更具深意的是,在云南昭通地区(主要集中于镇雄、彝良、巧家等地)的汉族端公祭祀中,“八蛮将军”(或称“八蛮先锋”)还有另外一个称呼——“黑垮将军”,并且还出现了“黑垮将军”的面具。据王勇先生的调查,镇雄县泼机乡邹氏端公所使用的黑垮将军面具,长约17厘米,宽为16厘米,木头雕制,彩色敷面,其面相为凶神,楞睁鼓眼,威严凶悍,头上饰以“官帽”,画焰状赤眉,大鼻子,当地人称之为“大鼻子官家”。据该坛门的掌坛师邹永祥(汉族,68岁,1990年卒)释:其帽饰系朝廷对彝族土司的封赐,因之,黑垮将军又被称作“官家”、“土主”、“地盘业主”;焰状赤眉,一是表现他的火爆性格,二是指彝族对火的崇拜。[5]215很明显,“黑垮将军”的形象,就是按照彝人的性格特点创造出来的。
由“八蛮将军”与“黑垮将军”的互名,我们可以得出二者其实为同一个神灵的结论。但这里的问题是:既然有了一个“八蛮将军”,为何还要再创造出一个可以与之互名的“黑垮将军”呢?对于此问题,当地的端公们都无法解释。我们认为,要解开此谜团,必须了解昭通的历史文化。昭通位于云南省东北部,是彝族的发祥地之一,可以说,彝族在昭通地区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在清雍正“改土归流”之前就更是如此。而昭通地区的汉族,均为移民迁入,或是随军征战,或是商贾贸易,或是逃荒避难而移入。面对强大的彝族土司势力,初入昭通的汉人能否生存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与彝族和睦相处。端公作为这支移民大军中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自然也要面临同样的问题。彝族作为当地的统治者,汉族人均称彝族土司家的人为“官家”、“土主”、“地盘业主”、“蛮王”。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端公们为了使其信仰能够得到更为顺畅、更为广泛的传播,便按彝族的形象塑造出了一个“黑垮将军”的角色。*事实上,“黑垮”之名却非凭空产生,其与镇雄一带的历史文化背景有较为紧密之关联。据有关研究,在昭通镇雄一带的彝汉间,流传着一个“海夸”的故事。传说,芒部(即今镇雄)彝族土司家有一个满身穿黑,又高又壮的大将,叫做海夸,他能吃下十二砣烧红的毛铁,力大无穷,几抱粗的大树都能够拦腰拔起来。他还有一支具有魔力的白牛仙角,抓一把豆子往天空一撒,同时吹响牛角,豆子即可变成千军万马。“海”字在镇雄人的口音里,即读为“黑”。此外,在彝族的历史上,冤家械斗中的勇敢者被称作“杂垮”。他们在械斗中,以冲锋在前,勇敢征战而赢得人们的尊重。在彝族土司统治区,“杂垮”不仅打仗充先锋,土司家死人时也要执矛走在前面以壮声威。(详参王勇《昭通汉族傩祭中的“黑垮将军”》,载《民族艺术研究》1993年第5期)端公正是综合“海夸”这一神话人物和“杂垮”这一勇敢者形象,并以“八蛮将军”为原型,塑造了“黑垮将军”这一特殊的神。


图1 云南昭通“八蛮将军“面具与“黑垮将军”面具*该面具现为云南省昭通市文化局王勇先生收藏。笔者于2013年7月22日在王勇先生家中拍摄。
三、结 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将“八蛮”表述成湖南人抑或马湖人(四川屏山或云南昭通一带),还是将“八蛮”认定为土家族或是彝族,其实都是汉族端公立足于本土区域所做出的一种“文化调适”。这种“文化调适”的目的就在于更好地融入土著文化,更好地传播其信仰,以获得更多的信众。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西南各地普遍流行的“八蛮”形象,已成为面向区域社会的“箭垛式人物”——端公及其文化活动进行集体想像与话语建构的对象。*胡适先生曾指出,古典文学中创造了许多“箭垛式人物”,如屈原、包公、关公等。人们借用某些人物作箭靶,将善恶、忠奸、智诈、勇怯、清浊等抽象质量射向他们,以致在靶子上集中了超量的箭镞(参见 胡适《〈三侠五义〉序》,载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38页)。对于“八蛮”形象而言,端公们立足不同的区域本位会有不同的表述,从而使“八蛮”这一形象日益丰富、变化。特别是云南昭通地区“黑垮将军”的出现,可以说是端公话语建构的一个最为集中的表征,当然这其中也深隐了“文化妥协”的意味。端公立足于区域本位对“八蛮”这一形象所做出的多样化表述,既可以说是端公的一种文化策略,但更为主要的,其实是端公的一种生存策略。
[1] 司马迁.史记: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 胡建国.巫傩与巫术[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
[3] 高登智.云南省志·文化艺术志:卷七十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342-343.
[4] 《中华舞蹈志》编辑委员会.中华舞蹈志·云南卷:上[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4:115-116.
[5] 王勇.昭通汉族傩祭中的“黑垮将军”[J].民族艺术研究,1993(5):16-17.
[6] 田汝成.炎徼纪闻校注[M].欧微微,校注.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114.
(责任编辑:李天喜)
Textual Research on Baman
Gong Dequan
(Guizhou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Guiyang,Guizhou550025,China)
“Baman” is a common divine image of Nuo-cult everywhere in the southwest. The ethnic identity of Baman is clearly recorded in the Duangong rituals, but there are different statements in different places about its life experience and ethnical belonging. The image of God has become a Jianduo type character which faces the regional society and has proved to be the object of the collective imagination an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Duangong and its cultural activities.
Baman; regional attribution; ethnical belonging
2015-09-0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XMZ1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751011)
龚德全(1977- ),男,内蒙古通辽人,贵州民族大学西南傩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民俗学博士。
K289
A
2095-4824(2015)05-006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