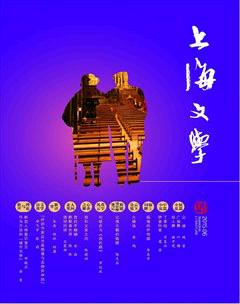隔墙的伊甸园
2015-06-19李美幸
李美幸
户口簿上记录我家从南市区人民路观音阁弄搬到虹口区周家嘴路三多里的日期是1961年初夏。换句话说,1961年,大部分上海人正在忍受“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馑,而篱笆墙另一边的“虹口区机关幼儿园”内,小天使们却过着“衣食无虑”的日子。
第一次看到这幢城堡似的建筑,是五岁那年。记不清是随父母来看房子,还是已经搬完家,独自一个人到晒台上玩耍。只记得有一阵轻微的喧哗,把我惊扰。隔着比我个头还高的磨石子栏杆,我看到隔壁两幢楼宇之间的楼梯上,排队走过一群花蝴蝶一样的孩童,轻微的喧哗,就是他们相互推搡发出的声响。
这个画面,在以后的日子里,演变成一种重复出现的场景。我也慢慢知道,这是与我家一墙之隔的寄宿制幼儿园生活的一部分。
很久之后我才明白,虽然我也是幼儿园的适龄儿童,但因为收费昂贵,还因为其他原因,我永远不可能成为这所幼儿园里的一个学生。其实我们弄堂里有很多有钱人家,他们都独门独户居住在一栋石库门里,但只有我们楼上房东家的小儿子世明(我们这条弄堂是他曾祖父造的),有幸成为里面的一员。
这栋坚固如城堡的方形建筑,包括外面的花园、儿童乐园,因为有一群像花朵一样的小天使,而成了我眼里的伊甸园。尽管,伊甸园是外来词语,小天使也是西方神话里的人物,而我,还不是一个能明白这些事理的男孩,但在我眼里,这里,无疑是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地方了。
伊甸园的生活是固定的,也是优越的。每天早上,小天使在老师的带领下,聚集在罗马圆柱大厅前的露天广场上,做自编的体操,或围成一个个圆圈,玩各种游戏;还有一些则列队到儿童乐园滑滑梯、走独木桥、荡秋千。下午,睡过午觉,小天使们排队去楼下洗澡,这也是我刚搬进来时,每天看见的场景。没有轮到洗澡的,则在打蜡地板的教室里唱歌跳舞;晚饭前一段时间,小天使们坐在教室小方桌边,分享美味可口的水果、糕饼、点心等等。伊甸园开饭时的饭菜香味,具有特别的诱惑力,惹得我们口水直流,并在我记忆里留下深刻印象。
每当这时,伊甸园无忧无虑的嬉戏声、率真快乐的欢笑声,穿越镂空的竹篱笆,传到我们弄堂。而我们,常常或站或蹲在一墙之隔的篱笆边,看着他们优越的、异于我们的生活状态,眼睛里充满了羡慕。
与伊甸园不同,我们这些野孩子常常聚集在小弄堂与前门的空地上玩“滚铁圈”、“打弹子”、“刮角片”、“一把抓”、“盯橄榄核”,甚至更粗野的群体性“斗鸡”。女孩子天生文雅,她们玩跳橡皮筋、“造房子”、“掼结子”、“扮家家”等等;或者,男男女女一起玩“笃笃笃,买糖粥,三斤胡桃四斤壳”。
这些游戏,这些儿歌,包括我们粗野的“斗鸡”,伊甸园小朋友不玩。老师不允许。所以,他们也羡慕,也会跑到篱笆墙边,透过篱笆缝隙,看与他们年龄一样大的小孩,玩与他们不一样的游戏。但老师不允许他们靠近竹篱笆,否则会予以非常严厉的呵责。
伊甸园与我家居住的石库门,只隔一道黑漆竹篱笆,两栋楼宇之间不超过两米。但是,这道黑漆篱笆墙,是无法打破和逾越的。它不仅是富人与穷人的标志,还是文明与野蛮的分界。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楼里几个最顽劣的男孩,用锯条把竹片锯断,又伪装成完好无损的样子,以便哪天需要了,偷偷抽出竹片,方便地钻进去。但很快,幼儿园那个满脸络腮胡子的烧饭师傅(好像姓方),在一位大眼睛、白皮肤、身材粗壮的女院长指挥下,又把新竹片补上。新补上的毛竹片,呈现一种肉欲的嫩白色,在黑色的篱笆墙上分外醒目、耀眼。
真正能堂堂正正走进伊甸园,是我十岁那年,陪房东家的大儿子去接他弟弟世明回家过周末。不知是因为害怕被院长认出,还是太兴奋了,当我从幼儿园大门走进去时,手心全是汗。可进入伊甸园,我的好奇心又战胜了一切,开始肆无忌惮地走动,从底楼大厅开始,一间一间地看过去。还忍不住跑到篱笆墙边,窥视自己的小弄堂。
伊甸园底楼大厅的地坪,与我们底楼一样,铺着图案非常好看的马赛克。但那时我还不知道这是马赛克,管它叫大理石。走在上面,可以像滑冰一样滑来滑去。从一楼到三楼,所有房间都铺着柚木地板,每间房间的窗子,也像我们房子一样,镶着五颜六色的玻璃。不过,楼梯比我们宽敞一倍,扶手是用整块木头做的,上面雕着花,非常漂亮。结实方正的扶手木柱子上,刻着一个大大的“H”,不知是什么意思。
那天,我本来想偷偷溜到三楼屋顶,去看屋檐上的雕龙,去掏上面的麻雀蛋,却发现上面的门锁着。
伊甸园三楼楼顶是一个庙宇似的大房子,挑出的四个角上,雕着昂起的龙头。上面还有人字形的屋脊,也雕着龙。这六条龙造型逼真,在透明的蓝天下,那旋转的龙身、闪光的龙鳞、铜铃般的龙眼睛、翘起的龙须,栩栩如生,好像馬上就要升天而去。
我经常爬到三层阁邻居家的屋顶上,眺望这座庙宇似的大房子和上面的雕龙,并盼望飞龙升天而去。可是,不管我多么痴迷飞龙升天那一刻,我看到的,只有不知疲倦的麻雀,在屋檐上面叽叽喳喳地跳来跳去,从屋脊上两条雕龙张开的龙嘴里飞进飞出。
夏天是个值得期待的季节。一是因为隔墙的广玉兰开了;二是暑假期间,伊甸园只剩下极少学生和老师,无意之中,篱笆墙内外都成了我们的天下。我们常常钻过篱笆,溜进伊甸园玩耍,但也经常被驱逐出来。
紧贴伊甸园篱笆墙的,是一棵又高又粗的广玉兰树,每年六月,都会开出无数纯白的“仙桃”。这“仙桃”,就像是伊甸园的苹果,无时无刻不诱惑着我们。
每年夏天,我们都会重复同样的勾当,攀爬上高高的竹篱笆,骑在摇摇晃晃的篱笆墙上面,用一根前面叉开的晾衣杆,隔空去摘桃子——我们不知道这花骨朵是广玉兰花,管它叫桃子,大概是因为它的花苞呈倒卵形,像一只刚长出来的小毛桃。
我们的行为,自然遭到院长和烧饭师傅的大声呵责,但他们不敢采取什么措施,因为我们是骑在篱笆上,一不小心就会摔下来。所以,他们仅是摆出一副如临大敌的阵势,仰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而大部分情况下,“桃子”会被我们顺利摘下,拿回家供养在盛了水的牛奶瓶子或其他玻璃瓶里。放入容器前,先用火柴在枝桠断裂处烧一烧,这样,“仙桃”能活上好几天,慢慢开出一种荷花形的白色大花,香上好一阵子。
广玉兰,也是我童年时代唯一看到会开的花。
广玉兰初开的季节,正是上海的梅雨天,气压低,湿度高,气温也高,香气不易散发。睡到半夜,我常常被花香熏醒,一边贪婪地嗅着沁人的馨香,一边分辨着混杂在其中的黄浦江江水的腥味。有时,睡意朦胧中,还能听到从江上传来一两声悠远的汽笛声。
每年的梅雨季节,因为有了广玉兰,一切似乎又变得美好起来。这就是属于我的、独特的仲夏之夜。
花香中,夹杂着黄浦江水的腥味。而我对黄浦江水的腥味,怀有特殊的感情。
五岁之前,我家住在人民路。穿过上海最短的马路——新开河路,再穿过中山东一路,就是上海母亲河黄浦江了。其实,站在人民路新开河,等于站在黄浦江畔。
儿时的黄浦江,堤岸很低,没有围墙,只是在堤岸边竖一排石柱子,用铁链连接,就像现在西湖湖堤。有一年大潮,黄浦江水几乎漫过堤岸。滂沱大雨中,父亲和邻居前楼外公,站在江堤边,用网捕鱼,居然收获颇丰。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怀疑这是我虚构出来的。后来问父亲,父亲甚是惊讶,因为按时间推算,那一年,我大概只有四岁。
搬到虹口后,出于对黄浦江的怀念,我经常与邻家小伙伴徒步走到公平路码头,去看外国轮船。
从我家抵达黄浦江畔,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沿公平路,还有一条走舟山路,都是往南。中间经过远东最大、也是最闻名的外国牢监——提篮桥监狱,然后横穿霍山路,就到东大名路提篮桥了。
霍山路上有一个“小人公园”,面积虽小,但因为是免费的,我们经常去玩。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小人公园”也叫霍山公园,里面埋葬着以色列总理拉宾的父母,还知道霍山公园对面那一整排欧式古典风格建筑,曾是“二战”时期犹太人集居的地方。舟山路59号,还居住过美国前财政部长布鲁门·塞尔。
不过,小时候,我对霍山路犹太人居住的公寓,包括塘山路(今唐山路)、公平路、熙华德路(今长治路)、汇山路(今霍山路)等街区曾是“二战”时期犹太人在上海的集居地,舟山路曾有“小维也纳”美誉的这段历史盛景,并不知情。还有,我们弄堂底就是虹口区第二医院的围墙,在围墙上往西“走”十几米,爬过医院太平间屋顶,顺墙而下,就是“外国弄堂”。但为什么叫“外国弄堂”,我也不知道。
其实,上海的老弄堂、老房子,大抵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这故事是辉煌,还是凄惨;是平淡,还是跌宕,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本身。如果说,豪宅上演的是豪门恩怨,反映的是时代风云变幻,那么,老房子展现的则是人间冷暖,世事无常。
伊甸园的主人是谁?母亲说是上海火柴大王。对此,我一直深信不疑。直到写这篇文章,我去调查,才知道伊甸园的真正主人是商务印书馆一个姓杭的股东老板。儿时看见伊甸园每根楼梯木柱子上都有一个“H”,原来是“杭”字的英文字母缩写。
杭老板花巨资建造这栋带花园的一千五百四十二平方米大房子,不是金屋藏娇,而是送给他母亲做佛堂——三楼屋顶上那个方形家庙,就是杭董母亲的佛堂。
我无法进一步考证这个孝子的身世故事,但我知道,上海滩开埠后,应该不会缺少这种孝子贤孙。他们来上海滩闯荡,发迹了,拿出巨资买地造楼,然后把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堂亲表亲接到上海,享受时尚的西式生活。我们这条弄堂,也是宁波一个地主在上海发迹后,买下虹口这块地皮,于1923年建造的。想来,与我们弄堂一墙之隔的伊甸园,建造年代应该相差无几。
孝子建造佛堂送给母亲全身心礼佛的故事,本来可以一直演绎下去。但日本人占领上海后,伊甸园——舟山路455号成了日军军警驻扎的地方。也有邻居说,這里曾做过日本宪兵司令部。日本投降后,这里成了民国政府机构。上海解放初期,这里又变成提篮区人民政府。
我家搬进来时,这座带佛堂的豪宅,又变身为虹口区机关幼儿园。区政府迁移了,他们的子女住了进来。因为是机关幼儿园,门槛自然要高一点,除了不菲的入托费,大概还有政治因素之类的讲究。
伊甸园前后两栋楼,与我家住的石库门面积一样。前面一栋四方形的建筑,外墙用耐火砖加花岗岩石砌成,看上去敦厚结实。大概时间久远了,外墙呈褐红色。与它相连的另一栋楼,则是土黄色。两栋楼中间是一个很深的天井,两栋楼之间,有楼梯连接,也就是我看见小天使从这栋楼穿到另一栋楼的部位。
土黄色副楼与我们晒台平行,但比我们高一层。那个凶狠的麻脸方师傅每天在底楼天井忙碌,用很大的竹箩筐淘米洗菜,有时与女勤杂工打打闹闹。每次我们用小石头扔他,他就抬头骂我们,骂的是苏北话。
土黄色副楼屋顶墙面上,有几道裂口。老邻居说,这是东洋人扔炸弹时震裂的。这种裂痕,我家墙壁上也有。老邻居还说,我们晒台上也曾有两间房子,是大房东家的佛堂,后来被炸了,现在还有墙基痕迹。
与日本人轰炸相印证的是,我们后门围墙外(从晒台上可以清楚看到里面的一切)有一个堆钢铁的大仓库,大家管它叫铁厂。但我一直奇怪,在我们这片新式里弄林立的寸金之地,怎么会有一个几百平米的废品仓库,以及仓库四周的简陋的矮平房。打个比方,仓库以及它四周的矮平房,就像女人漂亮的脸上留着一个不相称的疤痕。或许这是战争留下的伤疤,只是后人好忘事,没人说得清它曾经遭遇的血腥。
尽管在我们孩子眼里,伊甸园是一个无法企及的地方,但在老邻居中间,一直把它看作是一幢沾染血腥的凶宅,并私下流传对面大楼闹鬼的说法。大意是说,东洋人撤退后,对面大楼里,还经常能看见裸体的日本女人飘来飘去,还能听到日本女人淫荡的嬉笑声。那些日本女人皮肤白皙,身材娇小,披着白色丝巾之类的东西,从一间房间,飘到另一间房间,看上去就像是在相互追逐嬉闹。有些时候,这些日本女人到后面的副楼去洗澡,腰际挽着盛放洗涤用具的精美器皿,从主楼穿越楼道,一路上相互打趣、嬉戏。
之所以断定白色影子就是日本女人,理由之一是这里曾经驻扎过日军宪兵或者日本军警,有过职业女军人或者女性军警人员。理由之二是,我们邻居中有日侨,能听懂女鬼的话。再有就是,日本女人的妖娆、风姿、妩媚、柔顺,老上海市民,并不陌生。
当我听到这些私底下流传的黑暗故事,曾不止一次希望能看到或者遇到她们,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希望见到女鬼,还是希望看到作为鬼的裸体日本女人。或许,这仅仅是一个小男孩朦胧的性意识反应,距离作为男人的欲望,还有很长一段日子。
从虔诚的礼佛堂,到日本宪兵或军警驻扎的机关,这种巨大的反差,令人难以想像,也难以接受。但是,历史确实在这儿上演了,不同的是,又好像经过彻底的清扫,所有的主角,都已经缺席,不在现场。
等到我们这一代来到世上,这里已经成为伊甸园。但由于它非同一般的历史,依然深深吸引着众人的视线,吸引着我们孩童,包括一些大人探寻它隐秘的浓厚兴趣。其中猜测最多的是,既然这儿曾经做过日本鬼子的虎穴狼窝,肯定存在一个实施刑罚的地方,比如地下室。但地下室在哪儿?
我十一岁那年,一场虐杀野猫事件,终于使这个隐秘的地下室得以曝光。同时,也把篱笆墙的存废,置于风口浪尖。
我没有参加这次虐猫,但我知道这只黑猫。这是一只浑身漆黑,毛色发亮,眼睛闪着荧光绿的雄猫。因为它的个头比一般猫大,体格也壮硕,所以看上去更野性。更令人恼恨的是,它不怕人,反而让很多人躲避它,这也是导致它最终殒命的原因。
我与这只巨型黑猫,有过两次遭遇。一次是在我家后窗外的铁厂屋顶。那是个夏日的黄昏,我偶然看见它倨傲地蹲坐在石棉瓦屋顶上,两只闪着荧光绿的眼睛,炯炯地注视着我家窗户,似乎是在探究里面的秘密。此时,残阳如血,殷红的余晖照耀在它漆黑的毛皮上,发出绸缎般的光泽。我试图轰走它,打手势,扔东西,但它对我的驱赶,不屑一顾,懒洋洋地蹲坐在那儿,不时扭转一下脑袋,悠闲地看着四周风景。
还有一次,是我晚上回家。我们那楼没有公用路灯,一到晚上,伸手不见五指。一般情况下,我都是一边唱歌壮胆,一边摸索前行。那天,当我从小弄堂拐进后门时,明显感觉气场不对,黑暗中,似乎有东西存在。
踏上楼梯前,我像平时一样踏了几下楼板。这个动作,看上去是在试探脚与楼梯的距离,其实,还含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对黑暗中可能存在的东西发出告知。因为一直传说我们这幢楼闹过鬼。
果然,黑暗中,有两道绿莹莹的光射过来,闪烁着一种令人恐怖的寒意。我心里一惊:我与黑猫狭路相逢了。因为黑猫浑身漆黑,所以,这黑暗就像给了它隐身符。但它的荧光绿的眼睛,又暴露了它的存在。
正当我上下为难,进退失据时,突然感觉裤腿边一凉,似乎有一股风拂过。我想,大概是黑猫逃走了。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又让我陷于疑惑,以致我又怀疑刚才脚下碰到的是什么不洁之物。
当我以为黑猫已经从我胯下溜走,而连蹦带跳上到二楼时,一抬头,却看见通往晒台的石梯上,那黑猫正倨傲地蹲伏在那儿,两只荧光绿猫眼,炯炯注视着我。是我刚才碰到鬼,还是此刻我眼花了,一刹那,一股凉意,从脚底心升起。
它不逃,只能我逃了。
据参加虐杀黑猫的邻居说,那天晚上,隔壁门牌号一位新疆回沪青年(我们叫他新疆哥哥),与自家兄弟喝了点酒,出来散心,在小弄堂右手(我们后门这边),看见黑猫蹲伏在黑暗中,这时候,如果黑猫知趣地“喵喵”叫两声,退让一步,溜之大吉,也许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但偏偏,黑猫看见人,并不躲闪,还是倨傲地蹲在那儿。
这无疑是一种挑战,对人的尊严、权威的挑战。哪有野猫见人不躲闪的道理!新疆哥哥又是喝过酒的,于是好玩地朝黑猫嘘了一声,黑猫没动静。他弟弟说,这只野猫很凶,不怕人!新疆哥哥说,它不怕人,我也不怕猫,总不能我们躲它吧!
说着,朝黑猫走了几步。那黑猫懒洋洋地起身,竖着尾巴,不慌不忙地朝后走几步。看见新疆哥哥停住了,又回身蹲踞在那儿。
新疆哥哥恼怒了。骂了一句:老子不信你不怕!朝黑猫走过去。
那黑猫懒洋洋起身,不慌不忙地朝着小弄堂纵深处逃逸。因为小弄堂实在太黑,那猫一转身,就不见了踪迹。只有当它停下来,回头看人的时候,它的眼睛才泄露它的行踪。
这样走走停停,由东西向来到南北向。一到那儿,那黑猫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地盘,发出一声龇牙咧嘴的怪叫,一个纵身,跃上两米多高的篱笆墙。
新疆哥哥没提防黑猫有这一手,吓得朝后退缩几步,等他明白过来,那黑猫已高高在上,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俯视着篱笆墙下面的人。
新疆哥哥暴怒了,扑上去抓住篱笆墙拚命摇晃,试图把黑猫摇晃下来。嘴里喊着:我要杀了你,吃你的肉!喊叫声惊动了我们楼下的邻居(他们是表兄弟),门开了,灯光露了出来,照亮小弄堂一角。等明白是在抓黑猫,一声招呼,屋子里马上又涌出很多人,纷纷叫嚷道:那只猫呢?杀了那只野猫!
一场围剿黑猫的行动,在篱笆墙这边展开了。
暗黑的小弄堂,冷不丁響起的吵嚷声,首先惊动了底楼的其他邻居,然后就像石头投掷到水里,引起一圈圈涟漪,扩散开来。很快,旁边门牌号的邻居也从小弄堂两侧围观过来。
显然有人是误会了,手上拿着手电筒,一边用手电照射,一边惊恐地问:小偷在哪?
没有小偷,我们这条弄堂,从来没有发生过偷窃事件。于是,一道道光柱,投向篱笆墙。一些胆大顽劣的男孩,趁机爬上篱笆墙,骑在上面;还有一些人,翻墙进入伊甸园。更多的人,则加入摇晃篱笆墙的队伍。所谓人多势众,在这个时候完全体现出来,一会儿工夫,剧烈晃动的篱笆墙把黑猫震落下来。也活该黑猫背运,正好落在我们这边。
跌落在地的黑猫,还没来得及起身逃窜,已被反应快的人踹了几脚。黑猫“喵喵”叫了几声,左冲右突,看着无路可逃,再次跃上篱笆墙。但这回,身手已不再敏捷,只跃到一半,被大家齐心协力使劲一阵摇晃,又跌落在地。
但黑猫不愧是一只壮硕的野猫,尽管人们棍棒齐下,又踢又踹,打得它“喵喵”哀叫,但还是被它瞅个空隙,跃上篱笆,然后纵身一跃,跳下两米高的篱笆,逃到伊甸园。
伊甸园天井里,早有人恭候,一见黑猫滚落在地,蜂拥而上,操着顺手拿起的铁铲、煤钩、大扫帚等家伙,棍棒齐下。
黑猫一边“喵喵”哀嚎,一边往土黄色建筑逃窜。人们打着手电,一路追打,最后来到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地下室。无路可逃的黑猫,被人们紧紧围堵,逼到墙角。很快就有人找到电灯开关,灯光下,黑猫无处遁形。有人在地下室找到一根铁棍,砸黑猫的脑袋,结果被它用牙齿咬住,怎么也拔不出来。没办法,大家只能用现成的家伙,朝黑猫乱打一气。直到咽气,那根铁棍,还被它死死咬在嘴里,拔不出来。
黑猫被虐杀后,我们弄堂里的人,把它当战利品一样拖来拖去。一根粗麻绳套在黑猫脖子上,它的嘴里还咬着那根铁棍,两只曾经闪烁荧光绿的猫眼,半睁半闭,但已经没有懾人的寒光。
很多看到过死黑猫的人都惊叹:这只黑猫,足有八十厘米长。
当晚的虐猫,也惊动了伊甸园。次日一早,院长带着烧饭师傅和几位女老师,隔着篱笆墙与我们这边交涉。她们指着像遭遇强台风侵袭一样变成S型的篱笆墙,要我们赔偿修理。但因为我们这幢楼里,几乎每户家庭都参加了虐杀行动,所以,无论伊甸园这边怎样隔墙喊话,都没有得到回应。
本以为这件事情会不了了之,谁知我们错了。隔天上午,伊甸园里来了很多建筑工人,也运来红砖、黄沙、石子、水泥。他们单方面做出决定,推翻已经损坏的篱笆墙,砌一堵砖墙。
我们这边,新疆哥哥悄悄回新疆去了。
那个年代,虐杀猫,上纲上线的话,非同小可。何况,新疆哥哥家庭成分不好,他父亲在大西北劳改。他原来在上海工厂上班,后来响应“有志青年到新疆去”的号召,报名到新疆农场去了。
伊甸园地下室,除了墙上几个可疑的铁挂钩之外,空无一物。没有老虎凳,没有皮鞭,没有烧红的铁炉,没有烙铁,更没有血迹。
从20世纪20年代杭家的花园洋房和佛堂,到三四十年代的日本军警或宪兵驻扎地、“二战”后的民国政府机构,再到解放初提篮区区政府,以及1960年代的幼儿园,将近四十多年的时间跨度,即便曾经有过鲜为人知的秘密,也早已被冲淡、湮没。
篱笆墙被推翻,给我带来短暂的不适,原先从前门出来,眼睛习惯往东瞥去,透过篱笆墙的菱形空隙,隐约可见里面的景物。这一切已经在我的视网膜上烙下烙印,现在,篱笆墙拆除了,眼睛看出去空荡荡的,心里也感觉空荡了。
但很快,大家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便捷。以前,去一趟舟山路菜场,或者到唐山路、提篮桥买日用品,到霍山路小人公园玩耍,必须从弄堂底走到周家嘴路弄堂口,再右拐到舟山路。现在,穿过伊甸园就是舟山路。
没有藩篱的感觉真好。
伊甸园和我们弄堂,不,严格说来,和我们这幢房子,几乎成了一家人。那个用络腮胡子掩盖满脸麻子、平时看见我们凶神恶煞的烧饭方师傅,那些天,看着我们弄堂里大人、小孩,像串门走亲戚似的在伊甸园里进进出出,只能睁一眼闭一眼。那位长得粗壮有力、却并不难看的女院长,则知趣地把小天使堵在罗马柱子大厅里面,而她自己带着几位老师,像母鸡守护小鸡,守护着她暂时变小的领地。
一个星期后,一堵两米多高的砖墙,在原来篱笆墙的地方竖立起来。
从此,我的伊甸园被封闭、消失了。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伊甸园的主人——商务印书馆杭姓股东老板的子孙,带着地契回来,想索回所有权,当看到祖上留下的房子,现在成了舟山路幼儿园,答应继续无偿提供使用,唯一的要求是,屋顶佛堂,要按原样保留,不得擅入。可惜“文革”时,佛堂上面挑出的飞龙已被敲掉,无法恢复原状。
写这篇文章前,我在网上意外查到2003年公布的虹口区第一批不可移动文物名单,舟山路455号,也就是与我家一墙的伊甸园赫然在上。
现在,我家三楼晒台,已经变成了邻居违章搭建的房间。如果我还想伏在磨石子栏杆上朝东眺望伊甸园,只能在梦里了。小弄堂也成了楼下邻居蚕食的对象,大家按照各自房间的长度,朝小弄堂扩张,所以,也没有小弄堂了。伊甸园那个满脸络腮胡子的烧饭方师傅,肯定不在人世了。那位整天像母鸡呵护小鸡的女院长,如果在世,恐怕也有九十高龄了。
当年那些入托伊甸园的小朋友,早已云散各处,他们之间还有往来吗?他们还记得那群伏在晒台上朝他们吐口水,或者像鲶鱼一样钻过竹篱笆,入侵他们伊甸园的邻家男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