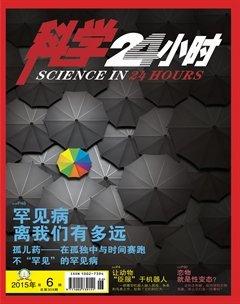我们该向世界学什么
2015-06-04程浩庆
程浩庆
在面对罕见病这一全人类的共同挑战中,世界各国的先行者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美国、欧盟、日本等针对罕见病的立法,已经形成了一套体系,并界定了各类机构的管理职能与孤儿药研发的特殊通道,形成了一套有益的促进机制。
对于常见病和罕见病,建立医疗中心或提供专业诊断和治疗某种疾病的医疗实践是一种常见的策略,这有助于提高护理的质量和一致性。我们应当学习发达国家的做法,设立“伞状结构”:伞顶是研究与统筹的管理“司令部”,它直接受国家卫生机构的管理,或者与该病症的研究基金与公益组织进行合作,形成各类信息的集成和处理中心。其下端如网状,覆盖各类各级诊所、治疗中心和综合医院,形成信息联动,资源共享。而为每一种或几种罕见病设立的专业中心,就好像雨伞的伞骨,既提供着支撑服务,又有利于统筹安排,实施掌握第一线的情况。对罕见病而言,专业中心可以以现有的证据和经验为基础,向临床医师提供咨询帮助或是护理指导方针,并在紧急或本地资源不足时成为转诊点。当然,这些中心还能发展成为研究基地。
此外,患者的力量也需要整合。在美国,不少患者及其家属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自主设立某种罕见病的基金会或者倡导组织(有的组织在创立之初,只有10个左右的患者)。他们发动社会力量进行筹款,呼吁社会的关注,针对该病症可能享受的医疗保险政策进行游说,并且联动议员、研究机构、医生、制药企业和社会各界力量(不乏社会名流)对该项病症进行研究,形成一种“众筹”机制。正是因为这些公益组织的力量,才使越来越多的罕见病进入大众视野,更好地推动了医疗研究和社会认知。这些组织甚至设立奖学金,以此吸引顶尖科学家进行某一领域最尖端的研究,并且促进研究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形成良性循环,整体受益。患者力量的崛起,有助于更准确快速地确诊罕见病,并为孤儿药的研究与研发提供第一手的样本。
就罕见病而言,患者人数的稀少,是制约其研究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恰恰是我国“弯道超车”的良机。虽然国内目前针对罕见病的研究相对落后,但由于庞大人口基数的存在,使得我国潜藏着得天独厚的研究样本库。目前一些知名的罕见病研究学者数据库中,还鲜见中国学者的名字,几乎所有的顶尖研究者都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教授或医生,拥有该领域最权威的话语权和最尖端的研究成果。
对罕见病的研究,可以改善和提高对常见病的诊治和认知,两者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而这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科技实力。希望我国可以加快立法制度建设和政策鼓励扶持的脚步,让关于罕见病之谜的解答和研究的权威发布之中,听到中国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