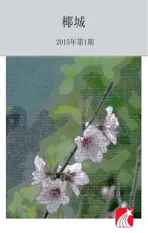只属于你自己——谨以此篇献给残疾朋友们
2015-06-02付明君
■付明君

一
如果我的腿上绣的是一朵花,而不是绑束的石膏,我的痛苦可能会轻一些;如果包围我的是花儿的馨香,而不是医院里来苏水的味道,我的忧戚也许会薄一些;如果亲吻我的是香吻情爱,而不是疼痛,我的泪水也许会少一些;如果我的世界是广阔的天地,而不是一张床上,我的愁眉也许会展开一些,如果每天面对我的是工作和学习,而不是天花板,我的哀怨也可能会淡一些……可是世上没有如果的转折,主宰命运的神,那天晚上一跺脚,使了一个魔力,就把我这只本来已伤痕累累的弱鸟的翅膀折断了。那种剧痛的袭来,使我觉得人生行与卧只在一刻间。
躺在病榻上的我,每天从窗口望着天上的雁阵不由得心生嫉羡,经常对看着窗外发呆。我觉得“天道无亲,常与人善”这句话根本就不是正确的,为什么灾难伤痛总降临在孱弱的生命上?难道我历经四次大手术还不够吗?还要在我羸弱的身躯上遭受痛苦的磨难才能得以身心壮大吗?难道断了一条腿还不够吗?非要让我献上血迹才能得以证明我顽强吗?我甚至恨恨地想,为什么哀痛不能平分给另一些人呢?
正当我兴叹、孤苦、烦闷、忧伤、痛楚、感慨时,手机响了,我没急着看是谁的电话,况且是谁的又有何意义呢?或许就是一声久违的问候,一声怜悯的叹息,一个高高在上的优越者的姿态。我真想把那久违的铃声按掉,可是它却轻灵地响着,给我多日沉寂的烦乱的病榻生活倒是增添了一抹新鲜的亮点,于是我按了接听键。是一个有磁性的声音,洪亮、高昂,甚至是有些震耳的男声:明君,你好!我是宋欣,听说你病了,我们一行多人,组团要去看你。没等我说话,他便兀自爽朗的大笑。——是残疾人作家宋欣打来的,电话里感觉到粗重的呼吸。我抬头看了电脑上的时间,下午一点多,这个时候他们应该刚刚上班,我在电话里对他说,我没事的,你们不要来了。那边连连说:“别废话了,你怎么不欢迎啊,赶快告诉我你的地址,同我一起去的还有瑞敏、赵凯、李茹、于晖……”他一连说出了一大串的都是残疾朋友的名字。我一再推辞,说你们行动都不方便,就不要来了,有的还正在上班。可是那边的嘈杂声传过来,都争着抢着说要过来,我沉默了一会儿,我知道,我不把地址给他们,他们决不会善罢甘休的,于是闹了一会,告知地址后,把电话给压断了。
因为自身和工作的原因,我经常接触残疾人,知道这些残疾人家庭的一些状况,大多是以残养残,有的是在残联工作,有的是在社区工作,有的开三轮车养家糊口,生活过得都很紧巴,所以我不想让他们为我破费,然我又很难搪塞他们的好意,特别是我无法对那真挚的一颗心说谎,对受过伤残的人说谎,太不道德了。就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还在纠结着,我是否真的有必要把他们写出来,是否应该永远把他们保存在我的记忆中、生活里。我深信,一旦把他们用文字表现出来,就会有不那么光彩的动机,这种动机是那样自私,甚至是剥开他们的伤疤给世人看,这种做法是残忍的,偏离了我要表达的实质意义。看,我是多么的狭隘、自私、功利。写出这些就能唤起对残疾人的重视和关爱吗?是为了这个吗?可是我想了想又不是,因为一个可怕的顿悟在我的脑中闪现了出来:在很多次关于写作的思考中,我认为文字不是让人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媒介,而是一个人想通过文字获得内心的愉悦和发泄,在这个过程中释放自己、呈现自己、表现自己,特别是写残疾人。悲悯、关爱、同情都是极富优越感的词,它来自于强者的优越姿态,我耻于提及。然而,有一种强烈的声音又不时地撞击我,我知道它是什么,但无法准确地说出它。面对电话里声音,毫无疑问地,他们忘了自己是残疾人。而我却被一场意外击昏了头,有了一种缠绕于心的生命困惑,开始了漫长的内心焦灼,每天不梳洗不打扮,不问卷,像一头猪似的在床上打圈。
放下电话。我把乱如蓬草的头发拢在了一起。然后让爱人把我塞到了轮椅里。来到窗前,看着窗外久违的绿色植物,恍惚间,我由一个健康的人一下子变成了什么都不能做的人。一下子由一个每天亲吻阳光花草的人变成了每天同沉闷的空气亲近的人。我甚至不愿意回答他人对我关切的询问,看来我是真的病了。
我笨拙地沮丧地滑动着不听使唤的轮椅,忽然对常年坐轮椅的人心生敬佩。想到了坐轮椅要来看我的李茹,我私下里叫她李姐。她两条腿都有残疾,而且是很重的残疾,两条腿软得像面条,每走一步都要站稳后才能挪动另一条腿,平时坐轮椅上,必要的时候,如上台阶时就拄着拐杖走路,我不愿意把她走路不堪的样子呈现在世人面前,我也不想细致地去描述她艰难走路的样子,那样太不敬了。然而她却是让我最敬佩的,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人是游泳健将,会开车,爱好文学,创建了《蓝星湖》残疾人文学社团,并且爱好旅游,坐轮椅游遍祖国的秀水山川。才坐了半个月轮椅的我,都要由家人把我搬来搬去的,我真的无法想象,一个双下肢重残的弱女子是怎样艰难地借着轮椅行走出了精彩的人生路的。
没有了腿,我们借条腿也要走。没有手,接个假手也要写,手和脚都没有了,我们也要旁借拐杖和轮椅也要行。这是残疾人共同的心声,他们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自强,不要依附他人生活。有一句话说得好,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时,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窗。其实,我是极不赞成这句话的,这是极不富同情心的话,如果一定要说有上帝给人打开一扇窗的话,这扇窗不是上帝给的,是残疾人自己开创的。
二
给我打电话的那位宋大哥,是一次车祸中,失去了双腿和右手。按理说,他是最最该坐轮椅的人,最最该悲叹世事的人、最最该颓废抱怨的人。可是他偏偏是最乐观、最阳光的人。
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都会滔滔不绝地打开他的话匣子,给我们讲生活中他遇到的糗事、趣事。特别是他讲到他被火车压断双腿时,他说当时旁人吓得手足无措,他却镇静地告诉旁人赶快绑扎止血,当裤带不够用的时候,旁人不知怎么办,他却冷静地告诉别人,你不是还有鞋带吗?血流满途。他讲述的时候我的心揪得紧紧的,可是我却全然在他的脸上读不到危险,死亡,疼痛,挣扎。威胁在他面前是无效的,他说,他不害怕这世间的任何东西,包括死亡。他害怕的是没有知识和文化。他说:其实是知识救了我,我就是闲着没事的时候,看了一本书叫《危难之时如何自救》,我清楚地记得那一个片段,就是流血时要绑扎止血。到那时就用上了。是啊!知识能改变命运,拯救生命。
也因为此,宋大哥自办残疾人福利工厂,自学文学创作,最近完成了一部二十多万字的写残疾人创业求索的自传体小说。小说写完后,他拿给我看让我提提意见,说心里话,我总认为我比他们能强点儿,当然指的是走路。可是读完小说后,我有那么的一瞬感受到了自身的弱,猥琐,还有难以启齿的羞愧。特别是接到电话后,这样的羞愧还是侵袭着我。在电话中我说,我站不起来了,连双拐都不会用。宋大哥先是爽朗的笑,然后说,我告诉你,你还有一只脚呢,我没有脚都能站起来呢!是啊!宋大哥虽然失去了双脚,他却安上了假肢,行走在世上。读完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我没有给他提意见,不是孤傲,是不配,低卑的我有什么脸面对一个大写的人品头论足呢?于是我只在他小说的扉页上留下了一行字:这个世上四肢三残的人不多,可能也不少,但是能站起来走路的我还是头一次看到,你是第一个,不仅在躯体上,也是在精神上。
我能站起来吗?一场意外就把我打垮了,身心都倒下了。我真想找出一堆自我辩解的理由。啊,上天更应该怜悯我。我是那么不堪,那么可笑。
三
我真不愿意说出,以前我一直以旁观者的身份、健康者的身份甚至以悲悯的心态潜伏在这些残疾人的生活中。这个感觉太可耻了,几近卑鄙。我太像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游弋在他们之中,来捕获他们隐秘的一切,以此来满足我的好奇心,满足我的惊喜及卑劣的一笑,特别是有一次我拿着相机在一个坐着轮椅的脑瘫残疾人面前一阵猛拍,然后想像着这些图片传给那些健康的朋友引起的惊叹。这位脑瘫者却毫不知情,她歪着头,眼睛却清澈如水,皮肤白皙细嫩,笑容、梗直的身体以及她的命运都裸呈在我的眼前。我甚至不正面看着她,心想这个样子了,还出来干什么?于是我以旁观者的姿态躲着她,看她那僵化的动作,那僵化了的双手和双腿。但当她那惊恐的大眼睛看了我一眼后,对我彷佛射出一道电光,并对我露出了莞尔的一笑,我莫名地被感动了。
“她太漂亮了,还对我笑哩!”我对她的护理员说。
“不,她的笑只是肌肉的痉挛而已,纯物理性的自然反应。”听到她的护理员这样冷酷地纠正,不知为什么我心里生出莫名的反感。
但是,我如何能相信,那一双双清澈的眼睛那莞尔的一笑是物理反应呢?她能写诗,不是用手,是用鼻尖在键盘上敲字,她能准确地用手机给你发信息,不是用手,还是用鼻尖。
这根本不像一个脑瘫者能做的事,也根本不是什么物理反应。其实,她跟我们没有什么不同。
“就这样,还想谈恋爱呢!”护理员的话忽然又从我耳朵飘入,我猛一抬头,她继而用全知全能的口气说道,她这种症状叫做“钟情妄想”……不知道为什么,我很不喜欢这个护理员,不喜欢她跟我说的这一切。还有她那不屑的表情,有一种自以为掌握了真相,然后是得意。我忽然觉得那种眼神比起那双大眼睛真的很丑陋。
我仔细端详着那位脑瘫患儿的脸,想着,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当她忽闪这大眼睛痴痴地跟一个男子示意,我喜欢你时,谁能抗拒呢?她凑近那个男人的脸,喃喃地把她的青春美妙的气息传到那个人的身上,这不正是她贞纯品格的裸露吗?人们太迷信书上的那一套了,那么冷酷,说她妄想症,说她是疯了。在我的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他们有家,有妻儿老小,可是他们还在坟墓外谈男女情爱,为了什么呢?毫无疑问,性,男女间最本质的关系。我觉得他们才是妄想症。我知道,相比脑瘫的这位,他们才是世俗的疯子呢!
我多么希望这位脑瘫美丽的女子,能好好地同一个男人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啊!
四
正思忖间,正赶往我这里的残疾朋友来了电话,问我准确位置,并打趣说:“我们组团来忽悠你来了,你残了并不可怕,我就怕你脑残对我们施加暴力。”
说到暴力,我想到了那时我工作的时候,经常接触一位小脑萎缩的大姨。
有一天她失踪了,我们费尽周折,四处寻找,还好,终于在一个脏兮兮的宠物市场上找到了她。当时,有很多人围着她,观看她疯癫的表演。当我们要领她回家时,可她就是不肯和我们走,还拿石子打我们,最后还是大姨的爱人赶到,她才像孩子似的跟着回去。
她甚至不会用言语表达思想了,每天总是简单的几句话:“不知道、你上哪去?”还有一句我们谁都没听懂的话语,就是“他老人家好受啊!”我们谁也不知她说的是什么意思。你若是问她,她便会答非所问道:“你上哪去?”
特别是每次看见丈夫进进出出的她都会没完没了地问:“你上哪去?”我们若是问她:“你吃饭了吗?”她还会回答:“你上哪去?”“你儿子叫什么名字?”“你睡觉不?”等等,她一律都是以“他老人家难受啊,或你上哪去”作答。因此,我有时也像有病似的,想尽办法引诱她说出或者做出那种意外的另类举措,可是大姨会向我怒视双眼,不予理睬我。但我若是问她:“你老伴叫什么名?”她却会毫不犹豫地响亮地答道:“王允德。”说完还会“嘿嘿”抿笑两声。我们知道大姨没有疯,她内心深处有着最真挚的爱。
她胖得肉在晃动,大小便失禁,有时一边走一边漓啦,有一次给她擦洗,我帮着托起她的后背。一阵腥臭味扑过来,我皱了一下眉头,表现出了异样。然后她就骂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给大姨喂食、换衣、洗澡,包括洗不完的屎尿裤。啊,我做到了,我都做到了!
有一次我把这事儿讲给我的一个朋友,没想到我的朋友居然恶毒地说,有精神分裂的人,残疾的人一定是上辈子没做好事儿。我痛恨死了这样的话儿,有那么一瞬间,我也想发作,想拿石头向那恶毒的人狠狠地砸去。最好是把他也打成残疾。可是我想想又罢了,真要是把他打残疾了,那是哪辈子做的孽呢?况且谁能同一个精神上的残疾人计较呢?因为精神分裂的不仅是大姨,当然还有我。我真的病了。
正踌躇间,敲门声响了,门打开的那一刹那,鲜花、水果,拥抱伴着笑声汹涌而入,有拄双拐的,有让人搀扶的,有一走一颠的,看着他们每一位的残疾都比我重,而每一位的笑声都比我爽朗,忽然地,一股悲凉从心底升起,无可名状,我被他们打败了。宋大哥说,你拄拐走两步。我试着走了一下,几乎跌倒,看来我还没有适应灾难的生活。李姐说,以后好了的时候,也要拄拐,那样安全些。并问我怕难看啊?说心里话,我真的怕难看,我无法放下自己,但是我没说出来,也是因为没放下,就像无法改掉的一种习惯,一种思想,只属于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