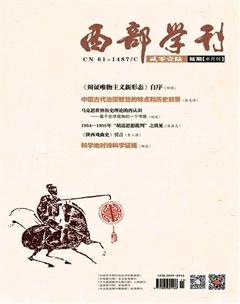像飞碟一样晃悠(短篇小说)
2015-06-01车海朋
车海朋
我妈或许是个勤勉的小学老师,打从我记事起,要不是周末,我在白天基本上看不到她的身影,她年年都从市里领回金光灿灿的“先进班主任”奖状。要说的是一个星期六,老妈回归传统家庭主妇的日子,晌午刚过老妈就在厨房咄咄咄咄忙开了,擀饺子皮、涮香菇、剁肉泥,这意味着我们家将迎来久违的猪肉香菇饺子宴,老妈支我去平水街上打醋,再三叮嘱:“要剥隘老陈醋,可记好啦,是剥隘老陈醋。”结果我果然就忘记了,因为这名字可真拗口,我兜里揣了十元钱,像得到了妈妈鼓励的小马驹一样,蹦蹦跶跶一路小跑,心无旁骛,嘴里只顾着来回念叨,“剥隘老陈醋,剥隘老陈醋。”就在快要跑出院门的一刻,险些被驶来的一辆车迎头撞上。那辆白色轿车紧急制动时轮胎在柏油地面擦出的一阵气流,将我掀翻在地,引擎盖离我的鼻尖,不过半尺的距离,我吓出一脑门的冷汗。一个大墨镜女郎探出脑袋,瞅一眼惊魂未定的我,冷冷地撂下一句“没长眼睛的”,一溜烟开走了。
我口中的念念有词被迫断篇,爬起来就忘记那个什么醋了,我坐在一堵矮墙上心急如焚,可是怎么都想不起来了,整个人好似掉了魂一样,一筹莫展。
这时候斜坡上来了一只漂亮的小柴犬,它圆滚滚的棕黄皮毛溜光水滑,两片扁桃树叶一般修长的耳朵警觉地竖在脑袋上,显得特别威风凛凛,我觉得它就是犬类中的“酷男”,我忍不住多看了它几眼,它也酷酷地看着我,我俩互不搭理,然后我抬头看着天空出神,它则坐下来,跷起后腿在头上挠痒痒,也许是地势不平坦,也许是它长得太胖了,大概没坐稳,它就生生从斜坡的边沿滚下去了。
我终于忍俊不禁开怀大笑起来,笑得泪花都出来了,笑得差点也从矮墙上掉下去。这时小柴犬已回到斜坡上,大概是自尊心受到刺激,它突然冲我吠起来,汪汪、汪汪,吠个没完,把我吠急了,我也冲它咆哮,吼道:“你自己滚下去了,管我屁事啊?”吼完我就跑回家去了。
这当然已经是十几年前我的童年往事了。每个人都有一个终将逝去的童年,也许你曾是熊孩子,也许是乖孩子,现在再来追忆童年,不管是哪一种色彩,总是意犹未尽趣味盎然。梳理我的童年,它与你的童年或任何一个人的童年并无多大的不同,一定要说不同,那就是——我的童年有点儿幻想症。
十几年前我家住在一个叫“桃苑”的小区里,稀稀落落的几株扁桃树,不知何年何月被移植到这个小区,我猜“桃苑”这么诗意的名字就来源于此。其实,就是一个南方城市常见的那种大杂院,这年夏天我常常一个人在楼下游荡,幻想着能遇着点什么莫可名状的事物,譬如,我还从没看见过真飞机(更别说坐飞机了),我曾听到院里的大孩子说,飞机上的人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天天吃鹅蛋,全身都长满了毛,所以当偶尔有飞机低空飞行,掠过我们十二楼楼顶的时候,我总是睁大眼睛奋力去追看上面的人,是不是真像他们所说的“全身长毛”,但是一次也没看清楚过。
当然,我主要还是幻想飞碟。这神秘的天外来客,大人們口中的UFO,我在一本书里看到过飞碟模糊的影子,我形容不出它的优美,说它像一个圆顶草帽也不确定,它应该是椭圆形的,中间好似凸起一个圆点,围绕这个圆点,有一圈一圈闪烁的光斑荡漾开去,我承认它流畅的曲线美极了,为之倾倒和深深沉迷,可是它会不会有一天就从我们桃苑的上空飞过哩。
我幻想中的飞碟和其他奇怪的事物都没有遇到,倒是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人和各种各样的狗。有一回我正在院里玩儿,左手持一根玉米棒,右手持一根热狗,一条短腿小黑狗远远地瞅着我,准确点儿讲,是小眼直勾勾地瞅着我手里的东西,狗嘴里都流出两条长长的馋丝来了,我把热狗扔给它,它毫不客气地享用完毕,从此成为我的伙伴。
你应该看出来了,我是个性格有些怪异的小孩儿。不知道为什么,我对玩具不感兴趣,在大城市南宁工作的舅舅每年来我们家,都会给我带一两件玩具,变形金刚、装甲车、冲锋枪之类,其他男孩儿爱不释手的宝贝,在我这里完全失去吸引力,我惟一深深着迷的,大概只有飞碟了,跟着了魔似的。据说在我更小的时候,曾经奢望要一个飞碟,可是任凭我如何纠缠,我妈就是不予理睬,直到后来我明白更多事理——飞碟这东西,就是传说中的玩意儿,我自己都不确定它长什么样,恁是我妈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没见过呀,上哪儿买去?
怪小孩儿最明显的缺陷,就是不擅长跟人打交道,因此我格外珍惜这个用一根热狗收买来的会摇尾巴的伙伴,它也喜欢我,有时候我跟着妈妈从外面回来,小短腿总是很兴奋,像一只皮球一样从远处连滚带爬地滚过来,用双爪扒我的凉鞋,用脑袋蹭我的小腿,有时候我会给它吃的,有时候两手空空,我就用脚背一遍遍地挠开它,它在地上打着滚,爬起来继续一路蹭我,直到把我蹭到楼梯口它才掉头走开。
从小我就认为,狗是世上最友善的动物。孤僻的小孩儿没朋友,所以我把它们当做最好的玩伴,用现在的话来说,我还是个“狗狗控”。
我们桃苑是一个有点儿年月的小区了,这里的日常生活嘈杂而乏味,院外就是熙熙攘攘的平水街。进得院门,是六七栋建于不同年代、混乱无序的住宅楼,住着两百来户人,什么单位的都有,没单位的也有,还有不少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租住户,大家进进出出,庸常地生活在拥挤局促的空间里,白天黑夜,日复一日,却极少能重现往昔那种其乐融融的邻里关系了,我经常看到大人们在院里相遇,大多数人互不打招呼,甚至头都不点一下,总是面无表情,目不斜视,生疏得跟大街上擦肩而过的路人没有什么区别,人们各进家门,大门一甩,老死不相往来。
我说不清是我性格怪异,还是因为没有小伙伴跟我玩使我变得孤僻。桃苑里的大人们关系生分,小孩儿们似乎也沿袭了这种人际风格,都不喜欢在院里逗留,那些比我大的孩子不上学的时候,尽往外面的平水街上跑,一头扎进网吧或者电子游艺室里,一玩大半天不回家;更大的孩子,则喜欢往隐藏在平水街夹巷里的录像厅钻,两三个小时过去,才神思恍惚地出来。
所以,我这样一个小孩儿,常常只能跟院里的狗玩,更多的时候我就独自坐在院墙上发呆,看天空有没有飞碟,可是我经常看见一架亮锃锃的飞机,或者两三只灰色的大鸟从高大的扁桃树枝桠间飞过去,却没有看到过期待中的飞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