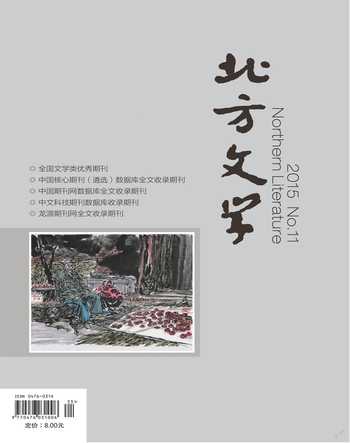空间焦虑下的身份追寻
2015-05-30卢佳婷
卢佳婷
摘 要:同为流散作家,面对身份无法被认同所带来的空间焦虑19世纪的约瑟夫·康拉德和20世纪的V.S奈保尔在身份追寻的过程实现了一次超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本文以空间理论为基础通过比较《在西方注视下》与《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主人公空间焦虑下身份追寻的不同表现形式,进一步体会两位作家在重塑精神空间的情况下对人生意义的共同追寻。
关键词:空间;焦虑;身份认同;拉祖莫夫;毕司沃斯先生
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F.R.利维斯在其著作《伟大的传统》中曾说“康拉德的人物是逼真可信的。”[1]P66不可否认康拉德政治三部曲中《在西方的注视下》的拉祖莫夫就是这样一个令人信服的角色。小说呈现了一位苦苦挣扎于俄国专制统治与暴力革命夹缝中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与拉祖莫夫相隔千里万里,一个身处大家族夹缝中生存的追梦者——毕司沃斯先生,来自于奈保尔早期创作的最高成就《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小说不仅以房子开始,以房子结束,而且房子又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它讲述了一位来自印度裔移民后代——毕司沃斯先生先后四次试图建造一所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无疾而终的悲惨一生。
一、空间转向中的精神构建
在20世纪激荡变革的社会发展中,空间理论逐渐摆脱时间与空间相互对立的桎梏,将空间从时间单一压抑的叙事逻辑中解放出来,这不仅意味着思想文化氛围中空间意识的觉醒,也实现了学术研究的“空间转向”。这一转向的起点可以追溯到法国学者列斐伏尔笔下,在其1974年出版的著作《空间的生产》中,“他力图纠正传统社会政治理论对于空间的简单和错误的看法,认为空间不仅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器或‘平台,相反,当代的众多社会空间往往矛盾性地互相重叠,彼此渗透。”[2]P8受列斐伏尔启发,福柯的空间理论转向权力与地理学关系,他于1997年在《权力的地理学》中表示,“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时间的关系更甚。”[3]P20无所适从的现代个人被迫经历着心理与生理空间双重支解,“为了改变生活……我们必须首先改造空间。”[4]P190
由此,从空间这一角度出发本文分析了19世纪波兰裔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和20世纪诺贝尔文学获奖者英籍印裔作家V.S.奈保尔两位伟大作家对空间体验的特殊思考,这其中前者笔下的拉祖莫夫和后者笔下的毕司沃斯先生表现尤为明显。两个人都是空间焦虑下的受害者,所谓的“空间焦虑多用来指人们在远离自己土生土长的熟悉环境后产生的一种无处可去、无家可归的恐慌。”[5]P7他们不得不直面自己无处遁藏的人生痛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与焦虑世界进行抗争的同时,也在身份追寻的过程中创造了生命的意义,这不仅是两部伟大作品的一个契合点,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两位作家在特定时代下身份追寻的缩影。
二、身份危机下的空间焦虑
康拉德笔下的拉祖莫夫本是一位渴求通过努力学习改变自己命运的大学生,却意外地被卷入一场政治斗争之中。为了保全自己,拉祖莫夫选择揭发信任自己的革命党人赫尔丁,并被迫成为政府的一名间谍。小说开篇便强调了双亲不明的拉祖莫夫孤独的身份——“他在世上孤单得像是一个在深海里游泳的人。”[6]P12毫无依靠出身平凡的他只是想专心学习获得体面的工作和他人的尊重,因而给自己界定了一种超然离群的相处方式,但当赫尔丁闯入他的寓所并亮明刺客身份时,平静安稳的生活对拉祖莫夫来说就渐行渐远,陷入精神困境的他不得不以背叛赫尔丁的方式逃离这次政治危机。在他的理念里,赫尔丁打乱了他的生活夺走了他的希望,他背叛赫尔丁来使自己的生活恢复平静也无可厚非。但是背叛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变化了。
“人之存在的焦虑源于‘无空间性,空间性之占领是人安身立命的前提,而空间性之丧失意味着存在之丧失。”[7]P71生理空间的丧失经常伴随着精神空间的瓦解。赫尔丁的突然出现使得拉祖莫夫越来越远离自己的初衷,他失去了生理空间稳定的同时精神空间也已经崩塌。在这种双重空间的瓦解下,拉祖莫夫一方面受专制政府的监视成为其控制革命分子的工具,另一方面不得不只身前往异国,他的信念不被任何人所理解,他无法确认自己对于他人和世界的意义,身份危机感的侵袭使拉祖莫夫即使身在无人熟知的日内瓦也极力拒绝与外界世界交流,试图伪装自己已然崩塌的精神空间。
对于奈保尔笔下的毕司沃斯先生来说,他穷尽一生追求的不仅仅是一套房子那么简单,更是对个人隐私空间和独立人格的渴求,然而这种渴求在毕司沃斯先生的整个人生中都像是奢望。他刚出生因为六个手指和胎位不正被梵学家预言他是不幸的化身,“这个男孩将会是个好色之徒和挥霍者,……也可能他三者全是。”[8]P4生来“克父”更是使他从一出生就背负着不祥的罪名。最终他的淘气间接导致了父亲的死亡。父亲死后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投靠姑姑,爱的缺失和童年时代生活空间的不停变换首先导致了他的漂泊感和焦虑感。其次,在等级森严的哈努曼家族大宅里,他并没有作为一家之主的独立性,嘲讽和谩骂充斥着他的生存空间。“在哈努曼大宅里……他那时只想赶快逃离那座房子。”[8]P65个体在这种家庭组织中不能发展自己的个性,一切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毫无隐私而言,“福柯说现代社会是一个纪律社会,而空间成为权力运作的重要场所或媒介,监视是‘权力得以实现的基本方式之一,这样每一个人都处于监视之下,在如此透明的空间安排下无所逃逸。”[9]P112对于自我意识强烈的毕司沃斯先生来说,这种被监视的社会空间压抑到他始终萦绕着一种自我身份无法被认同的焦虑。
三、空间焦虑下的身份追寻
康拉德的伟大之处不单单在于通过拉祖莫夫这一人物形象展现了人对外部空间的反抗,更是作者赋予了他对空间焦虑下自我身份认同的深刻理解。
被政府派遣到日内瓦当间谍的拉祖莫夫始终将自己隔绝在封闭的空间中,拒绝与周边的人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以写日记达到排遣孤独和寻找自我安慰的目的。但是赫尔丁妹妹娜塔莉娅由衷的信任和他内心深处对告密带来的负罪感使他下定决心要做一次彻底的忏悔和坦白。相对于以前的“无家可言”,坦白之后的拉祖莫夫却意外的得到了身份认同。“我处于痛苦的深渊,但终于我可以呼吸空气了。”[6]P304虽然疾病缠身,两耳也听不到任何的声音,默默回到俄罗斯小镇的拉祖莫夫却获得了娜塔莉娅无微不至的关怀。此外,不止一个革命者来看过拉祖莫夫,在他们的眼中,拉祖莫夫不仅是一个能直面自己道德污点的人,更是一个勇于捍卫自己精神独立的卫道士。由专制高压下的俄国逃离到日内瓦,空间上的转移引起了主人公心理的微妙变化,空间不仅仅是地理位置上的变化,更多的与社会相关联,两者相互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空间是一种做出自我选择实现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在这种因素的驱动下,拉祖莫夫不仅获得了内心的安宁,更为他实现了自我身份的认同。
当拉祖莫夫以自我忏悔的方式反抗着空间焦虑的世界,毕司沃斯先生却以坚持不懈自我追寻的方式在“围城”般的压抑世界中左右突围。这种反抗最显著的表现便是他通过不停的换房子以摆脱空间焦虑带来的平庸压抑的生活方式。
毕司沃斯先生的一生曾经住过很多地方,但是无论他身居何处都没有一处属于他。这些他住过的房子都不能被他称之为家,他从未感受过“家”应有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反之代替的是充满了压抑和焦虑的边缘感。因此,对于他来说追求属于自己的房子既是外界空间和自我尊严的驱使,也是为实现对抗空间下其精神重塑和身份追寻。在这种渴求的驱动中,毕司沃斯先生先后四次建立自己小家庭的独立空间。第一次是在捕猎村,他因祸得福得到了乡下捕猎村的一家小杂铺,拥有了自己的小家园,但是捕猎村恶劣的外部环境迫使他和家人不得不离开。第二次是在绿谷,这次毕司沃斯先生决定动手建造自己的房子,他花光了身上的每一分钱也没能建成他理想中的房子,勉强用劣质的材料搭建了一间房子,但他辛苦建造的房子却被愤怒的劳工们趁机焚毁了。在西班牙港的生活是他有生以来最得意的时期,拥有体面的职业和收入,慢慢有能力筹建自己的房子。但是由于交通的不便严重影响到毕司沃斯先生上班和孩子上学,不得不再一次搬家,搬到哈努曼家族所属的西班牙港的房子,这个房子重现了在哈努曼大宅的噩梦,嘈杂和混乱使毕司沃斯先生不堪忍受,促使他进行第四次的努力。第四次拥有自己的房子是在毕司沃斯先生被赶出哈努斯家族近乎绝望离开之后。他倾其所有买下了法务官文书的房子,“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房子该是怎样凄惨:……毫无意义且无所适从。”[8]P6很显然即便这套破旧的房子让他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直至他压力太大心脏猝死,但恰恰也是这座房子成为他超越自我精神空间的见证。在那样一种压抑的环境中,毕司沃斯先生一直都在追求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在他看来这是实现自己生存空间和心理空间独立、构建自我身份认同的唯一出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更是作者本人进行自我身份追寻的生动写照。
四、流散世界中的身份趋同
康拉德和奈保尔同样是具有多元文化身份的人,一个是游离于沙俄—法国—英国的波兰作家,一个是在特立尼达—印度—英国徘徊的印裔作家,两个人都苦苦挣扎于各自疏离无根的三角世界中,一方面对于故乡而言他们是一个逃离者,但本土文化的根深蒂固决定着他们不可能与其完全分离,另一方面,在新的文化处境中他们总是格格不入,即便是被新的文化逐步认同他们也随即产生一种背叛和内疚感。这种矛盾的精神空间所带来的焦虑感迫使他们不断的进行身份追寻,从而形成了两者流散写作中的身份趋同。正如奈保尔在《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中表明,“我认为他是我结识的第一位现代作家……他的作品渗透到了他认为是黑暗世界的许多角落,那是康拉德式沉思的主题,它告诉我们这个新世界的一些事情。”[10]P217两个人都并非是某一个民族或国家或某一种文化的代言人,其身上所具有的多语性、流动性和边缘性正再现了重叠空间下历史文化之根的追寻。
在这种焦虑世界衍生出来的拉祖莫夫和毕斯沃斯先生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在身份追寻过程中彰显了小人物在重压下的优雅气度,而这两人对自我身份归属的渴求恰恰是作者焦虑空间下精神的真实写照,其身上的双重性和外位性已经决定了焦虑将如影随形,即便如此,康拉德和奈保尔终其一生将写作成为他们自我定位和自我拯救的方式,其笔下拉祖莫夫和毕司沃斯先生对身份认同的坚持不懈的精神永远存在于人类执着前进的征途上,他们的追求对于身处狂欢化流散世界中急迫进行自我定位的现代个人极具启示意义。空间焦虑下的身份认同在康拉德和奈保尔笔下才绽放出不同的艺术魅力,或虚无或真实,其中滋味尚待我们细细咀嚼。
参考文献:
[1]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M].袁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3]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包亚明主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4] H.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 Blackwell Press,1991.
[5]赵娜.空间焦虑下的艰难逃离——对《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的分析[D].长春:吉林大学,2009.
[6]约瑟夫·康拉德.在西方的注视下[M].许志强译,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
[7]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空间转向视域中的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0.
[8]V.S.奈保尔.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M].于珉君译,南京:译林出版,2002.
[9]吴冶平.空间理论与文学的再现[M].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
[10]V.S奈保尔.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M].张敏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