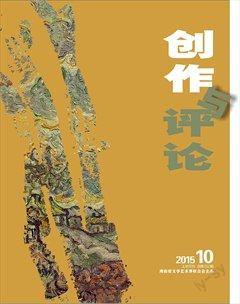“那些只在夜晚发光的事物,此刻还在缓慢的黑暗中”
2015-05-30方岩
一
“我们在干瘦的秋风里走出很远,看见
田野里的枯草浑身抽搐,
像天桥上的老乞丐
等待着,在一场瑞雪中被埋入地下”
这是彭敏那首广为流传的诗歌《我的同桌李梅英》的最后一段。在乡村意象的描述和情感表达中,城市形象(天桥、乞丐)及其隐含的情感/价值判断占据了一个很显豁的位置。正如彭敏在抒写城市境遇的困顿时,亦会把乡村当做疏通情感淤积的一个出口:“而他,是否应该停止上蹿下跳/返回偏远的故乡乐天知命?多少年了,他始终没能学会/在一次众目睽睽的跌倒之后,补上一个宠辱不惊的微笑。”(《Delete》)这些诗句大致预示了多年之后彭敏转入小说创作时的关注焦点:乡村的衰败,城市的艰辛,穿梭于城乡之间的叙事者对于此类经验的反复描述。
同名短篇小说《我的同桌李梅英》(《人民文学》2015年第2期)便是如此。“我”,文学博士,京城名牌大学的中文系教师,返乡休假的时候与昔日中学同桌、如今是某房地产商老板的情人的李梅英重逢。知识、职业、性别、生活环境所凸显的象征性文化差别横亘在这场相遇中,虽说在随后的故事进展中少不了阶层差异、经验隔绝这样的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彭敏的着力之处却是,两个人关于对方生活的错位“想象”如何被现实碾压,从而让这场相遇处处显现出坚硬的反讽:首先,一边是,李梅英无意中显露出的小镇的奢华生活,另一边是,“我”小心翼翼隐藏的窘迫的城市生活。于是,在这场相遇的开头,现实已经扬起嘲讽的嘴角。其次,用知识、职业等文化资本所包裹起的“高级知识分子”形象是李梅英想象的焦点。在她的想象中,生活状态与文化等级相关。而“我”却在盘算文化等级能否成为实现情欲的筹码。然而现实世界从来不会屈从虚幻的想象,所以,诗歌不能挑逗欲望,知识无法收编肉体。于是,一场拙劣的调情终究未能让相遇成“艳遇”。李梅英看到了文化等级背后的虚妄、廉价、无意义,而正是“我”在她面前演示了这个认知过程,并将自己的言行变成证据。最后,我躲在李梅英的床下偷听了她与情人做爱的整个过程。这个房地产商始终未作为一种可见的形象在文本中出现,在我被李梅英塞进床下后,他才以——“限量版的香奈儿”的购买者、消费者、拥有者——的声音这种形式出现,随后这声音又让李梅英发出肉体欢愉的声音,这欢愉声在我看来难免会有“炫耀和示威的味道”。坦率地说,这是个非常符号化的场景,它用一种多少显得苍白、直接的结论迅速地闭合了这个文本。而这一切源于彭敏稍显急切的社会表达和写作意图。
二
通过前述的文本分析中,我试图表明:原有的城乡二元对立框架或者将“乡村”或“城市”本质化理解,都无助于解读彭敏的创作。因而,发现新的问题、新的视角便显得非常重要。孙频曾在一篇未刊的创作谈中戏称自己的创作是“城乡结合部的屌丝写作”。我以为这种调侃无意中区分了80后作家在涉及“乡村与城市”的经验书写时的两类现象。简单说来,在城市里出生、成长并书写城市的作家,如周嘉宁、张悦然、张怡微、霍艳等人在描述经验时,“城市”本身只是天然背景而不是外在于自身的问题:城市塑造他们的身体和感觉,他们关于城市的种种情绪、观点,即便是“压迫”“异己”“逃离”等也是城市经验自然生长的结果。换而言之,描述“总体性”的城市是否成为、能否成为他们创作中的一种自觉意识,确实是个问题。而另外一部分作家,如甫跃辉、郑小驴、林森、双雪涛等人,则与前一类有所区别。这批作家通常出生于乡村或县城,经由“知识改变命运”这种阶梯,在成年以后进入城市生存、写作。他们的经验/视角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对城市和乡村都保持了疏离感和异己感。面对曾经熟悉的乡村经验却无法重返,试图拥抱新鲜的城市经验而又难以获得认同感,于是,他们只能在城乡之间无地彷徨。精神上、地理上游荡的结果,便是种种与城乡相关的多层次的经验在他们的写作中汇聚,因此,他们的身体与经验便成为文化意义上的“城乡结合部”。所以,我倾向于把这种说法作为描述此类写作现象的一种视角,甚至希望它能成为文学批评中的一个有效的概念。
值得强调的是,在当下的语境中,重新认识作为行政区划、地理意义上的“城乡结合部”在当下历史情境中的意义,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城乡结合部”作为现象描述视角、批评概念等方面的意义。在权力和资本成为新神、新的拜物教的当下,原有的城乡二元对立框架出现了新的历史表现,即城乡问题的同构性,或城乡问题的趋同性。不管是城市改造乡村,还是城市侵蚀、破坏乡村,抑或是乡村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城镇化、城市化进程,我们都应该看到城乡两大居住区域在精神状态、价值判断、利益诉求等层面的同步性、趋同性或者说相似性。这种趋同、相似、同步的最终前景指向哪里,尚未可知。但是,如果我们承认一个前提,即中国的城乡问题在根本上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建构过程的产物,或者说是作为总体性的中国故事/中国经验的一种表征,那么,我们就应该意识到,地理意义上的“城乡结合部”,它作为经验汇集场域的重要性和包容能力。因为,目前历史语境中种种暧昧不清、方向不明而又复杂的城乡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由此,衍生出的文学问题便是,如何跳出城乡的二元对立和价值预判,去具体地打捞、呈现、讨论、评价这些经验,这才是目前作家、批评家最为迫切的关注点。
三
彭敏的写作意图和社会关切正可以在这种视角下得到解释。彭敏的处女作《那时花开》(《西湖》2015年第2期)是乡村少年的暗恋故事。正如很多青年作家开始写作时,大多是从重构青春期的记忆开始。性的觉醒,死亡的想象,难以名状的快感和恐惧相互交织的情绪和心理,或阴郁或明媚的情节等,是他们作品中常见的内容。事实上此类同质化写作现象与彭敏的水平无关,亦与我们所谈论的城乡问题无关。在我看来,这只是大多数青年作家在拥有自觉的写作意识前,所面临的文学主题和经验范围的问题。
在《逃离》中,彭敏处理类似的主题时显然已经从容得多。“出走”或者说“逃离”是重构青春期记忆常见的主题之一。未成年的“我”的“出走”是为了逃离家庭关系中那些不伦的性事和情事,然而在县城与发廊技师的一场不伦的性爱却中断了我的“出走”,结果这场不道德的性爱反倒使“我”重新滋生了关于未来、关于性、关于成人世界的美好想象。青春期的“出走”、关于远方和未来的憧憬(“我去北京!”)、性的满足和幻象、成人世界的混乱和诱惑等因素相互缠绕、循环,使得这段青春记忆成为一个始终笼罩在成人世界中而“出走”未遂的故事。因此,与同类的青春期叛逆、冲动的故事相比,这个故事散发出强烈的“恶之花”气息。很显然,彭敏无意仅仅讲述一个现实世界(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抑或是县城)如何绞杀青春和天真的故事,他其实是在借用这个孩子世故、早熟的叙述语调来袒露自己关于这个世界的态度,即这世界根本无路可走。这一点在他直面现实世界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明显。《天下最好吃的咸鸭蛋》(未刊)讲述了成年人离家出走的故事。因为家庭关系,妹妹被迫出走,在东莞成为妓女并悲惨地死去。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出生农家的女子在城市中被践踏的底层故事,但是叙述者“我”却是一个拥有京城名牌大学学历同样在城市找不到尊严的人。不难看出,在这样的故事中,“乡村”(出身)成为时代的“原罪”,而“城市”正是将“原罪”制度化的原因,甚至知识、技能亦无法改变这种局面。正如前述《我的同桌李梅英》中那种对围绕着知识建构起来的文化身份、城市生活的无情嘲讽。类似的还有《阿细进城》(《北京文学》2015年第2期),这是个摆脱了家乡却又在城市中被囚禁的农妇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我们看到了彭敏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向,他试图超越城乡对立框架中那些逃离“乡村”、拥抱“城市”却又被拒绝的廉价、肤浅的伤感故事,而侧重于让某些城乡经验的描述和观点表达,与社会/时代、国家/制度等宏观层面产生联系。
这种倾向在彭敏描述城市经验时表现得尤其突出。《北京欢迎你》(《西湖》2015年第2期)这个小说题目难免会让人想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同名主题歌。当年这个口号在全世界四处飘荡,宣扬着一个大国的力量和情怀,与此对应的却是首都对待本国外来人口的制度性冷漠。因此,当“北京欢迎你”成为一部“京漂”小说的题目时,蕴含其中的嘲讽和解构意味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又不是一个在城市漂泊、打拼或悲情或励志类型的故事,文本中涉及的种种细节,如户籍、房价、区域差别、阶层差异等因素无不涉及的是总体性的“中国困境”。换而言之,这个农家子弟的进城故事最终指向的是,与国家现状、制度设计等宏观层面有关的公共经验的描述和传达。
彭敏的创作与80后文学创作中一个未得到充分讨论的现象有关:流动的生活状态,跨越区域、阶层、身份的艰难,使得各种与区域相关的经验在他们的文本中相互混杂、映照,然而他们在处理具体经验的方式上确实存在共同的趋向:把个体经验的描述作为公共经验传达的起点。这里有两个原因比较重要:一是,面对商业化的文学出版、文学传播环境,考虑到个人经验的可消费性,80后作家需要在写作策略上做出调整;二是,作为被指责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代,他们从未放弃写作中的历史担当,即重新激活文学的社会关怀、公共参与等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被视为1980年代的文学遗产在80后作家身上的承继。
尽管我把前述分析视为描述80后写作中“城乡结合部”问题的基本起点,但是在资讯传播和公共表达都异常发达的新媒体时代,当“公共经验”与“虚构”相遇时,如何避免叙事中的“问题小说”倾向,亦是我们在创作和批评中涉及此类问题时需要考虑的边界问题。或许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彭敏在最新发表的《关于黑暗房间里的假因果真偶然》里做出了新的尝试。彭敏在小说中最大程度地放弃了现实经验的直接描摹,转而碎片式地呈现城市经验的复杂性。叙事场景的跳跃,情绪转换的夸张呈现,不同境遇、阶层的人物身份、地位、相互关系的纠缠和颠倒,还有开放式的结尾,这些因素在文本中密集而错落有致地呈现。这大概得益于先锋技巧的运用,它不仅保证了小说结构的饱满和平衡,而且使得其中的经验描述保持了开放性。这一刻,我看到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和八十年代先锋派的某些资源在彭敏的小说中被激活。
四
总而言之,在诗人彭敏有限的小说创作中,我看到的是一个执着于发现描述新经验、不断探索新的形式的小说家的努力和勤奋。他的小说呈现的种种可能性让我想起他的另一篇诗歌代表作《安魂曲》中的一句话:那些只在夜晚发光的事物,此刻还在缓慢的黑暗中。我想,作为小说家的彭敏会继续给我们带来闪闪发光的惊喜。
注释:
{1}{2}参见,方岩:《80年代年代作家的溃败和80后作家的可能性》,《文艺争鸣》2015年第8期。
本栏目责任编辑 张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