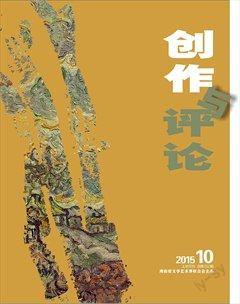栖身于“命名”之中
2015-05-30杨晓帆
杨晓帆
刚开始,我以为彭敏是严肃认真地开了个玩笑。精致诡秘的言辞缓缓道出一个悬念迭出但结局都在意料之中的故事。恰如开篇,朋克乐手、痴狂少女、躁动着汗腥味儿的酒吧里一场替人行凶的情杀,让匕首与“杀心”分离,让杀手和雇主的亲密友情恶意丛生,而小说最大的噱头就是“分身”。人生失意的阿顶,幻想出另外两个自己,阿丁和阿页,一个是衣食无忧、事业爱情挥手即来的光鲜的人生赢家,一个是龟缩在地下室里连反抗都要得到宿主批准的彻头彻尾的失败者,然后,影与影的厮杀开始了,他们彼此厌憎,又彼此成全。被安排的人生宿命、“我是谁”的身份之谜、精神分裂式的自我救赎,以及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塑形,这些主题当然深刻,但看过《搏击俱乐部》,读过太多80后小说中弥漫着的存在与虚无,这篇小说反而因其意义深刻,显得简白,仿佛作者在迷宫的每一个岔路口都已给出提示,引诱聪明的读者来玩一场志在必得的解密游戏。
然而就在我有些垂头丧气要宣判这是一篇失败之作时,小说结尾却让我不安了。在这则志怪传奇式的《前戏·十五年前》里,作者交代了分身的起源,巫蛊般的黑白人偶倒不新鲜,古怪的是那邋遢佝偻的中年人坚持要李简改名。“像惨白受伤的蛾子,一张小纸条从对方手中飞过来”。纸条上未被道出的名字,顷刻成为所有故事的开端。李简选择“阿顶”的名字,才会有“阿丁”和“阿页”,那么岂不意味着只有“李简”这个名字在世间消失,才能成全中年人口中李简命数该有的飞黄腾达。彭敏小说的结尾一贯惊惧,当读到中年人大步流星奔向录像厅的那一刹,我甚至也胡思乱想,那个中年人就叫“阿顶”,这个如诅咒般的名字终于脱手,被转让给刚从录像厅中窜出的少年。中年人的话一语双关,“你只要为我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可以了,简单得,就像你的名字一样”。这仿佛一个维特根斯坦式的哲学命题,早在由分身术的结果决定十五年后的旦夕祸福之前,新的名字已然框定了少年李简的人生。
从这一点重读小说,与其说它讲述了一个关于分身的寓言,不如说它突然暴露出我们栖身于“命名”之中的现实境遇。这个命名不单指名字,它还指那些标明了意义与价值的句子,比如“这样”才是美好生活,“那样”才是更好的自己。就像小说中的阿顶,虽然他最初的梦想是周游世界,在每个地方学一首民歌唱给所有人听,但当他觉得人生失意,幻想出阿丁作为“更好的自己”时,他还是选择让阿丁去过另一种当官发财、怀抱美人的幸福生活。阿顶在给阿丁命名的同时,已经顺从于自己“被命名”的人生,而唯一聊以慰藉的,不过是在被命名的等级秩序中创造出一个如阿页般更加低劣的自己。
按照后学的思路来看,所有人都生活在意识形态的话语网络中,但即使是在福柯的话语理论中,也有可能生成有自觉意识的主体。关键在于,由谁来掌握命名的权力,我们是不是有能力为自己的生活命名。当彭敏选择以阿丁为内聚焦叙述的叙事视点时,我愿意把阿丁的痛苦与挣扎看作是对“命名”的一次短暂觉醒。这十分类似于《黑客帝国》中尼奥发现“矩阵”的寓言,我是谁,我们据以为真的现实感从何而来?阿丁不只是在字面意义上认识到自己作为分身被命名的事实,这个在十五年来的好日子中都麻木无感的人,第一次在自己与阿顶的对比中,意识到究竟是什么在主宰着他们共同栖居的现实。当阿丁的虚拟人生被片片拆除步步崩塌时,所谓“一连串正确的选择媾和出几近完美的人生”中那些被称为“正确”的要素终于暴露无遗,富二代,良好教育,作为装点的精神生活,在资本链条的优胜劣汰与弱肉强食中游刃有余——当这些装备被一件件剥夺时,阿丁才第一次无比清晰地体会到它们如硬通货一般支配现实的权力。小说中一个场景把这种现实感的自觉表现得淋漓尽致:阿丁开着他的保时捷卡宴满大街乱转,“涉事的大众、夏利、雪铁龙吓的面如土色,我若无其事地丢下他们,扬长而去”。可以想象,面对现实生活中阿丁们的“若无其事”,阿顶们一定也曾咬牙切齿心怀嫉恨,但讽刺的是,阿顶们最终还是笃信——“这就是现实”。阿顶就是在这样的“现实感”中创造阿丁的,阿丁的存在只不过再次坐实了“正确”与“完美”的权威命名,而悲剧正在于此,一旦承认了“命名”的合法性,阿顶们就注定被“命名”所维系的等级秩序甩到一旁。阿丁对阿顶的第一次体贴与同情,因而更像是代上帝之手行使的最后审判:“他是这伟大时代最卑微的注脚,找不到收留的段落。并且终将像石头缝里的野草愤怒却悄无声息地老去,一事无成,两鬓苍苍。”
阿丁给予的也只能是同情罢了,有那么一刻,阿丁几乎要以“反抗者”的形象出现,拒绝被设定被摆布的生活,但他最终还是狡黠地选择了屈从,自愿交出阿丁的名字,甘心成为阿页。正如小说里那句,“满满的负能量,但令人心安”。阿页的出现仿佛一个暗示,人要活得有“现实感”,既然不能改造世界,不如先改变自己。于是,各安其份的他们,只不过再一次巩固了已被命名的人生“现实”:成功者历来精于计算,贫贱者最是没有自尊,而苟活着的平庸之辈们也就不必再徒劳挣扎了。
如此看来,小说里每一个人物都缺乏行动能力。无论是阿顶的杀心、阿页关于窘迫生活的喋喋不休,还是阿丁最终不甘坐以待毙的起意,他们都只不过是暂时借助分身,去释放自己越矩的情绪。没有“分身”又何妨,就像小说摘录的诗句那样,每个人都附耳于墙,伺机听到黑暗另一侧的声音,但又迅速将耳朵收回,无论隔壁是否真那么巧合地也有人附耳于墙,我们已经在比邻而居的认识里很好地约束自己。把一切行动意义都取消的,就是那如同“命名”一般的黑暗房间,而我们已经用另一个词“命运”,去坐实黑暗房间里的假因果与真偶然。如果不能重新发明一个词,去形容黑暗以外的可能的生活,所有的悲喜剧就只能在无边的黑暗中继续自导自演。
《关于黑暗房间里的假因果真偶然》出自西川的散文诗《鹰的话语》,小说题记引用的只是其中一小节。西川的“黑暗房间”是取消、置换和生产意义的场所,是弄假成真和将错就错。彭敏曾经说自己写故事常常是从一个场景、一个句子、甚至一个词演绎而来,或许他并非有意为之,但西川的诗和这篇小说确实构成了同题互文的奇妙关联。西川写道:“一位英俊小生杀死另外两位英俊小生只为他们三人长相一致”,“在黑暗的房间,我装神弄鬼,真有一个傻瓜进门跪倒在我的面前。我一脚踹开他,继续我的享乐,另一个傻瓜就破门而入,带着菜刀革我的命”。这样看来,小说仿佛只是在注诗,但反过来看,诗歌的意义凝练是否也掩护了小说,在那些铺排而出的故事中隐匿了更加具体的私人感觉?
与彭敏之前的小说创作相比,放下“南方小镇”“李梅英”等更易搭建故事的元素,这篇小说仿佛只是为了证明虚构能力的一次文体实验,但它其实包含着更为直接的自我表达。这篇小说起源于一场刻骨铭心而又七荤八素的恋情,“但在我没有触及问题的时候我便选择了逃避和偏离”。“黑暗房间”的诗意成全了“逃避”,以高度抽象的方式直接洞穿个人经验,指向更具普遍内涵的现实感,但或许也是这如“精致的瓮”般稳定自足的形式,造成了“偏离”,无法再向前一步,凿开我们习以为常的存在寓言。彭敏的诗《Delete》同样也复述了小说中那种失败的实感,“也许是/传说中的回光返照,他的眼里有时燃起纤细的火苗/他需要足够的想象力,才能在倾倒的垃圾筒旁边/在更冷的秋风中,站成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而不是/一只苍蝇”。但不再复述诗歌的小说应该要做的,或许就是用足够的想象力燃起纤细的火苗,让另一种现实感有迹可循。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