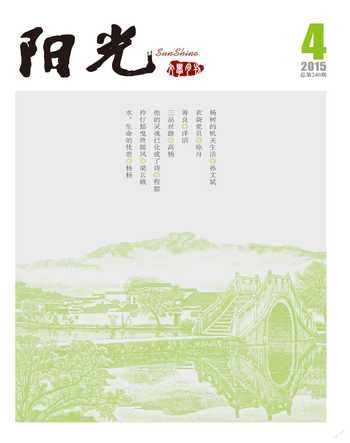现代诗困境探析
2015-05-30骆冰
骆冰
还是从现代诗不被国人认可说起。
我曾用两篇文章探讨过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那些优秀诗歌的晦涩难懂阻碍了读者们对它的认同。但后来随着进一步阅读,我发现晦涩难懂不过是这些诗歌的特点之一。它让人无法认同的方面还有很多。比如它不是唯美的,比如它繁琐深奥,还有它具象的表达方式等。而把这些特点一综合,正好就是西方译诗的特点。这让我突然醒悟,国人不认可这些诗,是因为这些诗太西化了。
后来跟一些诗人交流,发现认可“现代诗已被西化”人竟有很多,其中不乏一些有名的诗人。不同的是,这些名诗人认为现代诗的西化是正确的,比如著名诗人杨小滨先生说:“现代汉语本身就是西化的汉语,我们的社会经验本身很大程度就是上西化的,汉语当代诗只能是对这个不纯粹的汉语社会文化的回应,而不可能回到所谓的‘纯粹了……”(参见北京文艺网论坛)。
他的话让我想起之前看过的一本当代诗人访谈录。
这本访谈几乎包括了中国当代所有的顶尖级诗人。我注意到,他们在谈到自己的写作经历和创作标高时,所指向的诗和诗人大部分都是来自西方。他们认为诗歌没有民族性,并以“没有绝对不能被他者把握的精神空间”作为这种观点的强大理论支撑。而且,他们认为现代诗和传统诗词已经完全断裂,而西方译诗则是汉诗的一部分。他们还认为现代汉语已不是纯粹的汉语,甚至说它是一种“有意识自觉发明的语言”。
这样一综合,让我明白了中国诗歌被西化的原因。
这是因为诗人们根本就没认为现代诗是纯粹的中国诗歌,写作中也更多是以西方译诗为精神标杆的,“中国”充其量只是这些作品中的元素之一。像古语“楚王好细腰,宫中多瘦死”说的那样,由于这种理论首先被这些“大诗人”认可,众多“小诗人”为得到“大诗人”的认可,也就趋之若鹜地写这种诗了。这种现象被女诗人钟硕称为“政治正确”,实在是准确传神。就是这个原因,使西化现代诗在中国诗坛大行其道。
接下来,就回到了最初的问题:这种西化的现代诗在诗歌界认同度已是如此之高,为什么却得不到国人甚至是文学界的认可呢?诗歌的西化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
诗人们也经常会就这个问题发生争执。而且他们也各自都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言辞激烈的时候甚至会质疑和贬低对方。但是我想,一味地质疑贬低是没意义的,只有追溯一下东西方文化的本源,才能就这个问题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答案。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表面看去很庞杂,但归结起来就两种,一种是“世间法”,一种是“出世间法”。
所谓的“世间法”就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俗世文化,即指导世俗生活的经纶济世吃喝拉撒等,它囊括了世间的万物万象,并对万物万象做了理性的定位,如《礼记》。这种文化的特点,是无论它曾取得过怎样非凡的成就,都得不到普遍认可,这在中国历史中儒家文化和孔子的地位总是浮沉不定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现象说明,“世间法”不是中国文化的最高精神指向。
所谓的“出世间法”就是以老庄佛道为代表的世外文化。这种文化非常抽象,它不拘泥于世间的物象本身,而是从一个“点”出发,呈发散状外延至世间的万物万象,同时又不对具体事物做精确阐释,有很大的想象空间。这种文化的特点可用晋人皇甫谧著的《高士传》来说明。这本书称那些拒绝世俗超然物外的人为“高士”。而这些“高士”所代表的世外文化,正是中国历史长河中一以贯之的最高精神指向。即使是到了今天,如果有谁看淡了功名利禄超脱于世俗,依然会被称做“高人”。
从这里就不难看出,中国文化的最高精神指向是“出世间法”。
然后再来看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它无法用世间出世间来表述。众所周知,即使是作为“出世间法”的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逻辑理性(托马斯阿奎那就是用逻辑来证明上帝的存在)的“世间法”(指导具体的世俗生活)。综观西方文化两千多年的脉络,基本可以概括为“理性”和“非理性”。
所谓的“理性”,即西方的哲学和科学。
这种文化的特点和中国的“出世间法”相反,它是通过对世间万物万象的精准描述,然后把它们归类总结成一个“点”,基本不留想象余地。它是说理的,繁琐的,是为了聚合成那个“点”而对世间万物无所不包的。西方哲学的逻辑严密和科学的理性严谨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且,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代表这种文化的人才会被称为“高士”,一如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哲人和科学家,他们的名字贯穿了整个西方文化史。
所谓的“非理性”,是源自于古希腊的“酒神精神”。
“酒神精神”和中国的“出世间法”类似,特点是狂放不羁藐视理性,以世间万物的本源精神来对抗理性行为准则。不同的是,在西方文化中,代表“酒神精神”的人不能称为“高士”。因为自柏拉图起,他们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了(可参看柏拉图哲学)。这种情况贯穿了整个中世纪,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到尼采近600年的浮沉之后,代表“酒神精神”的非理性,才有了和理性抗衡的能力。即便如此,“理性”依然在西方社会占据着统治地位,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西方文化的最高精神指向是理性。
具体到诗歌,因为诗歌是一种语言或文化的最高精神总结,所以它的表达一定是符合这种语言或文化最高精神指向,并且,也只有符合这种最高精神指向的诗歌,才可能被这种语言或文化所接受。
也就是说,汉诗应该符合“出世间法”这一最高精神指向,西方诗歌应该符合“理性”这一最高精神指向,才会被各自的文化所接受。事实上也正是这样的。
从以上对西方文化的分析不难看出,就西方诗歌来说,它的写作应该以“酒神精神”为指导才对。但事实上,由于作为最高精神指向的理性才是西方文化的血脉,在实际写作中,西方诗歌也理所当然地表现出明显的理性特征。它是通过对世间万事万物的具象描述来表现“酒神精神”的,带有总结性痕迹,总体来说想象空间不大,而且西方诗歌也秉承了理性一以贯之的文化特点:语言繁琐,表述晦涩,注重深度而不注重美感。
晦涩和深度是西方诗歌久远的传统,早在公元前5世纪,巴门尼德就曾用诗的形式来表述哲学(《论自然》),现在我们国内流传的很多翻译名作,这个特点也很明显。而其他特点,则被惠特曼展现得一览无余。他的诗包罗万象粗野狂放天马行空,甚至曾被判决为“淫秽”,但仍然是西方诗歌的经典。
综上所述,这些西方诗歌特点是:
一、具象。
二、 繁琐。
三、注重深度,而不注重美感。
四、晦涩。
而中国诗歌就不同了。
自先秦以来,无论是诗歌精神还是表述特征,中国诗歌都是符合中国文化最高精神指向“出世间法”的。这种特色,让中国诗歌同时也秉承了“出世间法”一以贯之的文化特点:语言凝练,有巨大的想象空间,少有繁琐的世间具象描写,抽象,境界,美感。
这些特点,在那些传世名篇名句中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连屈原、辛弃疾、陆游这些作者,在表达自己属于“世间法”的经纶济世抱负时,所使用的表达方式依然没脱离“出世间”这个方向。还有《诗经》中被认为“淫诗” 的那首《野有死麕》,它的表现形式和世俗也有明显的距离。
从这些可以看出,中国传统诗歌的特点是:
一、 凝炼。
二、 优美。
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诗歌要有超凡脱俗的境界和精神。最起码,它不能看上去让人觉得“丑”。亦即不能世俗、低俗、淫秽和污秽。
四、通俗易懂。(可参看孙忠伟先生的《中国诗的语文风格》)。
从以上对比不难看出,中国诗歌和西方诗歌有非常大的差别。
虽然差别很大,你却不能用自己的标准衡量,就说另一种不好。因为这些诗歌都符合它母语文化的最高精神指向,在它的母语文化语境中,它们都是毫无疑问的诗歌经典。
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绝对不能被他者把握的精神空间”这句话非常正确。由于今天世界的文化交流,每个民族都能“把握”,至少是触摸到其他民族的“精神空间”。但如果把“他民族”的“精神空间”,直接移植到“本民族”来,那就有问题了。
举例说,如果把我们历史上流传的那些经典诗歌翻译到西方去,西方人还会认为它们是经典吗?他们知道这是中国的经典,却未必就会认同这种经典。因为这些诗歌的最高精神指向是中国式的。而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这种中国式的最高精神指向——“出世间法”,和西方的最高精神指向——理性,几乎是对立的。这些生生世世都被理性文化浸润的西方人,怎么可能完全认同这种诗歌呢?同理,中国人对西方的诗歌经典,也会持这种看法。
如果更进一步,以这种经典译诗为标准,来进行苦心孤诣的母语写作的话,那就会显得荒谬了。因为这种做法在中国来说,无疑是等于把自己的最高精神境界从“形而上”堕落到了等而下之的“形而下”,而在西方来说,则是把代表自己最高境界的“深邃深刻的哲思”堕落到了“浅薄缥缈虚无”的未知境界。这种做法显然会因背离各自文化的最高精神指向而不被认可。
我想,这才是被西化了的现代诗,虽然能站上诗坛的最高讲台,却不能被国人甚至是文学界认可的最根本原因。
但上面的讨论中有个问题,那就是建国前后和80年代初的诗歌,也有西方诗歌影响的痕迹,但那些诗歌为什么就能产生被国人认可的传世名篇名句呢?
这就可以讨论一下新诗和古诗的断裂问题。
众所周知,他者文化对本体文化的侵蚀,都是有一定过程的。而建国前后徐志摩、郑愁予那代诗人所处的时代,正好就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早期。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那个时代和古诗时代相距很近,和那代诗人所受的熏陶都是来自传统诗词的原因,就使那时的中国诗歌能很好地消解西化力量的冲击,从而保持其固有的中国文化最高精神指向。所以,那时的新诗,从表面看和旧诗是断裂了,在本质上,它的写作仍然是以中国文化最高精神指向为基础的。这就像那代诗人们虽然穿上了西装,骨子里却仍然是个传统的中国人一样,他们的诗歌作品,也必然是代表中国文化最高精神指向的传统审美范式。
1980年代初的新诗也是这个道理。那代诗人大部分生于新中国,长于“十年”文化断裂时期,在这种大环境中,连找本西方书都难,又何谈西化思维。他们所受的熏陶是古诗和上一代以中国最高精神指向为标准的新诗作品。所以,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新诗和建国前后的新诗是一脉相承的。
这两代人的诗歌会被国人认可,并有经典的名篇名句产生,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希特勒说“要毁灭一个民族,先毁灭其文化”,这话一点儿不错。到1980年代中期之后,西方文化在中国呈爆炸式发展,让中国知识分子和诗人受到了暴风骤雨般的精神洗礼,加上近两百年弱势文化的自卑心理,这几十年来,中国的方方面面都以西方为标准,方方面面都以向西方靠近为荣,这就使中国文化的最高精神指向虽然没被毁灭,却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代表这种精神指向的审美标准也开始向西方倾斜。再加上这本访谈录上说的中国诗人有“走向世界”的情结,我们这个时代会出现大批的西化诗歌,出现大批以西方诗歌为标准的诗人,并认为汉语“不纯粹”,是“有意识自觉发明的语言”,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一个民族的最高精神指向是流淌于这个民族的血液,是存于一个族群的永恒印记,它可能会因时代不同而有所波动,却绝对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消亡。这在西方的非理性文化,虽然曾在二战时期到达顶点,让整个世界陷入灾难,但代表其最高精神指向的理性文化依旧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就是最好的证明。
同样的道理,目前的中国,虽然呈现出了各种价值观扭曲和浮躁混乱的社会表象,但本质上,代表中国文化精神最高指向的哲学、审美,也一样会永远延续下去!
我们的现代诗也是如此,虽然它遇到了暂时的困难,但我相信,只要回归了中国文化本位的最高精神指向,就一定会走出困境,像古诗那样永放光芒!
所以,在此我也呼吁诗歌界的有识之士,请让现代诗回归汉语传统!
骆 冰:本名罗晓勇,山东莱芜人。 作品散见于《山东文学》《时代文学》《散文诗》《厦门文学》《当代小说》等。入选《安徽文学·年度最佳爱情诗选》《中国当代诗人诗歌精品专辑》《齐鲁文学作品年展(2012、2013卷)》《山东诗典2013卷》。曾获河北省第二届散文大赛奖。中国首届徐志摩微诗歌大赛入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