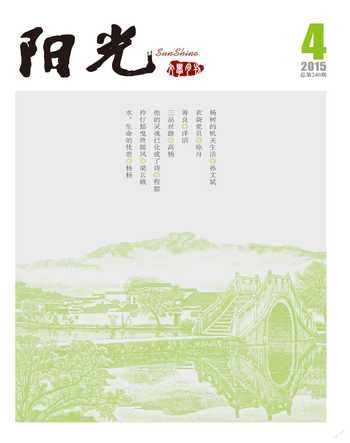三品丝路
2015-05-30高杨
高杨
主恩赐的馕
上大学的时候,有个闺蜜,她祖籍是内地却生长在新疆,常常操一口重口味的新疆普通话给我们这些没见过草原和牛羊奔跑的内地同学讲述“我们新疆好地方”。每当晚上宿舍熄灯,“卧谈会”开始的时候,总是听她一个人讲述新疆的美食。我从那个时候才知道有一种叫“馕”的饼。
有多香?是用奶和油和的面;有多脆?是在火坑烤熟;有多营养?一两岁的小孩子刚长牙就吃馕,不知道长得多结实;有多少种?连新疆人自己都数不清,肉馕、油馕、窝窝馕、芝麻馕、片儿馕、希尔曼馕……唉呀,啧啧啧,仿佛世界上最好吃的、最美味的,就是这馕了。宝鸡的同学不答应了,不就是个烤饼吗?还比我们的擀面皮好吃?“唉,你懂个啥?让你每天吃擀面皮,别的都不能吃,你行吗?要是天天光给我吃馕,我就能行!”这位新疆汉人忍不住吞咽着口水,在黑暗中,也能看到她的双眼放着绿光。
吃到馕是多年以后了,我有幸应湖南剧作家吴贤雕先生之邀,参加他的作品《到吐鲁番避暑》的研讨会,终于来到了闺蜜所说的好地方——新疆。那五颜六色的地方,具有多大的魅力呢?走进了她无法不被她征服。第一天午餐,吐鲁番宣传部美丽的女部长就招待大家吃到了馕,评价不一而足,有人说好吃,有人说香,也有南方来的作家们觉得太干,没有肉又没有蔬菜,完全是咀嚼面粉,无法下咽。我却因为这馕里沉淀着一份旧时回忆,觉得特别香甜。
会后,几位作家三五成伴儿,在吐鲁番的大街上散步,迎面吹来一阵凉风,无比惬意。宣传部女部长带着我们走到吐鲁番的城中湖旁散步。沿路有一个烤馕的摊子,一位维族中年妇女正在和面,宣传部长走上前用熟稔的维语与这位大嫂攀谈,我们几位呼啦一下围住了烤馕的摊子,拍照的拍照,合影的合影。这位大嫂似面露不悦,但听部长说了几句话便笑了起来。点着头用生硬的汉语说:欢迎欢迎。
大嫂自顾做起了活计,她一边把温热的牛奶缓缓倒入和了一半儿的面团里,一边用手蘸了澄亮的菜油,用力的揉搓拍打面团,她那双粗大的双手撑着上半个身子,所有的力气都压在团面上。汗水已经将头巾浸湿,两鬓的头发也贴在面颊上,当面粉牛奶和油都完全凝固成一团的时候,她直起腰活动了一下肩膀,将这团揉好的面放进一个盆里。从另一个盆里拿出一团光滑油亮的面团。揪成几个大的面剂子,用拳头把面剂子压成一张又一张四周厚中间薄的面饼,又拿出一个我从没见过的漂亮家什,这家什是用木头做得手柄,手柄上雕刻着波斯风格的花纹,可能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很古旧的样子,显现出说不清楚的美。在这个家什的另一头,镶满了不足一寸的钢针,有规律地排列成几行,宣传部长告诉大家,这就是新疆人每家必备的“馕扎”。大嫂握住漂亮的手柄用钢针在面饼上扎了一片片的花纹,极像盛开的牡丹。然后,打开桌面上一个小盖子,呼啦一下,热气带着火星子从盖子盖着的圆洞里冒了出来,女作家们惊呼起来,原来这是个火坑,我们面前这个石桌子,并不是一张普通的桌子,而是一个平地盘起的小火坑。探着头往里看,红彤彤的炭火烧得正旺,大嫂用两只手托起一张薄薄的面饼往热烫的坑壁上一贴,滋啦啦,面饼瞬间就变了颜色。等她一张张贴满了坑壁,已是香气四溢。奶香、油香,更有一种烤制面粉的香味,令人垂涎欲滴。馕熟了,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大嫂把馕一张一张从坑里取出。真是个技术活儿,那火星子乱飞的火坑里,徒手取馕,可不是一两天的功夫。女部长连忙大声叮嘱大家,千万不能数啊,那是对馕的不尊重。掰一块热烫的馕放在嘴里,酥脆可口,唇齿留香,那牛奶和芝麻的香味儿,由远及近越来越清晰地映在脑海里,再仔细的咂摸一下,还有淡淡的小茴香的咸鲜,那质朴踏实的口感令人品味到农耕文明的一缕芬芳。
维吾尔人对馕有一份特别的崇拜。在他们的教育理念里,是不允许这样长时间的注视着馕的,因为他们认为人类的目光里有一种邪恶,这是对食物、对他们赖以生存的馕极大的不尊敬。在维吾尔族群里,极小的孩子都知道,馕不可以扔不可以撒,掉在地上的馕渣要捡起来放在高处让鸟去啄食。维吾尔人说:“馕就是生命,馕就是信仰。”有了生命和信仰,才是信奉安拉的保证。这说明了维吾尔人对食物的崇拜,也说明了感性热情的维族人其实也都是唯物主义者呢。
比起馕,我更接受它的另一种称呼:胡饼。这个叫法应该是更适合汉族人的语言习惯。胡人所做之饼,说明馕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吃食,它是由中西亚传入中国的。到现在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埃及、巴基斯坦、印度等国依然保留着吃馕的习惯。营盘遗址出土的东汉魏晋时期的文物中有完整的薄面饼,是我国关于馕最早的记载。就“馕”这个字来看,它应是一种古波斯国的食物。丝绸之路的通达,使得这种耐放又抗饿的薄饼特别受到出使者们的欢迎。据说,当初玄奘就是靠着馕才走完了西行最艰难的路程。于是,它被装在出使者的背囊里,翻越葱岭来到新疆;又一路向西,由骆驼驮着去往了阿拉伯国家。这种其貌不扬的吃食,实在是游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商贾们生命和信念的保障。
没成想,它在新疆的生命力极为顽强,不仅落地生根而且花样翻新,变身为大如车轮、小似杯口、酸甜咸辣、包肉、撒芝麻、刷糖浆、加皮牙子(洋葱)等将近五十个品种的美食。与馕一起流入我国境内的有巴旦杏、石榴、无花果,还有美轮美奂的波斯地毯。当然中原文化也以不可抵挡之势流入中亚西亚、非洲及欧洲,近两千年来,浸润着西域诸国。
这么一说扯得远了。我想起母亲在世的时候,每年春天第一茬韭菜上市,她总是要买些回来,将细粉丝氽烫至半熟,再把土鸡蛋炒成嫩黄。春韭最是鲜嫩,不能马虎,母亲将翠绿的韭菜细细地切成末,再把这几样拌上姜丝、盐,淋上花椒油。和好的软面擀成极薄的面皮,中间铺上一层调制好的韭菜鸡蛋馅,再用另一张薄面皮包住,四周摁紧,平底锅烧油,油热八成时,两张韭饼一锅,煎至两面焦黄便可出锅了。其饼,面皮薄脆,韭菜鸡蛋鲜香,粉丝柔瓤,一口咬下去酥香可口,真是人间至味啊!
从新疆来西安上大学的姑娘,想家想得发狂,半夜躲在被子里哭,早上洗了枕巾却无法遮住一双红肿的眼睛。我带她回我家,美美睡了一觉,又洗个热水澡。中午,母亲端上新出锅的韭饼和用慢火熬成的小米粥。这姑娘吃得连话都顾不上说了,我看她快吃第七个的时候直问她:“喂,你姓啥?”她瞥了我一眼,傲慢地说:“你们西安人的馕咋还放韭菜呢?我们新疆的馕只放肉!” 一晃都过去快二十年了。
想起第一次去新疆也是五六年前的事了。同行的作家,《高山下的花环》的作者李存葆先生是一位身材高大个性耿直的山东汉子。当他听说这种叫馕的大饼因为几乎没有水分,存放一年也不会变质时,立刻买了两大纸箱,从吐鲁番空运回济南。不由得觉得好笑,两纸箱面饼坐上飞机忽忽悠悠来到济南,一落地就发现,不对,这里的空气里充满了海洋和泉水的味道,水土不服,找谁说理去?
且不说面饼坐了飞机,身价直线上升,只恐到了济南的馕,要将“决不变质”的清誉毁于一旦了。不过,读过《高山下的花环》的我,完全理解李先生对面粉、对食物的情感,因为他知道什么叫饥饿。
东奔西突
藏红花米饭
众所周知,手抓饭是新疆的美食。早年听我奶奶说,她跟我爷爷在一个山西富商家里吃过手抓饭,羊肉与葡萄干同烹,又腻又甜,并且要用手抓着吃。大家闺秀的奶奶当然是没办法吃,也没办法想象如何下手,只能看着身旁的富商太太吃得津津有味,并且,惊讶地发现人家非常节约地只用了三个手指头,就准确快速地吃完了一大盘饭。这位富商和他的太太长年跑新疆和内地做生意,谙熟于烹煮新疆的饮食。常常用新疆菜宴请宾朋,朋友们一般都用得极少。他们两口子倒并不介怀,只管自己吃个痛快。
多年以后,奶奶再讲起这段往事,也只是对这种用肉和干果同煮的饭表示不可思议。又甜又咸,还要用手,“也不嫌烫,也不嫌脏。”
没过几年,我的小女朋友初中同学霞请我去她们家吃饭。霞的父母均是从新疆建设兵团调回西安的。霞妈妈请我这个小朋友吃新疆人待客最好的饭菜,手把羊肉、手抓饭、凉拌木耳皮牙子。为了尊重个人习惯,霞妈妈给我准备了一套碗筷。我却十分挑战地看着她说:“吃手抓饭不是不需要筷子吗?”仿佛是对霞妈妈厨艺的质疑,又似乎显示出自己是见过世面的食客。于是,霞妈妈帮我们把饭盛进了盘子,眼看着我把饭吃了一头一身。
到新疆,吃上了原汁原味的手抓饭。第一口的感觉,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晰。米饭每一粒都非常Q弹,肉香菜嫩,干果虽有些甜腻,但也无大碍,再佐一杯地道的新疆红葡萄酒,实在是过瘾,维族人还爱就着生蒜,别有一番风味儿。极饿的时候,来上一大盘这样的饭,十分的顶饿。
同年,又为了当时所在单位组织的全球华人写作大赛三下扬州。繁忙工作之余,主办方对我们西安的来宾十分优待,顿顿扬州炒饭、各色河鲜管饱。我吃着扬州炒饭,心里生疑,这同样是饭里有肉有菜,有玉米有松仁,扬州的炒饭和新疆的抓饭,有没有血缘关系呢?
这恐怕还要往公元前捯一下。早在公元前六百年,有一种神秘的文化诞生在亚洲的西南部,古希腊人把这种文化诞生地称为“波斯”,也被称为“波斯第一帝国”。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公元一九三五年,波斯当时的国王礼萨·汗正式将波斯更名为伊朗。波斯古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为一千三百多年。
波斯帝国成立一百年后,也就是公元前五○○年,来波斯旅游的希腊旅行家希罗多德在他的游记中记录了当时波斯人奢侈的饮食习惯: “波斯人会将一头牛、一匹马、一只骆驼以及一头驴整个烤熟来招待客人……他们只吃很少的固体食物,但会吃大量甜点,有时在桌上同时摆着好几盘,他们非常喜欢葡萄酒并且总是喝很多。”“而古希腊人总是很节制的用餐,还没有完全吃饱便停了下来。”
在希罗多德的脚步踏上波斯的同一时期,有一朵神奇的粉色小花儿从波斯的土壤里慢慢生长出来,摇曳生姿,散发着神秘的香气。几百年后,这朵小花儿随着蒙古远征军的脚步从波斯流传到欧洲、中国和印度。僧侣们很快就发现,这朵小花鲜艳夺目,用它煮水来浸染僧袍实在是太漂亮了。接着,人们发现这种无毒有益的小花儿如果只用来染色就太可惜了,它还有很强大的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比如,可以治牙痛和胃痛,并且,它们还可以使食物有非常诱人的颜色。所以,当波斯人从印度人那里学会了做米饭以后,这朵被称为“番红花”的小花儿便登堂入室,成了贵族餐桌上的常客。
用途广泛的小花儿传到中国时路经西藏,又被中国人称为“藏红花”或者“番红花”。藏红花是聪明的植物,无论它被移栽到希腊、欧洲南部还是阿拉伯、西班牙、印度。它还是选择了在波斯本地开出品质最好的花朵。那里长年干旱,大片的沙质土地,是它最好的温床。
古代的波斯,现代的伊朗,有一种传统美食——藏红花米饭。当然,更准确一些,应叫作“番红花米饭”。据说伊朗人对这种饭的态度非常虔诚,他们坚持使用来自印度的大米做基本食材。先将大米在盐水中泡一天,第二天沥干后再放入热水中煮沸捞出,拌上特有的波斯调料——碾碎的藏红花和其它香料、黄油,再隔水蒸。出炉的米饭颗粒分明、晶莹剔透,又有黄白两种颜色搭配,赏心悦目。香喷喷的米饭配上炖肉或烤肉加上烤番茄和酸黄瓜,挖满满一勺这样的饭放进嘴里,立刻听到口腔里噼啪作响,那是味蕾欢呼的声音。
如果食欲大动,又不能前往伊朗,其实还有一种解馋的办法。用泰国香米替换印度大米,一样能做得晶莹剔透。大米放入电饭煲中煲熟,诀窍是生米里加两茶匙油,浸泡一小时。将煲熟的米饭取出一部分放在玻璃碗里,缓缓倒入泡好的藏红花水拌匀,两种不同颜色的米饭就做好了,简单方便又清香袭人。此时,再将用橄榄油炒好的胡萝卜、洋葱、芹菜铺在双色米饭上。真是一顿丰盛的西域大餐。如果凑趣,打开一瓶较好的葡萄酒,来一盘烤肉。就会有一种迷人的香气游荡在你的餐厅里,或许你该放上一张乌得琴的CD,古老的波斯音乐混杂着这种迷人的香气,能让你感受一下波斯妖娆迷醉的文化。
自从在新疆吃过类似于这种滋味的米饭,我就在西安的大街小巷遍寻吃手抓饭的去处。功夫不负吃货的心,在安东街的一个小角落里有一间新疆风味的餐厅。新疆手抓饭所用的食材要比藏红花米饭丰富多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种多色彩米饭流传到我国后,被我国的劳动人民因地制宜变了个身。除了选用大米和植物油外,还用黄油。除了用牛羊肉之外,还用鸡、鸭、鹅等家禽的肉;有的抓饭不放肉,就会选用葡萄干、杏干、桃皮等干果来做,称之甜抓饭或素抓饭;到了夏天,维吾尔族人吃的抓饭花样还更多一些。南疆的维吾尔族人喜欢在抓饭里放一种“毕也”(木瓜),有的还放鸡蛋和菜。最有趣的是在做好的抓饭上放一些酸奶,既是上等的充饥之物,又是消暑解热的食品。
隋朝的时候,有人把米饭蒸熟后,再用鸡蛋炒了吃,不小心传入扬州,如今成了一道名满天下的淮阳菜——扬州炒饭。后来的扬州人把这道主食做了多种革新。纯用蛋炒是“清蛋炒饭”,将打散的鸡蛋拌在米饭里再下锅炒叫“金裹银蛋炒饭”,放上酱油就是;“月牙蛋炒饭”,放些虾仁便成了“海鲜蛋炒饭”,放火腿、蔬菜就是“火腿蛋炒饭”、“什锦蛋炒饭”了。潮汕炒饭、广东炒饭、福建炒饭,也都是与这碗米饭结缘。
而当我这个十成十的吃货坐在新疆风味餐厅里,除了心满意足的咀嚼着美味的米饭,也不得不回想,早在西汉时期那位叫张骞的陕西城固男子,胆略过人、心怀天下,因为他在公元前一三八年及公元前一一九年两次从长安出使西域,才使古老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连接起来,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这碗米饭,正是经历了文化传递交流,东奔西突,走南闯北地来到我的面前。
感情深,吃烤肉
西安的鼓楼与钟楼遥遥相对,交相辉映。钟楼横亘东南西北四条大街最中,一副君临万国的架式。鼓楼,立君王之侧,身姿更像庄重沉稳的辅弼大臣。穿过鼓楼深深的门洞,便走入另一个世界——回民坊。坊者,村也,这个坐落在西安市中心的村子,堪称城中一景,亦是西安人人尽知的美食一条街。特别是对这条街上的烤肉摊,都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我家在钟鼓楼下的西一路上。常常要经过案板街,街口上有两个烤肉摊,从那个地方经过,是对意志的考验。孜然和辣椒粉和着羊肉的香味阵阵飘过,我只想站住多闻一会儿。一毛钱一串烤肉,对于一个一星期只有两毛零用钱的小学生来说,实在是天价。在八十年代中期,西安简陋的夜市上,总有不多的几个人围住烤肉的炉子,他们站着要几串烤肉打打牙祭,不一会儿就将仅有的几串肉吃光了,嘴一抹继续赶路。
九十年代,人们依然热爱烤肉,社会路上有几家回族馆子,有好吃的拉面和牛骨汤馄饨,当然少不了烤肉。鲜嫩的牛肉和大串羊肉,肥瘦相间,还有鲜嫩的牛腰子和肉筋。拌好的凉菜用不锈钢盘装了几大盘,无非黄瓜、花生米、炝拌莲菜、芹菜豆腐干,冰箱里有冰冻的啤酒。烤肉仍是一毛钱一串,烤腰子和烤筋八分钱,羊肉要两毛钱才能吃得上一串。来吃夜宵的食客们闷头就坐,语焉不详地点菜:来把肥瘦(有肥有瘦的肉串,还有纯瘦)、一把烤筋,啤酒冰的,拼两个凉菜。老板仿佛心有灵犀,无须多问。不一会儿,香烟滚滚中就端来烤得焦香的肉,爽口的凉拌菜,和冰冻的汉斯啤酒。那啤酒瓶身上一层薄雾,让人看着就冰爽透心。我现在还记得那时候的烤肉,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香。横拿烤肉钎子,与嘴平行,伸出牙齿,咬住一块还滋滋冒油的肉,头一甩把它从钎子上扯下来,嚼进嘴里。羊肉被烤得焦香,还有孜然和辣椒味儿,顺着鼻子直往脑子里钻。当你咯吱咯吱地咀嚼那块被炭火烤得脆嫩可口的羊肉时,美味就在你的口腔里开始舞蹈了。
一九九七年至二○○二年,西安市政府专项投资,整修了回民坊,这座在西安盘距了千年的穆斯林村落,成为西安第一个正规大型的民族夜市区,食客们终于找到了根据地。从此呼朋引伴,三五成群,聚餐就有了一个令人兴奋的目的地。上至六七十岁的阿伯大妈,下至十几岁的少男少女,谁都有熟识的几家老字号。大家不分长幼,不分高下,围炉而坐,畅饮啤酒、酸梅汤,热火朝天地吃着最正宗的烤肉。上了年纪的老西安人,还要讨一杯“胡茶”。这胡茶,现在很难考证是胡茶、糊茶,还是茯茶。总之那茶香味与烤肉实在是相得益彰,不可缺一。初入口苦,喝下嗓子眼,就有股子令人熨帖的香味和回甘。茶不要钱,放开了喝,只不过,此时的烤肉已经涨价至五毛钱一串啦。
有人说我有考证癖。我反正也不信这个邪,活活儿想当个“人肉百度”。对西安人的最爱——烤肉,我亦不能放过。
听说早在汉唐时期,长安城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就接待了来自西亚、中亚各国使节以及自由来往的商人、传教士、留学生。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六五一年),阿拉伯哈里发派遣使节来长安朝贡,与唐通好,此年被史学家认为是中国与阿拉伯正式缔结交往之始,也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起始年。
在此后的近一百五十年里,阿拉伯使节被派遣于唐都者达三十七次之多,人数已超四千。时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的李三有这样描述:“胡客留长安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当时唐朝欲将这四千胡客遣返回国,遭到了强烈反对,无一人愿归。唐皇网开一面,安排他们做了京城禁卫军的亲兵,留居长安。从此,穆斯林文化如同一颗种子,在盛唐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长安,生根发芽。
特别是在餐桌上,西安的汉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想念回民坊那一口香味浓烈的美食。穿成串的烤肉,更像是将西安人的心穿成了一串。正襟危坐的吃一顿西安饭庄,那只是普通的朋友,勾肩搭背吃一顿烤肉,才是掏心掏肺的哥们儿。
这会做烤肉的先祖,应该是远在横跨欧亚两洲的土耳其,这块土地在几百年前被称为奥斯曼帝国,生活在那里的突厥族人们,受到阿拉伯人的影响,大多数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将烧烤牛羊肉的饮食习惯又回馈给了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们。聪明的穆斯林将烧烤做得越来越细致,以供君王享用。此后几百年里,土耳其的宫廷清真菜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菜系、法国为代表的欧洲菜系并称为世界三大菜系。
烤肉的做法五花八门,咱们单说依然流行于世的土耳其烤肉。如果有机会去趟伊斯坦布尔,随处便可看到被称为多纳卡八的烤肉摊。土耳其人将牛、羊、鸡的肉,从骨上剔下,再用十多种调料浸泡腌制,待肉被腌得非常入味的时候,插在钢钎子上,旋转着烤熟了它,就是人们常说的旋转式烤肉。已经被腌透的肉,再被旺火一烤,香味四溢,瘦肉香脆,肥肉脆香,佐以沙拉菜、配料,卷入特制的面饼中,就可以大快朵颐了。还可以把羊排骨煮到半熟,然后刷上酱再烤,这种做法也是传统烤肉中的一种。排骨上的肉若肥中有瘦,也是瘦的不柴,肥的不腻,较生烤的肉更软嫩。
鲜辣可口的烤肉翻山越岭来到中国,登堂入室,成了明朝皇上们的心头好,作为宫廷菜流传开去。做法、用料都变得更加细致。清兵入关的时候,来自东北的满族士兵不仅烤牛羊肉,还烤鱼和烤菜,使得烧烤这种美食在中原的民间扩大了意义。十八世纪末,巴西的牛仔们用剑穿肉烤食,并且,他们还烤水果吃,又是一大发明。巴西烤肉流传世界每个角落,走到任何一间巴西馆子,都有戴着高帽深眼高鼻的帅厨师,右手执两根穿满了烤肉的如剑长钎,左手执短匕首,问你要不要来个鸡翅膀或是牛舌头。
土耳其人自豪地将他们的祖国称为“烤肉帝国”,他们认为烤肉这一全天下最美味的食物,就是由他们的祖先发明的。当然,爱申请专利的韩国人听了这话可能不大高兴。但是,不得不承认,烧烤这种料理食物的方式,对世界饮食文化影响十分巨大。
话说回头,在古长安,这烤肉由国外使节、商贾从丝绸之路带来。使长期居住在中国最中心的古城的人们享受了世间最好的美食,养成平起平坐的饮食方式——王子与庶民同食一钎肉,共饮一壶酒。享受的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平等谦和带来的快乐,千百年来,这种快乐深入长安人的心里,让长安人心胸宽广大度,重情重义。
这当然不只是因为长安人吃了烤肉,而是因为世界走入了长安,长安也接纳了广博的世界,长安,是世界的长安。
高 杨:女,现居西安。从事传媒工作十余年,曾为多家媒体撰写专栏。出版两本随笔集,《理想花》《醉香女儿红》。文字多次被《读者》《文苑》《青年文摘》等转载。曾获得第四届“漂母杯”全球华人散文奖,有作品选入中学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