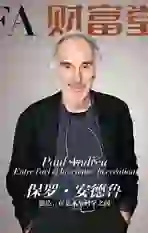挑战音乐的当代困境
2015-05-30归心
归心
2015年6月,由上海音乐学院蓝汉成教授和几位青年教师发起的 ELA 友人室内乐社即将举行他们的“彼时当代·此时现代”系列的第六场音乐会。他们成立于2008年,致力于推广室内乐、中国当代音乐,以及挖掘那些已被历史湮没的优秀室内乐作品。这是一支水准极高职业的室内乐组合。包括蓝汉成教授在内的室内乐社成员,均有长期海外在顶尖院校的留学或执教经历,并均有职业的室内乐经验——这在国内的室内乐组合中并不多见。更难得的是,同一些知名演奏家的临时组合不同,几位音乐家长期合作,演奏默契合一,又富有时代感,如果称他们是中国最好的室内乐,绝不为过。
早在2013年,我便听过他们的演奏,他们对艺术的执著和严谨终究带来了极高的品质。但有些遗憾,听完音乐会,回头一数,台下观众并不多,甚至塞不满本就不大的贺绿汀音乐厅的三分之一。极高的艺术质量,却如此缺乏知音,实为憾事。再想到如今中国古典音乐市场的盛况,此时冷遇与盛况并存情景,颇耐人思量。几年以来,中国的古典音乐市场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发展。由于西方古典音乐的颓势,诸多国外知名音乐团体争先恐后地进入中国演出。仅在今年5月8日,上海同时有包括圣彼得堡交响乐团、瑞典 Art Nova 合唱等四个国外知名音乐家或团体同时在不同场馆演出。音乐会集体撞车景象,让乐迷们面对诸多选择,甚难抉择之感油然而生。也不时听闻有爱乐者不惜代价,坐着飞机全世界听音乐会,疯狂程度让欧洲人都为之侧目。这一切好像都值得欣喜,也难怪西方人无不惊讶地说:“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中国”。但另一面,乏人问津也不是个案,几个月前,中国知名女指挥张弦率领上海交响乐团上演了极为精彩的音乐会,也同样是上座率惨淡。一面是一票难求或者选择苦难,另一面是我们错过了诸多精彩的艺术家的演绎。我愈发感到,我们的听众,在如今情景里,纵抱热爱艺术之心,也在种种迷惑之中无法选择地进入当下音乐的困境之中,被迫在一个狭隘的音乐世界中打转。作为一支立足听众,立足中国的职业室内乐团,ELA具有一种引导的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ELA 是小众的,因为他们选择面对音乐在这个时代里的重大困境。同国外诸多职业当代乐团相似,作为一支学院内的团体,ELA 成员不仅是演奏家,更充满艺术家的问题意识。他们演奏优秀的当代音乐作品,但更注重那些在历史上被湮没的室内乐作品。“彼时当代,此时现代”,似乎能够表明他们面对当下音乐会极端保守的态度。西方音乐的历史上,公共音乐会的欣赏恐怕从没有经历一个如此保守的时代。一百年前,音乐会上演奏的是当代的浪漫主义音乐,一百年后的今天,当代音乐从战后时代走进新浪漫主义时代,经历极端与复归传统的动荡,但主流的公众舞台却无动于衷。更为狭隘的是,在历史上浩瀚数量的音乐作品中,能够登上公众音乐会舞台的作品数量微乎其微,音乐会不断重复上演的舞台更像是一个保守的圈套。2015年是西贝柳斯纪念年,乐界掀起了大量纪念这位芬兰作曲家的音乐活动。在ELA 即将于6月举行的“彼时当代,此时现代”系列音乐会之六上,与西贝柳斯同时代的丹麦作曲家尼尔森(今年也是他诞辰150周年)的作品将与西贝柳斯弦乐四重奏“亲密之声”一并献演,这位北欧作曲家的音乐价值并不在西贝柳斯之下,这似乎表明一种态度:主流古典音乐界每纪念一个作曲家都促使人遗忘或阻止人知晓更多有价值的作曲家,但却都牺牲在主流乐界垄断的狭隘视界中。更为可贵的是,他们是愿意真正立足于中国的艺术家,正视所有中国艺术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文化传统与当代美学的关系。除去演奏西方创作,ELA 更加重视推广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他们演奏、委约了包括谭盾、杨立青、许舒亚、郭文景等诸多中国当代音乐家的作品,在6月即将举行的音乐会上,他们将演奏委约于陈晓勇的室内乐作品。
对于听众来说,这些问题乍看上去似乎并不重要。但是,真正卓越的艺术作品会让人感知到这些问题的伟大意义。艺术家与听众的关系有些像史蒂夫·乔布斯对待他的产品的态度:其实人们并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除去贝多芬、巴赫这类能够穿越时空的伟大人物,浪漫主义散发出来的更像是与现实生活毫无联系的煽情。人们需要这些,但总要为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留下空间。因为的确,要理解音乐并不容易。但对那些真诚执着于音乐本身的听众们来说,同样真诚的一群音乐家正以一种当代的方式,等待彼此在音乐中的共融与相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