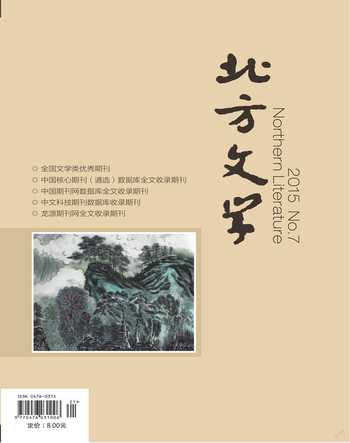人非圣贤
2015-05-30张培芳
张培芳
摘 要:本文结合替罪羊母题深入分析《红字》与《潘石榴园的喧闹》两部作品的架构与肌理,论证小说的人物设置和情节的安排皆是完美呈现替罪羊母题的必然需求,同时对比分析了两部小说在表现这一母题方面的相同和不同之处。
关键词:替罪羊人物;替罪羊仪式;民族精神
《红字》是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霍桑的代表作,《潘石榴园的喧闹》是当代美国印裔作家基兰·德赛的作品。两部小说创作年代相差甚远,但两位作家却不约而同地在文本中成功地移入替罪羊模式,使这一古老的母题历久弥新。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两部作品,阐释了其中体现的替罪羊母题,以及作家通过这一母题所彰显的不同时代与民族的精神。
一、 替罪羊人物形象对比分析
《红字》与《潘石榴园的喧闹》都成功刻画了替罪羊人物形象。《红字》中霍桑成功建构了著名心理学家艾里克·纽曼所划分的三类不同意义上的替罪羊:外乡人齐灵沃斯,道德败坏的人海斯特和像神灵一样杰出的人丁梅斯代尔。《潘》中的主人公桑帕斯集身体标记,精神异常与圣人巴巴的角色与一身,也成功地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
《红字》中的齐灵沃斯外乡人的身份注定了他替罪羊的命运。其次,海斯特因道德败坏(犯通奸罪)成为替罪羊。她被迫戴上红字A,并在邢台上示众三小时,成了耻辱的化身。而实际上,位于海斯特身上被视为邪恶的激情无不例外的位于每个人身上,不管他们多么受人尊敬。然而,清教徒否认这一点,海斯特成了他们宗教理念的燔祭。再次,丁梅斯代尔这位被视为神一样杰出的人也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他是一个接近圣人的牧师,被视为天才,上帝的使者。至始至终,他像耶稣一样被看做圣人,在清教徒眼里,他可以跟神交流亦或是神的使者。他们相信可以通过向他坦白罪恶来净化自己的灵魂。他最终承载了世人的罪恶,成了神圣的替罪羊。
吉拉尔认为,生病、精神错乱、遗传畸形、车祸伤残,甚至一般残废习惯上都成为迫害的对象(吉拉尔,21)[1]。《潘》中的主人公桑帕斯出生脸上就有胎记,而且遗传了母亲的精神病,具有很多不同常人的怪异举动。比如他曾穿着女性的衣服表演脱衣舞,最终一丝不挂。吉拉尔认为,挑选牺牲品不是根据人们给他们的罪名,而是根据他们具有的受害者的标记,根据所有可使人联想到他们和危机有罪恶的联系的标记。一个人的受难标记带得越多,他就越有可能大难临头。小说中桑帕斯的种种行为和特征注定了他替罪羊的命运。
二、替罪羊仪式对比分析
两篇小说中替罪羊人物都经历了较为明显的替罪羊仪式。《红字》中几位不同意义上的替罪羊经历了各自不同的替罪羊仪式。《潘》中的主人公桑帕斯从出生到最终神奇地变成潘石榴的过程中也贯穿了替罪羊仪式。
替罪羊的典型迫害范式就是当众惩罚,四处游街和单独隔离(弗雷泽,475)[2]。这在《红字》中的海斯特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她被强制性命令站在妇幼老少都能清楚看到的示众台上长达三小时之久。人群围着示众台倾泻着他们的愤恨。社区成员无情的羞辱和咒骂她。人群中甚至有人刻薄地说应该在海斯特额头上用烙铁烙上记号作为惩罚(霍桑,49)[3]。遭遇这样的直接集体迫害范式之后,海斯特又经历了单独隔离。她被驱逐到城外,孤零零地居住在一个废弃的茅草屋里,海斯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其次,丁梅斯代尔也经历了较为明显的替罪羊仪式。海斯特当众受辱时他也经受着内心的煎熬,特别是他被牧师指定为审问海斯特的人,逼问海斯特通奸者姓名时,他内心所承受的痛苦不比海斯特少。自此以后,丁梅斯代尔更是被愧疚和悔恨包围着。人们越是敬仰他,他负罪感越深。珠儿一次次地邀请他一同站在示众台上,齐灵沃斯不断地跟踪和窥视他,这一切使丁梅斯代尔心力憔悴,备受折磨。当他再也不能承受内心之痛时即将走向死亡时,他经历了一个完美的替罪羊仪式。这就是新英格兰节日那天的游行。霍桑在小说中深度渲染了这个节日,这次游行,正是照应了替罪羊的传统仪式。正如古希腊的农神替罪人一样,伴随着壮观的游行,丁梅斯代尔迎来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死前的仪式进一步彰显了他的神圣,使他成为万人敬仰的替罪羊。
《潘》中桑帕斯也经历了明显的替罪羊仪式。首先,桑帕斯的出场就伴随着某种仪式。他诞生在异乎寻常的环境中,那年夏天,夏考特异常炎热无雨的天气造成了严重的干旱。旱情严峻得甚至使红十字会在夏考特西边搭起了饥荒救援营,城中冒出了无数的求雨计划(德赛,3)[4]。持续几个月没下雨,人们烦躁不安,在一阵混乱之中桑帕斯诞生了。他的降生伴随着最狂烈的暴风雨,伴随着赈济饥荒的物资的到来,这种魔幻似的出场注定了他被献祭的命运。其次,长大之后,他被孤立于家庭和社会之外,成为人们眼中的异类。父亲看不惯儿子不成器的样子,总是数落他;妹妹不把他放在眼里;祖母看不起他;同事疏远他;老板鄙视他。桑帕斯被家人和同事孤立,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抑,当他再也不能承受时,独自一人自我放逐到郊区,爬到大树上,无论家人如何劝说都不再下来,主动实现了自我隔离,这也类似处置替罪羊的仪式。
三、替罪羊母题的实现与超越
霍桑借助替罪羊母题讽刺当时清教徒和神圣牧师们的虚伪;德赛利用替罪羊母题以及诙谐的语言,反讽的手法揭示了印度人民所崇拜的圣人的虚无。但与《红字》不同的是,《潘》呈现并戏仿了替罪羊母题,桑帕斯的消逝并没有给小镇带来宁静和谐的秩序,而是比以往更加混乱。
小说《红字》中替罪羊母题的实现在三位主人公身上都有体现。首先,海斯特从罪人变成了人们心中的天使,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女先知。原是受害者的她,现在既带回来秩序,又象征着秩序,甚至体现着秩序。她从违反者变成恢复者,甚至变成她预先违反的秩序的创建者,变成社会秩序的支柱。众人由对之恨之入骨到奉若神明,这体现了人们对替罪羊的万能信仰。替罪羊的魔力转变为有益的力量。这个悖论正是神话的突出特征,也是替罪羊母题的主要内涵。丁梅斯代尔在经历了各种内心折磨和明显与不明显的迫害范式之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进一步被神化了。他在神圣的步道之后,用尽最后的一丝力气,忏悔了自己的罪过,倒在了刑台上,成了光荣的殉教者。他带走了他自己的包括社区人们向他诉说的所有罪恶,完成了替罪羊的使命。
正如《红字》中的替罪羊形象被神圣化一样,《潘》中的桑帕斯也同样实现了向神圣化的转变,但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桑帕斯借助于偷窥信件内容以及吸食大麻后的梦幻语言实现了神圣化,人们把他当做圣人,万人朝拜他。因为他通过邮局的工作知道了镇上几乎所有人的通信内容与内心秘密,并熟记于心,当人们询问他时,他能对答如流,并用富有哲理的话语提供对策。以前的同事也恭恭敬敬地来拜他。整个夏考特镇的人都来洗耳恭听他的布道。就连在影院附近给女士带来无限烦恼的猴子在桑帕斯面前变得异常驯服。猴子们给他当保镖,并不时地梳理着他的头发。一位教堂的牧师索性将桑帕斯与画中被林中的兽物前呼后拥着的圣人形象联系了起来。
正如《红字》中的丁梅斯代尔,桑帕斯的神圣化伴随着他的死亡,正如书中所说的,“他们会要了他的命,他必死无疑”。猴群因醉酒捣乱使小镇上的人乱作一团。当局决定将猴群捕捉,并制定了严密的计划。随着捕猴计划的开展,桑帕斯脸上浮起绝望而迷茫的神情,就像琥珀里一枚沉寂的化石。在人群喧闹声中,他最终变成了一个带有标记的潘石榴,被猴王抱着,幽灵般消失在了林木中。
四、相同母题所彰显的不同时代与民族精神
《红字》与《潘》都成功地将替罪羊母题移植到了文本中,但两位相隔几乎两个世纪的作家通过这一相同的母题彰显了不同的时代与民族精神。霍桑的《红字》以17世纪的新英格兰为背景,成功塑造了不同意义上的替罪羊人物,并赋予他们替罪羊仪式。霍桑如此将替罪羊母题移植于文本中,是他对自己祖先驱巫案的反驳与指涉,更是对处于统治地位的清教和当时社会的讽刺。他借助于替罪羊模式,通过对人物被强制负罪的因由及受罚的仪式化过程的描写,深刻揭示了社会不公正、不人道的本质。正如弗莱指出的:“执著于对某位个人进行社会报复的主题(不管他可能是多么大的一个恶棍)只会使此人显得罪过较轻,而社会显得罪过较重”(弗莱,23)[6],霍桑利用替罪羊母题揭示了清教对人性的压抑,对人们精神自由的束缚,同时颂扬了人们对爱情家庭婚姻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不同于《红字》对清教的讽刺,《潘》充满了对印度佛学理念的思考以及作家对印度文化特别是崇拜圣人的指涉与讽刺。佛学的基本隐喻是“出家”:既走出以父母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纲常之“家”,又走出那个以天地为支柱的宇宙之“家”。它的本质是“解脱”,即解脱人生和宇宙的种种束缚,获得生命的“大自在”,“大解放”(李军,27)[7]。《潘》塑造了一个出走的浪子形象及其决绝的背影,桑帕斯“一脚跨出了通往屋顶的门;他展示了自己决绝的意志,尽管无人目睹”(德赛,15)[5]。他挣脱父母的羁绊,远离他们以寻求自由。他凭着一种面对虚无的决心,坚定地无所依傍地走向他的自性之路。印度文化对精神追求的认可乃至崇尚由来已久而且长盛不衰。小说肯定了个体寻求精神解脱的神圣性。同时揭示了印度强调精神启蒙的神圣传统的弱点。
总之,《红字》与《潘》两部作品在表达替罪羊母题方面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时隔近两个世纪的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将替罪羊母题成功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在不同的时代表达了相同的诉求,即人们对精神自由的向往,以及对神与人神圣性的否定,强调了人非圣贤这一理念,讽刺了美国清教徒对所谓神圣牧师的崇拜以及印度人们对所谓圣人的膜拜,从而颂扬人类的自然本性,充满了人文主义的关怀。不同之处在于,《红字》最终驱邪成功,替罪羊代表了秩序,同时给社会带来了秩序,而小说《潘》驱邪失败,结尾描述了驱邪活动失败后的情形:社会依然混乱,人们动用了警察,部队,法官控制局面,结果使本来混乱的局面更加混乱。这体现了小说对替罪羊模式的戏仿和超越,对驱邪行为背后的真正目的进行讽刺,对印度社会崇拜的圣人的讽刺。
参考文献:
[1]勒内·吉拉尔. 替罪羊[M].冯寿农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2] Frazer,James. The Golden Bough [M].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22.
[3] Hawthorne,Nathaniel. The Scarlet Letter [M]. New York: Bantam Dell,2003.
[4]基兰·德赛. 潘石榴园的喧闹[M].卢肖慧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
[5]诺思洛普·弗莱. 批评的剖析[M].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6]李军. “家”的寓言—当代文艺的身份与性别[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