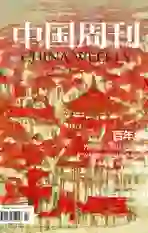如何为中国找到灵魂的家园
2015-04-29李人庆
中国乡村建设如果没有对于历史和文化的价值判断,就无法真正地建设起美丽和谐的乡村,而且会对乡村文化发展和历史景观保护产生极为广泛和全面的破坏。
当前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存在着对于物质建设,远重于精神和文化建设;重形式,远重于内涵和实质;重短期表面效果,远重于长期潜在的效果。诸多问题和弊端层出不穷,屡见不鲜,比比皆是。在建设过程中,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对西方城市文化的追求成为建设和发展价值导向和指南。其背后的潜在支配性逻辑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行政支配下,所谓理性的、效率的、缺乏主体性和价值主导的“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起着支配性地位。政治行政空间的无限扩大,政府权力的扩张,挤压了社会各个领域和方面本身应具有的社会空间。单一的、单项的思维逻辑和强权政治的文化理念统治和支配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造成社会文化生态和社会结构的结构性失调和单一与同质化。在所谓发展的话语下,扼杀了原有文化和社会自身所具有的活力和生机。中国乡村建设中美的匮乏和文化保护与发展的缺失,是与中国整体性的政治文化制度结构密切相关的。反映了其发展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结构性特征。因此,要实现乡村建设的文化重建,首先要赋予文化所应具有的主体性地位,给予其发展的必要社会文化空间。
“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能有如此之长的历史或保存如此完好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曾经产生了一个非常发达的文明。今天的希腊人或埃及人与他们的古代祖先都没有任何联系,而今天的中国人却是他们祖先的直系后裔。这样伟大的人民和民族怎么可能跌落到如此丑陋的地步呢?”在近代化过程中,优秀的中华文化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载体还存在着,但是作为文化实践和文化惯习已越来越堕落,丧失了原有优良的文化传统,不仅没有祛其糟粕,反而是祛其精华,取其糟粕。传统的官本位特权文化不仅没有祛除,儒家民本思想没有确立,反而在西方话语经济发展主导的体系下,大行其道不断扩张。
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文化问题,费孝通先生在晚年也进行了深刻的自省,并提出了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问题。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要保持自身民族和历史文化的自尊、自信和自强,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理念,反映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实质,确实值得我们深思。“没有理由一百年的革命可以推翻一千年的智慧”。现代化决不应只看作一个国家富强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和文明演进的过程,在这个进程中,美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建立了自身文化和道德伦理信仰等一系列与现代文明共通的文化价值理念,形成了与物质发展相匹配的精神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才能算是真正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国现代化需要建立在文化自觉、自省、自主、自信的文化复兴基础上,文化重建在乡村建设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核心作用。文化重建需要建立在文化自觉和自省的基础上,建构历史与现代、城乡和族群文化之间相互平等的、尊重的、沟通的文化关系,是文化重建和文化复兴的基础。也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不能用建设城市的思想思维方式来建设农村,城乡一体化并不是同质化发展,而是等值化发展;乡村建设要建立在尊重历史和民族的文化遗产基础之上。乡村建设要保持自身与自然生态和谐的关系。乡村人文文化景观建设需要重新思考现代和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继承关系。乡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要通过民主赋权激发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具体发展项目和人与文化的发展结合,实现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乡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文化重建,就需要从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的角度,对发展理念和政策本身进行反思,对乡村自身价值进行重估,确立其主体性和自主性地位。所谓的“一张白纸”是完全建立在历史和文化虚无主义基础上的发展理念主导和支配了中国乡村的发展理论与实践,对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地抛弃了。所谓文化重建,并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要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接续和再造。需要找到并重塑中华文化的魂魄和精神。乡村建设就是要恢复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优秀文化传统;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乡里文明和共同体的和谐,尊重农民其实就是尊重中国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和文化;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乡村是中华农耕文化的根,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在于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并不是基于西方理念生存信仰文化基础之上的现代生活,而是符合中国人的文化习俗生存信仰文化的现代化。因此,对于我们后发国家,尤其是中国具有优秀历史文化国家民族而言,现代化本身并不是简单地全盘接受和西化,而是要完成自我对于文化的更新和再生,也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完成一个符合中国人内生需求的自主性的现代化过程。
早在民国时期,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创始人之一的梁漱溟先生就认识到了中国文化重建和乡村重建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乡村,道德和理性的根在乡村,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从乡村人手。当前我们在建设农村文化的时候,应改“输入”为“生长”,找到农村文化的生长点。农村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以纯朴为特色的文化态势,若单纯地靠引入当前主流文化——城市文化,那么势必会冲击农村现有的文化,形成村不村、城不城的势态。梁漱溟认为要建设农村,必须依助农村文化的重构,且要改造旧文化,使失调的文化能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因为,中国的社会组织生长自乡村。在中国,集家成乡,集乡而成国,乡是寻求组织最适当的范围。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立足农村,真正从农村现实出发。
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新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在中国城乡互动和市场化发展转型背景下展开的,新的乡村建设要在发现和重估乡村价值基础上,结合城乡互动,通过市场化机制满足城乡的生产、生活和生态发展的现实要求,通过输入新技术新理念和社会创新实现乡村价值的创造性转化与价值实现,乡村在平衡和消解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文化问题,对于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和创造性转化,对于建设既内生于中国传统、又符合当代及未来发展需求的可持续发展方式,为中国找到灵魂的家园归宿和信仰,在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实现动态的、互补的、自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潜力和价值。要避免对于农民和农村的歧视和矮化,乡村建设中在强调农民主体性的同时,不能排斥和忽视外部发展援助在其中的作用,真正的乡村建设只有建立在重塑乡村精神基础上才有可能,只有建立在对所谓工业化和城市化单向度的现代化反思基础上才能实现,只有在文化自觉自主基础上重建建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城市与乡村新型关系以及基础性制度文明基础上才能实现和谐可持续的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文化和文明的复兴和再造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