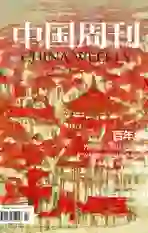诗意表达
2015-04-29刘晗
电影《转山》中,大部分场景处于中国滇藏边界,险峻与壮美并存,渺小的人面对着严苛的自然展开一番对话,可谓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完美再现。
比起美国公路电影中的各种混搭元素的构成,《转山》略显低调与平淡,一辆单车急速飞奔在崎岖不平、深渊莫测的路上,背景晴日蓝天或是“冰激凌”雪山若隐若现,就像明信片上的景色那般一成不变,不仅如此,也没有知名影星的加盟,即使是这样的拍摄手法,也并未使观者有单一冗长之感。
这部看上去颇有纪录片意味的电影产生的效果远远超过了电影本身所要阐述的,《转山》无疑为中国公路电影奠定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类型电影是按照同以往作品形态相近、较为固定的模式来摄制、欣赏的影片,类型则是按观念和艺术元素的总和来划分的。在电影《转山》中,无论是张书豪的身体力行,还是原作者谢旺霖的亲身体验后的诉说,均来自真人真事。虽然影片的主线只有一条,但编剧和导演独具匠心,安排了很多小插曲,如骑友晓川在半途中遇难,生命垂危时竖起的大拇指,更坚定了张书豪走下去的决心,藏族少女与张书豪一言一语间青涩情感的萌发,以及导演多次将特写镜头推进到张书豪的面孔,从出发时的稚气未脱到饱经风霜后的粗犷成熟,每一帧变化都实时印刻在观者的脑海中。这样来看,《转山》囊括了公路电影的行走特色,纪录片的真实以及文艺片的清新,集合了至少三个类型片的元素在其中,在平淡质朴的主题下深藏着多种玄机。
《转山》出其不意打出了一张底牌,它抓住了大多数人对中国西藏神秘色彩的猎奇心理,追踪骑行路上的全景式展现滇藏地区民族地域风情,就像当年美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开启了中国民族地域影像一页崭新的篇章。《转山》中的台词不多,但似乎每一句都值得推敲,张书豪在沿途偌大群山的对比下成了配角,对白也变为了画外音,这可以看作导演的特地留白,在如默片一般寂静且漫长中沉淀心情,获得灵光闪现时的顿悟。影片临近结尾时,漫天舞动的红色经幡象征着神祗的召唤,在点燃了蓄积已久的情绪的同时,也在铺垫的坎坷中奏响了属于张书豪,也属于跟随他一同费尽波折抵达目的地所有人的共鸣音,沉默在爆发中得以升华,也是“泛纪录片”视角发生的初衷所在。
《转山》从文学到电影的媒介转换中,不经意的细节被洗涤或是升华,纸质读物的魅力在大银幕得到了提升,以情节的拼贴道出了小说中未说之言,读者头脑中萌生的影像在电影中或扭转或重申的再现,这是从文学到影片的去魅过程。无论对张书豪还是谢旺霖来说,其西藏行不是闲适的观光旅游,也非特地向神灵祈福,而是以胆识和毅力战胜来自生活的悲怆,翻过心墙,到达一个被众人看来颇为神圣化的地域,去魅摆脱心中的神圣化,这无疑又是人生中的一对二律背反。
在路上,一切的矛盾都集中在这个看似无限却被摄影机镜头定格的有限之下,时代的冲突、社会阶级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以及个人自身的冲突都被放大,在这个距离观者最近也最远的地方上演着人性的拷问,乃至微小的细节都会升级为沉重的哲理思考。电影《转山》中一天天记录着的地理海拔挑战着张书豪的耐力和坚韧,也衡量着人心的高度。当自我的不平衡被现实击垮,也正是重新审视自身之时。长路漫漫,是重振雄心壮志,让心灵继续服上这番苦役,享受极度的孤独,还是掉转头返回原点归零,从此便找不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容身之地。转山“转”的是哪座山?是心中的山。迷失、彷徨、忧郁、裹足不前的城市生活经不起扪心自问,也许流浪能重新唤起厚重的生命信仰,也许只有身临布达拉宫才懂得,仪式感是生活的支柱,是人得以生存的诗意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