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觯铭文研究
2015-04-29曹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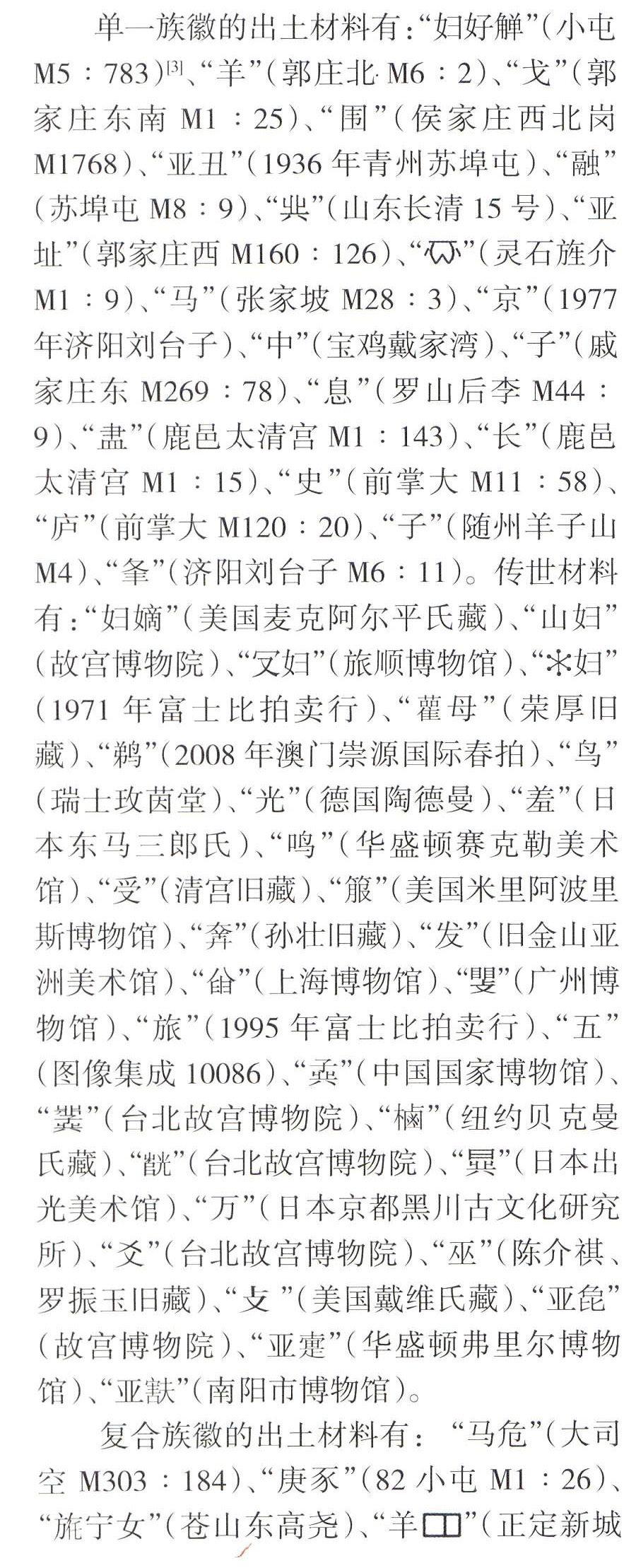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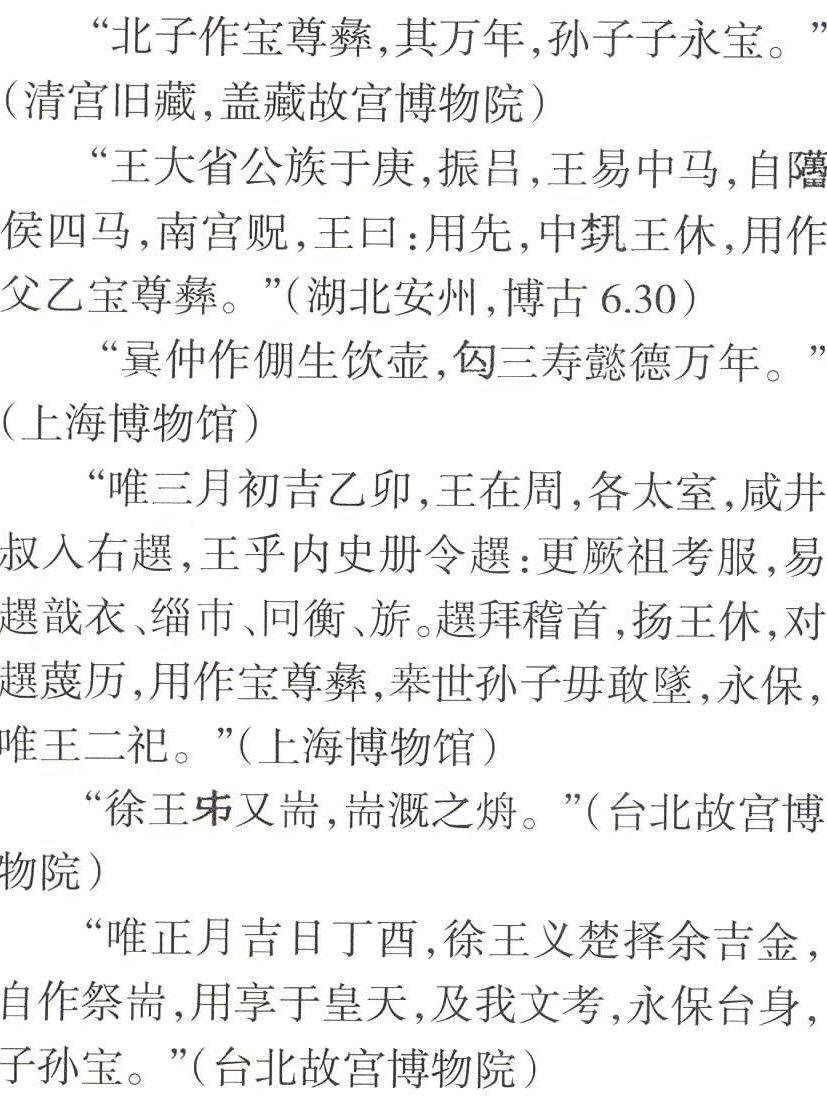
【关键词】青铜觯;铭文;时代性;族属;族群迁移
【摘 要】本文在系统收集青铜觯铭文材料的基础上,归纳出青铜觯铭文的自身特点,并利用这些特点,探讨相应铜觯的时代性和族属问题,以及商周时期的族群及商周王朝更替引发的族群迁移等问题。本文的研究不限于铭文本身,希望通过分析铜觯上的铭文现象,为研究相关问题提供思路。
铭文是铜器研究的重要方面,其记述的内容往往是我们研究历史事件、礼仪制度等的重要材料。同时,铭文可以帮助我们为铜器断代,确定铜器族属以及探讨相关族群及族群的迁移等问题。本文主要从青铜觯的铭文材料入手,在系统收集铜觯铭文材料的基础上,归纳其铭文的自身特点,并且利用这些特点,探讨相应铜觯的时代性和族属问题,以及商周时期的族群及商周王朝更替引发的族群迁移等问题,希望可以为利用铜器铭文解决考古学的问题提供一种思路。
一、青铜觯铭文的内容
青铜觯虽然体量不大,但现存仍有近半数的器物[1]上铸有铭文。其铭文内容分述如下:
1. 日名、族徽者
日名、族徽是青铜觯铭文中很常见的一类,其中有的仅有日名或族徽,有的两者同时存在,兹列举如下。
(1) 仅铸日名者
仅铸日名的出土材料有:“父戊”(张家坡M106∶7)、“父癸”(长安孙家岩)、“父乙”(山东长清县南3号)、“父己”(1960年岐山M8)、“辛”(灵石旌介M3∶9)。
传世材料有:“癸”(日本泉屋博古馆)、“祖丁”(清宫旧藏)、“祖辛”(台北故宫博物院)、“祖戊”(刘体智、容庚旧藏)、“文祖丙”(陈承裘旧藏)、“父辛”(1995年富士比拍卖行)、“父甲”(苏州博物馆)、“父丁”(钱坫旧藏)、“父庚”(故宫博物院)、“父乙宝”(故宫博物院)、“母戊”(刘体智旧藏)、“丁母”(清宫旧藏)等[2]。总体数量不是很多。
(2) 仅铸族徽者
仅铸族徽的数量相对较多。
单一族徽的出土材料有:“妇好觯”(小屯M5∶783)[3]、“羊”(郭庄北M6∶2)、“戈”(郭家庄东南M1∶25)、“围”(侯家庄西北岗M1768)、“亚丑”(1936年青州苏埠屯)、“融”(苏埠屯M8∶9)、“”(山东长清15号)、“亚址”(郭家庄西M160∶126)、“”(灵石旌介M1∶9)、“马”(张家坡M28∶3)、“京”(1977年济阳刘台子)、“中”(宝鸡戴家湾)、“子”(戚家庄东M269∶78)、“息”(罗山后李M44∶9)、“”(鹿邑太清宫M1∶143)、“长”(鹿邑太清宫M1∶15)、“史”(前掌大M11∶58)、“庐”(前掌大M120∶20)、“子”(随州羊子山M4)、“夆”(济阳刘台子M6∶11)。传世材料有:“妇嫡”(美国麦克阿尔平氏藏)、“山妇”(故宫博物院)、“妇”(旅顺博物馆)、“妇”(1971年富士比拍卖行)、“母”(荣厚旧藏)、“鹈”(2008年澳门崇源国际春拍)、“鸟”(瑞士玫茵堂)、“光”(德国陶德曼)、“羞”(日本东马三郎氏)、“鸣”(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受”(清宫旧藏)、“箙”(美国米里阿波里斯博物馆)、“”(孙壮旧藏)、“发”(旧金山亚洲美术馆)、“”(上海博物馆)、“”(广州博物馆)、“旅”(1995年富士比拍卖行)、“五”(图像集成10086)、“”(中国国家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纽约贝克曼氏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出光美术馆)、“万”(日本京都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爻”(台北故宫博物院)、“巫”(陈介祺、罗振玉旧藏)、“ ”(美国戴维氏藏)、“亚”(故宫博物院)、“亚”(华盛顿弗里尔博物馆)、“亚”(南阳市博物馆)。
复合族徽的出土材料有: “马危”(大司空M303∶184)、“庚豕”(82小屯M1∶26)、“宁女”(苍山东高尧)、“羊”(正定新城铺)、“冉贯”(宝鸡竹园村BZM13∶5)、“羊册”(扶风庄白76FZH1∶72)。传世材料有:“子弓”(台北故宫博物院)、 “虫乙”(西安大白杨废品库)、“天豕”(1993年伦敦佳士得拍卖行)、“子龙(龏汝子)”(美国卢芹斋)、“亚”(善斋)、“亚”(王辰旧藏)、“叔”(桓台县博物馆)、“册”(德国林登博物馆)、“”(1981年北京文物队拣选)、“北单”(刘体智、于省吾旧藏)、“舟”( 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馆)、“告田”(端方旧藏)、“钺”(英国Ingrom氏藏)、“大丐”(刘体智旧藏)、“爰”(1945年富士比拍卖行)、“冉”(容庚旧藏)、“史农”(罗振玉旧藏)、“羊”(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弓”( 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馆)、“妇亚”(哈佛大学福格美术博物馆)、“册享”(香港赵不波藏)、“西单”(纽约杜克氏藏)、“妇册”(刘喜海旧藏)等。复合族徽中出土材料数量较少,主要为传世材料。
(3) 日名、族徽同时并存者
日名、族徽同时存在的铜觯数量最多。出土材料有:“邑祖辛,父辛,云”(小屯西地GM874∶8)、“小集母乙”(大司空村M53)、“父己”(1958年大司空村)、“母戊翌凤”(安阳高家楼M1∶4)、“守父己”(安阳大司空村0980)、“子钺乙”(刘家庄村北M1∶20)、“父癸”(刘家庄村北M9∶36)、“辰卫父己”〔安阳郊区(新博0171)〕、“己父毛(或释玉)”(正定新城铺)、“羊父丁”(张家坡M2∶6)、“冉父己”(鹤壁庞村)、“臤父癸”(殷墟西区77AGM793∶9)、“交父辛”(洛阳唐城花园C3M417∶25)、“门父辛”(潍坊博物馆后邓M1∶3)、“冉癸”(宝鸡竹园沟M13∶5)、“史乙”(前掌大M30∶11)、“饮祖己”(洛阳东车站 M567∶15)、“榭父癸”(灵台白草坡M1∶6)、“榭父辛”〔陇县韦家庄(陇韦4)〕、“父癸”(灵台白草坡M1∶21)、“子父癸”(随县羊子山)、“覃父癸”(彭县竹瓦街)、“牧正父己”(彭县竹瓦街)、“亚父乙”(顺义牛栏山)、“戈父己”(泾阳高家堡91SJGM4∶11)、“保父丁”(泾阳高家堡91SJGM4∶12)、“鱼父癸”(岐山礼村)、“鸟父辛”(麟游后坪村)、“亚父丁”(前掌大M21∶3)、“亚父(癸)”(滕州庄里西M4∶3)、“父丁”(张家坡M2∶6)、“父己”(四川彭县竹瓦街)、“父乙”(黄陂鲁台山M28∶6)、“父乙”(随州叶家山M27∶11)、“父乙”(宝鸡纸坊头M1∶14)、“又父乙”(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史妣庚”(宝鸡嘴头BSM1∶2)、“保羽鸟母丁”(前掌大M38∶60)、“母此”(1972年周至解家沟)、“析父丁册”(大河口M1∶252)。
传世材料有:“冉丁”(吴云旧藏)、“冉戊”(故宫博物院)、“戈辛”(故宫博物院)、“子癸”(刘体智旧藏)、“齿兄丁”(罗振玉旧藏)、“兄丁”(博古6.21)、“兄(祝)父己”(综览·觯67)、“封祖乙”(罗振玉旧藏)、“史祖乙”(罗振玉旧藏)、“子祖己”(刘体智旧藏)、“子祖丁”(2000年富士比拍卖行)、“刀祖癸”(梁上椿旧藏)、“牧父己”(台北故宫博物院)、“父乙”(范季融藏)、“父乙”(上海博物馆)、“父丁”(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父丁”(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襄父丁”(吴宜常旧藏)、“子父己”(广州市博物馆)、“父己”(庐江李氏旧藏)、“木父己”(东平荣氏旧藏)、“父己”(刘体智旧藏)、“父己”(台北故宫博物院)、“子父庚”(陈介祺旧藏)、“竟父辛”(台北故宫博物院)、“戈父辛”(博古16.11)、“父辛”(刘体智旧藏)、“父辛”(台北故宫博物院)、“父辛”(上海博物馆)、“父癸”(王辰旧藏)、“爻父癸”(滕州市博物馆)、“重父癸”(罗振玉旧藏)、“()父癸”(庐江李氏旧藏)、“()父庚”(丁麟年旧藏)、“冉父甲”(善斋5.65)、“冉父丁”(1985年富士比拍卖行)、“万父甲”(普林斯顿大学美术博物馆)、“酋父甲”(中国国家博物馆、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天父乙”(宝鸡斗鸡台)、“翌父乙”(中华青铜器网、图像集成10405)、“父乙”(刘体智旧藏)、“父乙”(刘体智旧藏)、“辰父乙”(韩姆林寄陈柏弗罗科学博物馆)、“遽父乙”(罗振玉旧藏)、“父乙”(1970年富士比拍卖行)、“臤父丙”(图像集成10424)、“戈父丙”(上海博物馆)、“父丙”(1941年富士比拍卖行)、“父丁”(罗振玉旧藏)、“父丁”(图像集成10438)、“父戊”(善斋5.70)、“父己”(中国国家博物馆)、“父癸”(刘体智旧藏)、“父己”(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父己”(日本京都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父辛”(吴云旧藏)、“刺父辛”(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赆父辛”(陈介祺、刘体智旧藏)、“父辛”(罗振玉旧藏)、“弓父癸”(刘体智旧藏)、“父癸”(台北故宫博物院)、“亚大父乙”(孙壮旧藏)、“亚天父癸”(1969年富士比拍卖行)、“亚若父己”(故宫博物院)、“亚父乙”(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亚艅父乙”(综览·觯107)、“亚艅父辛”(曹秋舫、潘季玉旧藏)、“西单父乙”(故宫博物院)、“冉父乙”(徐同柏旧藏)、“子钺父辛”(上海博物馆)、“子父乙”(台北故宫博物院)、“齐豕丁父癸”(清宫旧藏)、“何父癸”(故宫博物院)、“亚祖辛”(罗振玉旧藏)、“尹舟父甲”(伦敦富士比拍卖行)、“天父乙”(台北故宫博物院)、“天父己”(吴云旧藏)、“大父乙”(潘祖荫旧藏)、“尹舟父丙”(美国费城宾省大学博物馆)、“遽徙父辛”(台北故宫博物院)、 “宁册父丁”(台北故宫博物院)、“母朱戈”(李泰旧藏)、“母乙”(西安大白杨废品库)、“秉母戊”(台北故宫博物院)、“戉母父丁”(伦敦大英博物馆)、“侯亚妣辛”(美国纽约魏格氏藏)、“父己,年,母壬,日壬”(西雅图美术博物馆)等。
从整体数量上看,日名、族徽并存的铜觯数量最多,其次为仅铸族徽的铜觯,相对较少的为仅铸日名的铜觯。
2.自作器或为某人作器者
自名体铭文的一种,数量相对较少,且多是记作器或为他人作器的几字简单铭文。已发现一定数量,传世材料相对较多。列举如下:
出土资料有:“伯作彝”(灵台白草坡M2∶6)、“作封从彝”(青州苏埠屯)、“夌伯作宝彝”(宝鸡竹园沟BZM4∶3)、“祖南雚作宝”(随州叶家山M27∶10)、“叔作新邑旅彝”(曲村M6214∶50)、“邑作宝尊彝”(洛阳北窑庞家沟M1∶5)、“伯作饮壶”(扶风庄白)、“伯作旅彝”(扶风庄白)、“史作父癸尊彝”(滕州庄里西M7∶9)、“作父乙彝,册”(宝鸡竹园沟M7∶9)、“其史作祖己宝尊彝”(北京琉璃河M253∶3)、“作父己宝”(洛阳北窑M418∶26)、“进作父辛,”(长安花园村M17∶38)、“应事作父乙宝”(平顶山M229∶4)、“小臣作父乙宝彝”(湖北江陵万城)。
传世材料有:“应公觯”(综览·觯102)、“龢作父乙”(台北故宫博物院)、“作父庚”(上海博物馆)、“作姞彝”(罗振玉旧藏)、“作宝尊彝”(伦敦大英博物馆)、“员作旅彝”(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季作旅彝”(清宫旧藏)、“冉作父己”(旅顺博物馆)、“姞亘母作宝”(旅顺博物馆)、“夨王作宝彝”(上海博物馆)、“丞仲作旅彝”(图像集成10589)、“徙作祖丁,齿”(丹麦哥本哈根国家博物馆)、“高作父乙彝”(台北故宫博物院)、“事作小旅彝”(清宫旧藏)、“伯作宝尊彝”(上海博物馆、旅顺博物馆)、“耳作御父辛”(刘鹗、罗振玉旧藏)、“祝儿作宝尊彝”(广州博物馆)、“彭妇作彝,父辛”(图像集成10611)、“敄作父癸彝,舟”(旅顺博物馆)、“朕作父癸尊彝”(上海博物馆)、“疑作宝尊彝,”(故宫博物院)、“作父丙宝尊彝”(容庚旧藏)、“子达作兄日辛彝”(端方旧藏)、“伯作厥祖宝尊彝”(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中作妣己彝,亚址”(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太史作宗彝,濂季”(陕西耀县)、“作祖辛彝”(曹秋舫旧藏)、“作父戊彝,亚册”(上海博物馆)、“凡作父乙尊彝,狈”(博古6.8)、“亚及,谏作父乙尊彝”(博古6.25)、“遽仲作父丁宝,亚”(上海博物馆)、“舌仲作父丁宝尊彝”(伦敦大英博物馆)、“鼓作父辛宝尊彝”(周鸿孙旧藏)、“齐史疑作祖辛宝尊彝”(故宫博物院)、“作父癸宝尊彝,用”(华盛顿弗里尔美术博物馆)、“何作日辛宝尊彝,亚得”(博古16.14)、“肇贾,用作父乙宝尊彝,册” (美国鲁本斯氏藏)、“伯作饮”(图像集成10855)、“义楚之祭耑”(台北故宫博物院)等。
以上有为其父作器的,如花园村M17∶38觯和平顶山M229∶4应事觯,也有自作器的,如竹园沟BZM4∶3夌伯觯。以上两类都有明确的作器者,作器对象亦很明确。但仍有作器者从略、作器者和作器对象不明者,如青州苏埠屯所出作封从觯。
3.记录某事件者
属记事体铭文,数量极少,一般记录受赏、册命或某个历史事件。目前所见出土材料主要有3件,传世材料有8件,列举如下:
“乙丑,厝易贝于公仲,用作宝尊彝。”(琉璃河M251∶9)
“乙丑,公仲易庶贝十朋,庶用作宝尊彝。”(琉璃河M251∶8)
“唯伯初令于宗周,史易马匹,用作父癸宝尊彝。”(滕州庄里西M7,范季融《首阳吉金》)
“王后克商,在成师,周公易小臣单贝十朋,用作宝尊彝。”(上海博物馆)
“公赏朿,用作父辛于彝。”(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
“北子作宝尊彝,其万年,孙子子永宝。”(清宫旧藏,盖藏故宫博物院)
“王大省公族于庚,振吕,王易中马,自侯四马,南宫贶,王曰:用先,中王休,用作父乙宝尊彝。”(湖北安州,博古6.30)
“仲作倗生饮壶,三寿懿德万年。”(上海博物馆)
“唯三月初吉乙卯,王在周,各太室,咸井叔入右趩,王乎内史册令趩:更厥祖考服,易趩戠衣、缁巿、冋衡、旂。趩拜稽首,扬王休,对趩蔑历,用作宝尊彝,世孙子毋敢墜,永保,唯王二祀。”(上海博物馆)
“徐王又耑,耑溉之烐。”(台北故宫博物院)
“唯正月吉日丁酉,徐王义楚择余吉金,自作祭耑,用享于皇天,及我文考,永保台身,子孙宝。”(台北故宫博物院)
徐王觯和徐王义楚觯为春秋晚期的复古作品,所以形制虽与西周中期偏早阶段的圆口细体觯接近,但铭文的附着方式和文体都与其他铜觯不类。
二、青铜觯铭文的特点
通过前文的罗列,我们注意到,青铜觯上的铭文有着非常明显的自身特点,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两点:
1.字数少,以日名、族徽为主,特征明显。
青铜觯上的铭文,可能受限于载体体量较小的缘故,字数普遍较少,5字及以下的铭文占到90%以上,即便记述作器或为某人作器者,也多是5字左右的简单文字。9字以上的记受赏、册命或者历史事件的有器形可证的铜觯仅11件,其中还包括2件为春秋晚期的复古作品,而这些字数相对较长的铭文,无一例外都铸在粗体觯上(2件复古的春秋晚期觯不在讨论之列)。可见铜觯上铭文字数较少的主要原因是其体量较小,难有空间铸较多的文字。到西周时期,青铜觯器体相对矮胖,才有可能附着较多的文字,如已知铭文字数最多的趩觯,完整地记述了趩接受册命的整个过程,铭文达到69字,而其器形已相当矮胖,形制为粗体觯的最后形态,甚至有学者称之为“尊”。所以铜觯在西周时期铭文字数仍不多的原因,并非铜觯在铜器中地位不高之故,概因其体量相对较小。此外,另一个原因是相当一部分的铜觯时代处在商代晚期,进入西周后较多地延续了商的传统,铭文依然以日名、族徽为主。这也揭示了青铜觯铭文的另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日名、族徽现象。
青铜觯上的铭文以日名、族徽为主,可以说是其铭文的最大特征。仅有日名、族徽的铜觯就占到有铭铜觯总数的70%左右,而前文所举自作器或为某人作器一类中,基本都涉及日名,多数涉及族徽。如将这些加在一起,铜觯上有日名、族徽的数量远超过有铭铜觯总数的90%。而不涉及日名者,基本为自作器、作尊彝或宗彝、作旅彝或作某类器四类,如“应公觯”(综览·觯102)、“伯作彝”(灵台白草坡M2∶6)、“邑作宝尊彝”(洛阳北窑庞家沟M1∶5)、“太史作宗彝,濂季”(陕西耀县)、“叔作新邑旅彝”(曲村M6214∶50)、“伯作饮”(图像集成10855),均不涉及其他作器对象。凡涉及除自己以外的特定作器对象者,均有日名。这些日名铜觯的作器对象,有祖辈的“祖”“妣”,也有嫡系一支的“父”“母”,基本涉及到铜器铭文中的所有纪念对象。而这其中,又以为“父”作器者的数量占据绝对多数(这一项的数量是其他三项总和的好几倍),可见在商周时期“父”为铜器的主要作器纪念对象,亦应是祭祀的主要对象,因此,在商周祭祖礼中,主要祭祀对象可能就是祭祀其嫡系一支的“父”。虽然在商代晚期有着“周祭”制度,但是 “父”才是主要的祭祀对象和最普遍的现象,也体现了此时对于“父”的尊崇,以及父权在礼制和社会秩序中的特殊地位。当然,从铭文中日名最多的现象也可以看出,日名制是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恭王以前)的重要礼制习俗,是从商代延续至西周前期的一种社会传统。
除了日名,族徽为青铜觯铭文的另一大宗,数量仅略次于日名者。在这些族徽中,有单一族徽者,也有复合族徽者,其中以单一族徽为主,如“冉”“戈”“”“”等。复合族徽中,有的是两种族徽的复合,如“子钺”“”“册”等,也有多种族徽的复合,如“宁册”“册享”“妇册”等。而无论单一族徽,还是复合族徽,均有加“亚”形者,如“亚”“亚册”“侯亚”等。多数情况下,单一族徽在“亚”形内,甚至有的将日名也都置于其中,如“亚祖辛”。但是复合族徽中,有的族徽全部在“亚”形内,有的只有某一个或几个在其内,而另一个在其外,如“亚”,有的“”在“亚”形内,有的却在其外,情况十分复杂。总之,铜觯族徽的特点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商周时期族徽铭文的复杂性。
2.史料价值高
青铜觯上的铭文虽然字数不多,但是却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这首先体现在记述历史事件的文字中。小臣单觯铭:“王后克商……”,记周王朝二次克商之事,即周公平定武庚和“三监之乱”的史实,为成王时期之标准器。滕州庄里西M7出土的史鼎铭“唯伯初令于宗周,史易马匹,用作父癸宝尊彝”,类似的铜器铭文体例有匽侯旨鼎的“匽侯旨初见事于宗周……”等,一般均指各封国在首封之后的各代诸侯即位后,至宗周觐见周王获取周王认可之事。因此该器虽只有18字,但由于出土自滕国墓地,所以结合该器的时代,可认为其记述了周初分封于滕州庄里西一带的滕国第二代滕侯即位后第一次觐见周王,受命于周王的史实。同时,该铭也进一步说明了西周时期分封制中中央王朝与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各诸侯虽亦为嫡长子继承制,但只有得到周王的承认和“受命”才能真正取得侯位,中央王朝对于即位诸侯的人选有着相当的决定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周分封制下,周王朝对于诸侯国的控制力和统治模式。中觯作为北宋重和元年(1118)在安陆(今湖北孝感)出土的“安州六器”之一,记中受赏于周王之事,内容涉及“南宫”。而同为“安州六器”的中甗铭文又涉及曾国。近年叶家山墓地讨论的焦点即为曾国的族属问题,新出犺簋记曾侯烈祖为“南公”,而发掘者认为此“南公”之“南”即为文献和金文中“南宫”的省称,从而推定叶家山一带的曾国应为姬姓[4]。而中觯铭文因涉及“南宫”,其必将是日后学界讨论曾国与南宫氏关系时不断提及的材料。
此外,青铜觯铭文涉及的西周封国,记有应国(应公觯)、史国[5](史觯)、逢国(夆觯)、齐国(齐史疑觯)、邶国(北子觯)、宋国(长觯)等,其为研究西周早期的封国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同时,铜觯铭文也体现了使用者的社会等级。从铭文看,使用铜觯等级最高的在商代晚期是商王的配偶,如妇好觯,西周前期为诸侯,如应公觯,至今没有发现商王或周王的有铭铜觯,或与商王陵被盗、周王陵未曾发现有关,但能使用铜觯者显然都是当时社会的贵族阶层。而趩觯铭文记述了一段完整的册命过程,对于了解西周的册命制度亦有意义。
三、青铜觯铭文体现的族群
及族群的迁移
青铜觯上的族徽除史料价值外,还揭示了存在于商周时期的部分族群及其发展、迁徙的过程。
关于商周青铜器上的族徽,虽有从事美术史研究的学者对其性质提出过异议,但是多数学者相信这些铭文就是郭沫若先生早在1930年就指出“此等图形文字乃古代国族之名号,盖所谓‘图腾之孑遗”的说法[6]。作为研究商周时期族群的重要依据,青铜器上的族徽代表了生活在此时期的族群。而这其中,有明确出土地点的铜觯为我们讨论族群的生活区域以及迁移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如商代晚期基本都出土于殷墟的族徽有“羊”(郭庄北M6∶2)、“戈”(郭家庄东南M1∶25)、“子”(戚家庄东M269∶78)、“围”(侯家庄西北岗M1768)、“亚址”(郭家庄西M160∶126)、“庚豕”(82小屯M1∶26)、“守父己”(安阳大司空村0980)、“子钺乙”(刘家庄村北M1∶20)、“父癸”(刘家庄村北M9∶36)、“辰卫父己”〔安阳郊区(新博0171)〕、“母戊翌凤”(安阳高家楼M1∶4)、“小集母乙”(大司空村M53),这些无疑都是生活在殷墟以殷人为主体的族群集团,他们与商王朝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息”族铜器集中出土在相当于殷墟三、四期的河南罗山县天湖村墓地,由于近年荥阳小胡村和正阳润楼两处族墓地的发现,可确指此时商王朝的南界就在信阳罗山一带[7],因此“息”(罗山后李M44∶9)族也应是殷人族群之一。而在商代晚期,商王朝在西方、北方、南方全面收缩的情形下,始终未放弃对于东方的控制,特别是鲁北地区。已知青州苏埠屯四条墓道大墓正是商王朝此时控制鲁北一带,掌握环渤海沿岸盐业遗存的重要据点[8],因此铜觯上的“亚丑”(1936年青州苏埠屯)、“门”(潍坊博物馆后邓M1∶3)等也应是殷人集团的族群之一。
这些族群在商、周王朝更替之后的周初多被分散至王都地区以及各个封国。通过青铜觯铭文可以探明的有“子”族及以其为主的复合族徽“子钺乙”族和“戈”族、“羊”族等。“子”族铜觯发现于殷墟的戚家庄东(M269∶78),“子钺乙”族铜觯发现于刘家庄村北(M1∶20),而进入西周后,“子”族(子、子父癸)铜觯见于噩国西周早期的中心区域随州羊子山的两座墓,“子钺”与“单”复合(单子钺)的1件尊和1件卣见于琉璃河燕国墓地M251。“戈”族铜觯发现于郭家庄东南M1,而戈父己觯发现于西周成康时期的泾阳高家堡91SJGM4,该墓地被学界公认为西周早期的“戈”族墓地。“羊”族铜觯发现于郭庄北M6,而羊父丁觯发现于西周早期的张家坡M2,与“羊”族相关的复合族徽“羊册”发现于西周中期的扶风庄白76FZH1。这些晚商就生活在殷墟的族群,其铜器在西周时期王都以及封国的出现,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赗赙、助祭等原因,另一部分则可能是族群迁移的结果。后者主要是因为商、周王朝的的交替,特别是平定武庚叛乱之后,殷人集团被周王朝分散至各处,以分而治之。这方面的文献依据有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的记载,而早些年授予鲁国的殷民六族之一的“索氏”铜器在兖州李官的发现[9],更印证了这些记载。考古的证据就是这部分殷人集团墓葬甚至墓地在西周早期的发现,泾阳高家堡戈族墓地就是典型的例证。因此,青铜觯的族徽铭文还体现了周初分封殷遗民、分而治之的统治政策,对于研究商周族群迁徙、商周统治政策的异同具有重要意义。
四、青铜觯铭文反映的时代性和族属问题
铜觯铭文所反映的时代性,一是某类铭文体例所揭示的时代特征,可以直接帮助我们判断其相应物质载体的时代;二是最具特色的铜觯铭文的存在时期,体现了一定的时代特征。当然,以上是两类不同形式的铭文,但二者又有着一定的关系,这种联系有助于我们分析铜觯的族属以及揭示出西周礼制的变革。
第一要分析的是前文所举的第2、3类铭文。这类铭文无论是前者的“自作器或为某人作器”者,亦或后者的“记受赏、册命或历史事件”,从出土材料看,其时代特征都非常明确。如滕州庄里西M7(史觯)、灵台白草坡M2(伯觯)、宝鸡竹园沟BZM4(夌伯觯)、宝鸡竹园沟M7(觯)、随州叶家山M27(祖南雚觯)、北京琉璃河M251(公仲觯)、北京琉璃河M253(其史觯)、曲村M6214(叔觯)、洛阳北窑庞家沟M1(邑觯)、平顶山M229(应事觯)、洛阳北窑M418(觯)、长安花园村M17(进觯)、扶风庄白窖藏(伯觯)、湖北江陵万城墓(小臣觯),都是明确的西周前期墓葬或窖藏。只有1931年出土作封从彝觯的青州苏埠屯墓需要讨论。青州苏埠屯墓地由于发现有四条墓道的大墓,早年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其时代为殷墟晚期,但是近年有学者指出该墓地的时代在西周时期[10],而我们也认为,虽然苏埠屯墓地以四条墓道大墓为代表的墓葬的时代约在殷墟四期,但是该墓地的时代可进入西周[11]。而具体到这件铜觯,吴镇烽先生亦认为其出土的墓葬为西周墓,时代为西周早期[12]。因此,出土材料均证明该类铭文体例的铜觯时代为西周前期。传世材料虽没有明确的出土单位,但是从其形制判断,时代与出土材料所反映的情况比较一致,只有个别形制的或可早至商周之际,但具体到某个铜觯上,其绝对时代基本都应进入了西周。
第二要分析的是前文所举日名、族徽铭文。这类铭文主要出现在商代晚期,以殷墟的发现为代表,这点前文已有涉及。具体讲,日名作为一种礼制和社会习俗,出现的时代集中在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13]。族徽除商代晚期集中发现于商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域,其所代表的族群在西周前期亦随着周初的分封迁徙到各处,因此其时代也主要集中在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当然,它也揭示了附着这类铭文的铜觯的时代集中在这一时期,而这也是铜觯最主要的存在时段。
结合时代性,此类铭文还能帮助分析铜觯的族属。既然铜觯上的日名、族徽在商代晚期集中发现于商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域(特别是殷墟),而这一时期铜觯上凡有铭文者均为日名、族徽,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将铜觯的族属与殷人族群集团联系在一起。而进入西周后,铜觯上许多有据可证的族群都是从商代晚期的殷墟地区迁徙至西周王都地区及各封国的,坚持不用族徽者,是以姬姓周人为代表的族群。有学者早年提出“周人不用族徽说”的命题[14],并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西周前期不用族徽的铜觯情况亦与之相近。坚持不用日名的也多为姬姓周人,如琉璃河M251出土的公仲觯和庶觯。该墓位于琉璃河墓地不使用腰坑、殉狗葬俗的Ⅱ区,学界公认为墓区的性质是以匽侯为代表的姬姓周人,因此该墓出土的这两件铜觯不见日名的现象,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西周时期姬姓周人在较多地排斥日名制。因此,青铜觯的族属应主要为殷人集团,其在西周时期的使用者是以殷遗为主的族群集团,西周时期其他一些族群集团的使用主要是由于此时期铜觯在酒器核心组合中地位的提升,并且在这些族群中,姬姓周人的铜觯不用族徽,同时也较多地排斥日名制。但是日名、族徽现象的大规模消失,是以西周前、后期为界的,这在铜觯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文献中有“穆王修典”“恭王礼制改革”的记载,日名、族徽现象正是经过这一时期的变革,数量明显减少,殷遗也普遍放弃,并在西周后期基本消失。关于西周前、后期的礼制变革,有学者从铜器演变的角度进行过讨论[15],而日名、族徽的演变应是礼制变革的另一个方面,体现了这一时期以姬姓周人为主的统治集团对周文化因素的巩固和对商文化因素的彻底排斥,并以此来规范上层集团的礼制秩序。
五、小 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由于青铜觯体量较小的缘故,日名、族徽是其铭文的主要内容,这一特点从晚商一直延续到西周前期。而自作器或为某人作器和记述某事件两类铭文则具断代意义,凡使用该类铭文的铜觯,其时代均已进入了西周。此外,通过铜觯的日名、族徽现象,以及主要出土在晚商时期的安阳殷墟地区的特点,使我们认识到铜觯的族属应是以殷人为主体的族群集团。由于日名、族徽是晚商时期重要的社会礼俗,即使到西周成王六年(前1037)周公“制礼作乐”之后,周王朝开始有意识地排斥殷礼、施行周礼,相应的铜器组合也发生了变化[16],但是日名、族徽依然为殷人为主的族群集团所固守,直到“穆王修典”“恭王礼制改革”之后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族徽横跨商周王朝的现象,为我们讨论商、周王朝更迭时期出现的族群迁移现象提供了证据,也为研究周王朝对殷遗集团和异族的统治政策提供了依据。总之,本文的研究不限于铭文本身,希望通过分析铜觯上的铭文现象,为研究相关问题提供思路。
[1]由于传世器的特点就是以有铭铜器居多,因此本文数字仅为大致估算。从目前出土青铜觯的数字统计,有铭铜觯所占比率不到40%。
[2]本文的统计范围为有器形可证确为铜觯者,仅存拓片的不在收录范围。
[3] “妇好”一般理解为人名,但是书写方式、位置均与族徽相同,且意义与族徽接近,因此暂将其归入此处。
[4]黄凤春,胡刚:《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公”——兼论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江汉考古》2014年2期。
[5]曹斌:《前掌大墓地性质辨析》,《考古与文物》2015年2期。
[6]郭沫若:《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载《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61年。
[7]曹斌:《从商文化看商王朝的南土》,《中原文物》2011年4期。
[8]刘绪:《商文化在东方的拓展》,载《夏商周考古探研》,科学出版社,2014年。
[9]郭克煜等:《索氏器的发现及其重要意义》,《文物》1990年7期。
[10]黄川田修:《齐国始封地考——山东苏埠屯遗址的性质》,《文物春秋》2005年4期。
[11]曹斌:《周代的东土——山东地区西周时期的文化谱系及其文献的整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12]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1055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13] 我们采用大致以恭王为界,将西周分为前、后两期的说法。
[14]张懋镕:《周人不用族徽说》,《考古》1995年9期。
[15] a.罗森:《古代中国礼器——来自商和西周时期墓葬和窖藏的证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b.曹玮:《从青铜器的演变试论西周前后期之交的礼制变化》,载《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c.罗泰:《有关西周晚期礼制改革及庄白微氏青铜器年代的新假设:从世系铭文说起》,载《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四》,(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
[16]曹斌:《试论青铜觯的组合和墓葬的关系》,待刊。
〔责任编辑:成彩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