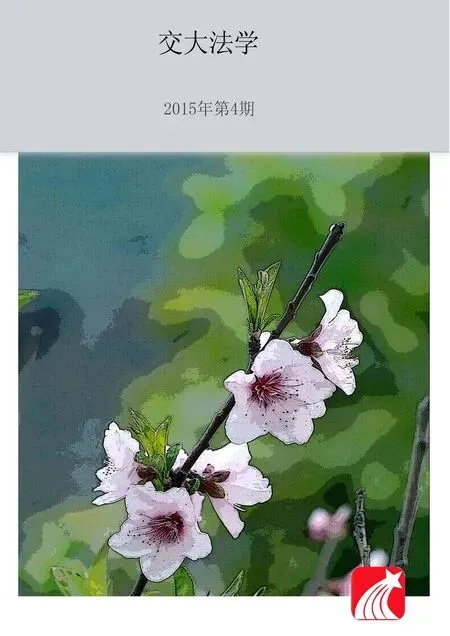论浮动账户质押的法律效力——“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诉张大标、安徽长江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保证金质权确认之诉纠纷案”评释
2015-04-18其木提
其木提
一、引 言
账户是会计学上的用语,系记载资金流动的载体。账户本身并无交换价值,真正具有实际价值并产生法律意义的是账户中的资金。因此,所谓账户质押实际上就是对账户资金进行质押,〔1〕参见王利明:《收费权质押的若干问题探讨》,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2期。即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在金融机构开立的账户质押给债权人,承诺到期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以账户中的资金优先受偿的担保方式。
我国《物权法》未明确规定账户质押担保,最高人民法院则肯定这一金钱质押担保方式。〔2〕《物权法》第5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物权法》第223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也可以出质。账户质押未被法律和行政法规所规定,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依照物权法定的原则,账户质押缺乏法律依据,不能产生物权效力。不过,《物权法》第5条所言之“法”是否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评价不一。有的认为,物权法定的“法”不包括司法解释(参见黄松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有的则认为,司法解释所创设的物权,如果具有符合《物权法》的公示方法,就应当予以承认(参见江平:《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本文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虽有解释之名,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行立法之实,应具有法源的功能(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出口退税托管账户质押贷款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规定:出口退税专用账户质押贷款银行,对质押账户内的退税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审理和执行案件时,不得对已设质的出口退税专用账户内的款项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或者执行措施。
事实上,账户质押可以分为固定账户质押和浮动账户质押。固定账户质押是指出质人以其账户出质后,由作为质权人的开户行监管该账户,账户内的资金被“冻结”,出质人不能自由使用账户内的款项,当债务人到期不履行债务时,开户行就账户内的资金优先受偿的担保方式。浮动账户质押则是指出质人以其账户出质后,在发生约定事由以前,质权人允许出质人在一定额度内使用账户内的款项,亦即账户内款项并不完全“冻结”,账户资金处于浮动状态,会因质押人提款或者存款而减少或者增加,当债务人到期不履行债务时,质权人就账户中的资金优先受偿的担保方式。
我国司法实务和学界一般认为,《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适用于固定账户质押。〔3〕参见曹士兵:《中国担保诸问题的解决与展望》,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页;董翠香:《账户质押理论与实务问题探析》,载刘宝玉主编:《担保法疑难问题研究与立法完善》,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10页。那么,浮动账户质押是否属于《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的金钱质押?对此学界意见分歧,有观点认为,《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应适用于浮动账户质押,〔4〕参见楼建波:《化解我国融资融券交易担保困境的路径选择》,载《法学》2008年第11期。也有观点认为,浮动账户质押,不符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的“特定化”的要求,因而不具有担保物权的效力。〔5〕参见前注〔3〕,曹士兵书,第311页;前注〔3〕,董翠香文,第310页。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不同的认识,有判决持肯定意见,〔6〕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2)东一法执外异字第12号执行裁定书(参见毋爱斌、陈渭强、刘晓宇:《保证金账户可以特定化并构成货币质押》,载《人民司法》2012年第10期);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惠中法民二初字第14号判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粤高法民二终字第12号(2012)民申字第1070号判决书(参见陈宜芳、吴凯明:《保证金账户资金质押的成立要件探析》,载《人民司法》2013年第24期)。另,未经特别说明,本文案例均出自北大法宝案例数据库。有的则持否定态度。〔7〕参见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合民一初字第00505号民事判决书即本案一审判决。在此理论及实务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1期公布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诉张大标、安徽长江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保证金质权确认之诉纠纷案”(以下简称“本案”),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肯定了浮动账户质押的物权效力。这一裁判规范对于明确司法解释之适用范围,增加法律的可预见性,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具有积极的作用。
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遵循解释论的研究范式,拟以《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为前提,分析本案浮动账户质押担保问题,论证其物权效力,当有助于浮动账户质押问题之理解,法律解释适用之安定。
二、案情概要〔8〕本案详细案情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1期,第39~43页。
(一)基本案情
2009年4月7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以下简称“农发行安徽分行”)与安徽长江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担保公司”)签订一份《贷款担保业务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案《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第3条“担保方式及担保责任”约定:甲方(长江担保公司)为借款企业借款向乙方(农发行安徽分行)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第4条“担保保证金(担保存款)”约定:“甲方在乙方开立担保保证金专户,担保保证金专户行为农发行安徽分行营业部,账号为2033×××××××××××××××9511(以下简称‘本案账户’);甲方需将约定的保证金在保证合同签订前存入本案账户,甲方需缴存的保证金不低于贷款额度的10%;未经乙方同意,甲方不得动用本案账户内的资金。”第6条“贷款的催收、展期及担保责任的承担”约定:“借款人逾期未能足额还款的,甲方在接到乙方书面通知后五日内按照第三条约定向乙方承担担保责任,并将相应款项划入乙方指定账户。”第8条“违约责任”约定:“甲方违反本协议第六条约定,没有按时履行保证责任的,乙方有权从甲方在其开立的担保基金专户或其他任一账户中扣划相应的款项;甲方担保专户的余额无论因何原因而小于约定的额度时,甲方应在接到乙方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补足,补足前乙方可以中止本协议项下业务。”
上述《合作协议》签订后,长江担保公司按约在农发行安徽分行处开立了本案账户。长江担保公司按照协议约定缴存规定比例的担保保证金,并据此为相应额度的贷款提供了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此后,自2009年7月至2012年12月,本案账户发生一百余笔业务,有的为贷方业务,有的为借方业务。
2011年12月19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张大标诉安徽省六本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长江担保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过程中,根据张大标的申请,对本案账户内的资金1 495.785 2万元进行保全。该案判决生效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账户内的资金1 338.313 257万元划至该院账户。农发行安徽分行作为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该院于2012年11月2日裁定驳回异议,并告知农发行安徽分行有权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2012年11月,农发行安徽分行以本案账户内的资金系长江担保公司向农发行安徽分行提供的质押担保为由,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农发行安徽分行对本案账户内的资金享有质权,人民法院对该账户内资金停止强制执行。张大标辩称:本案《合作协议》没有质押的意思表示;本案账户不符合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人民币专用账户开户条件,不构成账户的特定化;农发行安徽分行为长江担保公司开设的账户资金本身是浮动的,不符合特定化的要求,故请求驳回农发行安徽分行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长江担保公司认可农发行安徽分行对账户资金享有质权的意见。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担保法》第63条、第64条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的规定,质押合同成立并生效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签订书面的质押合同,二是完成质押物的交付。金钱作为特殊的动产质押须具备以下要件:一是双方当事人要签订质押合同,有将金钱作为质押的意思表示;二是要对质押物的金钱进行特定化,并移交债权人占有。首先,本案《合作协议》并非质押合同,且约定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整个合同行文中没有质押条款,表明双方并无将金钱作为质押的意思表示。其次,本案《合作协议》中虽然约定长江担保公司向约定账户存入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但没有约定农发行安徽分行就保证金在债务人不清偿到期债务时享有优先受偿权的相关内容。再次,本案账户是长江担保公司开立,在形式上不符合法定的“移交债权人占有”。第四,本案账户多次有进出账的情形,账户内的资金的数额不断浮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特定化的要件。上述事实表明,长江担保公司并无就本案账户中的资金提供质押担保的意思表示。农发行安徽分行主张其与长江担保公司存在质押担保法律关系,对本案账户中的资金享有优先受偿权的理由不能成立,驳回其诉讼请求。
农发行安徽分行不服,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质押合同不成立与事实不符;本案《合作协议》约定未经农发行安徽分行同意,长江担保公司不得动用保证金专户内的资金,表明该保证金的占有权实际上已经完成转移;本案账户内的金额浮动属正常情形,一审判决认定不符合特定化要求没有依据。张大标辩称:本案《合作协议》约定长江担保公司不得动用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只是说明长江担保公司对资金的处分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并不能说明占有已经发生了移转。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以下简称“本案判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撤销一审判决;农发行安徽分行对长江担保公司账户内的资金享有质权。
(二)裁判理由
《物权法》第210条规定,设立质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质押合同。《物权法》第212条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金钱作为一种特殊的动产,具备一定形式要件后,可以用于质押。本案中,农发行安徽分行主张其对本案账户内的资金享有质权,应当从农发行安徽分行与长江担保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质押合意以及质权是否设立两个方面进行审查。
1.农发行安徽分行与长江担保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质押关系。依据本案《合作协议》第4条、第8条约定,农发行安徽分行与长江担保公司之间协商一致,达成对长江担保公司为担保业务所缴存的保证金设立担保保证金专户,长江担保公司按照贷款额度的一定比例缴存保证金;农发行安徽分行作为开户行对长江担保公司存入该账户的保证金取得控制权,长江担保公司不能自由使用该账户内的资金;长江担保公司未履行保证责任,农发行安徽分行有权从该账户中扣划相应的款项优先受偿。该合意具备质押合同的一般要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关于金钱质押的规定。
2.本案质权是否设立。依照《物权法》第212条规定,交付质物为设立动产质权的生效要件。金钱质押作为特殊的动产质押,不同于不动产抵押和权利质押,依照《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金钱质押生效的条件包括金钱特定化和移交债权人占有两个方面。(1)长江担保公司依约开立本案保证金专用账户后,按照每次担保贷款额度的一定比例向该账户缴存保证金,该账户亦未作日常结算使用,故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的金钱以特户形式特定化的要求。另占有是指对物进行控制和管理的事实状态,因本案账户开立在上诉人农发行安徽分行,农发行安徽分行作为质权人,取得对该账户的控制权,实际控制和管理该账户,符合出质金钱移交债权人占有的要求。故本案质权依法设立。(2)关于账户资金浮动问题。保证金以专户形式特定化并不等于固定化。本案账户在使用过程中,账户内的资金根据业务发生情况虽处于浮动状态,但均与保证金业务相对应,除缴存的保证金外,支出的款项均用于保证金的退还和扣划,未用于非保证金业务的日常结算,即农发行安徽分行可以控制该账户,长江担保公司对账户内的资金使用受到限制,故该账户资金的浮动仍符合金钱作为质权的特定化和移交占有的要求。〔9〕张大标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239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再审申请:本案《合作协议》所约定条款具备质押合同的一般要件;本案账户专门用于本案合作协议所约定的担保业务,且质权人依据约定实际控制该账户,故本案账户质押符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的要求。
三、案例评释
(一)焦点问题提炼
法院判决是法院以法律事实和相关法律规范为前提的裁判。因此,分析典型案例特别是指导性案例的规范性逻辑,首先应以其定型化事实为前提。
以质押账户内有无资金作为分类标准,浮动账户质押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空账户质押,即设立账户质权时,账户资金可能还是零,〔10〕例如,“在出口退税账户质押中,出质人实际上是以一笔固定的金钱质押,只是质权人并非在控制退税账户的同时占有退税款项,而是需待出口退税款项实际进入退税账户后才能占有退税款项。”张雪梅:《解读〈关于出口退税托管账户质押贷款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载黄松有主编:《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2004年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页。或者账户质押后,因账户资金浮动而变为零。〔11〕例如在项目融资业务中,贷款人往往采用账户质押或者债权质押担保方式。基于质押合同的约定,会有源源不断的收益汇入该账户中,质权人可以以存入账户的资金用于偿付贷款。但在有些情况下,贷款人依约以账户资金受偿后,至债务人将其收益汇入账户为止,账户资金很可能会变为零。参见森田宏樹「普通預金の担保化·再論(下)」『金融法務事情』1655号26頁(2002年)。二是实账户质押,即账户资金处于一定幅度的浮动状态,但始终保持一定数额的资金,如出质人质押账户资金后只能汇入不得汇出,〔12〕参见罗小红:《账户质押法律问题研究》,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4期。或者质权人允许出质人在一定额度内使用账户内的款项。〔13〕参见道垣内弘人「普通預金の担保化」中田裕康·道垣内弘人編『金融取引と民法法理』〔有斐閣·2000年〕43頁以下。本案属于实账户质押之情形,即长江担保公司按照约定将保证金存入了本案账户,未经农发行安徽分行同意,长江担保公司不得动用本案账户内的资金。
以质权人是否为开户行作为分类标准,浮动账户质押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出质人以其账户向开户行质押;二是出质人以其账户向开户行以外的第三人质押。本案属于第一种情形。于此情形,出质人可以是债务人,也可以是债务人之外的第三人。出质人若为债务人,开户行无须设定质权,可依债法上的抵销制度,〔14〕参见其木提:《抵销权之法理探究》,载《中日民商研究》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方建国、蒋海英:《商业银行保证金账户担保的性质辨析》,载《金陵法律评论》2013年第2期。即可获得与设定质权相同之担保效果。〔15〕参见森田宏樹:「普通預金の担保化·再論(上)」『金融法務事情』1654号59頁(2002年)。若出质人为债务人之外的第三人,由于抵销权的行使以“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为要件,第三人对开户行并无债务可言,故开户行实有必要第三人提供担保以担保其债权。本案属于债务人之外的第三人,以其账户向开户行质押之情形,即长江担保公司为担保借款企业履行债务,以其在农发行安徽分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向该行提供质押担保。
其次,判决理由是法院以法律事实和相关法律规范,支撑其法律事实和适用法律的根据。因此,准确把握案件争议焦点,是评析判例规范性逻辑的关键所在。
正如本案判决所述,本案焦点问题有二:一是质押合同是否成立;二是质权是否设立。关于本案质押合同,一审判决认为,本案质押合同不成立;本案判决则认为,本案质押合同具备质押的一般要件。质押合同是否成立属于法律事实认定问题,从案例评释以及实体法角度而言,本案最为关键的争议焦点应是质权是否设立问题。关于质权是否设立问题,一审判决认为,本案账户资金具有浮动性,不符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的“特定化”要求,其形式也不符合该条规定的“移交债权人占有”要件;本案判决则认为,特定化不等于固定化,浮动账户不影响特定化的构成,质权人实际控制和管理账户即应认定符合出质金钱“移交债权人占有”的要求。可见,如何理解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的“特定化”和“移交债权人占有”这两个基本要件是本案最为关键的焦点问题。此二要件,其实质就是物权的特定性和公示性问题。物权是物之支配权,物权的客体必须是特定物;物权是对世权,涉及第三人的利益,故物权必须公示。动产质权是以特定的动产为标的物的担保物权,且以质物的交付占有为其生效要件和公示方法。因此,如何从物权的特定性、公示性角度,解释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是解决本案账户质押效力问题之关键所在。
不过,在探讨上述焦点问题之前,首先须明确其前提条件,即账户质押的动产质权属性。因为,依动产质押制度,动产质权的成立以出质人交付质物给债权人占有为要件。易言之,出质人虽将质物移转于质权人占有,但并不因此丧失其对质物的所有权。《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明确规定,账户质押属于特殊的动产质押即金钱质押,本案判决也认为账户质押属于金钱质押。这就表明,出质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形式移交质权人占有之后,仍保有该金钱之所有权。然而,按照传统民法理论,货币是特殊的种类物,其权属确定遵循“占有即所有”原则。特别是在银行与客户之间,客户将货币存入银行账户,即丧失对该货币的所有权,存款人仅享有债权性的返还请求权。如是,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账户资金成为动产质押标的物的可能性,也就否定了账户质押的动产质权属性。〔16〕参见赵一平:《论账户质押中的法律问题》,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8期;前注〔14〕,方建国、蒋海英文。因此,在探讨本案焦点问题之前,实有必要依据货币所有权理论,考察《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的法理基础,论证其动产质押之性质。否则,账户质权就无从谈起。
(二)账户质押之定性
关于货币所有问题的归属问题,在比较法上,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17〕关于货币所有权理论之形成与发展,参见其木提:《货币所有权归属及其流转归责——对“占有即所有”原则的质疑》,载《法学》2009年第11期。
一是,占有即所有理论。〔18〕参见川岛武宜『所有権法の理論』〔岩波書店·1949年〕197頁。货币之占有与所有合而为一,货币不发生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与占有回复诉权问题,仅发生债法上的请求权。因为,(1)货币贵乎流通,并于流通过程中,全湮灭其个性,因而于现实占有之外,若谓尚有法律的可能支配(所有权),实属不可想象;(2)货币之购买力,并非基于作为货币之物质素材的价值,实因国家的强制通用力及社会的信赖,因而对于货币的现实占有人,即不问其取得原因如何,有无正当权利,而径认其为货币价值之归属者;(3)于交易上,若货币之占有与所有可以分离,则于接受货币之际,势必逐一调查交付货币之人是否具有所有权,如此则人人惮于接受货币,货币的流通机能势将丧失殆尽,有碍交易甚巨。〔19〕参见郑玉波:《民法物权》,台北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417~418页。
二是,占有即所有及其例外理论。〔20〕参见能见善久「金銭の法律上の地位」星野英一主编『民法讲座·别巻1』〔有斐阁·1984年〕111頁。占有即所有理论仅适用于货币充当商品交换媒介,如买卖、投资、储蓄等事由而发生的货币现金的流转关系之情形。在不涉及货币流通手段机能,且当事人无移转所有权的意思表示时,则不应适用该规则。例如,占有辅助人、监护人、财产代管人、法人代表、合伙执行人、信托财产之受托人、破产清算人等为他人利益而占有保管货币者,若该货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则委托人不丧失其货币所有权。〔21〕参见末川博:「貨幣とその所有権」『经济学杂志』1卷2号1頁(1937年)。再如,窃取他人之货币,该货币在窃取人处具有可识别性时,被窃取人不丧失其货币所有权。〔22〕参见好美清光:「赃物である金銭と即時取得」『金融商事判例』73号2頁(1967年)。相反,若无可识别性,如占有辅助人、窃取人以该货币作为交易媒介,或者挪用其占有之钱款或者与其金钱相混合而不具有可识别性时,占有人取得该货币的所有权,原所有人只能对之享有债法上的请求权。
三是,物权性价值返还请求权理论。该说在上述“占有即所有及其例外理论”基础上,进一步主张货币所有权人的价值返还请求权。〔23〕参见四宫和夫「物権的価値請求権について」我妻栄追悼論文集『私法学の新展開』〔有斐閣·1975年〕183頁;松岗久和:「アメリカにおける追及の法理と特定性」林良平先生献呈論文集『現代における物権法と債権法の交錯』〔有斐閣·1988年〕366頁。货币作为权利客体,具有双重性,它是一种价值符号,但其载体又是有形之物。货币之权利变动不能脱离其载体而存在,但其实质仍然表现为价值,故货币返还请求权的标的并非有体之货币本身而是其价值。因此,只要当事人没有移转货币所有权之意思表示,且丧失之货币具有特定性,即应排除适用占有即所有原则,货币所有权人应享有物权性价值返还请求权(Geldwertvindikation)。例如,在委托、行纪、信托关系中,委托人并无移转其货币所有权之意思,且受托人负有分别管理受托财产的义务,受托财产因而具有特定性。同时,货币又是一种价值符号,不发生分割不能的问题。因此,即使发生混同,应依物权法之混合物原理,按其价值成立共有,〔24〕参见王泽鉴:《民法物权(一)》,自版1992年,第145页。委托人在其价值范围内享有物权法上的优先受偿权。〔25〕参见道垣内弘人『信託法理と私法体系』〔有斐閣·1996年〕176、202頁。
我国通说采占有即所有及其例外理论。“占有即所有”原则仅适用于货币充当商品交换媒介,如存入银行,〔26〕参见曹新友:《论存款所有权的归属》,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2期。但也有观点认为,存款是存款人在保留所有权的条件下,将货币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权能暂时让渡给银行的信用行为,因此存款归存款人所有。参见徐志珍、黄莹:《论银行存款的所有权归属》,载黄莹、孟勤国主编:《中国物权法的理论探索》,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霍楠、夏敏:《保证金账户质押生效则不能成为另案之行标的》,载《人民司法》2014年第4期。或者借贷他人等情形。在不涉及货币流通手段机能,且当事人无移转所有权的意思表示的情形下,则不应适用该规则。例如,职工、受雇人等占有辅助人占有、管领单位或雇主的货币现金,属于持有而非占有;货币收藏者基于研究、爱好收藏的号码特殊的货币、印制有误的纸币等,虽有货币之名,但不注重其流通性;以封金的形式特定化的货币,货币实已不能发挥其流通手段的职能,货币之所有权与占有可同时成立。〔27〕参见梁慧星等:《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王利明主编:《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张庆麟:《论货币的物权特征》,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5期;刘保玉:《论货币所有权流转的一般规则及其例外》,载《山东审判》第23卷总第176期。
不过,我国学说在某种程度上亦肯定价值返还请求权理论。〔28〕参见周显志、张健:《论货币所有权》,载《河北法学》2005年第9期。占有即所有规则不应适用于某些专用资金账户中的钱款,这些特殊的商业账户规则已经使受托人、行纪人等自身的财产和由其管理的委托人的货币相区分,〔29〕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通过特户形式予以特定化,且当事人双方均无转移货币所有权的意思。〔30〕参见杨立新:《民法总则重大疑难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76页。因此对于这些专用账户中的钱款,没有必要适用“占有即所有”规则。〔31〕参见前注〔27〕,刘保玉文。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例如在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保证金是股民委托广东国投公司证券营业部代理买卖股票的结算资金,证券营业部只是代管,股民在证券机构缴存保证金的行为属于委托行为,即使证券营业部没有设立专门保证金账户分账管理,并不能改变保证金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属性。〔32〕参见“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年第3期,第27页。
那么,在上述我国货币所有权理论下,如何认识《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的账户质押中的资金归属问题,从而确定其动产质权之性质?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账户资金具有封金的性质,即将质押的货币封存,因此账户质押属于动产质押。〔33〕参见前注〔12〕,罗小红文。然而,封金是封存的货币,与将质押的货币存入银行提供的特定保险箱相同,已不能发挥其流通功能,其返还请求权的标的系有体之货币本身。而账户质押中的资金,仍然充当商品交换媒介作用,其返还请求权的标的并非有体之货币本身,而是金钱之价值。同时,《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明确区分特户和封金,二者属于不同的范畴。由此我们可以说,《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实际上采纳的是价值所有权理论,即所有权人将其货币从实物性财产利益转化为价值性财产利益,并通过特户形式特定化后,即应排除适用占有即所有原则,从而使账户质押具有动产质押之性质。
(三)账户资金的特定性
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金钱可以作为物权的客体。但金钱作为物权的客体必须具有特定性。《物权法》第2条第3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物权是权利人支配特定物的权利,其客体如不能特定,权利人则无从支配。因此,物权的客体必须是特定物,这是物权法上的一个基本原则,即物权客体特定原则。担保权属于物权范畴,〔34〕关于担保物权的性质,立法上亦有不同的做法,有的侧重其债权性,如《法国民法典》将担保物权规定于债权编;有的侧重其物权性,如《德国民法典》将担保物权规定于物权编。学说意见亦有分歧,主张债权说者认为,担保物权只是对一定的债权赋予优先受偿的功能(参见[日]加贺山茂:《论担保物权法的定位》,于敏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5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76页)。主张物权说者则认为,担保物权尽管与债权有密切的关系,但本质上仍然是担保物权(参见刘得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2页)。系以支配担保物之交换价值为内容的限制物权,故担保物权只能及于特定物之上,否则担保权人无从确定和支配标的物的交换价值。动产质权属于占有担保,其成立以出质人交付质物给债权人占有为要件。因此,质物必须是特定的动产。账户质押为特殊的动产质押即金钱质押。《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金钱以特户形式被特定化后,可以作为质押的标的物。因此,账户资金是否符合特定化要求,是金钱质权成立的要件之一。
那么,如何理解《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的“特定化”要件?浮动账户质押是否符合该要求?学界一般认为,固定账户质押完全符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的特定化要件。“符合特定化要求的账户,必须有特户的性质,该账户一般不再供债务人自由使用,资金在账户出质后应当‘冻结’,不能浮动。”〔35〕参见前注〔3〕,曹士兵书,第312页。也就是说,金钱质押要求相应账户的封闭性和独立性,故金钱质押须以一笔固定的金钱出质,以保障金钱的特定化。〔36〕参见前注〔3〕,董翠香文,第310页;参见前注〔12〕,罗小红文。相反,账户质押后,如果出质人仍然可以使用账户,账户中的资金处于浮动状态的,则不符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的特定化的要求。〔37〕此说否定浮动账户质押为金钱质押担保,但其性质如何,意见不一。有观点认为,浮动账户质押不符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的特定化要求,因而不具有物权担保的性质,债权人仅取得债权性质的担保(参见前注〔3〕,曹士兵书,第311页);也有观点认为,浮动账户质押是一种典型的以未来债权出质的权利质押形态(参见李国光等:《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理解与适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前注〔3〕,董翠香文,第308页)。
本文认为,质押账户资金的浮动性并不能作为否定其特定性的理由。传统民法采一物一权原则,物权的客体须为单一物,集合物不能成为物权的客体。〔38〕参见[日]田山辉明:《物权法》(增订本),陆庆胜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现代民法则突破一物一权原则,承认集合物在例外情况下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39〕参见前注〔18〕,川岛武宜书,第188页。我国《物权法》第181条规定,〔40〕《物权法》第181条规定:经当事人书面协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可以将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等抵押,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时,债权人有权就实现抵押权时的动产优先受偿。本于降低交易成本,融通资金的需要,引进了英美法上的浮动抵押权制度。〔41〕参见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15页。根据《物权法》第189条规定,〔42〕《物权法》第189条规定:动产浮动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依照本法第181条规定抵押的,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浮动抵押权设定后,抵押财产具有不特定性,其形态变动不居,价值飘浮不定。〔43〕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修订版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2页。抵押人在其正常经营活动中处分抵押财产的,抵押财产即逸出抵押权的效力范围,抵押财产的范围因之减少;抵押人新增加的同类财产亦自动归入抵押权的效力范围,抵押财产的范围因之增加。也就是说,与固定抵押相比,浮动抵押的特点是抵押财产系“非特定物”。此谓“非特定物”即指浮动抵押物的浮动性。但抵押财产并非永远漂浮不定,当出现《物权法》第196条规定的浮动抵押财产被“确定”(也称为“结晶”或“固定化”)事由时,〔44〕《物权法》第196条规定:依照本法第181条规定设定质押的,抵押财产自下列情形之一发生时确定:(一)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债权未实现;(二)抵押人被宣告破产或者被撤销;(三)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四)严重影响债权实现的其他情形。抵押物形态及价值特定,浮动抵押自动转化为固定抵押。可见,抵押物的浮动性并不影响其特定性,特定之时并非抵押权设定之时,而是在浮动抵押权因特定事由的出现而确定之时。〔45〕参见高圣平:《物权法与担保法:对比分析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页。同理,源于英美法的账户质押担保,〔46〕参见前注〔3〕,董翠香文,第301页。其客体也具有浮动性。同动产浮动抵押权,账户质押客体的特定性也可以表现为质权实现时的特定性,一旦出现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事由时,浮动账户质押即转化为固定账户质押。
或许有人会认为,集合物只有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47〕参见王利明、尹飞、程啸:《物权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陈本寒:《新类型担保的法律定位》,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2期。账户质押客体既非集合物,亦无适用动产浮动抵押之明确规定。因此,直接套用动产浮动抵押制度,解释账户质押客体的特定性,缺乏说服力。〔48〕事实上,物权客体的浮动性,不限于动产浮动抵押。例如,在应收款质押中,质押标的物特别是未来债权也具有浮动性。《物权法》第228条规定虽未明确应收账款质押制度系固定担保抑或浮动担保,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采肯定态度。该办法第4条规定,权利人因提供一定的货物、服务或设施而获得的要求义务人付款的权利,包括现有的和未来的金钱债权及其产生的收益,但不包括因票据或其他有价证券而产生的付款请求权。但退一步而言,即使我们依据传统民法理论,浮动账户质押客体亦可满足特定性的要求。详言之,在存款法律关系,存款人将其货币存入银行账户时,开户行会按具体业务笔数分别反映存款的收支情况。理论上,存款人每笔存款债权系因金融机构的记账行为而成立。事实上,每笔存入款项并非因银行记账行为而分别成立数笔存款债权,开户行记账行为会使每笔存款瞬间丧失其特定性,使存入款项与既存存款余额合计成为一个存款债权。〔49〕参见我妻栄:『債権各論中巻 民法講義V3』〔岩波書店·1962年〕742頁;前注〔13〕,道垣内弘人文,第49页。也就是说,开户行所为记账行为具有类似于更改的法律效果,每笔存款行为使既存存款债权消灭,同时成立一个新的存款余额债权。〔50〕参见前注〔15〕,森田宏树文。同理,在浮动账户质押中,质物表现为账户中的资金,质押账户之资金虽然会因质押人的存取款而增加或者减少,但开户行所为记账行为,会使浮动后的资金瞬间丧失其原有的特定性,同时就其余额范围内,转化为固定账户质押。
事实上,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明确规定金钱质押这一前提下,上述结论也符合我国动产质权担保制度。《担保法》第89条规定:“质押合同中对质押的财产约定不明的,或者约定的出质财产与实际移交的财产不一致的,以实际交付占有的财产为准。”也就是说,如果质权人依自己独立的意志将质物返还给出质人,不论其返还的原因如何,其质权概归消灭。同理,在账户质押这一特殊的动产质押中,质权人允许出质人使用账户内的资金的,出质资金应以质权人实际占有的账户资金余额为准。换言之,账户质押在该余额范围内具有固定账户质押之性质。
落实到本案,本案《合作协议》约定,出质人长江担保公司依约开立本案账户后,“自2009年7月至2012年12月,本案账户发生一百余笔业务”,账户资金虽处于浮动状态,但账户内始终存有约定的保证金额度。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本案判决关于特定化的裁判理由,即特定化不等于固定化,质押账户资金的浮动性并不影响账户质押客体特定化的构成。
(四)账户质权的公示性
《物权法》第2条第3款规定,物权是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所谓直接支配,从客观上看,是指权利人对物进行控制和管理的事实状态;从主观上看,是指物权人对物可以以自己的意志独立进行支配,无须得到他人的同意。〔51〕参见前注〔47〕,王利明、尹飞、程啸书,第3页。物权的支配性决定了物权具有对世性。物权的对世性,涉及第三人的利益,由此决定物权必须公示。根据物权变动公示原则,公示方法包括不动产的登记和动产的交付。担保物权是对物的交换价值的支配权。质权系担保物权,包括动产质权与权利质权。《物权法》第212条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物时设立。”即动产质权的成立以出质人交付质物给债权人占有为要件。占有是指对物进行控制和管理的事实状态。因此,质物的占有不仅是动产质权的成立要件,亦为动产质权的公示方法。〔52〕动产质权这一公示方法在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典中已成为共识。如《德国民法典》第1205条规定:设定质权时,所有权人需将物移交于债权人,并由双方当事人就债权人应享有质权达成协议。债权人已占有其物的,只需有关质权成立的协议即可。《日本民法典》第344条规定:“质权的设定,因向债权人交付标的物而发生效力。”《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账户质押属于特殊的动产质押即金钱质押,故其成立须满足质物“特定化”要件以外,还须具备将质物“移交债权人占有”这一动产质权的成立要件和公示要件。〔53〕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060号判决书认为,根据物权公示原则,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以交付为公示方式。以动产设置担保的质权,也需满足交付的公示要求。依照《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的规定,金钱作为特殊的质押财产,必须达到特定化,并移交债权人占有。银行作为具有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将出质人交付的金钱作为质押财产,应当依法将质押金钱放置于专门的账户,并且对任何第三人均能显示出设立质押的外观,否则难以区分该金钱是出质人交付的普通存款还是质押财产。
那么,如何理解《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的“移交债权人占有”这一成立要件?浮动账户质押是否符合这一要求?浮动账户质权是否具有支配性?学界一般认为,账户质押中的金钱是特定的,“出质账户一般不再供债务人自由使用,资金在账户出质后应当‘冻结’,不能浮动,作为债权人的银行取得对账户的控制权,并因其实际占有(作为开户行)和控制质押账户……”〔54〕参见前注〔3〕,曹士兵书,第312页。因此,固定账户质押符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的“移交债权人占有”要件。〔55〕例如《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担保合同纠纷案件若干法律问题指导意见》认为,《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说明,“货币被特定化后,可以作为质押的标的物。同时,债权人与出质人签订质押合同约定以出质人在该银行所开账户上的资金出质,该账户上资金实际上已受控于质权人,故质押有效”。参见奚晓明主编:《担保案件审判指导》,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427页。与之不同,在浮动账户质押中,账户中的资金处于浮动状态,因此不符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的“特定化”要求。〔56〕参见前注〔3〕,曹士兵书,第311页;前注〔3〕,董翠香文,第309页。也就是说,由于质押客体不特定,即所设质权无支配性可言,也就无法满足《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的“移交债权人占有”的要求。
本文认为,质押账户资金的浮动性不能作为否定浮动账户质权支配性的理由。事实上,浮动账户质权的支配性,与动产浮动抵押权的效力并无二致。依据我国《物权法》第189条规定,动产浮动抵押权有一个效力休眠期。〔57〕参见前注〔45〕,高圣平书,第254页。浮动抵押权在抵押财产“确定”之前,抵押权人没有支配具体抵押财产的权利,或不产生禁止抵押人在正常经营范围内处分抵押财产的权利,除非在抵押合同中对某些财产或处分行为作相反的规定。换言之,浮动抵押权只是笼罩和悬浮在浮动的集合抵押财产之上或者说与其一起浮动,直到浮动抵押权“确定”之前,对抵押财产之集合体及构成集合体之个体并无支配力。〔58〕参见前注〔45〕,高圣平书,第251页。当出现抵押财产“确定”事由时,抵押物形态及价值特定,抵押人丧失对抵押财产的自由处分权,抵押权人获得对抵押财产的控制权。同理,源于英美法的账户质押担保,也具有浮动性。作为一种浮动担保,质权人对质物的支配力也可以表现为质权实现时的控制性。〔59〕参见前注〔3〕,董翠香文,第312页。在质权实行的约定事由出现以前,质押账户中的款项是可以浮动的。当出现实现质权的约定事由时,质权人获得对质物的控制权,从而具备《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的“移交债权人占有”这一质权成立要件。
退一步而言,即使按照传统民法理论,我们也不能否定浮动账户质权的支配性。如前文所述,《物权法》第212条规定,动产质权的成立以出质人交付质物给债权人占有为要件。账户质押属于特殊的动产质押即金钱质押,表现为对账户内一定数额资金的支配。浮动账户虽具有浮动性,但质物仍表现为账户内一定数额资金即账户资金余额。《担保法》第89条规定,约定的出质财产与实际移交的财产不一致的,以实际交付占有的财产为准。账户质押属于动产质押,表现为质权人实际占有的账户资金余额的支配。质权人依自己独立的意志将质物返还给出质人的质物,不论其返还的原因如何,质权对该财产并无追及效力。当然,账户出质后,若出质人可完全自由支配账户,质权能否实现完全取决于偶然因素,则难谓质权对该标的物之支配力。〔60〕参见前注〔13〕,道垣内弘人文,第53页。但是,在浮动账户质押中,出质人对其出质账户资金的处分权并非完全不受限制。早在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业务的通知》:“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是商业性贷款,由商业银行自主审查、自主决定。商业银行应当与借款人约定:自银行发放贷款之日起至该笔贷款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借款人同意由贷款人监控该账户,未经贷款人同意,借款人不得擅自转移该账户内的款项。”也就是说,当事人在设定账户质权时,对出质人处分质物多设有限制。作为质权人的金融机构往往会与出质人约定,由质权人监管出质账户的现金流,未经质权人同意,出质人不得擅自处分账户内的资金,从而约束出质人对账户资金的处分权,显示质权人对质押财产的控制和支配力。〔61〕参见前注〔13〕,道垣内弘人文,第54页。
落实到本案,本案《合作协议》约定,“甲方需缴存的保证金不低于贷款额度的10%;未经乙方同意,甲方不得动用本案账户内的资金”。正如本案判决所述,出质人长江担保公司对账户内的资金使用受到限制,质权人农发行安徽分行可以控制该账户,故该账户资金的浮动仍符合金钱作为质权的特定化和移交债权人占有的要求。
四、结 语
综上,本文以《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为前提,通过分析本案判决理由,论证了浮动账户质押之物权效力。《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不仅适用于固定账户质押,亦适用于浮动账户质押之情形。本案判决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明确浮动账户质押的物权效力,符合物权客体特定原则及物权变动公示原则。
不过,如前文所述,指导性案例是以定型化事实为前提的裁判。这就意味着,案情略微一变,其参照价值即或成泡影。那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是否适用于本案定型化事实,即是否适用于出质人以实账户向其开户行质押以外的情形?具体而言,本案判决是否适用于前述空账户质押,是否适用于出质人以其账户向开户行以外的第三人质押之情形,颇值思量。
以账户向开户行以外的债权人质押之情形,有观点认为,因债权人既不占有账户,也不控制账户,债权人不能取得《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的账户质押担保权。〔62〕参见前注〔3〕,曹士兵书,第312页。本文认为,质物的交付不限于现实交付,也包括简易交付与指示交付(《物权法》第25条、第26条)。〔63〕参见前注〔47〕,王利明、尹飞、程啸书,第508页。《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8条规定:出质人以间接占有的财产出质的,质物自书面通知送达占有人时视为移交。〔64〕《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8条原文为:“出质人以间接占有的财产出质的,质押合同自书面通知送达占有人时视为移交。”此规定实际上是将质押合同的生效与质权的成立混为一谈,有违《物权法》第15条规定的债权物权区分原则。按照区分原则及《物权法》第212条规定,质押合同应自依法有效成立时起生效,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因此,所谓“质押合同自书面通知送达占有人时视为移交”,应为质物自书面通知送达占有人时视为移交。因此,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明确肯定金钱质押这一前提下,出质人以其账户向开户行以外的债权人质押之情形,债权人可以取得《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的账户质押担保权。
于空账户质押之情形,有观点认为,应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65〕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4)二中民初字第2764号民事判决书。例如,在出口退税账户质押中,质权人并非在控制退税账户的同时占有退税款项,而是需待出口退税款项实际进入退税账户后才能占有退税款项,但这并不影响账户质押的动产质押性质,其完全符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的“特定化”要求,其实质是以特户形式体现的附期限的账户质押。〔66〕参见前注〔3〕,董翠香文,第310页。本文认为,《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不应适用于空账户质押之情形。因为,账户质押须具备《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的“特定化”与“移交债权人占有”要件。而在空账户质押中,作为质物之金钱尚未存入账户,债权人无从确定和支配质押客体,无法满足“交付占有”这一动产质权成立的基本要件。〔6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出口退税托管账户质押贷款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第2条曾规定:“以出口退税专用账户质押方式贷款的,应当签订书面质押贷款合同。质押贷款合同自贷款银行实际托管借款人出口退税专用账户时生效。”之后,由于《物权法》的出台,法释[2008]1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以“与物权法有关规定冲突”为由,废止了该第2条规定,但并未具体阐明与物权法哪一条规定冲突。本文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废止该条规定,是因为该条规定有违《物权法》第15条规定的合同效力和物权效力相区分原则,将质押合同的生效与质权的成立混为一谈。除此以外,该条规定与《物权法》第212条“动产质权交付生效”之规定相冲突,或许也是废止该条规定的理由之一。事实上,同项目融资中所采账户质押担保,〔68〕参见前注〔11〕,森田宏树文。空账户质押是一种典型的以未来债权出质的权利质押形态。〔69〕参见前注〔11〕,森田宏树文,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