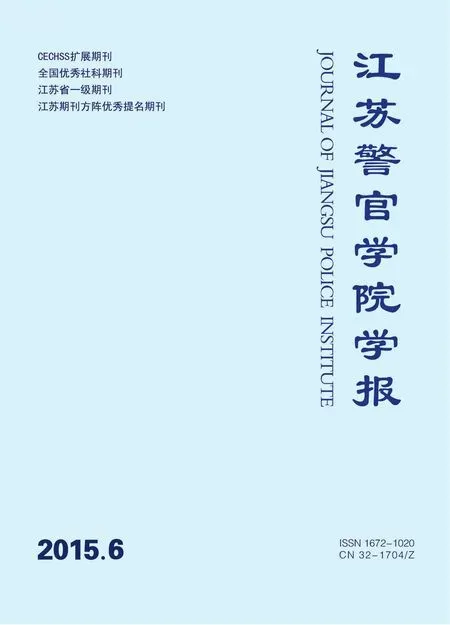刑事司法行为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两分论
2015-04-18蒋鹏飞
蒋鹏飞
刑事司法行为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两分论
蒋鹏飞
学术界对刑事司法行为存在着混淆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的现象。对于欺骗性取证、引诱性取证等有着“相对之恶”的司法行为,这种混淆容易使人们依据司法实践中对这类行为的现实容许而反推其合法性,从而质疑刑事诉讼法第50条的效力。应当在逻辑上严格区分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同时将程序性制裁只是作为法律处遇可用的手段之一。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两分论有着更强的解释现实的能力,可以为妥当的利益平衡创造理论空间,为刑事诉讼法的合理解释提供理论支持。
刑事司法行为 法律评价 法律处遇 刑事诉讼法
刑事司法行为是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发现犯罪、证实犯罪、追诉犯罪与惩罚犯罪等行使刑事司法权的职权性行为。对刑事司法行为进行合法性的辨识与以容许性分析为基础的后续处置,在理论与实务上存在着区分不清、界限模糊,以及以“程序处置”反推司法行为是否合法的现象。本文提出刑事司法行为的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的术语用来分别指称合法性评价与容许性分析,在理论上将两者予以严格区别,同时将程序性制裁只是作为法律处遇的一种具体方式。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两分论,对于容许某些有着“相对之恶”的非法司法行为的现实,有着更强的解释能力;对通过制定不同的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的法律依据而更好地进行利益平衡,有着更好的指引能力。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两分论,可为更为合理地解释刑事诉讼法(特别是解释刑诉法第50条与第54条),提供理论支持。
一、刑事司法行为的法律评价
(一)法律评价:广义与狭义
法律评价的概念引发理解混乱的首要节点,简单地可以表达为法律评价是对法律的评价,还是依据法律进行的评价。孙国华教授认为,法律评价包括这两者的内容:“法律上的评价,即根据已有的法律规章或与相适应的法理对有关法律现象或相关的社会现象所进行的评价”,其中心问题是合法性、法律调整的效率与法的实现程度等问题;“对法律本身的评价”,则“侧重于把法律置于更大的社会系统中来从总体上考察法律现象”,其中心问题是法的合理性、适当性问题。①孙国华:《中华法学大辞典 法理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页。很明显,孙教授所指的“法律上的评价”就是“依法评价”。有学者则认为法律评价仅仅是指对法律的评价,如,董学春教授认为“法律评价作为社会主体对法律及其运作过程的价值判断”②董长春:《法律评价的意义及其作用》,《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谢晖教授认为“法律评价乃是人们基于对法律的不同心理感受作出的一种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反应”。③谢晖:《法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57页。此外,有很多学者对法律评价持“依法评价”式的理解。如,李建明教授在刑事诉讼的语境中指出“所谓法律评价,不是指对法律或法律的实施进行的评价,而是特指法律专业人士基于法律理性、运用法律思维对于诉讼过程所进行的客观评价”。④李建明:《诉讼过程法律评价与社会评价的冲突》,《法学评论》2007年第6期。这种对法律评价的理解,最为重要的地方在于强调评价活动的以规范性为核心的法律属性。在部门法研究的领域,学者一般都对法律评价持这种理解。笔者认为,从汉语的通常惯例看,法律评价这一概念中的法律应当是形容词,即“法律性”评价,这种评价重在强调评价的规范性、强制性与国家性,从而与伦理性评价区别开来。学术界对法律评价持“依法评价”式的理解更为合理。
就算对法律评价理解成“依法”进行的评价,依据如何认识“法”以及如何确定评价的对象,对法律评价可以有着广义与狭义两种不同的理解。如果对法律评价作广义理解,法律评价实质上等同于依照法律规范进行的分析、判断与处理。这种理解的重点在于把法律评价视为法律发挥规范功能的途径,强调评价依据的规范性特点,对评价的对象、方式等没有作出限定。如有学者指出“法律评价是指在‘认定的案件事实’,包括定罪基础事实和量刑基础事实的基础上,从法律角度来判断其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是否构成法定或酌定的量刑情节以及这些情节对量刑的具体影响”。⑤孙锐:《司法裁判考量社会舆论的正当性》,《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在这里,法律评价其实就是法律分析的同义词,与案件处理相关的任何事情都可以作为法律评价的评价对象,而不仅仅限于对某具体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识别与判断。还有学者提出对证据进行法律评价,“对证据的法律评价(即最终认证)是证据质量、效力及使用结果的最后归宿”。⑥徐伟、鲁千晓:《诉讼心理学》,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页。很明显,此时所指的法律评价亦不局限于合法性辨识。
对法律评价的狭义理解,是在广义理解的基础上对评价的对象作进一步的限缩:法律评价仅仅是依据法律对“待评价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分析与辨识。如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律评价的直接目的是区分行为合法与否”⑦张文显:《法哲学基本范畴研究(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杜2001年版,第92页。;原魁社博士指出,法律评价是“司法机构运用法律规范作为评价标准,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合法、违法或犯罪等的评价,并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评价结果实施的评价活动”⑧原魁社:《诚信:“铁笼”内外》,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1-85页。;邓云教授在刑事诉讼行为的法律评价的语境中认为“刑事诉讼行为的法律评价就是对已经成立的刑事诉讼行为是否合法作出的判断”,“刑事诉讼行为法律评价的直接目的正是要区分诉讼行为的合法与否的问题,并为诉讼行为的价值评价创造前提”。⑨邓云:《刑事诉讼行为基础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7-318页。这都是从狭义的角度认识和把握法律评价的内涵。
(二)刑事司法行为的法律评价
对刑事司法行为法律评价内涵的理解也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狭义的定义仅仅指所谓的行为性法律评价,即对刑事司法行为本身进行合法与否的辨识与判断,不包括从行为后果的角度所作的容许性评价。从广义角度看,合法性评价是法律评价的重要形式,但并不是唯一的形式。如宋远升教授对侦查行为的法律评价进行研究,提出“侦查行为的法律评价,是指对已经成立的侦查行为进行是否合法及有效的评定和衡量活动。”①宋远升:《刑事侦查的行为视角》,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4页。他所指的法律评价,不仅仅限于合法性评价,也包括有效性与否的评价。
笔者认为,应当对刑事司法行为的法律评价予以狭义的定义。对刑事司法行为的法律规范进行研究有合法性辨识和容许性分析两大部分。如果对法律评价持狭义理解,可以在法律评价领域中只是处理对刑事司法行为合法性进行辨识的问题,将容许性分析置于法律处遇领域可使论述框架简洁而合理。这种逻辑安排可以突显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各自的主体性与独立性,可由此抵制混淆合法性与容许性的现象。如果对法律评价持广义理解,固然可以保证以该概念为基础的论述体系的逻辑自洽,但是在法律评价的领域中要同时论述合法性评价与容许性分析,这两种评价或许还要依据不同的法律规范,这样就显得内容过于复杂。另外,如对法律评价持广义理解,会导致将刑诉法第50条与刑诉法第54条都作为法律评价的依据进行解释。但是,很多学者对法律评价的狭义理解有着共识,会对在此处分析与解释第54条在直观上难以理解。虽然可以通过加强说明消除误解,但是这样会加大论述的复杂性。
二、刑事司法行为的法律处遇及其分类
(一)刑事司法行为的法律处遇
对刑事司法行为进行法律处遇,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进行适当的法律评价的基础上,对被辨识为非法行为的刑事司法行为进行程序上的回应、处理或者处置。学术界较少有人使用法律处遇这一概念,很多学者面对非法诉讼行为进行程序责任方面的研究时,使用的是程序性制裁及相关术语。“程序性制裁”的术语,其实渊源于王敏远教授提出的“程序性法律后果”。②王敏远:《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检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这些术语在主流的法学知识网络中都与“法律责任”有着本质的关联,都意味着“不利后果”的承担。但是程序性制裁及相关范畴不能全部涵盖对司法工作人员违法诉讼行为的所有的后续处置,其描述与指称现实的范畴能力有所不足。试举一例:李奋飞博士认为,程序性制裁具有轻重不同的制裁方式,“如对轻微违法行为只要予以补正,对严重违法行为可宣布行为无效或将非法获取的证据予以排除,对极其严重的违法行为还可以直接终止诉讼,对被告人作无罪处理”③李奋飞:《通过程序制裁遏制刑事程序违法》,《法学家》2009年第1期。。这位学者将对轻微违法行为的补正称为程序性制裁的一种具体方式,但是“补正”重在对合法状态的恢复,并不违背违法人员的诉讼利益,这与“制裁”的一般意蕴不相吻合。对轻微违法行为的补正,虽然是对违法行为的程序性处置,但不宜称为程序性“制裁”。这样,程序性制裁的术语就不可以涵盖与指称这种对违法人员并无不利后果的处置。本文提出的法律处遇的概念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二)刑事司法行为法律处遇的分类
1.容许性法律处遇。对刑事司法行为的法律处遇在逻辑上分为两种可能:容许性法律处遇与否定性法律处遇。容许性法律处遇亦可以称为对非法司法行为的程序性容许,是指在诉讼法的意义上默认这些行为的存在,不仅仅因为其非法性而影响该诉讼行为的效力、相关证据的证据能力,以及刑事诉讼的程序运作与实体处理。如侦查人员从犯罪嫌疑人处非法地扣押某物证,侵犯了其财产权,对这种违法行为的程序性容许是指认可该物证的证据能力,不将其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再如,一审法院在庭审时没有让被告人作最后陈述,程序性容许这种违法行为,意味着二审法院不会仅仅因为这个原因撤销一审法院的有罪判决。需要强调的是,对司法工作人员违法行为的容许性法律处遇,是基于实现案件的实质正义而做出的无奈选择,即不因司法工作人员的个人过错影响对犯罪的追诉,并非默认违法行为的正当性,不是免除司法工作人员可能承担的个人责任,也不是要求公安司法机关放弃对违法行为人进行调查、处罚的责任。有学者指出“大多数的公安机关领导、讯问人员,对于适当强度的刑讯逼供保持比较宽容的心态,甚至对受到处罚的参与刑讯逼供者抱有一定的同情”。①吴丹红:《角色、情境与社会容忍 法社会学视野中的刑讯逼供》,《中外法学》2006年第2期。这里涉及到宽容与同情并非本文所指的程序性容许。此外,对司法工作人员违法行为予以容许性法律处遇,只能针对具有“相对之恶”的非法司法行为;对刑讯逼供来说,刑讯手段震惊人类良知,不可能通过“无害错误”的分析,对这种非法行为不存在程序性容许的可能。
2.否定性法律处遇。否定性法律处遇是指对公安司法机关的特定非法司法行为予以否定,不认可该司法行为在法律与事实上的效力,不将相应的证据材料作为案件处理的依据,这就是传统学说所指的程序性制裁。陈瑞华教授指出,所谓程序性制裁“一般是指刑事诉讼法针对程序性违法行为所建立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刑事诉讼法所要制裁的并不是技术意义上的‘程序性违法行为’,而应当是那些严重侵犯公民权利甚至宪法权利的行为”,“离开了公共侵权的属性,程序性违法就可能带有技术性违法和手续性违法的性质,而在受到程序性制裁方面就不具有充分的正当性。”②陈瑞华:《程序性制裁制度研究》,《中外法学》2003年第4期。从制裁方式上来看,程序性制裁“主要是通过宣告程序违法者的证据、行为或裁决丧失法律效力的方式,来发挥惩罚违法者的作用的”③陈瑞华:《程序性制裁制度研究》,《中外法学》2003年第4期。。进一步地,陈教授概括出五种程序性制裁模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诉讼终止制度、撤销原判制度、诉讼行为无效制度及解除羁押制度”④闵春雷、杨波等:《中国诉讼法学30年理论创新回顾》,《当代法学》2009年第1期。。值得指出的是,笔者对程序性制裁的理解与陈瑞华教授等人有些细微不同。为了在逻辑上更好地突显“程序性制裁”与“程序性容许”之间的对立关系,可以在内涵上对程序性制裁进行更为极端、更为理想意义上的界定:只要对程序性违法行为的处置在本质上对行为人“不利”,比如排除了原有证明力的证据、终止原本应当正常进行的诉讼等,就可以从“承担不利后果”的意义将该处置理解成程序性制裁。
三、刑事司法行为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相混淆的学术现象及评析
刑事司法行为的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应当在逻辑上将两者清楚地区分开来。如果把两者相混淆,就会人为地制造逻辑冲突,也会导致出现理解错误。龙宗智教授2010年在《两个证据规定的规范与执行若干问题研究》一文中指出,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则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被排除,“据此,可以认为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已经在实际上不为法律所‘严禁’”,“可见,本次规定,实际上限缩了法律及司法解释所禁止的非法方法的范围”⑤龙宗智:《两个证据规定的规范与执行若干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10年第6期。。笔者认为,龙宗智教授在这里就把法律评价的层面与法律处遇的层面混同起来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处理的是证据是否排除的问题,是法律处遇条款。法律处遇与法律评价之间有着相互独立的关系,在解释“等非法手段”时,即便将欺骗性取证、引诱性取证予以排除,在逻辑上也不影响刑诉法第43条对欺骗性取证、引诱性取证予以“严禁”的法律评价。如果按照龙宗智教授的观点,把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第43条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条、第2条放在一个层面上,那么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4条完全认可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相关规定,这一条文岂不是与完全继承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0条有着不可协调的冲突?立法者在修正刑诉法时,既然把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0条与第54条同时置于一部法律之中,就表明立法者本身也是把行为规范与后果规范相互区分开来的,而行为规范与后果规范相区分,又是以刑事司法行为的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相区分为前提的。龙宗智教授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排除了“威胁、引诱、欺骗”方法的非法性“并不妥当”①龙宗智:《两个证据规定的规范与执行若干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10年第06期。,其实该司法解释并未涉及到这些方法是否合法的定性问题。
万毅教授、何家弘教授与龙宗智教授有着相类似的观点。万毅教授认为,“据此,可以认为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已经在实际上不为法律所‘严禁’,只有一种例外,即以威胁方法获取证言及被害人陈述,才被‘严禁’(即触犯后有不利法律后果的禁止)”②龙宗智、夏黎阳:《中国刑事证据规则研究:以刑事证据的两个规定为中心》,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7页。。何家弘教授指出“采用《刑事诉讼法》明令禁止使用的方法获取的证据却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③何家弘:《论“欺骗取证”的正当性及限制适用——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之管见》,《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1期。。如前所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条、第2条或2012年刑诉法第54条处理的是法律处遇问题,其核心是对被确定为非法行为的刑事司法行为进行容许性分析,它并不是进行法律评价的依据。对欺骗性取证与引诱性取证等具有“相对之恶”的司法行为来说,法律评价的标准与法律处遇的标准自然不必等同,也无法等同。所以,从法律处遇层面上的“容许”来反推法律评价上的“合法”,是不合逻辑的。何家弘教授所说的对取证方法的“明令禁止”与证据的“使用”分别是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它们作为不同的概念处于不同的逻辑层面,就无法进行比较,因此也就不存在是否“自相矛盾”的问题。
笔者试从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二分的角度,对龙宗智教授的另一观点进行评析。龙宗智教授指出:刑诉法2012年修改后,“严禁威胁引诱欺骗,但排除非法证据的时候,主要强调刑讯逼供。法律规定前面严禁后面酌定,逻辑上有一点问题,但不禁止不行,都禁止也不行,立法者也比较为难。威胁引诱欺骗的侦讯方法实际上存在一个合法性界限问题。”④龙宗智:《理性对待法律修改 慎重使用新增权力——检察机关如何应对刑诉法修改的思考》,《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一,龙教授把“严禁”与“排除”区别开来是十分重要的。刑事诉讼法对待刑事司法行为分为两个层面,“严禁”处于法律评价层面,“排除”处于法律处遇层面。如果把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的法律规范放在一个平面上,自然是“逻辑上有一点问题”。但是,如前所述,我们把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错开,对具有“相对之恶”的司法行为来说,还要分别依据宽严不同的法律规范进行合法性评价与容许性分析,那么就不存在逻辑冲突与矛盾。只是在学理上,我们还没有就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二分论的观点形成共识,所以才有逻辑有问题的假象。第二,应对欺骗性取证、引诱性取证等刑事司法行为不仅仅是“合法性界限”问题,这只是一个法律评价的问题。我们不仅要在法律的概括禁止的前提下经过法律解释确定某些行为是合法行为,同时还要确定哪些非法的欺骗性取证、引诱性取证等行为可以被容许,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后者这个法律处遇的问题。
四、刑事司法行为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两分论的涵义与价值
刑事司法行为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两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第一,在逻辑上区分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使之分别处理合法性评价与容许性分析的问题。第二,法律处遇包括容许性法律处遇与否定性法律处遇,程序性制裁只是法律处遇的一种具体手段。第三,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的法律依据,可以视利益平衡的情况而有所不同。第四,存在着容许特定的非法刑事司法行为的法律空间。这是一个针对所有刑事司法行为的框架。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剥夺被告人辩护权的审判行为等都有着“绝对之恶”,应被绝对禁止与彻底否定。对这类司法行为,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的标准是同样的,而且法律处遇体现为绝对的程序性制裁,这是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两分论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对欺骗性取证、引诱性取证等有着“相对之恶”的司法行为来说,则适用一般的理论进行分析。
针对非法的欺骗性取证、引诱性取证等行为,刑事司法行为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两分论可使研究思路更加清晰,对普遍应用这类取证方法的司法实践有着更强的解释力,除此之外,还有如下价值:
第一,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两分论为更合理的利益平衡创造空间。对有着“相对之恶”的刑事司法行为应错开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的视角,构建宽严有异的标准。一方面,坚持较高标准的法律评价,可以不动摇与降低立法的伦理标准,坚持对不当的刑事司法行为依据高标准进行否定与谴责;同时,对进行非法行为的司法工作人员追究个人责任,使其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在刑事司法中某些司法行为如利用亲情对被追诉人进行引诱与欺骗,的确可能更好地实现实体正义,但不能从实体正义得以实现的良好效果进行倒推来证明其行为是正当的,合法的,否则实体正义将吞噬程序正义,良好的办案结果会成为容许司法工作人员肆意妄为的许可证。另一方面,适用相对较低的法律处遇的标准,主要是从现实司法实践的功利逻辑来处理案件,考虑到某些案件实物证据蕴含着客观信息,考虑到对社会公众和被害人利益的保障,明知某些司法行为的非法性却又不得不在案件办理时予以容许。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二分论可以错开分析所针对的不同对象,在既表达出国家肯定与否的基本态度的同时,又使利益平衡符合社会的基本观感,不仅使法律具有和保持理想性,同时又使案件办理满足实践合理性。
第二,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两分论为合理解释刑事诉讼法提供理论支持。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是法律评价条款。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是法律处遇条款。法律评价是法律处遇的前提,那么刑诉法第50条对刑诉法第54条有着固有的前提设置的功能。对刑讯逼供来说,刑诉法第50条与第54条自然是无缝对接。对欺骗性取证、引诱性取证来说,既然第50条已作出“严禁”的规定,为了保障其规范效力,自然应当秉持第54条对被识别为非法行为的欺骗性取证、引诱性取证予以适用的立场。具体如何适用,可以另外讨论,但是不能以第54条没有含有“欺骗”、“引诱”等术语,便反过来倒推刑诉法第50条是不合理的,或者认为第50条与第54条存在本质的矛盾。只有将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区分开来,才可以理解刑诉法第50条与第54条的不同地位与功能,理解法律设置不同的判断标准的合理性,才可以抵御从欺骗性取证、引诱性取证得到普遍应用的功利角度对刑诉法第50条的质疑与否定。
On the Separation of Legal Evaluaion and Legal Disposal of Criminal Judicial Acts
JIANG Peng-fei
In academia,there exists the confusion of legal evaluation and legal disposal of criminal judicial acts.As to the deceptive investigation and enticing investigation which has relative evil,the foresaid confusion may make scholars infer legitimacy of the acts from the condoning phenomenon in judicial practice,thus questio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rticle 50 of criminal procedure law.The legal evaluation and legal disposal should be separated strictly,and the procedural sanctions should be regarded as one means of the legal disposal.This theory has stronger ability of interpreting the reality,can create theoretical room for interests balance and offer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criminal judicial actions;legal evaluation;legal disposal;criminal procedure law
D915.3
A
1672-1020(2015)06-0022-06
[责任编辑:尹 瑾]
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司法过程中利益衡量问题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AHSK11-12D21。
2015-11-05
蒋鹏飞(1975-),男,安徽省亳州市人,回族,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刑事诉讼法学,安徽蚌埠,233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