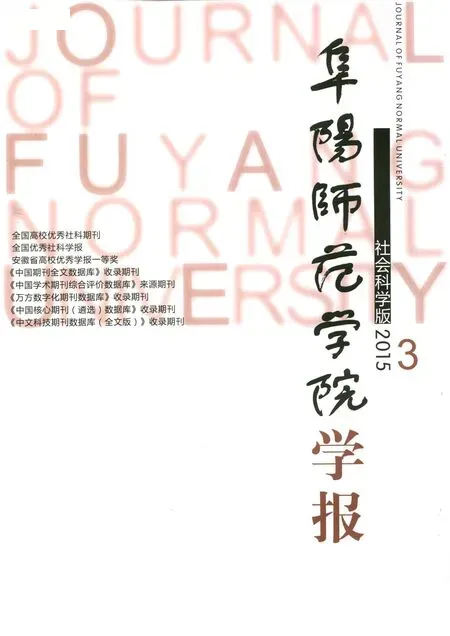文学批评的歧途与正路
2015-04-18杜红梅李长中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阜阳236037
杜红梅,李长中(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文学批评的歧途与正路
杜红梅,李长中
(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当代文学批评身份意识的淡化,使批评资源的西方化、批评价值的暧昧化、批评对象的随意化、批评生态的同仁化等病象由来已久,各种批判或指责之声呈一时之盛。与此相应,诸多的“重建”“重构”“创新”等对策或方略也时有登场。然而,迟至今日,当代文学批评的病象及症结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批评危机或批评理论的原创性问题仍然是学界的显在焦虑。明确批评定位,使批评成为审美价值的发现者、先进文化的生产者和理论话语的创造者,应为当代文学批评的身份归属,如此,当代文学批评才能承担起转型期的批评功能。
文学批评;歧途;正路
如果说,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因参与或承载着“新启蒙主义”这一意识形态而取得整个社会文化场域内的话语权,从而赢得尊重或身份认同,这一时段的文学批评也因批评者之间、批评者与批评对象之间、批评话语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合谋而成为当前学界记忆中的“辉煌与梦想”;至 1990年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再次复兴,由“失语”“缺席”等问题所激发出的话语重建激情,也彰显出批评在场的必要与合法性。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却失去了言说的激情与批评的活力,缺少了观点鲜明的争鸣,缺少了追踪文学热点的动力或勇气,缺少了对本土现实问题阐释的冲动,缺少了求新求变的生机与活力,缺少了对社会问题介入的担当,在当代文学大发展、大繁荣的当下,文学批评却“未老先衰”。诸多的不满、指责和批评之声现已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主体症候。作为国家主流话语代言人的《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媒体近几年对文学批评的持续关注,表述着对批评危机的焦虑。批评者问题意识的淡化、批评资源的他者化、批评价值的暧昧化、批评主体的同仁化等问题,一直纠缠其间,成为当代文学批评尾大不掉的病象及症结。
一
任何意义上的文学批评都要承担起本土问题的发现或解决,抑或为本土问题的发现或解决提供某种路径或方法之重担,如此方能彰显批评在场的必要及其存在的合法性。近年来,由于受各种后学思潮或消费逻辑影响,当代文学批评却渐趋丧失了对本土问题的自觉观察与省思,批评者也渐趋从“立法者”退化为“阐释者”,不再致力于人类灵魂的重铸和高擎人类文明的灯火,而是甘愿依附于个人的利害得失,俯就于市场的消费逻辑,缺乏本土问题意识与中国经验建构等问题的思考,而“问题意识”的淡化又逻辑地生成一种对他者话语的套用或借用式批评现象。在很多情况下,理论的追新逐异使得批评者有意或无意间忽视了对他者批评话语的语境化考察和理论旅行有效性的理性审视,便以他者文化语境中的有关概念与术语想当然地套用于中国文学批评实践,结果许许多多的批评就成为批评者“拉大旗做虎皮”式的自吹自擂,批评的民族性与本土意识闪身幕后。曾几何时,对先锋小说研究成为对罗兰·巴特、德里达、鲍德里亚、福柯等人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再利用,什么“差异”“延异”“空缺”“重复”“播撒”、 能指/所指、语言/实在等等满天飞,批评得越离谱、越出格,就显得越新潮、越现代。其它如“民族主义”“文化认同”“身份建构”,后殖民主义、话语霸权等各种各样宏大却无本土针对性的药方开列。使真正的本土问题反而躲在了批评背后,以至于连西方学者霍尔都看不下去了:“你们要研究自己的问题,以中国现实中提取的问题……重要的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对于理论,你要让它对你发生作用。”[1]与此相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与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一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渐盛(加诸新儒学、新左派的推波助澜)并日趋异化为一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文化中心主义,将中国问题看作只有中国人以自己的方法来解决的问题:“现在是一个中国崛起的时代”,“崛起”的中国文化应当重申自己的文化主体性;由“中国自己的学者”来掌握,把抵制或质疑西方话语作为中国崛起的表征,进而将西方话语当作拦路虎、绊脚石而欲与之一刀两断。特别是近年来,一种通过批评张扬民族形象建构和民族认同呼声渐趋高涨,甚至被认为是爱国与否的体现。“自己的中国当代文学观”“自己独特的理论问题”“中国式自己独特的文学理解”等等,成为这一思维模式在文学批评领域的经典表述。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们不是探讨如何深入理解或阐释莫言作品的问题,而是将莫言获奖看作是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胜利,是“基于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主体对于‘他者’的想象性阐释,充满了主体自身的文化优越感”[2]。从根本上说,只要能够深化我们对本土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本土问题的解决,他者话语的选择并非对他者的“缴械投降”或“束手就擒”。在全球化的当下,持一种立足本土、胸怀全球的开放的民族主义立场,才是当代文学批评者的基本选择,才能彰显出批评自身的成熟。
当前,文学批评越来越“不务正业”,凸显出权责不清、身份不明问题。文学批评是对“文学”的批评和对“文学批评”的批评,这是文学批评的主业或专业。尽管随着网络传媒的发达和信息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越来越呈现出式微或疲软态势,“网络文学”“手机文学”“微信文学”“新媒体文学”等大行其道,读者之多也远超传统文学的接受群体。这一文学“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必定影响到批评生态,这是难以否定的事实。对此类现象的关注也是文学批评的应有之意。不过,当代文学批评在面对这一问题的时候却走向了极端:将文学批评“扩容”到网络文学或其它新媒体文学,将消费化、休闲化作为批评的基本目标,放弃对传统文学批评方法、立场、价值和对象的守护或维持,甚至认为文学的本质也要随之而变,电脑/网络所改变“将重新定义我们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其中无疑也就包括了我们的文学及其价值观和标准”[3]。谁都不能否认,电脑/网络对当今社会生活的根本性变革,但是这种变革能否影响到“文学及其价值观和标准”,还真要另当别论。人类社会从有记录以来经历了几千年的革命性突变,文学至今仍是关注人类生存、思考终极问题并寻求诗意栖居的最佳载体(不管你承认与否)……。在笔者看来,文学外部生态改变的只是文学的存在形态、传播方式、接受途径和生产机制而已,电脑/网络并非文学批评的“天敌”,批评的责任是如何尽可能通过电脑/网络这一传播方式将经典或优秀的文学或文化产品推广出去,尽可能扩大影响,消解消费或市场文化对人们精神需求和情感诉求阵地的占领,而不是相反。若论网络、市场、商品化等对文学批评的影响问题,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能远比我们国家更为严重,若论批评向网络、媒体转型问题,西方国家也远比我们更有基础和资本。然而,西方国家的媒体批评、市场批评、实用批评与职业批评之间因为能够做到“耶稣的归耶稣,撒旦的归撒旦”,批评生态的改变才没有根本上影响到批评自身的发展,他们通过批评实践创造出的一系列理论、概念或方法等一再成为我们的话语资源。反观当前的中国批评界,我们看到的只是批评者灵活地在“媒体批评”“市场批评”“文化研究”等之间“长袖善舞”。真正纯粹的学院式批评在当下中国其实仍属于一种稀有现象。
批评价值的暧昧化制约了批评对社会问题的介入和对文学(文化)问题的干预能力,是当代文学批评最值得警觉的病象之一。尽管批评不负责给社会提供规范性的原则和标准,不负责为人类提供诗意生存的法则和路径,不负责为文学创作设置必须遵守的条例或律令,但是,文学批评通过对文学价值或意义的阐释与总结,却能给人类以思考或潜在的规约和引导,即使如新批评、形式主义批评也并非纯粹的学院式批评,而是蕴含着典型的意识形态质素和对现实政治的干预意识。在萨义德看来,批评者应针对社会时局发表见解,体现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和社会良知,注重文本的“现世性”,就是把文学作品看成现实社会当中的一个现象,批评则为了促进人类自由而产生的非强制性的知识。反观国内的文学批评,由于受商业化、市场化以及后现代多元价值观念的影响,诸多的批评者失去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诸多的“时评”“炒评”现象不绝如缕,一些作品研讨会、学术交流会变异为相互吹捧会和拜亲访友会;众多的文学排行榜、风云录的评委们也只是那么几个人的权力狂欢,批评价值观的混乱与迷乱,已严重影响到文学价值的阐释与规约。
论及至此,一种似乎远较商业批评对批评价值观影响更为深远的当是“同仁”批评。放眼当前的批评界,同仁之间的互捧、惺惺相惜已经严重影响到批评的文风、批评的风骨与批评应有的学术容量。而作为同仁互捧的显在症候即是刊物的同仁化趋势渐趋明显,一些在学界有相当分量的刊物现已退化为同仁间的交流或对话,其他人等,特别是一些初出茅庐者(如果这些初出茅庐者与刊物所钟情的那些著名人物无关的话)很难在这些刊物发文(同仁刊物也能够集中力量去形成合力对某些问题作为集体性回声,不过,真理只是掌握在某些同仁或某些已形成权威的同仁之手吗?)同时,刊物或同仁间的赋魅又使一些本不具相应实力的批评者却成了“著名的”“有影响力的”“杰出的”“资深的”的批评家了。所以,当前的文学批评文章大都有套路可总结:傍名家,说大话,玩理论,造新词。基本写作模式是:先谈当代文学状况的不堪(所谓“不堪”要由自己的批评对象而定,如若强调XX作家作品的语言有特点,就说当前文学的语言存在几乎令人难以容忍的堕落现象等,其它论述基本模式大抵如此),进而对自己中意的作家作品开始评价。因为前面已做了铺垫,后面就可以任意拔高了。
二
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文学是人学,文学批评应属于人文学科,最终目的是以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需求的学科,是建构适合人类健康需要的文化系统的学科,“人文科学是研究人的生存状态及其意义和价值的学科,目的是为了使人按照自身应该有的状态来进行生活,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知识系统,而且也是一种价值学说”[4]。就此而论,当代文学批评其实是一种文化生产行为,应该承担起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建构或生产重任,以先进文化生产自觉意识作为当代文学批评的精神内核,“引导人们对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凝聚和振奋民族精神,激发人们奋发图强开拓进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5]。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各种“新”知“后”学思潮纷至沓来,解构价值,虚无历史,消解传统,推翻道德,唯洋是举,以“后”为上等错误思潮甚嚣尘上。一些作者以“零度写作”或者“文化多元化”为幌子,对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和道德传统加以冷嘲热讽,越来越表现出对一切事物的无所谓式的游戏态度,消弭了是非,抹平了善恶,混淆了美丑,严重侵蚀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文化根基;还有些作者抱着“外国一切皆好,我们一切皆坏”的价值立场进行写作,骂完我们的祖宗,再骂我们的父母,同时又不遗余力地鼓吹各种国外的所谓先进思想并以之为我们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更有些作者在作品中鼓吹各式各样的“厚黑学”“成功学”“官场或职场关系学”等,宣扬只要为了成功一切手段都可以使用的“唯名利”论……针对上述状况,作为文化生产的文学批评理应以“弘扬民族正气,抵制歪风邪气”的责任担当意识,大胆而理性地予以批评和剖析,并通过倡导先进思想和现代性价值观来凝聚民族意志,激扬民族精神,以抵制去价值化、去思想化、去道德化、去正能量化,以及虚无历史、解构传统等文化虚无主义行为及其它不良倾向,使之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国形象塑造的重要文化资本,而不要在上述问题面前闭上了眼、站错了立场、发错了声音,更不能对那些鼓吹享乐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价值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的作品以鸵鸟式心态说些“今天天气哈哈”式的无关痛痒、不涉价值判断的语言游戏,只有如此,才能使“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为了提升生命本质上反对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制和虐待,批评的社会目标是为了促进人类自由而生产的非强制性的知识”[6]。从而彰显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中华性或民族性特征。
“文化主义”批评的甚嚣尘上现象,更值得我们关注。“文化主义”批评的基本逻辑是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为“文化问题”,以“文化”来解释和阐释一切,“文本之外,别无他物”是此类批评最为彰显的口号。在“符号的嬉戏”与“能指的狂欢”中将那些社会生活中的本质、真理、道德伦理等都认为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而不问不顾,这种批评消解了谈论问题的实践性,将诸多的现实问题诸如贫富不均问题、社会公平问题、农民工再就业问题、社会稳定问题、多民族关系建构问题等,转换为晦涩拗口的话语游戏和概念狂欢,不再面向现实发言,不再倡导批评的“宏大叙事”,甚至怀疑、否定或拒绝宏大叙事对文学批评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那种历史观与美学相结合的观点不再受人们的追捧,转而注重于福柯意义上的“微观政治”,日益陷入“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收编之中,不再关注现实政治与真理或将现实关怀悬置,俯就于日常生活中的性、欲望与消费的盛宴,并与消费文化合流而甘愿享受消费盛宴带来的快感,患上了伊格尔顿批评的“政治失忆症”。
在文化主义批评思潮影响下,当前的许多批评者“躲进小楼成一统”,社会功能担当意识日渐弱化,为批评而批评、为职称或晋升而批评、为生存需要而批评现象不绝如缕;不断翻新批评的话语资源以获得进入批评市场的资本,不断提出各种新名称、新概念以彰显自身的与众不同,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批评意识严重影响到批评者介入社会、变革现实的勇气与力量。当前,如何重振文学批评的民族精神,强化文学批评的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避免文学批评在歧途上越走越远,就成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文学不能成为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这是对文艺创作的总体要求,同时也是对文学批评的根本性指导。作为批评者,一方面,要坚守人文学者的根本立场,不媚俗,不奉承,不追名逐利,更不浪得虚名,甘于忍受寂寞或孤独;另一方面,应尽力拓展自己的知识视野,汲取多方面的理论滋养,丰富多方面的知识结构,并以自觉的理论建构意识去从事批评实践,最终以生成本土化、中华性的批评理论而能够理直气壮地参与他者对话。这一批评话语是姓“中”的却是参与世界对话的,是民族的却是建构人类共同精神家园的,是现代的却又关联着中国传统文化命脉的。参与是最好的坚守,对话是最好的继承,发展是最好的保护。批评是批评者的武器,真正的批评者是优秀文化的建构者与传承者。在此,强调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建构性”“文化生产性”与“审美发现性”,是其走向正路的基本选项,更关涉到中华文化的再生产。如此,才能使文学批评作为参与重塑中国话语的重要资源。就此意义而言,当代文学批评危机未尝不是一种转机,弱势亦未尝不可以转化为一种后发优势。
[1]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J].文艺研究,2011,(7).
[2]洪治纲.主体意识的回归与文化身份的认同[J].文艺争鸣,2014,(2).
[3]吴俊.文学批评、公共空间与社会正义[J].文艺研究,2008,(2).
[4]王元骧.也谈文学理论的“接地性”[J].文艺争鸣,2012,(5).
[5]柯琳.文化自觉导引文艺理论发展趋势[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4,(1).
[6][美]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M].李自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译者序.
I06
A
1004-4310(2015)03-0073-04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5.03.017
2015-02-25
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审美观照”(13FZW034)。
杜红梅,河南永城人,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地域文化/文学教育研究。